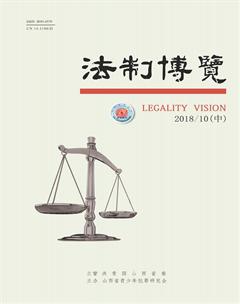商譽貶損與自由輿論間的界限
劉芳伊
摘要:本文通過對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構成要件進行分析,并以“捏造并散布虛假事實”這一要件為切入點,首先對“虛假事實”進行法理分析,并探討“虛假事實”與“價值叛貶”之間的區別;而后從公眾言論自由權以及企業容忍義務的角度對商譽貶損與自由輿論間的界限進行分析。
關鍵詞:損害商譽罪;虛假事實;商譽貶損;自由輿論
中圖分類號:D924.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8)29-0167-02
一、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的構成要件
根據《刑法》第221條之規定,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是指“捏造并散布虛偽事實,損害他人的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給他人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如何界定該罪的構成要件,實踐中經常引發爭議。正確理解構成要件,對于相關犯罪的認定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根據本條規定的文義,不是所有造成商品聲譽的行為都能成立損害商品聲譽罪,只有那些通過“捏造并散布虛偽事實”這一特定行為方式,致使商品聲譽受損的情形,才有可能構成本罪。因此,判定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應當重點考察是否具備捏造并散布虛假事實這一特定行為。本文以構成要件“捏造并散布虛假事實”為切入點,對“虛假事實”的認定以及商譽貶損與自由輿論間的界限進行分析探討。
二、“虛假事實”的認定
如何認定本罪的“虛假事實?可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探討:什么樣的事實屬于“虛假事實”,是否行為人捏造的虛假事實都屬于本罪中的“虛假事實”;價值判貶是否等同于“虛假事實”。解決好上述問題才能合理界定本罪中“虛假事實”的內涵。
(一)“虛假事實”的法理分析
“事實”是指真實存在并具備可證偽性的事物或對象。“虛假”即是指不真實、虛構的。“虛偽事實”應當是虛假的、與客觀情況不相符合的情況,它不應當包括真實存在的客觀事實。如果是真實存在的客觀事實,無論行為人散布的行為對商譽權主體是否造成損失,也不管這種損失究竟有多大,都不可能構成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與此同時,并非行為人捏造的一切虛假事實都應當歸屬于本罪的“虛假事實”。我們在考察“虛假事實”時應將重心放在商主體商譽權受損,即商譽權的受損是否由于行為人捏造并散布虛假事實這一行為所引起。同時,“虛假事實”亦當是與商主體商譽情況不符的誹謗之詞,而不應擴張為行為人所散布的全部“虛偽事實”。
(二)“虛假事實”與“價值判貶”之間的區別
事實描述與價值判斷的關系可以概括為以下三種情況:1、通過事實描述達到價值評價;2、拋開事實描述僅談價值判斷;3、兼具事實描述與價值判斷。在判斷是否構成侵害商品聲譽罪中,兩種情況較好判斷,而在第三種情況下,應注意要把握好側重點,是側重事實描述還是屬于價值判斷。如果明顯側重于價值判斷,則不可等同于侵害商品聲譽罪中“捏造事實”這一構成要件。具體到法律規定中,我們可以通過比較對自然人與商主體名譽權保護的法條進行分析。對自然人名譽權的保護,《刑法》第246條侮辱罪和誹謗罪做出詳細規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的”,是侮辱罪;“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是誹謗罪。侮辱,指對他人予以輕蔑的價值貶損,至于表述內容是否真實并不重要。相反,誹謗,是捏造并散布有關事實,足以敗壞他人名譽。即對自然人名譽損害所散布的事實,如不足以使法律對其追究責任的,不是誹謗,但可能構成侮辱。
在上述分析下,可以把侮辱與誹謗理解為相互補充的關系,即對于那些沒有捏造事實因而不能被誹謗罪涵攝,但又通過價值貶損損害他人名譽權的行為,用侮辱罪加以堵截和補充。而我國《刑法》第221條規定的損害商譽罪僅對“編造并散布虛假事實”這一特定的行為方式進行規制,而并未像侮辱罪那樣,將公然性的價值貶損納入打擊范圍。換言之,如果行為人損害了他人商譽,但不是通過捏造事實的方法,而是通過價值貶損的方式實施的,就不能夠認定為損害商譽罪。這不僅是與第246條的侮辱罪和誹謗罪對比而出的結論,同時也是罪刑法定原則的明確要求。
不可否認,虛假事實和價值貶損,都能損害商主體商譽。但并非所有損害商譽的行為,都能構成刑法上的損害商譽罪。在刑法明確規定該罪的行為方式僅限于“捏造事實并散布”的情況下,如果把價值貶損的行為也納入該罪的,那就不是依照法律規定而是根據危害性來定罪了。而這樣一種脫離法條文字、根據社會危害性進行實質判斷的做法,不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
三、商譽貶損與自由輿論間的界限
(一)商譽損害與公眾自由言論權
言論自由與輿論監督是現代法治的重要基礎。言論自由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在世界各國普遍受到憲法的保護。企業和產品,應當積極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與批評。輿論監督并不專指完全正確的評論,而應包括各種并非惡意捏造的、不完全虛假的否定性意見。
如何防止在遏制謠言的同時也扼殺有益言論,這就需要在憲法所規定的言論自由、監督權、公共利益之間進行衡量。網絡作為公眾言論平臺,不能其要求具有“過濾”機制,任何公眾都有權發表對產品、商業服務的體驗感,當然也會有情緒不滿,而不滿之中又往往包含著改善機制所需要的智慧和動力。給予公眾更多的言論空間,當公眾的言論或行為造成商主體名譽權損害時,應正確區分是基于客觀事實的價值評判亦或是“捏造并散布虛假事實”。司法實踐中應當注重對于網絡自由言論權的維護,給予公眾更多參與社會監督的機會,但同時也要通過一定的司法干預來正確引導公眾的輿論,促使良好的輿論監督氛圍的形成。
(二)企業的容忍義務
作為企業,應持有正確的心態,接受社會公眾廣泛的批評,甚至參與到公眾討論中。對于網絡上的一般性批評和指責,應以包容大度的心態予以接受。具體而言,商業廣告制度允許企業為了宣傳的需要,對商品性能進行一定程度的夸張與虛飾。因此,企業在享受廣告制度帶來的利益同時,就應當承擔與此相應的代價和責任。這種代價就是接受公眾對于產品的評價和建議。既然企業可以利用廣告制度進行在價值上進行一定程度的夸張宣傳,那么消費者和社會公眾,同樣有權通過各種方式,對上述夸張成分進行個人價值判斷。因此,現代企業對于商品的負面評價特別是價值性的負面評價,應當承擔必要的容忍義務。
為了保證言論自由權的充分行使,只要不存在明顯的惡意,公民的言論即便存在錯漏之處,也應當得到容忍,而不宜動輒得咎。過度維權不僅會在法律上造成諸多不利后果,更有可能引發社會公眾的抵觸情緒,從而為企業的信譽造成更為嚴重的不利后果。過度維權甚至有可能適得其反,對商品聲譽造成更進一步的損害。依法通過各種方式維護權益是企業的權利無可厚非,對于網絡空間中批評與指責,企業可通過網絡進行正面回復與公開辯論的方式,也可以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行為人補償其經濟損失,不失為更為穩妥的維權方式。
[參考文獻]
[1]高銘瑄,馬克昌.刑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442-444.
[2]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3]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4]徐強.論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J].法制與社會,2017(11):77-78.
[5]邱瀟可.網絡環境中言論自由權與名譽權保護之均衡[J].東岳論叢,2012(7):169-173.
[6]王峰,李薇.損害商業信譽罪邊界之辯[N].21世紀經濟報道,2013:10-24.
[7]繆因知.損害商譽罪研究:自輿論監督的視角[J].法治研究,2017(02):5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