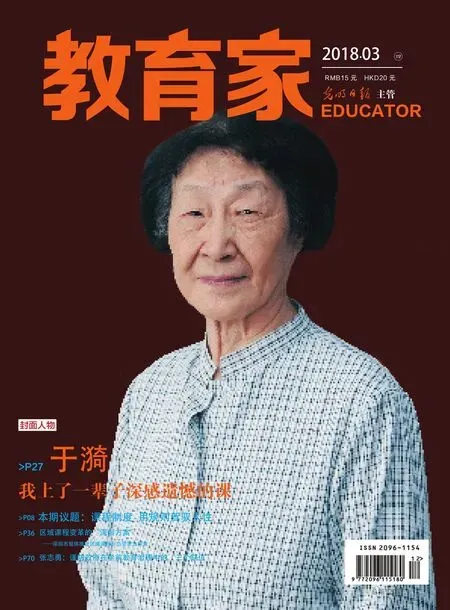教師要會“七十二變”?
趙 楠/北京市十一學校
一段時間以來,似乎人人都可以以情懷或責任之名指摘教育,并對基礎教育和教師進行“場外指導”。要求廣大教師既要能博聞強識,又要做道德完人;既要高質量完成一系列行政工作,又要強化“服務意識”給學生做“保姆”;昨天聽領導訓話上班考勤,今天又來了各路“專家”指導工作,后天還要按照媒體顧問要求把課堂辦成展示晚會……疲憊不堪的同時還要做好最為本職的教課、答疑、批作業,仿佛教師個個要變成“七十二變”的孫悟空。
我們不禁要問:教師的專業性體現在哪里?專職教師的主業是什么?應當怎樣培養?要知道教師的本職就在于“傳道授業解惑”,在于“教書育人”。從教學的層面說,教師要在專業知識過硬的基礎上,系統學習教育學知識,并通過終身學習來不斷提升職業素養;教師的職業勞動是非常能動的,不僅要學習,更要反思、探索,做好知識的落地與傳播,開展課程研發、教材開發、學習研究等一系列工作。從教育的層面說,每位教師都是管理者,對未成年人個體、班集體乃至整個學校的管理,以及對學生學習、生活、心理健康、成長規劃等的指導和關切,其專業難度不可小覷,而且要投入大量的職業良心。在廣大農村、在走讀學校和特殊教育學校,教師要付出的則更多。
當今社會高速發展,使得知識迭代加快、學習路徑增多,社會分工也日益明細,教師職業的專業性更加強化。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劉云杉老師有一本專著《從啟蒙者到專業人》,很好地概括了在中國現代化歷程中,教師角色演變的歷程。即便受過系統教育,也并不等同于“懂教育”。年高德劭、曾是“孩子王”的老教師并不敢隨意判斷和管理今天的學生,中學優秀教師亦不敢妄談小學教育教學。眼下社會上種種“談教育者”(而非“教育從業者”)不斷引介和推銷所謂新理念,甚至僅僅借由修辭術,“創新”種種教育名目;一天書都沒教過的記者、官員,發聲都大于一線從教者本身,甚至直接“指導”一線教學工作,指揮教師的工作方向和重點。廣大教師的主要精力不是用在回歸本職、提升專業素養上,而是疲于應付各種行政事務、績效考核、未待充分評估論證就匆匆上馬的各種新試驗,以及為教育界日漸興起的“造星運動”做嫁衣,本末倒置,越發背離教師工作的專業性。
然而,很多一線教師本該是教師專業性最好的注腳,卻對業外人士的“教育理念”作為頗為仰慕。究其原因,一是教師的專職培訓與職前培養均受到各種因素的限制和干擾,出現了很多令人失望的問題:相關部門過于看重和施行權力、行政干擾太強,培訓內容落后、不切中教學重點與痛點,培訓形式和考核機制僵化……相關師范院校或專業則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想方設法“去師范化”,因為培養一名企業家所獲得的短期收益要遠高于培養一名老師。這些都使教師無法更好定性自己的專業,并渴望聽到“外界”的聲音。
二是當前的教師隊伍選拔與構成問題多多。由于職業專業性未得到充分重視、勞動待遇和社會地位相對較低,晉升通道狹窄,使得如今部分教師的整體素質低于社會期待。我們需要反思的,不是教師不讀書、不專業,而是會讀書、好讀書、本可以成長為優秀專業教師的人,為什么沒有選擇教師崗位。
今年年初剛剛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改革的意見》中明確提出,要“大力振興教師教育,不斷提升教師專業素質能力”,并強調“不斷提高地位待遇,真正讓教師成為令人羨慕的職業”。《從啟蒙者到專業人》書中寫道:“作為一個專業人,要小心守護學術與教育的有效性范圍,需要有一種具有相對自主性并且‘價值中立’的學術,對所置身的世界,方能有所貢獻。”可見對教師專業性的重視與呵護迫在眉睫。
讓學習真正地發生,不是把孩子從課桌上“拯救”到地板上,而是靠教師的學識與智慧引領;讓教育真正地發力,不是讓“教書匠”學會時髦的“七十二變”,而是要依靠一大批專業過硬、與時俱進的教師。培養和選拔優秀教師,不斷加強教師專業建設,方能踐行“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教育大計,教師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