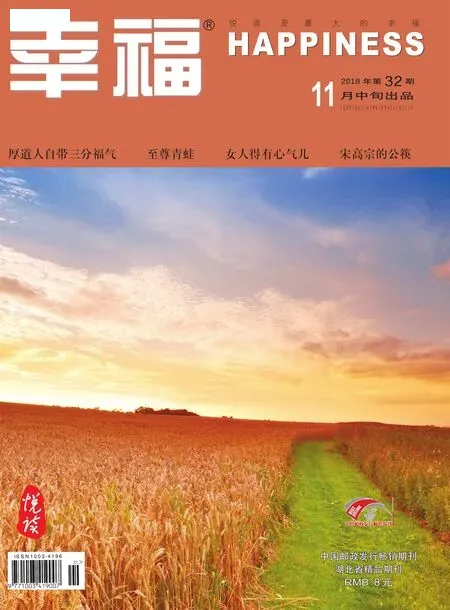這是吃仙物呢
文/賈紅妞

買了一些山竹回去。
先給女兒剝開一個,遞給她吃了。又給婆婆,突然想著她沒吃過這南方水果,于是也幫她剝開遞過去。
“叫孩子吃,我老大一個人吃什么。”
“你嘗嘗嘛,這是山竹,南方的水果,在老家恐怕吃不到。”
婆婆不再推辭了,接過去吃起來。
“嗯,有味。”婆婆吃了一口笑贊道:“這是吃仙物呢。”
仙物?
這應該是對山竹最高貴的稱贊。在我們老家,把非常珍貴的東西叫“仙物”。
又有一天,女兒嚷著要吃蛋撻。剛學會做的我自然是趕緊鼓搗一番,給她烤了幾個。烤熟后,又拿出一個讓女兒送給奶奶吃。
“孩子喜歡吃,讓孩子吃嘛。”婆婆在旁邊又推辭。
我又勸:“她一個人也吃不了這么多啊。再說小孩子吃獨食慣了,不知道分享,長大只會變得很自私。”
于是婆婆接過吃了,剛吃一口,清瘦的臉開了花:“這是吃仙物呢。”
聽她又一次說吃仙物,我也笑了。我為能給她幸福感而笑,同時又因她帶著情味的回應而感激。坦然接受對方的一點心意,并贊之嘆之才是最妥帖的成全。
其實這些算不得珍貴東西,因為她第一吃,也因為她內心簡單的滿足感,這些不算仙物的東西才升級成了仙物。
在很多人心里,“仙物”怎么能輕易吃得到呢。天庭里的蟠桃,萬年才得吃的人參果,那才是仙物吧。
小時候,我也有很多吃仙物的感覺呢。
記憶最深的一次,是某個雨過天晴的傍晚。
那天天空是否掛了彩虹不記得了,但屋頂的青瓦一定還沒干透,濕漉漉黑幽幽,青瓦上的瓦松剛被雨水澆了個透,一定也是肥嘟嘟亮油油。
那天,父親背著挎簍從地里回來,臉上流動著神秘的笑,對著正在玩耍的我喊:趕緊回家來啊。
我好奇地跟進去。父親又立刻把大門關上,悄聲說:“看看,挎簍里有啥?”
我懵頭呆腦揭開蓋在挎簍上的泡桐葉,哇,竟然有,足足有半挎簍的蘑菇露著白胖的腦袋在朝我笑。
“采蘑菇的小姑娘”的唱詞都是騙人的,要知道在平日,我們小朋友費多大勁兒才能在地里踅摸出一兩棵蘑菇呀!可是雖就一兩棵,只夠塞個牙縫,在火上烤熟吃了,那也真是讓人久久回憶的美味呢。而父親,我的父親變戲法似的,一下子帶回這么多這么多。
我蹲下身去,眼睛只敢盯著蘑菇看,手不敢摸,生怕一不小心就會把這些可愛的胖娃娃糟踐了。
“爹,你在哪里尋得這么多,改日我也尋去。”
“在后坡樹林里。去,趕緊讓你媽炒了吃。”
那一天中午,母親多倒了點菜籽油,我們一家人喝著小米粥,配著一大盤蘑菇,在嘖嘖的感嘆聲中吃了一次“仙物”。
后來,我的腳印畫滿了那個小樹林,蘑菇那白胖的可愛腦袋再也不肯與我相見,而它的清香在齒間,與時光相隨一下子飄蕩了幾十年。
清苦的年代遠去,當所有的“仙物”唾手可得,視覺、味覺在琳瑯滿目中麻木,舌尖上的味蕾只剩下了挑剔。
不記得上次的大快朵頤在什么時候,不記得享受美食的知足安寧在哪個時分,整天拖著便便大腹在生活中穿行。
如果可能,我真想撇卻今日的衣食無憂,走回往日的清貧,讓自己的腳印再畫滿老家后坡的小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