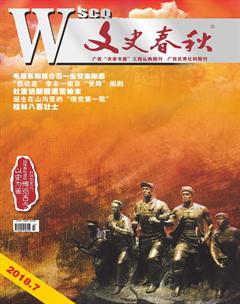追尋千年的記憶
蒙土金
1963年的春秋之交,一場傾盆大雨洗刷了羅鴉塘(中和村)的村子,竟然將一堆影青陶瓷的碎片沖刷到了人們的面前,這堆碎片的出現引起了考古專家的極大關注。次年9月,經過,一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專家的復核和試挖掘,驚人地發現這個坐落在廣西藤縣北流河邊村莊里的“小山包”竟然是大量陶瓷碎片的堆積,燒制的瓷器極為精美,而且在以往史書及相關資料里從未有過記載。
一
在這批出土的文物中,發現了刻著“宣和四年”字樣的印花模具和“嘉熙二年戊戌歲春李念龍參造”落款(“宣和”是北宋徽宗趙佶的年號, “嘉熙”是南宋理宗趙昀的年號):挖掘出土的文物造型大多為仿植物之類,碗、盤、盞、碟等網器為敞口小圈足,多為葵瓣或蓮瓣形,這是明顯的唐宋時代風格,并且這種瓷品在國內未見有同類產品,而在東南亞國家的博物館中卻有收藏。由此可以斷定:這是一個燒造青白瓷器而且以外銷為主的宋代窯址。1973年10月23日,《中國新聞》對這座廣西藤縣藤州鎮中和村宋代中和窯址的發現及試挖掘情況作了報道,立即引起了文物界的極大震動。
中和村古時叫羅鴉塘,坐落在北流河的拐角處,距藤縣縣城約15公里,與北流河邊上一個叫白泥塘的村子遙相呼應,而白泥就是燒制精美瓷器的主要原料。
村中發現了20多座瓷窯,主要分布在沿江2公里長的小山丘上,由于窯址過于龐大,加上當時技術方面的限制,對中和窯的開發僅僅只停留在試挖掘而沒有做大規模的考古挖掘,因此這座千年前的窯址伴隨著寧靜祥和的中和村始終未被大眾所知,沉寂在如夢幻一般的神秘之中。
中和窯的窯室結構既科學又十分精致,龍窯窯體依山的斜坡而建,長51.6米、寬3米,已出土的各種瓷器標本、印花模具、窯具等近2000件,除了極少數成品外,其余基本上都有殘損,以青釉為主,白釉次之,有碗、盤、杯、壺、罐、燈、枕、腰鼓以及匣缽、墊托、模具等等。在一號窯火膛附近還出土了7枚北宋的銅錢,其中1枚為“咸平通寶”,其余6枚為元豐、元祐的年號,這也證明了中和窯燒造的年代應始于北宋中后期,盛至南宋時期。中和窯瓷器配飾花紋多以纏枝菊、牡丹、海水游魚、孩嬰嬉水、流云飛禽等為主,印花模具則花紋繁縟細膩,布局嚴謹。關于中和窯瓷器的傳說很多,現在流傳到日本的“九龍杯”據說就是中和窯的產品,杯子盛滿水后,杯中九條龍的龍須在水中還會動呢。
如今,在中和村南起芝麻坪、北到來山口長達2公里、寬0.5公里的范圍內,當年20多座龍窯的瓷器碎片、匣缽遺留下來的堆積仍然靜靜地躺在這里。這些堆積品從山腳一直延伸到山頂,嶺腳殘存堆積厚約0.5米,山腰及頂部堆積一般在1米至1.5米,堆積物上雜草叢生,樹木茂盛,仿佛還在向人們訴說著當年“晝則白煙蔽日,夜則紅光沖天”的繁榮鼎盛景象。據考證,中和窯一座窯口可燒造2萬多件瓷器,《宋史·地理志》中記載,宋時藤州戶籍6422戶,若按每戶5口人計,約為32110人,如按每人每年用或損壞3件瓷器計算則需約10萬件左右,這樣僅需一口窯每年燒四五次便足以供全州人使用,這是中和窯的產品應為大量外銷的另一個佐證。另外,中和窯中出現的摩羯紋印花模和青白釉摩羯印花盞以及淺喇叭形碗等都未曾在國內出現,而在泰國、馬來西亞、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的皇宮、博物館卻收藏有不少同類的藏品,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中和窯遺址的發現,擴大了我國青白瓷窯址的分布范圍,同時也為研究宋代手工業的發展和社會經濟關系,以及我國與東南亞各國的歷史交往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證據。但是,中和窯究竟具體建于何年,又因何原因悄無聲息地湮沒在歷史的塵埃里,而又在這長達近千年之中,竟然沒有在任何史料中留下蛛絲馬跡,始終是個未解之謎。
中和村,就這樣彌漫著宋朝的氣息,徜徉在千年之外。
二
中和村注定是為北流河而生長的,因為它源于北流河,見證了古藤州大地上“宋瓷”與“宋詞”水乳交融、商文并重的一段歷史。
北流河,珠江流域西江干流潯江段的重要支流,又稱繡江,發源于云開大山南部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流縣平政鎮上梯村與沙垌鄉交界處的雙孖峰南麓,全長259公里,流域面積9359平方公里,年徑流量80.1億立方米,于藤縣縣城匯入潯江。秦統一中國后,為了推進對嶺南的統治,鑿通了靈渠,使長江水系與珠江水系相通,接著又鑿通桂門關,使北流河與南流江相通,成為當時由京都(現西安)沿黃河經漕運溯長江入洞庭進湘水越靈渠,過漓江經梧州,再從梧州溯潯江到藤州人繡江到玉林,過南流江達北海通南洋的南方水上絲綢之路。《永樂大典》2343卷《藤城記》曾載“廣右之地,西接八番,南連交趾,惟藤最為沖要”,古藤州段的北流河作為當時重要的嶺南水道要塞,在南北交往和中國通向海外中擔當著重要的角色,歷朝的商賈、官員、軍旅、流寓雅士、云游高僧、趕考才子等出入北流河,或休整、或留宿、或游歷山水,他們在歷史的長河里共同渲染了北流河的商業濃度和文化厚度。而中和村恰到好處地生長在北流河注入潯江入口處的一個拐彎地段,和北流河靜靜地相依相偎,相互守望。
北流河流域自古就有制陶的歷史,到兩宋以后,北流河流域影青瓷、青花瓷的生產則達到了封建社會制瓷業的鼎峰。于是,中和村就這樣地設天造般的成就了宋朝外銷瓷器的燒造,成為絕代的扛鼎之作。
而幾乎同一時期,就在中和村的宋代瓷器燒制、外銷正旺的時候,宋代“豪放派”詞人的代表、大文學家蘇東坡與“婉約派”的一代宗師秦少游也淌著這條北流河水而來。北宋紹圣四年(1097年),62歲高齡的蘇東坡從惠州再貶儋州,途中,與其弟蘇轍相會于藤州北流河口的得月樓。蘇東坡望著樓下波光滟滟的河水,浮想聯翩,作下《吾滴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尚在藤也。旦夕將追及,作此詩示之》以記之:
“九嶷聯綿屬衡湘,蒼梧獨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煙梅里,落日未落江蒼茫。
幽人拊忱坐嘆息,我行忽至舜所藏。江邊父老能說子,白發黃頰如君長。莫嫌瓊雷隔云海,圣恩尚許遙相望。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共存亡。天其以我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古真吾鄉。”
宋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駕崩.徽宗即位,5月宣布大赦天下,65歲的蘇東坡獲赦奉命回還,于9月7日至玉林經北流河乘竹筏下容縣再到藤州,受到藤州太守徐疇元及其子徐瑞常的熱情接待,并一同暢游東山,蘇東坡逐又作《浮金享戲作》一詩以記之:
“昔與徐使君。共賞錢塘春。愛此小天竺,時來中圣人。松如遷客老,酒似使君醇。系舟藤城下,弄月鐔江濱。江月夜夜好,山云朝朝新。使君有令子,真是石麒麟。我子乃散才,有如木困輪。二老接白籬,兩郎烏角巾。醉臥松下石,扶歸江上津。浮橋半投水,揭此碧粼粼。”
詩中盡顯蘇東坡對古藤州的由衷贊美,蘇東坡的詩在古藤州的土地上代代相傳,浸潤著這一方水土,讓古藤州伴隨著北流河水的流淌在墨韻中文脈飄香。
蘇東坡的得意門生秦觀,字少游,于宋哲宗紹圣元年(1094年)被貶,命運一再坎坷。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后,秦少游被放還湖南衡陽,在回程的途中也走到藤州,他饒有興趣地游覽了北流河口的光華亭,并將晚上睡覺時夢見自己填的一首詞《好事近·藤州與客誦夢中長短句》:“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橋深處,有黃鸝千百。飛云當面化龍蛇,妖嬌轉空碧。醉臥古藤蔭下,杳不知南北。”他正念著的時候覺得口渴,便叫人取水來。待取水到來.不料秦少游競對著那水大笑起來,并在笑聲中溘然長逝,循著北流河水而來的絕代詞人就這樣將一縷清魂永遠地留在了藤州的秀麗山水間。
中和村就是這樣生長在北流河邊上,與北流河相生相依、相得益彰。中和窯精美的陶瓷經過窯工的燒制在北流河的碼頭上源源不斷地沿著這條水上絲路輸送到東南亞的泰國、馬來西亞、柬埔寨等地,在大國的歷史上書寫著“宋瓷”的輝煌:而隨著蘇東坡、秦少游順著北流河水的游走,則將另一個“宋詞”的巔峰流淌在古藤州北流河的清波里。
三
中和村是有著渾然天成的瑞祥之氣和內涵深厚的文化張力的。
孔子在《中庸》中說過“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又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至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李耳在《道德經》中則說,“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為和。”因此,是否可以說“中”是“和”的本來面目,“和”是“中”的具體表現和必然結果,把“中”推廣到“和”,就可以使天地萬物各處于它們合適的位置,世間的事物也就可以正常地生長、發展,這或許就是“中和”的本質。
就象“中和”的本質“土生萬物”一樣,從航拍的照片看,中和村如同是一只張開了翅膀的老鴉,安祥地停靠在北流河的岸邊,它是那樣的率然隨性,而又恰到好處,所以從遠古的時候開始,村子便有著一個顯得粗俗而又十分形象的名字叫做羅鴉塘。然而,就是這個叫做羅鴉塘的村子,竟然天降大任一般承擔起了在千年以前與江西的景德鎮、福建的德化瓷比肩扛鼎的瓷業三雄的重任,成為中國在世界的代名詞——精美的外銷瓷器的窯址所在地,不得不令人驚詫于這鬼斧神工般的造化。北流河流域自古以來就有制陶的歷史,據陳遠璋《廣西考古世紀回眸與展望>中記述,北流河流域在新石器晚期可能就出現了原始陶器:至秦漢之交,已經出現了胎陶:到東漢,更出現了陶器作坊,而且規模有所擴大:再到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北流河流域已有了零星燒制瓷器的窯爐,出現了制瓷工藝:而到兩宋及以后,北流河流域影青瓷、青花瓷的生產則達到了封建社會制瓷業的鼎峰。而《藤縣志》則記載著,除中和窯外,在藤縣的北流河口還有兩處窯址,一處是勝西窯址,共有窯室4座,呈馬蹄形分布:另一座是1964年發現的雅窯窯址,距鐔津古城約1公里,也為唐宋時期的窯址,疊燒的瓷囂有碗、盤、碟、杯、壺、罐等,是否就是這樣的“天地位焉”造就了“萬物育焉”,使羅鴉塘本能而又隨性地孕育成了大雅的“中和”,而中和村就這樣地設天造般的成就了宋朝外銷瓷器的燒造,成為了絕代瓷器的扛鼎之作,定格在千年以前那個叫做大宋的歷史朝代里。
經過了將近1000年的歲月輪回之后,我們走進這個叫“中和”的村子里,依然能讓我們觸摸到當年窯爐燒制的火熱場景。在村子靠近北流河的一邊,刻印著歲月斑駁記憶的幾個原始碼頭依然靜靜地躺在那里,仿佛還在喧囂著當年槳聲帆影的鼎沸之情:而中和圩的街道上,兩旁店鋪富有嶺南水鄉特色的騎樓則在默默地向行人們述說著它昔日繁華的景象。街道村巷幾乎全部是清一色的瓷器匣缽壘徹而成,雖然建了不少新的房子,但以匣缽作墻體建起來的傳統四合院老屋依然散發著古香古色的歷史遺光。在村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廣西壯族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兩塊牌子赫然在目。
我們走到一堵由匣缽徹成的圍墻前,看著一行行由光潔精美的匣缽排列壘成的墻體,發現一些匣缽上刻印著一些符號,仔細一辨認竟然是字,再仔細分辨發現許多匣缽上都刻有諸如“肆”“梁”“李”“伍”等字樣,同行的一個朋友說他很早就注意到這些了.并且正在收集這些匣缽,現在已收集到了“謝二”“李一”“六十六”“莫二”“李二十”“覃貳”“生”“小李”等幾十個字樣,計劃要收集到100個,然后再做成一個“百匠碑”,鐫刻在中和村里。我們揣摩著這些刻在匣缽上的字符,這是當年窯工們計量的依據?還是燒制質量的憑證?抑或是有著更深厚的未解文化內涵?這確實讓我們不得而知,但透過“百匠碑”的姓氏讓我們去體會將近1000年以前中和窯的窯工們精工細琢的大國工匠精神,這也著實是一件莫大的好事。
這就是中和村,一個古時叫羅鴉塘的地方,因為有了這條北流河,有了這座千年前的窯址,就如此這般的如詩似夢,讓人摸不透、看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