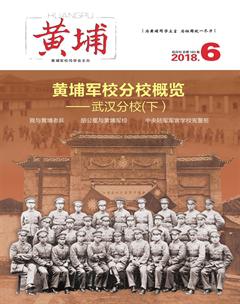我是臺灣人更是中國人(十二)
我要沖破“新戒嚴”
一
我創(chuàng)造“新戒嚴”這樣一個概念,主要來自李登輝2016年出版的書《余生》給我的靈感。李登輝說,“余生”指的是他用最后的生命,來提出他對臺灣的主張、指引臺灣的未來。我立即想起,先前蔡英文說過,馬英九已經(jīng)是即將卸任的領導人,卻在人民事先不知情的情況下,和大陸領導人習近平見面,呼吁馬英九“不能框限臺灣的未來”。
然而,李登輝所謂的“余生”,不也正在用他的路線來框限臺灣的未來?事實上,李登輝雖然卸任多年,但他的路線一直繼續(xù)操控臺灣政治最核心的統(tǒng)獨議題。試問:一個九旬老人的余生,憑什么封鎖我們這些年輕人的出路?臺灣青年必須奮起,掙脫這個老人給臺灣安上的桎梏!
李登輝在臺灣翻云覆雨,做了整整12年的領導人,他一路拔擢的徒子徒孫、黨羽早已遍布臺灣產(chǎn)官學各界,牢牢掌控臺灣的思想、歷史、政治、經(jīng)濟、新聞等方方面面的話語權。因此,李登輝時代看似早在2000年就結束,其實仍在延續(xù)。
陳水扁上臺后,李登輝隨即在2001年便出手,刻意扶植、成立“臺灣團結聯(lián)盟”,利用“極獨”路線掣肘、框住陳水扁。“臺聯(lián)黨”是一個以李登輝為精神領袖的政黨,以“一邊一國”“臺灣本土化”“臺灣國家正常化”為訴求,完全繼承李登輝路線的政治主張,在兩岸政策上堅持李登輝提出的“兩國論”,對大陸市場主張“戒急用忍”,反對大陸成為臺灣經(jīng)濟的出路。“臺聯(lián)黨”的出現(xiàn),使得陳水扁不敢采取中間路線,為了爭取選票,陳水扁只能繼續(xù)在“極獨”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新一任臺灣的執(zhí)政者蔡英文,宣稱即將卸任的馬英九“不能框限臺灣未來”,然而繼承李登輝路線、繼續(xù)框限臺灣未來的,正是蔡英文自己。回顧李登輝執(zhí)政末期,提出兩岸是所謂“特殊國與國關系”的“兩國論”,就是由時任“國安會咨詢委員”的蔡英文,奉李登輝之命領取“國安局”專款補助撰寫的。當時蔡英文同時擔任政治大學教授,在1999年8月16日,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國安局局長”丁渝洲,稱需要臺幣262萬元(約人民幣52萬元)來研究“特殊國與國關系”,丁渝洲隔天就撥款,此事被稱為“816專案”。
李登輝的路線是什么?他的陰謀已在新書《余生》當中全盤托出,那就是要徹底利用“中華民國”的殼來實現(xiàn)“臺獨”。所以李登輝宣稱,不需要真正的“臺獨”,他也從未主張過“臺獨”,他要的是“中華民國臺灣化”。他聲稱臺灣實質已經(jīng)“獨立”,和中國是海峽兩岸兩個“主權國家”,這套論述就是不折不扣的“兩國論”,就是“臺獨”。所謂“中華民國臺灣化”,實際上就是“去中國化”,就是“臺獨”分裂的另一種說法。
這就是李登輝的本質,也就是所謂的李登輝路線。從1996年到1999年,李登輝就一直不斷地把他的李登輝路線提到臺面上。早在1996年李登輝當選后,便接受美國CNN專訪,主張所謂的一個中國,必須是未來統(tǒng)一之后才會出現(xiàn),目前的中國是分裂的,在臺灣就叫作“中華民國”,這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本來就有的。
李登輝的此番言論,很巧妙地將兩岸“分治”偷換成了“分裂”,再用“中華民國”作擋箭牌,掩護其“臺獨”的本質,為之后他在1999年提出“兩國論”做鋪墊。三年后,李登輝借由接受“德國之聲”專訪的場合,提出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系”的“兩國論”,之后再通過陸委會正式宣布,宣稱臺灣的兩岸政策從此進入新的階段。
“兩國論”提出后,當時國民黨的人幾乎都在替李登輝打圓場,包括連戰(zhàn)、胡志強、蘇起這些國民黨大人物,當時都在幫李登輝的“兩國論”圓場。但大陸非常清楚,“兩國論”就是將兩岸指為分裂,分裂就等于“臺獨”,不管用什么名稱、什么形式來包裝,宣稱兩岸分裂為兩個國家,那就等同于“臺獨”。
二
李登輝路線的核心是,他相信臺灣可以利用國際強權之間的角力完成獨立。李登輝路線看似縝密,卻有一個他無法保證的前提,那就是他自認為的中國必然會崩潰。許多反華學者,都自稱多少年前就看出中國將會崩潰的影子,結果多少年過去了,中國不但沒有崩潰,而且快速崛起,但李登輝卻還是對中國崩潰論深信不疑,又或者是不愿意承認現(xiàn)實,并且用盡手段不讓臺灣人認清現(xiàn)實。
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許多臺商便看到了中國崛起的機遇,準備進入大陸市場,但李登輝卻提出“戒急用忍”,警告臺商中國會崩潰,并對兩岸經(jīng)貿發(fā)展做出種種限制,斷送臺灣一代人的發(fā)展契機。
然而中國不但沒有崩潰,而且正以前所未見的速度崛起。而當年沒有聽李登輝的話,仍然勇敢進入大陸市場的郭臺銘與蔡衍明,今天都是臺灣首富級的人物。
李登輝無法回答“中國會不會崩潰”這件事,執(zhí)行李登輝路線的一干黨羽也無法回應中國崛起的事實,所以只好用盡方法蒙騙臺灣人,想盡辦法蒙蔽、丑化一切關于中國的資訊。當全世界都爭相與中國崛起的潮流接軌,認真研究中國模式的內涵,臺灣卻被圈養(yǎng)在無知的同溫層,像極了當年的“戒嚴”時代,臺灣當局拼命阻擋人民看見外頭真實的世界,以維持統(tǒng)治的穩(wěn)定。
我們這些臺灣的年輕人,自以為成長在“解嚴后”,孰不知是活在無形的“新戒嚴”里。曾經(jīng),這種把臺灣封鎖起來的“新戒嚴”結構,在2005年連戰(zhàn)訪問大陸后被撼動,并一直到2008年馬英九開放“三通”后,才成功打破了這個結構。然而,從“太陽花反服貿”開始,這個結構又重新恢復。散布在產(chǎn)經(jīng)學各界、李登輝所拔擢的徒子徒孫們,繼續(xù)通過有意挑選過的教育及新聞,不讓臺灣人了解中國崛起的真相。
李登輝心里很明白,現(xiàn)實世界中,“臺獨”只能說不能做,“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所以他才堅稱自己不是“臺獨”,仍要死抱“中華民國”的招牌,認為借此就能逃避中國大陸的壓制,并維持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上的支持。
他始終不敢走完他口中“臺灣國家正常化”的最后一里路,實現(xiàn)2004年他曾高喊的“公投制憲、正名建國”,卻又不肯認同“九二共識”“兩岸同屬一中”,寧可讓臺灣永無止境地在“不正常”中浮沉,宣稱附屬于臺灣的釣魚島屬于日本,爭取日本右翼的支持,等待遙遙無期的“中國崩潰”之日,斷送一代又一代臺灣人的未來。
難怪他在任時就急著用行政資源推行“去中國化”教育,把年輕人都教育成“臺獨”分子。造成的結果,是我們這一代在“解嚴”后出生、成長的臺灣青年,從國家觀到世界觀,統(tǒng)統(tǒng)都為李登輝路線所框限,就如同我們說“戒嚴”時代成長的父母輩,人人心里都有一個“小警總”,那么我們這代的臺灣人,甚至比我們更小的學弟妹,心里也都有一個“小李登輝”。
身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臺灣人民理所當然有權利分享中國崛起的機遇,但現(xiàn)在卻被李登輝路線制造的“反中”“仇中”民粹所壓迫,封鎖了臺灣人民的出路。臺灣因此只能繼續(xù)惡斗內耗,政客們忙著分贓,分的還是臺灣所剩不多的老本,再將發(fā)展停滯、民生凋敝的禍源都指向“中國”。
如今,李登輝用他所剩不多的政治生命,將這條路線交給了蔡英文,如同該隱的封印,重現(xiàn)他經(jīng)常自比的摩西與約書亞的傳承。自命臺灣新世代的“太陽花”領袖,像是黃國昌、林飛帆等人,在選后也一一接受李登輝當面授記,成為“新戒嚴”體制的接班人。
難道臺灣的命運,就只能跟隨李登輝的余生,一步一步走向毀滅嗎?我不甘心、并且有決心沖破這樣的“新戒嚴”!這將是一場臺灣人民的自救運動,沒有人能阻擋我們的意志,關鍵在我們自己對信念的堅持。
附錄
臺大座談會紀實:王炳忠VS獨派快問快答
2014年11月19日,我受臺灣大學研究生協(xié)會邀請,以新北市議員候選人身份,到臺大主講青年從政的甘苦,約200名學生及民眾參與。
臺灣大學研究生協(xié)會,即代表臺大全體研究生的學生自治團體,由臺大研究生選舉出的代表擔任干部。多年來,“獨派”團體一直在臺大各學生團體中著力甚深,通過臺大各學生團體培植從政人才,如“太陽花”運動的學生領袖林飛帆,就曾擔任臺灣大學研究生協(xié)會的會長。
當天的座談會開放聽眾對我提問,內容卻幾乎都圍繞在統(tǒng)獨議題。由于大家都知道我是大統(tǒng)派,當天幾乎是“獨派”學生總動員來挑戰(zhàn)我,形成了我與“獨派”的一場快問快答。
以下即根據(jù)當天講座的錄影,節(jié)錄出我與提問者之間的問答內容。
問(年輕學生):“臺灣獨立”的議題,講了20幾年還是沒有結果;但從1949年后到現(xiàn)在60幾年,統(tǒng)一也是沒有結果。不知相比之下,您對于獨立、統(tǒng)一之間的比較利益和機會成本,有何看法?
回答:機會成本上,對臺灣下一代最有利的選項,是追求終極統(tǒng)一。請聽清楚我這句話,“維持現(xiàn)狀”和“追求終極統(tǒng)一”,其實差別只在一線間,但是前者是不負責任地回避問題,后者則給予人民明確的方向。
也許你會說,那為何不講“追求終極獨立”?但現(xiàn)況是,講到“獨立”會遇到很多阻礙。“獨立”可以是很多人的理想,但在可行性上,如果我們硬要“獨立”,會遇到以下幾種情況:
一是戰(zhàn)爭,如果打起來,難免生靈涂炭,就像大家看到過去國共內戰(zhàn)那樣家破人亡。又或是拖上很長時間,大家俱損,一直這樣耗下去,東亞大亂。當然也有可能,臺灣打贏了,“臺灣獨立”真的成功了,那你還是要面對,如何與“中國”這個最大的鄰國相處問題?他與你變世仇,那將是歷史難解的恩怨。
所以接續(xù)你的問題,估算機會成本,權衡現(xiàn)實和理想之間的考量,“追求終極統(tǒng)一”對臺灣人民才是最有利的。臺灣人不須放棄對中國大陸的話語權。看看歷史,臺灣承載了自日本殖民以來的恩怨情仇,包括國共內戰(zhàn)的悲歡離合,這都是中國近兩百年來被帝國主義壓迫后的產(chǎn)物,在臺灣具體而微被表現(xiàn)出來。
臺灣人應該多下工夫的是,我在現(xiàn)實權力上和大陸斗爭斗不贏,那我可以在話語權和你爭,爭話語權最有利的方法,就是大聲主張我也是中國人,我也要中國崛起的紅利,包括對未來中國發(fā)展的藍圖,我也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對臺灣最有利的利器,便是中華文化的正統(tǒng)。
我祖先跟著鄭成功軍隊來臺,當年本來要“反清復明”,可后來反清復明不成,就留在臺灣,等時間久了,再反過來講別人是外省人,我們是臺灣人。
今天對臺灣最好的道路,就是不要放棄“我是中國人”,不要放棄我們對“中國”的話語權。事實上,中國崛起的趨勢,各種數(shù)據(jù)都很清楚,從宏觀的角度來講,統(tǒng)“獨”不只是兩岸問題,更是國際強權的變動。美國主導的弱肉強食的西方價值觀,能否繼續(xù)領導下一個世紀?或者應該會有新興的力量出現(xiàn)?我們應該把自己看得更大,站在中華民族這股新興的力量上,而不是像可憐的小媳婦一般。
主持人(臺大研究生協(xié)會干部):對于統(tǒng)“獨”立場,炳忠認為“臺獨”會面臨戰(zhàn)爭,而跟“中國”統(tǒng)一的話,炳忠認為臺灣的歷史定位是什么?
回答:先更正一下,不是“跟中國統(tǒng)一”,兩岸同屬中國,應該說是兩岸追求統(tǒng)一、創(chuàng)造新的中國。今天我們在話語的表達上,本身就充滿了很多問題,比如“跟中國統(tǒng)一”“被中國統(tǒng)一”這種說法,都是我們把自己當小媳婦的怨懟或自卑心理。事實上,大陸和臺灣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是個更大的概念,很多人說大陸財大氣粗,不滿他來代表中國,那你為何又要自己放棄呢?
主持人(臺大研究生協(xié)會干部):所以炳忠的意思是,在中國崛起的這個時刻,臺灣不能放棄對中國的詮釋權,否則會喪失臺灣人本身的利益。
問(年輕學生):我們有一個女兒叫“臺灣”,隔壁有一個很有錢的惡霸叫“中國”,“中國”一直想要侵犯臺灣,但我們這老爸管得好,房門一直不給他開。結果后來換了爸爸,這個新爸爸就說,你嫁給他也不錯啊,可以從里面分化他們、分他們的財產(chǎn)。但為什么一定要嫁呢?
所以我想,剛剛你提到“會不會戰(zhàn)爭”等,這絕對是一種恐嚇的意味,因為以經(jīng)濟層面和政治層面來講,我都不認為“臺灣獨立”是會戰(zhàn)爭的。第二個部分,你說我們跟他們在一起了,我們可以爭取到更高的話語權和利益,但我認為更多人想要掌握的是,我們家就是我們家,我們不用跟別人交往。很明顯地,你今天不知道那惡霸背景就算了,那今天我們到“中國”能用臉書嗎?(注:2015年11月,大陸部分地區(qū)開始能上臉書,大批大陸網(wǎng)友到蔡英文臉書留言表達不同立場,竟又引起支持“臺獨”的臺灣青年要求管制。)
回答:剛剛你用女兒和惡霸來詮釋我剛剛的話,剛好讓我有機會,和大家分享我對兩岸關系的另一種比喻。本來中共跟國民黨是兄弟,國民黨是大哥,中共是小弟,而母親是中國。或者可以說,中國就像“鼎泰豐”老字號(臺北賣小籠包的名店),本來這老字號是傳給大哥的祖產(chǎn),但后來小弟把大哥給趕走了,然后大哥跑到臺北來繼續(xù)開他的鼎泰豐,牌子也堅持沒有換,所以我們還是堅持自己是中國,兩蔣時代還堅持自己是正統(tǒng),相信我們的小籠包比中共的更好吃,因為我們才是原汁原味的中華文化。
可隨著時間慢慢過去,對岸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客人也慢慢變多,都改跑去吃北京小弟開的“鼎泰豐”。面對這種情勢,原來臺北的“鼎泰豐”開始分裂,這分裂就是20年來的統(tǒng)“獨”爭辯,有人說我們干脆不要叫“鼎泰豐”了,也不要賣小籠包了,開始臭豆腐也賣、蚵仔煎也賣,結果人家更不吃了。
本來人家還因為你小籠包好吃挺你,現(xiàn)在你連小籠包也不好好賣,到最后甚至搞出“正名運動”,說我們換個名字說不定能更好,結果卻是更慘,沒有人要承認這新招牌。所以我的比喻是這樣,本來是兩個兄弟爭家產(chǎn),是兄弟內斗,但現(xiàn)在心態(tài)轉成我是可憐的小媳婦,變成剛剛提問的朋友說的“要嫁不嫁”。
在這種心理下,就是既不敢說我就永遠不嫁,又不愿意現(xiàn)在就嫁過去,甚至不給承諾。大陸說,那我和你先協(xié)議簽個婚約,臺灣也不愿意,還經(jīng)常跟美國、日本暗通款曲。過去臺灣嫌大陸太窮,現(xiàn)在大陸富了,又嫌人家不文明,但同時又要對方讓利,這就是今天臺灣的窘?jīng)r。
剛剛提問的先生說,我提到戰(zhàn)爭是恐嚇、是下流的說法,那是剛才有同學要我計算統(tǒng)“獨”的機會成本,所以我必須衡量現(xiàn)實條件。
要說惡霸,美國才是全世界最大的惡霸,但美國都不敢說不理中國。既然要談現(xiàn)實利益的機會成本計算,那我就客觀地做衡量,“臺獨”必然存在戰(zhàn)爭的風險。這不是我一個人講的,而是《反分裂國家法》擺在那,要“臺獨”的人,應該先要兵推看會不會贏!
問(中年男子):我在“中國”待過很長時間,在上海、廈門、深圳都有,我為什么回到臺灣?因為那不是個法治的社會,而是人治的社會,如果你真正對中國了解的話!所以回到我的問題,我想請問你剛才的一個論述,就是你說“臺灣人也是中國人”,這是你自己想象,還是臺灣人授權給你講的?我就不屑當中國人有什么不對嗎?
回答:首先,請你也證明,那又是誰授權你來問這個問題?好,那你就代表你自己,我也代表我自己,你講你的,我也可以講我的,對不對?
剛剛我說我自己的主張,我認為對臺灣最有利的道路,是臺灣人不要放棄對“中國”的話語權,這是我的意見、我的主張,你要聽便聽,不聽便罷,不用授權,沒那么復雜!如果要談授權,就立即“統(tǒng)獨公投”,立刻攤牌,這是最簡單的授權,不需要喊、也不需要沖,大家直接用投票,最后結果若是不當中國人要“臺灣獨立”,那要走的走,要留的留,打仗了也要自己承擔。
你們又說,我談打仗是恐嚇,那我剛剛也講,說不定臺灣打贏了、“獨立”了也是有可能啊,可就算打贏了還是要跟鄰國“中國”交往。所以不用那么情緒化,不用那么緊張說誰授權,謝謝!
主持人:我相信各位對臺灣的歷史脈絡和國際現(xiàn)實的理解可能有相當大的落差,那這方面我們可以再補充,還有問題嗎?
問(年輕學生):首先我想先謝謝炳忠愿意支持“統(tǒng)獨公投”,因為“統(tǒng)獨公投”是勢在必行,不論結果如何。再來我要跟炳忠說的是,你剛剛講的話有點不對,你剛剛試圖用客觀的分析來包裝大中國,陳述的內容大概是:第一,為什么我們不能“臺獨”,因為“臺獨”有戰(zhàn)爭;第二,為什么要統(tǒng)一,因為我們要搶大中國的話語權。
但這事實上是有很嚴重的謬誤。為什么呢?因為你雖然用很客觀的現(xiàn)實來講“臺獨”會發(fā)生戰(zhàn)況,但卻忽略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去搶到“中國”的話語權。炳忠完全忽略了這一點,天真地認為我們可以用現(xiàn)在“中華民國在臺灣”這樣一個邊疆地區(qū)的特殊情況,跟中國大陸爭法統(tǒng)、爭正統(tǒng)權,我認為是不切實際的。
炳忠一方面天真地認為,爭正統(tǒng)能贏得共產(chǎn)黨,但是對于“臺獨”方面又變得很實際,說一定會打仗。所以我認為你對利益的分析并不客觀,其實是非常主觀的,所以我想請炳忠對于這塊再多加思考。
回答:首先先表達一下我的感想,其實今天我們座談會的主題,應該是青年參政碰到的困境,而不是統(tǒng)“獨”辯論,但是我覺得大家討論統(tǒng)“獨”也不錯,因為這本來就是現(xiàn)在臺灣的核心問題。
對于他剛剛說我的分析其實非常主觀,我從來都不回避,我是主觀你也是主觀嘛!就像之前問“誰授權你說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的老先生也是主觀,還有很多問題都是主觀啊!這也沒什么不對,我思故我在,一個人沒有主觀,像柯文哲那樣變來變去、搖搖擺擺,才是假的啊!
柯文哲你是“臺獨”就講是,就認同你自己的理念,不應該閃躲。主觀很好,大家都應勇敢講出自己的理念。剛剛提問的朋友說,我好像是用一個現(xiàn)實的分析去包裝一個大中國的理念,其實大中國理念也沒什么對錯,關鍵要面對現(xiàn)實,對我來說不用包裝。
關于“統(tǒng)獨公投”,我已經(jīng)在各電視臺發(fā)聲多次,還幫各位去問民進黨板橋議員候選人黃俊哲,問他愿不愿意支持“統(tǒng)獨公投”,他卻說這不是主題,不愿意正面回答。大家要算賬就找他,自己在板橋選又掛民進黨中央職務,不敢面對“統(tǒng)獨公投”也不敢面對年輕人的聲音,請大家找他算賬去!我已經(jīng)很多次幫“統(tǒng)獨公投”發(fā)聲了。
主持人:如炳忠所說,今天是青年參政論壇,雖然說青年參選人的理念很重要,但還是希望大家能夠聚焦在市政問題!
問:我對于你剛剛講的“鼎泰豐”比喻很有興趣,試圖幫你補充兩個脈絡,看你同不同意。一是被趕走的大哥跑去臺北開店的時候,那個店址本來就有人在賣東西了,有人在賣少數(shù)民族風味餐,有人在賣日本拉面,大哥開那個店只標榜賣小籠包,對大家說我們要用原汁原味的小籠包搶回我們對“鼎泰豐”的正統(tǒng)招牌,那原本在賣少數(shù)民族風味餐和日本拉面的也很好吃啊,為什么變成只有賣原汁原味的小籠包?二是臺北店有老顧客,老顧客原本覺得就只有臺北店好吃,后來也想去對面小弟開的那一家試試看,結果就被關起來或是被殺掉了,請問你同意這個現(xiàn)象嗎?
回答:你剛才講,有人開日本拉面、有人開少數(shù)民族風味餐,當初我的祖先跟鄭成功來臺灣,也沒問少數(shù)民族要不要繼續(xù)賣風味餐,就賣起“媽祖婆”“王爺公”“初一十五要拜拜”這些文化,而這些文化現(xiàn)在已經(jīng)變成臺灣主體文化。就像所謂“臺語”,不也是我們祖先過來,占的人口多了,就硬說我們講的閩南語就是“臺語”啦?
再怎么說多元文化,一個地方還是有主體文化,那就是由民間長時間以來組成的主體脈絡。這文化脈絡,不可諱言還是以閩南人為主體的歲時節(jié)慶,變成今天大家說的臺灣人的風俗,這風俗也是漢人從大陸帶過來的啊!所以要講這東西是講不完的。
就像我說,今天大家認為要以臺灣為中心來論歷史,但臺灣是個沒有生命的島嶼,那到底是誰在創(chuàng)造臺灣文化,讓我們有歷史可以寫?不還是這些人啊!整個臺灣形成共同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體系,乃是奠基于中華文化的典章制度,由此產(chǎn)生后來對抗日本殖民侵略的“臺灣認同”“祖國認同”。在此之前的臺灣少數(shù)民族,只是分散各地的部落社會,遑論形成今天“獨派”愛扯的“臺灣主體”。
跟各位報告,荷蘭人來臺就三四十年,僅局限在幾個地方建立據(jù)點,能代表什么臺灣人呢?說是臺灣原本還有“賣日本拉面的”,但在日本統(tǒng)治50年期間,除了少數(shù)階層、一些媚日的“三腳仔”能夠躋身“皇民化”階層以外,多數(shù)臺灣人還是過著原來閩、粵二省傳來的風俗習慣沒有變,出身最臺南鄉(xiāng)下的我怎么可能不清楚呢?
我阿嬤走過日據(jù)時代,她說日本人硬要拿王爺?shù)纳裣袢_灣人都是要把神像藏起來的啊!大家都說看到日本警察很恐怖,都還得要跪在地上。金美齡和李登輝這些“皇民化”分子,把日據(jù)時代說成是他們美好的“跳舞時代”,那是因為他們是權貴階級的人,所謂的“高級本省人”啊!我阿嬤這些人沒權沒勢,所以所謂本土的話語權就被“皇民化”分子壟斷了。
主持人:感謝炳忠剛剛為我們做的回答,這是最后一輪提問,請各位聚焦在市議員要處理的市政上。
問(中年男子):我本人從事統(tǒng)“獨”問題研究多年。炳忠是希望我們選擇統(tǒng)一能和中國大陸爭話語權;很多人不同意,認為“臺灣獨立”才能成為一個國家。那我想請問炳忠,你身為“議員”候選人,對于統(tǒng)“獨”的實際計劃和配套措施是什么?因為我們知道,統(tǒng)“獨”都會面對很多不確定的風險,例如說統(tǒng)一后可能搶不過共產(chǎn)黨的話語權,“獨立”我們可能害怕戰(zhàn)爭、會有很多不確定性,那這些東西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實例,謝謝!
回答:我想這問題是大哉問,因為這是所有“總統(tǒng)”參選人現(xiàn)在都要回避的問題,那我王炳忠何德何能呢?但我盡量不回避啦!我就以我的淺薄知識,及我27年淺薄的人生資歷,加上我家族背景給我的一些觀念,來和大家聊聊。
我思前想后,對于臺灣最好的道路,就是“追求終極統(tǒng)一”這個答案,才是對臺灣最有利。這句話,我希望在座的朋友,你們用心好好去想想,我說的“追求終極統(tǒng)一”這個目標。我不是急統(tǒng)派,真的要馬上統(tǒng)一,事實上也統(tǒng)不了。但我們把它當成是終極目標,這是對臺灣最有利的。
至于配套措施與否,那真的是非常復雜的大哉問。我的建議是,臺灣內部趕快先凝聚共識。說起來,每個參選人都喜歡講共識,蔡英文也提了“臺灣共識”,但過了兩年,也沒講那到底是什么。如果她的“臺灣共識”,就只是聆聽每個人的意見,那這叫做不負責任。因為選你干嘛?選你就是要你幫我們總結啊!你總要先告訴我們,你的所謂共識是什么,我才曉得我們之間的共識一樣不一樣,才能決定投不投你嘛!
但是現(xiàn)在的候選人都在閃躲,都說我聆聽、我尊重,那到底是主張什么?我們仍然不知道!現(xiàn)在我只是先選一個小小的民意代表,要我講配套措施,我所能講的就是以上這些,就是建議大家追求終極統(tǒng)一,盡可能凝聚內部,大家對于國家民族認同有一個共同的認知,那就是按照“憲法”,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分治但不分裂;按照歷史文化的道統(tǒng),臺灣人是中國人,不放棄對于中國的話語權。這是我的解答,有了共識盡早跟對岸談,越早談籌碼越多,越晚談籌碼越少,則可能情況越不利。這是我的解讀,謝謝!
問(政治大學日文系教授,中年女性):我是政大黃老師,是做日本文化研究的,你剛剛講到“小籠包”又講到“話語權”,你認為的所謂“中國的一統(tǒng)”,它本身在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也在不斷地變化,不斷地商品化、不斷地大眾化和全球化。你說要忠于原汁原味,但我們臺灣其實就是“混種雜交”,尤其經(jīng)過日本殖民時代。
而事實上,中國大陸也正在大大地融和,搞不好真的統(tǒng)一以后,你連原本“鼎泰豐”的口味都找不到了!所以我想要說,請炳忠對于你剛剛提到的“話語權”“原汁原味”這些詞注意一下,因為近一百年以來,尤其是在消費社會的文化流動以來,要找所謂的原味,我認為在中國已經(jīng)沒有了。
至于你又認為,臺灣保留了正統(tǒng)的文化,你又把它說成是話語權,話語權和文化的源流是不一樣的。所以我認為,炳忠你對于歷史的傳承、以及階級所造成主體性的觀點是錯誤的。所以我請教你,你認為原汁原味在中國還有嗎?
還有就是所謂的話語權,應該就是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就像剛才我問東你可以答西、他問南你可以答北,這就是話語權,話語權就是尊重每個人現(xiàn)在想要表達的,這是我對于你剛剛歷史話語權的反駁,請你解釋,謝謝!
回答:黃老師用了很多她的專業(yè)用語,又講到話語權,又講到文化源流。其實我剛剛講的“原汁原味”沒那么復雜,一直細究哪家賣的小籠包,那是脫離主題。我其實就是單純從我的專業(yè),從國際關系的角度,探討所謂的“國家承認”及“政府承認”問題,只是用“鼎泰豐”及小籠包的例子,方便大家理解臺灣及大陸兩岸分別主張代表中國這個國家的問題。
至于談到話語權,我從沒認為誰的意見比較偉大,統(tǒng)派、“獨派”都有理想,當然都可以講話,所以我都非常正面地回答每個人的問題。剛剛黃老師說,“原汁原味”可能找不到了,因為有近百年的“雜交”過程,那么我要說,中國已經(jīng)雜交兩三千年了,但是中華文化從不是講血統(tǒng)種族,而是在大脈絡底下,兩千年來有一套共同觀念傳下來的文化,那就是以仁義禮智取代弱肉強食,以王道取代霸道的“天下秩序”,只要認同這套價值觀,就是中國人,就傳承了中華文化。
簡單講,過去我們在臺灣,都說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是中華文化的傳承者,而這樣的定位在近20年產(chǎn)生不同的見解,內部發(fā)生了些矛盾和不同的討論,而這個討論在我看來,拖垮了臺灣整體的競爭力,如果我們可以團結一致,和大陸共享這個話語權,今天也許我們能跟對岸談判的籌碼更多,這是我的意見。
大家也許認為,也不一定是我看的這樣,但我只想提醒各位一句,我們學國際政治的,知道現(xiàn)實是必須要去面對的。國際政治最講究現(xiàn)實大環(huán)境,而這確實是每個人都逃不掉的權力結構。不管是主張統(tǒng)一還是“獨立”,都不能偏離國際權力結構。當然,每個人對這個權力結構的詮釋可能不一樣,至于誰的判斷精準,最后只有讓歷史來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