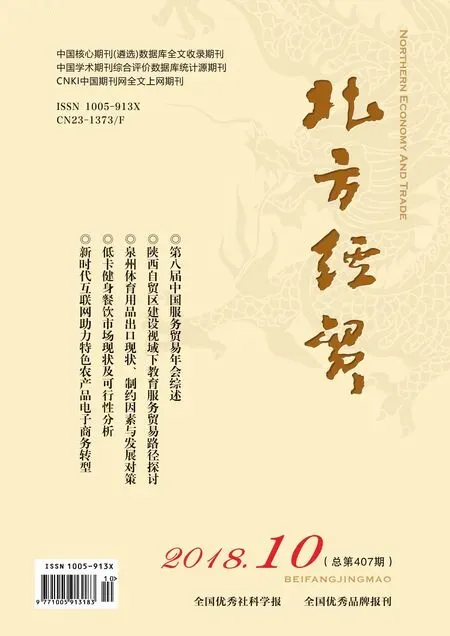新時代城鎮化的資金困局與對策
楊 華
(九江學院會計學院,江西九江332005)
一、引言
城鎮化發展歷經改革開放以來近四十年的快速增長,逐漸形成了以大城市為中心,中小城市為輻射,小城鎮為發展基礎的多層次城鎮體系,[1]長三角、珠三角和津京唐等核心城市群集群效應凸顯,成渝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武漢城市圈、皖江城市帶等都市圈初步成型。發展速度與發展質量并行、經濟發展與可持續增長并重的城鎮化模式,已經成為新時代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的普遍共識,[2]保障全體群眾均衡享受城鎮化發展帶來的改革紅利,實現城鎮化發展中結構與空間的協調統一,是當下城鎮化建設中的重要話題。城鎮化的協調發展離不開充足的資金供給和合理的資源配置,政府財政投入和轉移支付在城鎮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資金支持作用,但也帶來了地方政府債務高、資金利用效率低、資金供給嚴重不足等社會問題。如何解決城鎮化建設對財政投入的高度依賴,充分發揮金融體系的資金供給作用,建立多元可持續的資金保障機制,是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構建城市與城鎮協調發展新格局的現實要求。近年來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發展水平與城鎮化的互動關系(伍艷,2005;韋福雷等,2013;唐未兵和唐譚嶺,2017)、[3-5]金融支持機制的改革和完善(黃國平,2013;韓敘等,2016)[6,7]等方面,缺乏對城鎮化建設中資金供給問題的系統詮釋,現將系統梳理城鎮化實踐進程中資金支持的成績和問題,探索符合新時代中國特色城鎮化發展的資金支持體系。
二、新時代城鎮化建設的資金困局
(一)地方政府債務壓城
城鎮化建設的重點是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提供公共服務需求,以實現改善民生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宏觀目標,其資金需求的社會性本質與金融業的逐利性屬性背道而馳,[8]決定了城鎮化建設的資金來源主要依靠于地方政府的財政投入和自籌資金。地方政府通過成立投融資平臺向金融機構大舉借貸,是近年來城鎮化建設中重要的資金來源,在客觀上促進了土地城鎮化的高速增長,但受制于地方政府財力有限,這種資金供給模式缺乏可持續性,相當一部分地方政府已經陷入舉債擴張、賣地還債的惡性循環,債務風險急劇凸顯。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截止2017年12月,全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為16.47萬億元,這其中尚不包括地方政府融資平臺、PPP模式和政府性基金等隱性債務。WIND提供的包括政府債和城投債在內的地方債券規模已超22萬億,并在2017年末規模首次超過國債,地方債務違約事件已經開始顯現,防范地方債務風險已經引起政府和監管當局的高度重視。2018年3月財政部連續出臺關于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和規范的相關通知,進一步明確了金融機構不得再向地方政府提供直接或間接的融資,遏制債務增量和降低杠桿是現階段財政政策的主要指導思想,地方政府用于城鎮化建設的資金缺口將進一步加大。
(二)正規金融高度抑制
高質量的城鎮化依托于工業化和現代農業化的協調一致,如何給予現代農業和中小企業充沛的資金支持,促進區域經濟的健康發展,是當前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推動力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金融市場發展逐步深化,從建國初期集中于國有銀行的單一格局,發展為當前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大型國有銀行和中小股份制銀行并存的新格局,但金融抑制的基本特質并未根本性改變。[9]金融抑制下存貸款利率的嚴格管控使得資金提供方將空閑資金另投他途,銀行等金融機構存款流失顯著,與此同時貸款資金運用在無差別利率的引導下,導致資金配置效率低下,資源浪費現象突出。正規金融機構往往將資金投入利潤較高的大型企業和非農產業,甚而將縣鄉鎮吸取的資金傳送到中心城市和發達地區,在銀行系統效益攀升、經濟總量大幅增長的形勢下,中小企業和農業產業缺乏金融支持的融資困境卻始終無法解決。商業銀行等正規金融對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尤其是欠發達地區的資金支持與迅猛增長的金融需求極不匹配,極大的制約了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影響了城鎮化的進程。
(三)民間資本亂象叢生
金融抑制下的民間金融結合現代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突破了原有以熟人借貸為主的空間限制,規模總量持續攀升,參與主體和機構形式日益多元,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民間資本投資難和中小企業借貸難的資金迷局。與此同時,當下的民間金融存在著信用機制的先天不足,加之缺乏有效的行業監管和行政約束,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傳統高利貸的部分特質,金融風險隱患急速發酵,此前接連不斷的民間借貸崩盤事件即為明證。[10]超常的利息收益席裹了大量的民間資金,卻無法借貸于企業正常的生產研發,而是瘋狂涌入房地產、礦產等高利潤行業,資金鏈極易斷裂,嚴重影響了正常的經濟生活秩序和社會安定。可見民間資本尚未真正發揮其普惠金融的歷史使命,拓展資金配置途徑和金融市場的作用有限,無法為城鎮化發展提供穩定的資金支持,反而容易成為經濟和社會不穩定的誘發因素。據此,強化對民間金融的法律規范和行業監管,強化其在多元可持續資金保障機制中的有效地位,民間資本才能充分發揮其服務于新時代城鎮化建設的積極作用。
三、對策與建議
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改變以城鄉發展不協調、空間區域不均衡和規模結構不平衡為表征的城鎮化失衡現狀,構建以城市群為主體的城市與城鎮協調發展的新格局是新時代城鎮化的戰略目標,在此過程中既要進一步增強中心城市和發達城市群的引領作用,更要加快中小城鎮和中西部地區的跨越式發展。[11]
(一)轉變政府理念并合理調整角色定位
地方政府要從注重城鎮化規模的擴張逐步過渡到城鎮化質量的提高,加強城鎮化發展動力培育的投入,切實提升城鎮居民和轉移人口的社會福利和生活水平,推動城鎮化與現代農業化和工業化同步聯動,促進不同地域、不同規模城鎮化的協調統一。一方面要進一步加大城鎮化發展進程中對產業發展的資金支持,優先解決農業現代化和中小企業生產資金的融資需求,將產業促進、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資金需求進行綜合考慮,圍繞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作出統籌安排。政府要鼓勵金融企業創新金融產品,提高金融服務水平,優先為農業現代化產業和中小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加快構建信用評價平臺,提供嚴格規范的企業信用評級,提高資金供需雙方的信息透明度,切實提高貸款資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起主導作用的城鎮化模式中,深化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充分利用市場需求來調配各種資源和力量,通過政策引導積極探索多層次的資金市場,拓寬城鎮化發展的融資渠道。要發揮財政資金的導向作用,將財政支出重點投放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提供公共服務上,通過創新投融資機制和模式,廣泛運用市場化手段,鼓勵企業,社會和居民積極參與城鎮化建設,促成以政府、企業和個人為多元主體的投融資機制。
(二)規范民間資本并構建多元金融供給機制
城鎮化發展中多層次的資金需求必須依托于多元化的投融資供給機制,在傳統的財政資金投入和商業銀行信貸體系之外,民間金融是當前極具創新活力的資金融通模式。民間金融扎根本土具有天生的信息優勢,相對正規金融手續簡便、方式靈活、融資和放貸效率較高,特別是對商業銀行覆蓋不足的欠發達地區、農村地區,以及中小企業、涉農產業和城鄉居民生活等方面發揮了正規金融的有益補充作用。與之同時,相當長時間游走于地下的民間金融缺乏頂層設計和法律規制,監管體制不夠健全,風險防控機制極度缺失,蘊含著極大的金融風險。基于此,必須根據市場經濟法制化的內在要求,依托現代化管理手段和方法,有效引導和監管民間金融的有序發展,真正發揮其普惠金融的歷史作用。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放寬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條件,培育和規范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擔保公司、理財公司、網絡平臺等民間金融組織機構,為城鎮化建設提供資金保障。總之,新時期城鎮化發展的資金需求需要建立一個包括財政撥付、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地方債券、民間資本的多級金融供給體系,為不同層次、不同規模、不同地域的城鎮化建設提供全方位的資金支持。
(三)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并適度創新金融產品
長期存在的金融壓抑制約了銀行體系的規模優勢和渠道優勢,商業銀行占據金融市場絕對主體地位,卻無法充分發揮與其量級相匹配的資金輸血能力,必須加快以利率市場化為核心的金融體制改革,盡快建立符合市場經濟的供需機制以提高資金配置效率,滿足城鎮化發展對建設資金的迫切需求。通過有序開放金融市場準入,引入民間資本、國外資本充分參與金融市場競爭,逐步改變國有商業銀行的金融壟斷格局,凸顯資金供求和風險等市場要素在決定存貸款利率中的基礎性作用,重構多元化的商業銀行體系,實現貨幣資本的優化配置。商業金融機構應當立足城鎮化發展不夠協調的現實背景,加快探索與新時期城鎮化相適應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適度創新,拓寬對欠發達地區和對中小企業及農業產業的支持途徑,發揮其資金融通的主渠道作用。各類金融機構要在控制金融風險的基本前提下,進一步創新抵押貸款方式,在政策允許范圍之內完善多樣化的融資擔保體系,針對不同的資金需求對象提供差異化的金融支持,對符合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和核心競爭優勢的企業給予優先支持。大力發展商業保險市場,進一步深化銀行業和保險業的廣泛合作,探尋保單質押等銀保金融新模式,努力滿足城鎮化建設的金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