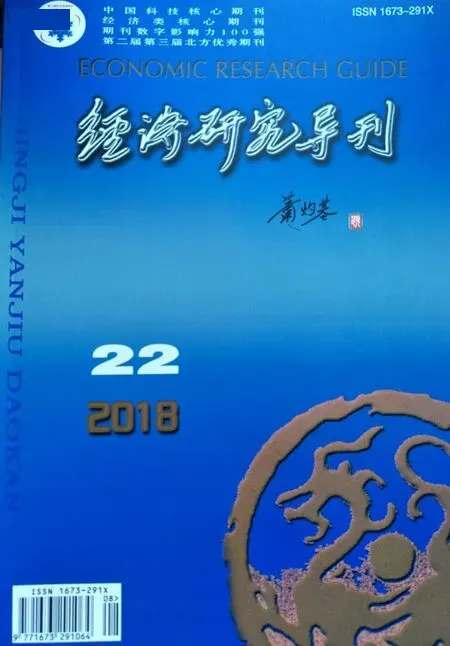農村人情及禮俗消費行為研究文獻綜述
崔永江,衛錦荷,王 瑤
(佳木斯大學,黑龍江 佳木斯 154007)
當前,關于農村人情及禮俗消費行為方面的研究,國內己經有相當數量的研究文獻。不同學者從各自學科特點出發,以其不同的研究視角、研究重點和研究標準為我們提供了較全面的研究視野,為正確認識這一復雜社會現象提供了廣闊的視角。
一、從社會學視角的研究
社會學視角對人情及禮俗消費的研究,主要從人際關系、情理社會、身份角色定位等角度展開。研究者主要圍繞人情及禮俗消費的現狀、特點、危害,產生這種現狀的原因,社會功能及作用等方面進行闡述,并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類觀點:
1.人情及禮俗消費作為復雜而長期存在的社會現象,有其客觀存在的必然性。翟學偉(2004)以“情理社會”入手,從人際交往的現實出發,對人情和禮俗消費進行了研究,指出:“中國社會就是一個講人情面子的社會。”[1]中國人對“人情面子”尤其重視,沒什么就是不能沒“面子”,原因在于“它的運作方式同情理社會相契合”[1]。費孝通(2006)使用社會結構分析方法整體宏觀地考察了人情禮俗消費現象,提出了獨創的“差序格局”理論,準確地區分了中國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關系,并被國際社會學界所接受。在此格局下,每個人都以自己為中心結成網絡,并在這個特定的網絡圈內維持著各種利益均衡[2]。
2.人情及禮俗消費存在的原因是復雜而多方面的,但在具體的原因分析上,觀點存在“地域性”差異。金曉彤等(2010)以豫南楊集村為例,通過實證考察,闡述了在傳統與現代的雙重背景下農村居民人情消費行為存在的基緣,指出這種基緣是中國傳統社會所獨有的。并得出結論:“我國農村居民的人情消費行為既有源于中國傳統社會的‘村落’文化的傳承,又有中國社會現實帶給中國農村居民的‘擠壓’的結果。”[3]潘曉華等(2016)以山東某農村“人際關系”類型為切入點,通過“互動”角度分析了禮俗消費“作為一種行為過程和心理取向,在一定的社會結構和體制中的變化和發展”[4]。并指出,這“不僅是一種表達性的過程,還是一種建構過程”。
3.關于人情及禮俗消費正、負兩方面的作用和影響,哪一方更大些,目前尚無定論,還需進一步的研究探討。胡杰成(2004)指出,農民的人情禮俗消費行為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考慮了道德、工具理性計算及情感因素后的“社會理性”行為[5]。曹海林(2003)認為,關系網絡親疏、人情往來的平衡及情感認同是維持農村人際交往平衡性與連續性的“關系”準則[6]。楊慰春(2010)運用社區研究方法對山東省臺頭村進行實證研究,為我們展現出了人情禮俗消費背后更為真實存在的人際關系[7]。陳柏峰(2011)提出,傳統的“熟人社會”即是一張微觀權力關系網,人們的行為往往都是圍繞著“人情關系”展開,并體現為感情、關系、規范和機制等層面[8]。
二、從經濟學視角的研究
運用西方經濟學相關理論分析人情及禮俗消費行為,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劉軍(2004)嘗試從經濟學的角度,探討人情消費對農民生活產生的影響。人情消費也是一種“變相的成本投入,所以也存在收益預期”[9],既然存在收益預期,沒有人會愿意白白浪費了成本,這就是為什么雖然很多人倍感厭煩,卻又不肯單方面退出“人情圈”的原因。陳云等(2005)運用經濟學“博弈論”方法,對農村人情禮俗交往中非常規現象的產生進行了剖析,并圍繞人情禮俗消費行為的核心禮金確定過程(初始出禮和若干還禮),對這種現象對農民生活造成的重負給予了理論解釋[10]。孟濤(2006)從一個典型家庭生命周期的角度,考察了農村人情禮俗消費行為中經濟理性算計因素的影響和作用,指出隨禮行為雖然是農民的自主選擇,但“這種家庭之間的禮金循環過程,并不總是處于平衡狀態,‘理性算計’是貫穿于整個家庭生命周期的通盤考慮”[11]。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農村中最傳統的社會交換領域,已經大量滲入了經濟計算理性,農村社會關系呈現“理性化”趨勢。田學斌等(2011)借助經濟學中的“交易費用”范式,嘗試對非正式制度約束下的農村人情消費現象進行解釋,并指出:“農村人情支出與交易費用之間存在著一種內生的而不是任何外在強加的聯系。”[12]
三、從文化人類學視角的研究
近年來,通過文化人類學視角對人情及禮俗消費進行的研究成果較多,學者們多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依托開展研究。歸納起來,主要存在以下幾種觀點:
1.人情及禮俗消費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且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閻云翔(2000)從中國傳統社會文化視角出發,以中國農村(下岬村的典型個案)中的“禮物交換”為媒介,通過實證研究,分析了一個具有代表性中國鄉土社會中的禮物交換體系,并對這一社會現象從文化差異性和社會實踐角度進行了評介。“相對于特定的中國文化,傳統人情禮俗文化已深深根植于人們的思想意識中。”[13]與西方的社會關系結構不同,中國的社會關系結構是以由人為中心的網所支撐著的,是非制度性的。
2.人情及禮俗消費之所以如此受到中國人的重視,是因為它的表現形式、運作方式及價值取向同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情理”社會相契合。秦廣強(2006)基于情感維系、道德支配、理性權衡三個理論緯度,在實證調查(魯西北A村為典型個案)的基礎上,從文化功能角度概括出當前農村人情禮俗消費主要由“禮尚往來”型、“欠情—報恩”型及“工具目的”三種類型構成[14],并指出,這些類型和特點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正逐步發生變化,“即人際交往中傳統的‘人倫關系’與‘契約關系’相互滲透。”[14]
3.中國人的人情消費或禮物交換是以情感相依及個人關系為紐帶,而非理性計算為基礎。李倩(2007)以農村社會交往的“人情圈”為切入點,指出:“傳統農村家庭間的人情往來是鄉村社會文化的重要特征。”[15]它的“產生、進行的過程以及中止都遵循著特定的原則”[15],是農村社會中人與人、家庭與家庭之間維持利益均衡的重要手段。田維緒等(2010)指出,中國人重視人情消費是因為受中國傳統“禮”文化深刻影響所致,禮尚往來,互惠互利,感情投資、講究回報是人情交往的一個重要法則。他指出:“如何處理好人情禮俗關系至今仍然是我們日常社會交往中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16]
四、從心理學視角的研究
目前為止,從心理學視角出發對于人情及禮俗消費的研究成果較少。心理學方面探討的觀點主要圍繞“為什么在普遍認為人情及禮俗消費是一種負擔的情形下,多數農村家庭仍然無休止地進行的心理關注”進行的。研究者大多側重于探討:農民們到底是基于什么樣的從眾“心理動機”進行人情禮俗消費的?這種“心理動機”產生的根源和社會背景又是什么等。李偉民(1996)從本土化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探討了人情禮俗行為及實際運作過程,指出:“作為一種行為規范它是人與人之間建立關系、進行交往的行為準則。”[17]蔡恩澤(2004)總結了人情禮俗消費行為人們的幾種常見心態:一是從眾心理[18]。雖然對人情債很反感,但別人都這么做了,為了“后路”(以后可能會有事求到對方)也只好隨大溜。二是補償心理[18]。認為如果自己遇“事”不“辦置”酒席,就收不回以前的人情投資,長時間下去自己就吃虧了。三是攀比心理[18]。“投之以桃,報之以李。”認為人情往來的頻繁程度,禮金的多少才是感情厚薄、關系遠近的象征,為了“面子”也不惜舉債送禮。四是報恩心理[18]。認為就是利用別人家辦“事”的機會還個人情,對方也容易接受,這種心理尤其常見。牛娜(2010)從傳統消費心理角度分析了當前農村人情禮俗消費行為,并歸納了六個方面的心理過程:即攀比、從眾、補償、虛榮、斂財及投機心理。她認為:“農村家庭人情禮俗消費主要受到傳統消費心理及消費習慣的制約。”[19]對于送禮者來說,心態也不一樣,有真正表示賀意的,多集中在關系較密切的人群,而大多數人送禮者都是本著“禮尚往來”礙于情面而來,“至于送多送少,送禮者心中自有一把尺子。”[19]
五、結語
通過對現有代表性文獻的總結和分析,筆者認為,國內學者對于人情及禮俗消費行為的相關研究,無論是從范圍還是成果數量上來說,都是比較廣泛和豐碩的,也提出了很多有建設性的意見。但這些研究還過于分散,體系性不強,并不能十分完整而準確地解釋這一社會現象,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學科的分散性。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方面的研究比較集中,成果較多;經濟學和心理學方面雖有一定的研究,但成果較少;個案研究較多而運用多學科,從多角度、全方位進行的綜合研究則較少。二是視角的局限性。運用中國本上化理論進行的研究相對較少。三是缺乏對比性研究。對于西方社會相對于中國傳統社會、制度性相對于非制度性、個案調查相于對區域性差異、農村社區相對于城市社區特殊性認識不足。三是結論的不確定性。當前學者們對于人情及禮俗消費產生的負面作用和由此產生的消極影響基本都持批評態度,但卻沒能清晰地闡明是否由于其諸多消極因素而將其消除,還是由于有它“必然存在的 意義”而任其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