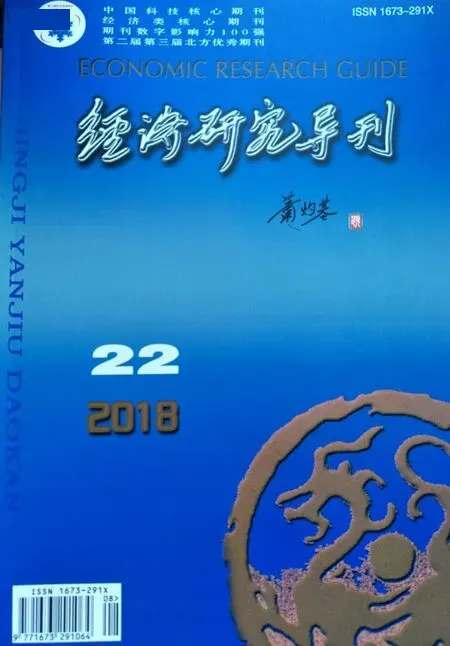民營經濟發展研究文獻綜述
周 麗,華國江,李文燕,林楚凡,林永寧,賴曉純
(肇慶學院,廣東 肇慶 526061)
引言
民營經濟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概念和經濟形式,是富有活力和潛力的經濟成分和推動經濟社會加快發展的重要引擎,雖然曾一度在中國消失,但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漸進發展中得以復興。改革開放前,國家對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固守著原有的意識形態,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公有制經濟,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的唯一實現方式。但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人們越來越多地關注公有制經濟以外的所有制形式,民營經濟作為非公有制經濟的一種實現方式,逐漸受到人們的關注,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從“公有制的有益補充”逐漸發展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伴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民營經濟已經成為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主力軍,在國民經濟中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
一、關于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演進軌跡
成玉琴(2005)對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政策法律環境存在的深層次問題進行分析,指出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民營企業的政策經歷了從允許發展到支持、鼓勵和引導其發展,對私營企業主經歷了從“不要動他”到肯定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1]。多年來,對民營經濟的政策在認識上不斷深化,在法律上不斷完善,對促進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陳宗仕和鄭路(2015)對制度環境與民營企業的績效關系進行研究,他們認為,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是合法性[2]。改革開放初期興起的一些個體民營經濟不得不掛靠在公有實體下取得合法地位。1987年,中國第一個民營企業立法(即《溫州私人企業管理暫行條例》)于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溫州地區通過。1988年,全國人大以此為基礎頒布了國家層面的《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民營企業的合法性終于浮出水面。1992年,黨的十四大進一步確立民營企業的合法地位。而在2002年黨的十六大上,民營企業主被允許入黨,此舉被視為提高民營企業合法性的重大舉措。
陳齊芳(2016)對激發民營經濟發展動力視角的供給側改革路徑進行研究,他指出,中共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推出了一系列擴大非公有制企業市場準入、平等發展的改革舉措[3]。主要有: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負面清單之外領域,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運營,鼓勵社會資本投向農村建設,允許企業和社會組織在農村興辦各類事業等等。
李政和任妍(2015)在對“新常態”下民營企業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研究中指出,黨的十七大報告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和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4]。在此背景下,頒布了一系列與民營企業自主創新等方面①此處指科技投入、市場準入、融資政策、財政投入、稅收優惠、保護權益、創新人才引進、研發機構建設等。相關的政策措施。②此處指“非公經濟36條”、《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中小企業29條”、“新非公經濟36條”“小微企業29條”。為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黨的“十八大”更是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2015年,中央適時推出“中國制造業2025計劃”,推動中國制造由大變強的戰略藍圖與“互聯網+”的發展大勢相融合,順應網絡時代“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趨勢。
二、關于民營經濟發展的成就
謝倫盛(2015)基于對廣東省民營經濟發展環境的研究,指出民營經濟對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已超過60%,特別是其解決了近80%的就業人口,民營經濟在保持經濟增長、穩定就業水平、優化產業結構和提升社會創新力等多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已成為影響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因素[5]。他總結出民營經濟的發展幾年來取得的成就包括:民營經濟增加值逐年上升;民營經濟單位戶數規模擴大;民營經濟產業結構轉型加速;民營投資增速加快、占比上升;民營企業繳稅減少;民營經濟從業人數增長迅速,吸納就業能力增強。
吳玲蓉(2012)對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及對策進行了探討,她提出從我國經濟發展的增長量來看,民營經濟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最大驅動力來源,推動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民營經濟整體經濟規模實力在不斷壯大和增強[6]。民營經濟成為企業自主創新的主要力量,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約70%的國內技術創新、65%的國內發明專利和80%以上的新產品都來自于中小企業。并且,在全國53個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以及政府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中,民營科技企業也分別占到70%、80%和以上,推動了我國企業開展自主創新和轉型升級的戰略的進程。
張維迎(2015)對國企和民企的發展進行了發展歷程的探討,他提出民企的發展在漫長的過程中取得一個又一個成就,個體戶在1982年獲得合法地位,私營企業經過長時間的爭論后,在1988年獲得法律地位[7]。1989年政治風波以后,政府發動了又一輪對民營經濟的打壓運動。因此,自然地,幾乎所有在19世紀80年代成立的非國有企業都注冊為“集體企業”(在農村地區則是“鄉鎮企業”),盡管其中許多實際上為私人所有并運營。1992年同樣是民企發展的轉折點,在鄧小平對改革的重新推動下,政府轉變了對私企的反對態度,民企的發展甚至受到鼓勵,越來越多的新民企建立起來。
宋子鵬(2016)[8]基于“十二五”期間的廣東民營經濟發展取得的成就研究,指出民營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產業結構持續優化,第三產業占比上升;民營單位數量大幅增長,質量顯著提升;民營投資快速增長,投資領域趨于高端化;“走出去”步伐堅定有力,高端產品出口份額顯著提升;民營企業創新投入強度加大,產出水平顯著提高;民營單位從業人員穩步增長,成為吸納社會就業的主要渠道[8]。
對于改革開放后民營經濟所取得的成就,郭今萃(2009)認為,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后的發展中,民營經濟發展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內容和形式;民營經濟在吸收人員就業方面取得十分突出的業績;民營經濟創造了社會財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民營經濟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力量;民營經濟優化了城鄉結構,構筑社會和諧基礎[9]。
三、民營經濟的困境
對于民營經濟在發展中遇到的困難,余力和孫碧澄(2013)這樣認為,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已成為制約其生存和發展的最大瓶頸[10]。利率管制、所有制歧視、資本市場嚴格準入等金融抑制政策導致民營企業正規金融渠道狹窄。
趙麗和馬程程(2017)認為,在論述民營經濟發展障礙時,“傳統思想的認識歧視”這一觀點極具代表性[11]。傳統理論認為,社會主義只能有公有制一種所有制形式,而私有制是產生一切剝削、壓迫和不平等的根源,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自然也要實行公有制。這種思想觀念反映到實踐領域,就會轉化為對民營經濟的各種歧視與限制。
此外,高福一等(2015)以山東省民營經濟發展情況為例,指出魯地重農輕商、重義輕利和小農意識較濃,并且受官本位、學而優則仕等傳統思想觀念的束縛,部分成長型企業只看眼前卻看不到將來,因此初期發展迅速,但后勁不足,再投資創業的意愿下降,缺乏做大做強的投資膽量和發展氣魄,難以去突破自有瓶頸[12],這與浙商的“重利尚義”、蘇商的“重商主義”新義利觀不同。
褚敏和靳濤(2015)將地方政府主導、國企壟斷和民營經濟發展放入同一個邏輯框架進行分析,嘗試著揭示阻礙民營經濟發展體制的因素[13]。研究發現,地方政府行為對民營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而國企壟斷對民營經濟的發展則具有明顯的“擠出效應”。此外,政府主導與國企壟斷的結合體—行政壟斷更是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障礙。
張杰(2000)認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對中國的漸進改革與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但近年來卻面臨著嚴重的金融困境[14]。而民營經濟的金融困境是漸進改革過程中內生的現象,其實質是信用困境。民營經濟金融困境的解除不能依賴于現有的國有金融框架,而要尋求以內生性為特征的金融制度創新。其中關鍵的一點是,外部金融支持機制的建立不能以破壞民營經濟的內源融資基礎為代價。沒有良好的內源融資機制,民營經濟的發展將失去起碼的資本結構基礎,會重蹈國有經濟的覆轍。
結語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國家相關政策的限制和落后傳統思想的束縛,民營經濟曾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改革開放后,民營經濟開始進入復原、摸索、初期成長的時段,經濟體制全面改革,民營經濟在穩定經濟增長、調整經濟結構、保障民生三個方面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中堅力量。1992年鄧小平發表重要講話后,民營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在鄧小平對改革的重新推動下,政府轉變了對私企的反對態度,鼓勵個體、私營、外資經濟發展。至此,民營經濟開始進入蓬勃發展期。伴隨著十五大的召開,民營經濟逐漸得到了地位的提升,被視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十一五”期間,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環境不斷改善,民營經濟快速成長,占國民經濟比重快速提升,能力不斷增強,大大縮小了與其他經濟成分之間的差距,民營經濟的社會效益不斷提升,在增加就業、擴大出口、提高收入、創造稅收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十二五”期間,民營經濟規模不斷擴大,單位戶數規模大幅增長,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加速,民營投資增速加快,從業人數增長迅速,吸納人才就業能力增強。總的來說,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后的發展中,民營經濟創造了社會財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力量。但中國民營經濟發展仍存在著很多問題,一方面,民營經濟發展面臨著競爭力不強、產品與服務低端化、融資難、技術進步乏力、管理水平低等一系列內部問題;另一方面,國有經濟壟斷和政府干預等外部環境因素也嚴重制約著民營經濟的發展。而且,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已成為制約其生存和發展的最大瓶頸。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民營經濟發展不僅要進一步推動傳統產業結構升級、擴大民營經濟規模,還要優化融資環境,重視人才培養,以提高企業競爭力。更重要的是,國家進一步完善民營經濟發展制度和信用制度,營造良好的發展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