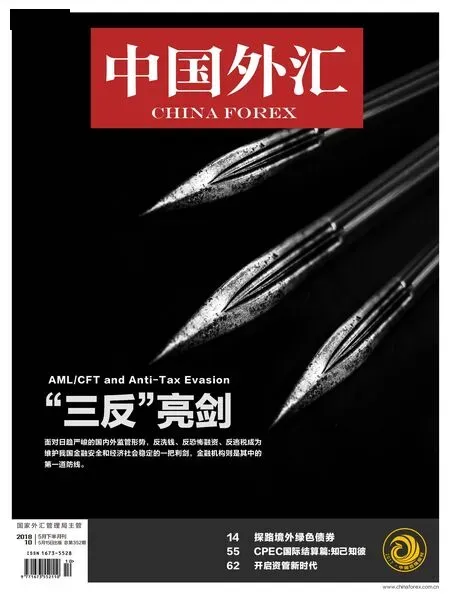基建投資大幅放緩的背后
沈建光
瑞穗證劵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
去杠桿導致的貨幣收緊對基建投資雖有沖擊,但并非導致其大幅回落的主要因素,相對而言,財政收緊以及債務約束增強的影響則更為顯著。
2018年一季度,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累計增速為7.5%,比1—2月回落了0.4個百分點。在其三駕馬車——房地產投資、制造業投資和基建投資中,基建投資放緩最為顯著:一季度同比增長13%,增速比1—2月回落了3.1個百分點,創2012年以來新低。基建投資大幅回落的原因是什么?又是否會對今年經濟增長造成壓力?
有觀點認為,基建投資大幅下降源于去杠桿作用的顯現。但筆者認為,雖然始于2017年的金融去杠桿與嚴監管將當前貨幣政策帶入中性偏緊,對基建投資產生了沖擊,但并非導致其大幅回落的主要因素,相對而言,財政收緊以及債務約束增強的影響則更為顯著。
筆者對固定資產投資中民間與非民間投資進行比較后發現,近三年二者的走勢出現明顯背離:2016—2017年,非民間投資(與基建投資高度相關)明顯高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民間投資則顯著低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而2018年,在非民間投資大幅回落的背景下,民間投資卻得益于經濟內在動力的增強出現反彈。
在筆者看來,用貨幣政策收緊難以解釋二者走勢的背離,畢竟相較于非民間投資,民間投資在資金緊張的背景下,受到的負面影響會更大,包括更難獲得貸款資源,以及需要承擔更高的資金成本等。這說明,基建投資的大幅回落應另有原因。
分省份看,一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回落最快的三個省份(含自治區及直轄市)分別為天津、內蒙古、新疆,三者投資增速分別為-25.6%、-26.2%和-30.3%,比2017年分別回落了個26.1、33.4和50.3個百分點。而考察上述省份今年來的變化可知,其均面臨嚴格的財政約束。
繼去年遼寧公開承認統計數據造假之后,今年天津、內蒙古也紛紛“擠水分”,這與兩地的固定資產投資大幅回落不無關系。各地方政府紛紛從“虛報”到“擠水分”,其背后最深刻的原因在于干部考核機制的改變。相比于以往的唯GDP論,當前對GDP考核的弱化,以及對債務風險、環保、民生等變量的重視,使得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債務風險的控制,注重增長從速度到質量的轉變。
從另一個角度看,上述下滑最明顯的三個省份,恰恰是上一年債務風險最突出的省份。如在2017年地方政府債發行增速超過10%的6個省份中,新疆、天津債務增速最快,分別達到19%和18%。而2018年,新疆在各省份中率先叫停政府類項目,要求PPP項目全線停工,對于已開展前期工作的建設項目,凡資金來源落實不了的,一律不得上報,不予受理。而此前,內蒙古多條地鐵線路已被叫停,也源于債務風險過高。
由于GDP考核機制的改變,2018年以來,越來越多的省份降低或者放棄了固定資產投資目標。此外,伴隨著去杠桿與債務收緊,基建投資的多個來源在2018年也均在收窄。如作為地方建設低成本資金來源的抵押補充貸款(PSL),2018年以來增速就有所下降。2017年年底以來,財政部就整肅規范地方融資和PPP業務多次發文,要求全面規范金融機構對地方政府的投融資行為,并用四個“不得”為金融企業與地方政府合作劃出了紅線。
基于上述舉措,筆者認為,基建投資在今年余下的時間或整體延續一季度以來的下行態勢。特別是對于一些債務風險過重的省份,下降幅度會更為顯著。但據此就認為基建投資會失速,甚至對經濟增長造成嚴重拖累,則筆者不能認同:今年區域投資仍有亮點,特別是海南自貿區與雄安新區的建設加快,可以抵消負債過重省份投資快速下行的風險。
2018年一季度,海南投資增長25.3%,明顯高于2017年的10.1%,在所有省份中表現突出。習近平主席在海南經濟特區設立三十周年的講話中,明確了未來海南四大新定位,這對于當前經濟發展與基建水平較低的海南而言是很高的要求,也意味著未來海南的基建投資諸如港口、公路、橋梁、水道和機場等將會出現快速發展。
而4月21日發布的《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則提出,到2035年,要基本建成綠色低碳、信息智能、宜居宜業、具有較強競爭力和影響力、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水平社會主義現代化城市。筆者認為,雄心勃勃的雄安新區規劃的落地必將帶動環保、基建、軌道交通等多項投資快速增長,或將成為未來十年帶動區域投資的重要一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