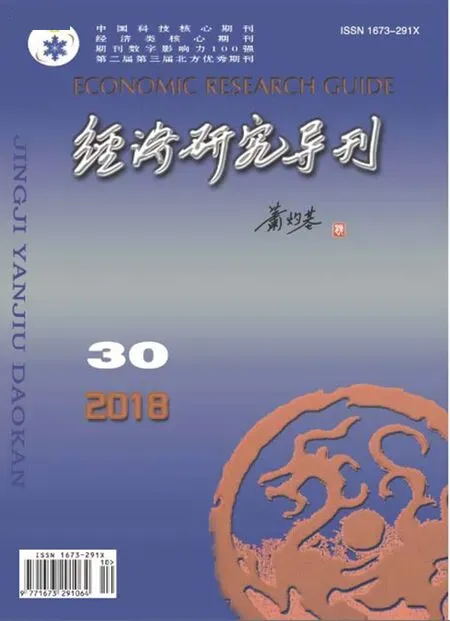流動人口參與城市“三變”改革的路徑構建
杜良杰,周 怡
(貴州大學管理學院,貴陽 550025)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其中提到,“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新背景下,如何管理好流動人口群體、實現城市融入和市民化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貴陽作為貴州省內唯一的大型城市,外來農民工不斷增加,其住房、就業、收入等現實問題亟待解決。2017年,貴陽市委、市政府提出開展城市“三變”改革,以此全面統籌推進“五位一體”戰略布局。目前而言,貴陽推行的城市“三變”改革,更多的還是市民的加入,如白云區的“梵華共享”項目,實際上作為收入低微的流動人口還未能參與進來。因此,為順利實現流動人口參與城市“三變”改革,本文擬從理論層面探討貴陽市流動人口參與城市“三變”改革的可能性。通過探索流動人口參與城市“三變”改革的影響因素和路徑,以期為政府構建促進公平分配、先富帶后富的有效手段提供思路,力推城鄉融合發展。
一、文獻綜述
當前,具體從城市“三變”改革這一視角研究流動人口的文獻還沒有,但針對流動人口城市融入、社區參與等方面的研究已較為深入。流動人口城市融入的影響因素研究。多數學者認為城市流動人口遷移決策主要受人、自然、社會、經濟特征及區域環境條件等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1]。流動人口的差序格局會影響其城市融入[2]。個體層面的性別、婚姻年齡等因素及家庭層面的家庭規模、家庭總收入等因素均對流動人口的家庭遷移狀態有顯著影響[3]。除個體特征外,有學者認為對法律規范以及現代城市組織有較多的了解、家庭經濟收入高以及有正能量的流動人口相對容易融入城市[4]。
流動人口社區參與的研究。通過提升公民素養、提高社區參與的意識和能力、加強社區自身建設、提升社區的服務質量能有序推進流動人口的市民化[5]。有學者基于流動人口在融入城市社區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從而探尋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社區的途徑[6]。學者認為,戶籍制度而形成的制度性身份是影響流動人口社區參與的核心變量,流動人口的社區參與受其所居住的社區場域的影響,流動人口的融入城市意愿和本地人歸屬感對社區參與具有顯著的影響[7]。
二、貴陽市流動人口參與城市“三變”改革的可能性分析
(一)“推—拉”理論:流動人口參與城市“三變”改革的雙向性
就“推—拉”理論來看,流動人口往往是從成本和效益角度進行流動決策的[8]。因此,流動人口參與城市“三變”改革往往同時源自于外部的機會和個體層面的發展訴求。首先,作為城市“三變”改革載體的社區組織要承認并重視居民流動人口參與的權利,為流動人口提供參與城市“三變”改革的平臺和機會,鼓勵流動人口參與改革,從而提升流動人口的社區組織歸屬感和責任感;另一方面,流動人口需要樹立參與城市“三變”改革集群發展的意識,作為行動者而不僅是成果的接納者參與其中,在參與過程中實現權力并獲得自身發展。
(二)流動人口參與城市“三變”改革的影響因素分析
1.內因:流動人口的能動性參與。年齡、受教育程度對流動人口落戶意愿影響顯著,而性別和婚姻狀況對流動人口落戶意愿有一定影響[9]。據此,筆者推斷貴陽市流動人口參與城市可能性與流動人口個體特征中的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有一定關系。其中,流動人口年齡階段的不同,思想有所不同,其追求夢想可能有較大差異,參與城市“三變”改革可能性也不同。其次,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的等級越高參與城市“三變”改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受教育水平越高,思想層次就越高,理解能力越強,這部分流動人口也就更可能主動參與到城市“三變”改革。較高文化程度的流動人口更容易獲得較為穩定的工作和較高的收入,其生活圈也就較穩定,也更可能參與到城市“三變”改革。就性別而言,女性受家庭、婚姻因素影響大,其受到的約束或就更強,所以性別對于其參與城市“三變”改革可能會有一定影響。另外,已婚流動人口更趨向于成熟和落戶城市,所以參與城市“三變”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流動人口在流入時間長短和個人月均收入對城市融入影響顯著[10]。所以,貴陽市流動人口在城市的工作時限與工作收入也可能對其參與改革有影響。在城市待時間較久的流動人口,自身積累的資源可能更為豐富,也就有更多資源入股企業、合作經濟組織,獲得更多收入,因而更傾向于參與城市“三變”改革。而有較高收入的流動人口,也有更充裕資金可入股社區合作經濟組織、企業等經營主體,預期收益更高,所以也就更愿意參與城市“三變”改革。
2.外因:外部環境的導向性。流動人口的城市融入受到結構約束的影響[11]。良好的結構整合主要是指政府、市場與社會三者之間的協同契合:政府政策規范、許可、激勵與引導,如戶籍制度的改革;市場機會公平、創造、拓展與豐富;社會多樣性且包容力大,共容性空間大。政府系統、市場系統、社會系統內部整合良好,三個系統之間契合度高。如果三系統的力量較為協調,整合資源的能力較強,共同作用形成較好流動人口參與城市“三變”改革的風險機制、退出機制,更好的保障流動人口的權益,形成良好的外部條件,流動人口就更可能參與到城市“三變”改革。反之,如果上述三個系統之間或者內部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結構整合比較差,外部環境堪憂,流動人口對參與到城市“三變”改革會有諸多顧慮,其參與的可能性會受到消極影響。
三、貴陽市流動人口參與城市“三變”改革的路徑探討
(一)貴陽市流動人口參與城市“三變”改革的原始路徑探討
原始路徑,即流動人口—市民化—城市“三變”改革,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流動人口—市民化,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12];二是市民化—城市“三變”改革,即通過市民化后獲得相應的市民權,也就恰好符合城市“三變”改革中提出的“市民變股東”。如此,流動人口就能更廣泛和穩定的參與到城市發展中,參與到城市“三變”改革。總體而言,此路徑屬于漸進性的參與過程。
1.流動人口市民化。基于現實的制度困境,筆者提出貴陽市流動人口市民化的三個途徑:其一,順應城市化現代化發展的一般規律,把握貴陽加速發展的階段特征,科學選擇城市化發展戰略,走多元的城市化發展道路。把城市圈發展與城鎮城市化發展相結合,構筑科學的城市體系,充分發揮不同等級城市吸納和承載人口的作用,如貴安新區的打造。同時,培育就業取向的城市主導產業,扶持城市非正規經濟主體的發展,并通過城市間縱向產業鏈的聯結和延伸,為農民工在城市穩定就業和定居融入城市提供機會。如貴州黔中新興產業示范園區的打造,立足黔中經濟區大背景下做出的一項加快融入黔中經濟核心圈,實現與貴陽同城化發展的戰略舉措。其二,以農民工權利復歸和制度重構為途徑,進行流動人口市民化的農村退出的土地制度、城市進入的戶籍制度、城市融合的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以及住房、教育等相關制度的建設和創新,優化流動人口市民化的制度環境。其三,以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本積累和提升為途徑,增強流動人口市民化所需要的城市進入的職業轉換能力、城市生存的獲取穩定就業和收入的能力、城市融合的發展能力,包括反映其經濟地位變化的比較收益的決策能力、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談判能力、交易能力、規避市場風險的能力;反映其政治地位變化的參政議政能力、自我組織能力、自我維權能力;反映其社會地位變化的社會交往并獲取社會資本的能力、自我抱負與人生目標實現的能力,以及改變歧視的“可行能力”。
2.流動人口市民化后的城市“三變”改革參與。本路徑的第二階段,首先應充分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在城市“三變”改革中,政府作為主導力量,進行頂層設計,堅持推進“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的引領發展。政府整合流動人口分散的資源、激活資源活力、釋放資源紅利,政府資源和資金向這一群體傾斜。同時,政府聚集分散資金、撬動社會資本,改善城市環境、完善社會功能,提升城市供給質量。
然后,社區經濟組織和市民合作經濟組織應創新完善基礎治理體系,激活基礎社會活力。將政府依法依規配置的自然資源、經濟資源、社會事業資源和政策資源等公共資源使用權,以及發展資金通過股份投入享有股份權利。發展壯大社區經濟,完善社區服務功能,提升社區服務質量,增強基礎黨組織的凝聚力、戰斗力和號召力。使得市民化后的流動人口更為自愿的將資源、資產、資金、技術、知識產權等,通過與社經濟區組織、市民合作經組織訂立協議等方式,入股經營主體。
(二)貴陽市流動人口參與城市“三變”改革的綠色路徑探討
1.綠色路徑:直接參與。綠色路徑是流動人口—城市“三變”改革,即直接參與的過程,此路徑可以理解為突發式參與。首先,讓流動人口在參與城市“三變”改革后,再考慮其市民化的問題。通過上文對城市“三變”改革與城市融入關系的簡要分析,此處可理解為先讓流動人口參與城市“三變”改革就是在促進其市民化,兩者是并行不悖的。綠色路徑相對原始路徑可能更為省時有效,但同時需要認識到的是,此路徑對政府的主導作用以及社區經濟組織的治理體系要求更高。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完善基礎黨組織的管理體系,完善社區經濟組織基礎治理體系,是走此路徑的前提和必要條件。需各參與主體協同作戰,形成合力發展。
2.流動人口參與的多樣化模式。在有政府、企業、市民、經濟組織、流動人口等多主體參與的城市“三變”改革中,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可呈現“三變+”多樣化模式。社區經濟組織等主體為載體,流動人口參與發展分享紅利。如“三變”+政府+企業+流動人口、“三變”+流動人口、“‘三變’+……”等。無論任何模式,其實都需政府扶持。流動人口參與城市“三變”改革的模式可能是多樣化的,利益聯結機制不同,運作方式也各有不同,但究其有一個共同的內核:增加流動人口收益。
四、結語
原始路徑、綠色路徑是兩條有區別性的參與路徑,原始路徑主要考慮從市民化這一漸進實現途徑,流動人口—市民—股東。綠色途徑則是考慮讓流動人口直接變股東,跨越戶籍制度的約束。兩種途徑各有優劣,但發展條件亦各有差異。不可否認的是,兩條路徑的具體推行以及發展條件需要基于實踐作進一步研究。同時,不管是流動人口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參與城市“三變”改革,都應關注其內外部影響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