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球迷的裝腔指南
☉孫佳音
一夜成名
20 歲時,開始在酒吧駐唱,風花雪月,夜夜笙歌。30歲時,剃了板寸,戴著金項鏈,穿著夢特嬌無奈下海,開過餐廳、美容院、酒吧、公司,全數失敗。34歲時,淪為無業游民,天天坐在上島咖啡和人打撲克,體重一百七十多斤,挺著大肚腩,彎腰沒法為自己系上鞋帶……

吳秀波
42 歲時,又主演了一部電視劇,比八年前在《馬大姐和鄰居們》里客串一個書商,處境只是略略好轉。開播伊始,經紀公司的宣傳每天給記者打電話,重復著令人厭煩的推銷“這個劇真的非常好”,回應者寥寥。但幾乎一夜之間,媒體再邀約采訪,得到的回復是:“得協調下吳老師的檔期,最近可能沒有時間。”是的,這個男人叫吳秀波。
“中年得志,一夜爆紅”,哪怕你跟我一樣,昨天恰巧讀過一篇題為《還原一個不為人知的吳秀波:前女友因吸毒而死》的文章,也很難抹凈如此的印象。我不大喜歡“一夜成名”的勵志傳奇,就像我不大喜歡這專訪惡俗的標題。盡管它看起來是事實的一部分,盡管文章其實娓娓道來,細膩飽滿。
與其說我不大喜歡“一夜成名”,不如說我擔心這樣的標簽,會讓很多人產生錯覺,以為成功得來便宜。就像王寶強的故事,讓萬千“北漂”和“橫漂”不甘放棄,一等十數年,哪怕全無天賦。“他可以,我憑什么不可以”,還振振有詞。又如李宇春的成功,縱容無數少男少女癡心做夢,不愿醒來。“我比她還漂亮”,但傳奇本無法復制。
在這個最講究“命數”的行業,我依舊愿意相信努力和實力。討喜地說,吳秀波十年前為了討生活,拍戲要從六樓跳下,毫不遲疑;十年后業已成名,每天連續拍攝14個小時,他亦無怨言。刻薄地講,新劇開播前,他跟姚晨為了稿子里誰的名字排在前面,公關團隊分毫必爭。時間洗刷掉浮躁,這行的成功者無不是專注、刻苦而執著的。
偷偷生出幾分驕傲來,又很快生出幾分哀傷。畢竟確有一些地方,更講究人脈、資源或者其他,而靠讀書、靠個人奮斗,徹底改變命運,也越發困難了。
“大黃鴨”的奇幻之旅
1992年一艘從中國出發的貨輪,打算穿越太平洋抵達美國的塔科馬港,但途中遇到強風暴,一個裝滿2.9萬只浴盆玩具的貨柜墜入大海并破裂,里面的黃色鴨子、藍色海龜和綠色青蛙漂浮到海面上,從此隨波逐流。那些黃色充氣橡皮鴨,用它們微弱的浮力與堅忍的耐受力,在無邊無際的大洋里克服萬難,歷時15年,終于從中國漂洋過海,登陸英國、美國。

大黃鴨
這奇幻旅程,像是一個童話故事,其不可思議的樂趣與令人欽佩的勇氣,激發了荷蘭藝術家霍夫曼的創作靈感,他很快創作出首只“大黃鴨”。是年,充氣大黃鴨就開始游歷世界,這個可愛的家伙每到一地都會引來當地粉絲的瘋狂追捧,2013年的香港也不例外。岸上的男女老幼里三層外三層,在他們舉起的相機屏幕里,高樓林立的維多利亞港因為大黃鴨,瞬間變身童年的大澡盆,天真爛漫。大黃鴨沿著維港戲水,每轉一個方向就引來一陣咔嚓咔嚓的快門聲。
從人造雞蛋到仿冒的美國白宮,中國模仿者以善于突破世界的想象力而著稱,這一次他們同樣沒叫人失望。大黃鴨還沒來得及告別香江,就踏上了“山寨奇幻之旅”,環肥燕瘦的黃色充氣鴨子已在杭州、佛山、蕪湖、無錫、重慶、杭州、天津、西安、淡水、東莞等地招搖過市。它們或大或小,或被戴上了藍色的蝴蝶結并有了一雙長睫毛的大眼睛,或被可憐巴巴地關在商鋪門口的金屬圍欄里,相同的是都沒有得到著作權人的授權,都是赤裸裸地抄襲、侵權。
東施效顰,一哄而上,我們似乎已經習慣。山寨大黃鴨,不過是又一個笑柄。獲利微薄的國產山寨手機、行銷世界的“名牌”服飾和箱包、電視里滿滿當當的選秀相親節目;還有梳個大背頭一臉油膩相的金身彌勒佛、堪比美國國會大廈的縣委辦公大樓;對了,還有家門口那“金碧輝煌”的武寧路橋。粗陋的模仿者,無所畏懼地袒露出庸俗的審美趣味和膚淺的功利覬覦,并不在乎恥笑和唾棄。
盡管模仿可能是最大的恭維,但大黃鴨的設計者霍夫曼說,中國一下子冒出這么多大黃鴨,他一點也沒覺得有趣,“如果我是中國人,我會反感,我真的會很反感,這種行為會毀掉社會文化。”我是中國人,我不只反感,還覺得很羞恥。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精力充沛的廣場舞大媽們令人歡欣地跳出國門、走向世界了,紐約布魯克林的日落公園已經成為她們展示風采的舞臺。只可惜,因為公園周邊居民不堪噪音多次報警,舞蹈隊的領隊王大媽近日被當地警方戴上了手銬,還收到了傳票。在傳票上,警方列出她被控罪的理由是“在公園內沒理由地制造噪音”——當地法律規定,公園內播放音樂以及制造聲音所帶來的噪音必須低于35分貝,超過就是違法。

中國大媽的廣場舞
制造噪音并且不受待見的,還有數以百萬計的中國游客。“先聞其聲,后見其人”,這是別人對我們的印象。大約從農耕文明發展而來的中國人在大自然中生存與奮斗,習慣了大聲說話,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很多時候我們還用聲如洪鐘、振聾發聵這樣的褒義詞來形容聲音嘹亮,出門在外一樣推杯換盞劃拳斗酒,卻忘記了角落里低聲耳語或許正在嘲笑我們的老外。還有,那些在盧浮宮里大聲喧嘩的黃皮膚或許比在門外洗腳的更丟人現眼,不敢相認;甚至,一路歡歌笑語并且留下滿地果殼紙屑的旅游大巴上已用漢語寫下了警示標識,叫人羞恥。
對了,相比我們的國家電視臺曾在大衛像局部打上了馬賽克,煞有介事地講究“文明”,華人當街或在公眾視野內晾曬內衣內褲則經常討得他們的鄰居憤而上門,甚至無果后還不得不投訴至警局。去年秋天,嫁到伯明翰的北京姑娘只是在窗把手上晾曬女式內褲,就引得她的英國鄰居無比詫異,甚至敲門來問“這兒是不是提供色情服務”。后來她還收到了警局來信,因為附近居民懷疑其從事“非正常活動”。
以上種種,大約并不能簡單歸罪于文化差異引發的摩擦,一笑置之。而是隱隱地滲出我們對現代文明規范、對規則和法律的忽視,甚至無視。令人遺憾的是,從隨意闖紅燈到制售假冒偽劣產品,從學術論文造假到貪污腐敗盛行,渴望融入世界的中國依舊在肆意地破壞規則,從封建社會一路沿襲而來的“刑不上大夫”“法外開恩”等思想如今依舊時不時借尸還魂。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要真正贏得世界的尊重,起碼先要學會遵守“游戲規則”。比如艱難地適應世界貿易組織的種種規范,也比如逐漸習慣在交響樂樂章間不再鼓掌。而后一點,上海的觀眾,經過多年熏陶和培養,就做得很好。
偽球迷的裝腔指南
怎么才算越位?相信大部分人會回答,攻方傳威脅球的一瞬間,攻方球員超越了最后一名防守球員。非也,應是超越了倒數第二位防守球員,不能忽略了對方守門員嘛。如果守門員出擊,后衛在門前,超越了守門員也算越位。有沒有覺得我很厲害?其實我只是趁德國隊摧枯拉朽時翻翻雜志,里面剛巧有篇《一個偽球迷的自我修養》,姑且摘來試試。文章還教導說,為了掩飾弱點絕不能討論比賽細節,甚至可以帶著幾分失落說,我的足球賽季,在冠軍杯決出的那天,就結束了。或者說,童年看到的最好的世界杯,是巴喬憂郁地把點球踢飛了,在那之后,也許有更好的球星,更好的比賽,但就像魯迅在《社戲》里說的羅漢豆,以后吃的,再也沒有那夜的好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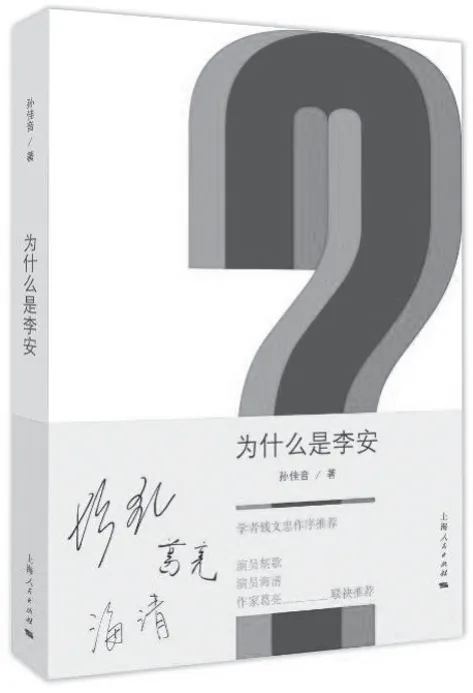
暗自揣摩了一下,嘿嘿。但我們又為何要學習這些裝腔作勢的小訣竅?是因為平時跟我們一樣不大看球的左鄰右舍一夜之間都成了范佩西和穆勒的發小,得收復談話中心的失地?就像陳道明的話劇和莫奈的睡蓮來了,不曾排隊買票,怎么好意思跟人說自己是文藝青年。還是因為熬夜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意義?于是一邊感懷大學時候在禮堂通宵看球的激情歲月,一邊在暗夜翻開領口端詳“年輕”的標簽,小小竊喜。
惶恐被時代和人群拋棄的我們,佯裝熱愛世界杯。其實異類未必有錯,只是不好意思突兀。就好像小時候哪怕刻苦溫書,交完卷子也要跟小伙伴討論一下前晚的港劇,其樂融融;就好像聽說好多名家,私下都不大喜歡《繁花》,但目力所及幾乎交口稱贊,畢竟已經名聲隆隆;就好像有些人沒有勇氣面對自己,最終娶一個不愛的女人回家,以逃避社會對同性戀的壓力。很多時候,自由而獨立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想起來,這些佯裝球迷的日子,倒有一張照片打動了我。日本隊首戰不敵科特迪瓦,但日本球迷在賽后冒雨撿拾丟棄在球場的垃圾。據說早有傳統,但也叫我覺得,哪怕“裝腔作勢”,哪怕從眾,也不全是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