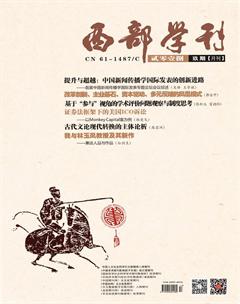英美意象派詩歌的視覺想象
梁晶
摘要:英美意象派詩歌是現代詩歌的起點。本文分別從意象主義與同期視覺藝術變革、意象派詩歌理論的視覺闡發、詩歌意象的視覺生成機制三個層面入手,分析闡釋英美意象派詩歌的視覺特質及由此生發的視覺想象。視覺想象不僅促成了英美意象派詩歌中充溢著強烈的通感意識,并且多種視覺媒介的互涉交融,還不斷完善豐富了其意象的視覺指涉,從而借助詩歌文本,達成主體間以及主體與客體的想象共鳴。
關鍵詞:英美意象派詩歌;視覺意象;想象
中圖分類號:I1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61-1487-(2018)09-0084-04
興起于二十世紀初的英美意象派詩歌運動盡管歷時并不長久,但其重要性一直得到詩人與學者的公認。其中,艾略特的一句話最常被引用:“出發點,即人們通常地、便利地認作現代詩歌的起點,是1910年左右倫敦的一個名為‘意象主義者團體。”[1]2意象派詩歌的權威論者威廉·普拉特在其經典論著《意象派詩歌——微型現代詩》中甚而將意象派詩歌創作與伊麗莎白時期的十四行詩相提并論,認為正是源于二者,才催生出之后兩個時代偉大詩人們的皇皇巨作。[2]11
視覺性是英美意象派詩歌的一個鮮明特質,根據意象派思想奠基人休姆(T.E.Hulme)的說法,“意象”一詞的最初起源即為“視覺意象”(visual image)。而從意象派初始理論的萌蘗直至后期的艾米主義、漩渦主義,英美意象派詩歌始終注重汲取并合成同時期繪畫、攝影、雕塑等多種媒介的全新話語元素。這一方面促成了在英美意象派詩歌創作中,充盈流溢著強烈的通感意識;另一方面,多種視覺媒介的互涉交融,也不斷完善豐富了其“意象”的視覺指涉,從而借助詩歌文本,達成主體間以及主體與客體的想象共鳴。
一、意象主義與同期視覺藝術變革
英美意象派詩歌的誕生與同期視覺藝術變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正如意象派詩人弗林特所言,在意象派看來,“藝術是一切的科學,一切的宗教,一切的哲學,一切的玄學”。[3]133世紀之交的藝術包括詩歌都深受傳統的牽絆,如何破舊立新成為彼時有志之士的共同吁請。與威廉斯同時代的詩人華萊士·史蒂文斯在寫給未婚妻的信中曾充分表達了這樣的心緒:“我獨自參觀了國家研究院。經過色彩繁雜的展覽廳時令人不覺耳目一新。但那些圖片,一幅接著一幅,卻很難再使人精神振奮……藝術家們一定如同詩人們一般變得愚蠢至極。一個熱愛色彩、形式、熱愛土地和人民的人對這些垃圾會怎樣做呢?”[4]116可見,無論詩歌抑或視覺藝術,都亟待變革與創新。
在所有現代藝術中,視覺藝術可謂最早啟動革新。以繪畫為例,自文藝復興時期始,西方傳統的作畫方式是以達·芬奇為代表的透視畫法,即強調畫面的“看似逼真”或鏡像式精確描摹。簡言之,西方傳統繪畫的根基是創作主體基于數學原理上的精準預設。而現代派繪畫則一反此傳統,它摒棄了傳統意義上的透視畫法,著意打破傳統畫面上的色彩、明暗、結構、線條等設計,轉而以凸顯物質本體的作畫方式以取代對現實世界的寫實性再現。在現代派藝術中,藝術想象的作用無以復加。一方面,從構思到作品的完成斷然少不了創作主體思想意識的參與;另一方面,鑒賞者在臨賞繪畫時,也需倚仗想象的馳騁,以達成與創作主體意識上的交融匯合。
對現代派繪畫的這一創作精髓,意象派詩人們顯然心領神會。譬如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就曾宣稱:“我已經嘗試將繪畫的設計融合到詩的設計中。二者性質相同。”[5]53而在回答“何為意象主義”這一問題時,弗萊徹給出的解釋更是與現代派繪畫的意旨如出一轍:
……意象派詩人應從最具想象的層面上對待其詩歌題材,并且從視覺上呈現它。對讀者而言,倘沒有經歷詩人創作時的那種情感,對之是無法領會的,除非他借助更高級的視覺與聽覺以便達成直接且徹底的想象感知。通過激發這些感官經驗以及運用合適的詞語表達,意象派詩人旨在引發讀者通達這樣的高度,即讀者可以憑借想象再度創造出詩人創作時的那種情感復合體。故而,意象主義首先是通過想象引發情感的一種手段(Imagism is,therefore,first of all a means of arousing the emotions through the imagination.)。[6]
可見,想象不僅在意象主義詩人的創作中不可或缺,同時,詩歌文本經由視覺感官經驗促發,又直接通達至讀者的想象,進而達成與創作主體想象相融合的視界。作為意象派詩歌的經典之作,龐德的《地鐵車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或可謂較好地詮釋了詩歌創作中的主體視覺感知與視覺想象:
人群中這些臉龐的隱現;
濕漉漉、黑黝黝的樹枝上的花瓣。[1]85
在《高狄埃-布熱澤斯卡》中,龐德曾如是追憶該詩的創作起因:“八年前在巴黎,我在協約車站走出了地鐵車廂,突然間,我看到了一個美麗的面孔,然后又看到一個,又看到一個……忽然我找到了表達方式。并不是說我找到了一些文字,而是出現了一個方程式。……不是用語言,而是用許多顏色小斑點。”[7]552也是在《高狄埃-布熱澤斯卡》這部回憶錄中,龐德再次述及該詩:“在巴黎的那段經歷與繪畫直接相關。假使我感知的并非色彩,而是相互關聯的聲音或多個平面,我就會采用音樂或雕塑的形式加以表達。但在當時的情境下,色彩是主要顏料,我是說色彩是最先進入意識當中,并與意識構成充分的匹配。”[8]101如果說正是“色彩”或“顏色小斑點”引發詩人的視覺感知與想象,那么,由這些“色彩”以及“臉龐”“樹枝”“花瓣”并置疊加的意象同樣傳導撞擊著讀者的視覺“意識”,進而在一次次的視域融合中,延展并豐富了該詩的解讀空間。
二、意象派詩歌理論的視覺闡發
如果說意象派之前的英美詩壇,到處充斥著抽象說教與主觀情感泛濫的詩作,那由龐德、休姆等人發起的這場意象派詩歌運動,無疑從根本上扭轉了這樣的詩歌困局。這一方面固然應和了當時藝術界盛行的“大范圍的叛逆意識”:“畫家、作家、音樂家、建筑家們感到自己正處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轉折點上,哲學思想與社會生活同樣處在決定性轉向上。轉變正在逼近。這種情緒激發了大范圍的叛逆意識以及隨時準備迎接大事件的到來。……藝術界從未像現在這樣渴望采取行動。”[9]205另一方面,意象派詩人有意識汲取現代視覺藝術思想與技法也是促成這一轉變的誘因所在,誠如威廉斯在《自傳》中所言:“ (文學作品)據此始觸及那些實實在在的東西。脫離開純粹想法之上的文學表達使詩歌與繪畫創作得以更緊密的結合。”[10]236這當中,比較重要的創作思想當屬意象主義著力倡導的意象“呈現”(presentation)。
倘細察意象主義相關宣言,不難發現“呈現”一語被多次提及。首當其沖的便是龐德對“意象”的經典定義:“一個意象是在瞬息間呈現出的一個理性和感情的復合體。”[11]135與之相關的,還有弗林特在1913年發表的《意象主義》一文中,將“呈現”明確納入意象主義的三大創作規則:“直接處理‘事物,無論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絕對不使用任何無益于呈現的詞。”[1]50而在1915年4月出版的《意象主義(1915)》“序”中,“呈現”一語更直接指向繪畫:“呈現一個意象(因此我們的名字叫‘意象主義)。我們不是一個畫家的流派,但我們相信詩歌應該精確地處理個別,而不是含混地處理一般,不管后者是多么輝煌和響亮。”[1]158換言之,意象派的“呈現”意在表明詩人在“處理事物”時應恪守既“直接”又“精確”的原則。茲以意象派的另一首經典短詩,威廉斯的 《紅色手推車》(The Red Wheelbarrow)為例:
顯而易見,全詩無任何“無益于呈現”的修飾語,僅僅是將三個視覺意象(wheelbarrow,water,chickens)簡單而直接地加以并置,通過對每個意象色彩、體積以及意象間結構的精心編排和處理,最終為讀者營造了無窮無盡的想象空間。事實上,威廉斯對事物的“直接”處理絕非偶然,這一方面受益于他的好友龐德及其領導的意象主義運動的深刻影響,另一方面,與他同當時蜚聲藝術界的斯蒂格雷茲群體的交往不無相關。
阿爾弗雷德·斯蒂格雷茲(Alfred Stieglitz)是二十世紀初一位知名的攝影家。他年輕時曾在歐洲研習繪畫,后回到美國,斯蒂格雷茲的攝影一方面深受當時歐洲現代派視覺藝術的影響,另一方面,他堅持自己的創作一定要立足美國本土。作為1913年震驚紐約藝術界的“阿莫瑞展覽”(Armory Show)主要發起人之一,斯蒂格雷茲畢生致力于美國現代藝術的創新。他開辦的美國本土藝術展數不勝數,受他提攜的藝術家也相繼成長為美國藝術界的中堅力量。威廉斯便是這些展覽中的常客。斯蒂格雷茲藝術群體對威廉斯詩歌創作影響深遠。通過與這個群體藝術家們的密切交往,威廉斯也將現代派藝術包括斯蒂格雷茲的攝影技巧成功挪用到自己的詩歌實踐中。
“直接”(straight)是現代攝影創作中慣常采用的一大技法,即攝影家在洗印底版的過程中,避開人為技術性的強制干預,不對底版做任何技術處理而徑自成像。斯蒂格雷茲的攝影作品常采用“直接”的方式聚焦并呈現美國本土事物。同樣,運用到詩歌的創作中,威廉斯也極力反對詩歌中的種種人為修飾,強調直接摹寫周遭的美國生活圖景。經由“直接”處理的詩在威廉斯的前期創作中可謂屢見不鮮,除《紅色手推車》外,《在墻之間》(Between the Wall)、《偉大的數字》(The Great Figure)等都是這一創作思想的突出體現。
在意象派詩歌創作中,像威廉斯這樣深受現代視覺藝術影響的詩人不乏其例,譬如意象派創始人龐德的詩中即隨處可見現代繪畫、現代雕塑的視覺元素。那么,對于意象派的這一創作思想,即取自現代藝術,進而講求詩歌意象直接而精確的“呈現”,隱含在其背后的主旨究竟為何?還是在那篇《意象主義詩人(1916)》的“序”中,或許我們可覓得些許解答:
“意象派”并不僅僅意味著畫面的呈現。“意象主義”指的是呈現的方法,而不是指呈現的主題。它意思是說要清晰地呈現作者想表現的一切。他也許會想表現一種猶豫不決的情緒,在這種情形下,詩也應該是猶豫難決的。
他也許想要在讀者眼前喚起那在一片風景上不斷地變換著的光,或一個人在激烈的情緒中變化著的思想的不同姿態,那么他們的詩也必須不斷轉換變化著,來清楚地呈現這一點。……“精確”的詞給讀者帶來物體的感受恰像詩人寫這首詩時物體在詩人頭腦里呈現的那個樣子。[1]158
不難看出,意象派倡導的“呈現”一方面要“清晰地呈現作者想表現的一切”,另一方面,它還要注重“給讀者帶來物體的感受”,在讀者心中喚起與詩人相似的“情緒”。一言以蔽之,“呈現”在于打通詩人、描繪的物體與讀者間的阻隔,以實現三者間想象的最大融合。
三、詩歌意象的視覺生成機制
既然在意象派詩歌創作中,無論詩人抑或讀者,其想象生成都與描繪的物體即詩歌意象休戚相關。那么,意象派詩人又是如何在詩歌實踐中,通過汲取現代視覺藝術的靈感,具體踐行著對詩歌意象的視覺構建?
首先,正像許多評論家指出的那樣,現代主義繪畫經常在作品中變幻所描繪對象的體積、形狀、大小。廣為人知的如立體畫派,典型的立體主義繪畫常將物體處理成形狀各異的幾何圖形,這些幾何圖形互相滲透、彼此交疊,進而建構出全新的意義表達。意象派詩人對此無疑情有獨鐘并深受啟發。在他們的詩歌創作中,也常常會出現將一個詩歌意象投影于另一個意象,從而交織成一個全新的意象,而這新的意象又兼具有前兩個意象的特質。評論家冠之以意象的并置與疊加。譬如女詩人H.D.的短詩《奧麗特》(Oread)①(注:龐德對該詩曾大加贊賞,認為它嚴格遵循了意象主義的創作規則,堪為意象派詩歌的典范):
翻騰吧,大海——
翻騰起你尖尖的松針,
把你巨大的松針
傾瀉在我們的巖石上,
把你的綠扔在我們身上,
用你池水似的杉覆蓋我們。[1]27
這里,大海的驚濤駭浪被比擬為“尖尖的松針”在“翻騰”,這浪濤不單傾瀉在巖石上,也拋灑在駐足于海邊的“我們身上”。詩的最末“用你池水似的杉覆蓋我們”讓讀者既感受到浪濤如杉般的繁茂綠意,同時又兼具有海浪奔流不息的流動質感,而在杉的綠與水的動的交相疊映下,駐足于岸邊的“我們”此刻仿若化身為奧麗特,如精靈般的仙子形象躍然于紙上。
其實,H.D.的這首《奧麗特》不僅采用了意象疊加的手法,同時它還突顯了意象派詩歌意象生成的另一慣用技法,即意象的暗喻。在上文提及的《意象主義詩人(1916)》的“序”中,也不乏對意象暗喻的表述文字:“意象主義者很少使用明喻。雖然他們詩的大部分是暗喻性的。這樣做的理由是:盡管他們承認形象是所有詩歌的一個主要部分,但他們覺得在一首詩里不斷地把一個形象放到另一個形象上,會模糊總的效果。”[1]161確乎如是,在意象主義詩歌創作中,意象暗喻的手法可謂比比皆是,還是以威廉斯的另一首短詩為例:
在白楊樹間有一只小鳥!
它是太陽!
樹葉是黃色小魚
在河中游。
鳥兒在他們身上掠過,
它雙翅馱著白晝。
菲白斯(太陽神)呵!
是他使
白楊發光!
是他的歌聲
壓倒風兒吹弄樹葉的聲音。
正如鄭敏先生對該詩的讀解,這里樹葉的意象經過太陽的投射,變成“黃色小魚在河中游”,而這黃色的小魚又兼具有陽光的色彩和樹葉在風中搖曳的動感,不僅形似又繪聲繪色,從而恰到好處地烘托出詩末的高潮——“菲白斯呵!/是他使/白楊發光!/是他的歌聲/壓倒風兒吹弄樹葉的聲音。”[13]9
除此之外,還有前文提到的龐德的《地鐵車站》,“臉龐”被比擬為黑色枝條上綴滿的“濕漉漉的花瓣”。作為暗喻的兩極,“臉龐”與“花瓣”除卻視覺上的明暗對比沖擊外,觸覺上的“濕”與充滿動感的“臉龐的隱現”亦充分調動起讀者全方位的感官經驗,從而將讀者自發地引入到創作主體的情感當中。不難看出,與意象派詩歌的其它技法類似,意象暗喻所指向的,也正是“作者想表現的一切”,包括作者的“情緒”等。這不由讓我們聯想到保羅·利科在《活的隱喻》中論及的隱喻指稱,其中,隱喻的“第一級指稱(或日常描述性活動的指稱)”關涉的即為創作者的創作心理機制。[14]304作為意象派詩人的代表,威廉斯的以下詩句無疑是意象暗喻的一個絕佳注腳:
——用隱喻使人與石頭
相調和。
創作。(沒有思想除
非在物中)創造![15]55
事實上,英美意象派詩歌的視覺意象生成機制絕不僅限于前文提到的意象并置、疊加與意象暗喻/隱喻,但因篇幅所限,故本文無法在此一一展開詳述。但有一點毋庸置疑,正是由于詩歌意象蘊含的巨大張力,才最終成就了英美意象派詩歌無窮無盡的想象與語義表達空間,并對繼之其后現代派詩歌的發展產生無以估量的深刻影響。這當中,意象的視覺想象委實功不可沒。
注 釋:
① 奧麗特是古希臘神話中守護山林的女神。
參考文獻:
[1](英)彼得·瓊斯.意象派詩選[M].裘小龍譯.北京:漓江出版社,1986.
[2]William Pratt.The Imagist Poem:Modern Poetry in Miniature[M].New York:E.P.Dutton,1972.
[3](英)弗林特.意象主義[M]//黃晉凱,張秉真.象征主義·意象派.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4]Wallace Stevens.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M].Ed.Holly Stevens.Alfred A.Knopf,1966.
[5]William Carlos Williams.Interviews with William Carlos Williams:“Speaking Straight ahead”[M].Ed.Linda Welshimer Wagner.New York:New Directions,1976.
[6]Edward G.Fletcher.Imagism—Some Notes and Documents[J].Studies in English,1947(26).
[7]黃晉凱,張秉真.象征主義·意象派[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8]Ezra Pound.Gaudier-Brzeska[M].London:The Bodley Head,1916.
[9]Meyer Schapiro.“Rebellion in Art,”in America in Crisis[M].Ed.Daniel Aaron.New York:Knopf,1952.
[10]William Carlos Williams.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M].New York:New Directions,1967.
[11](美)龐德.論文書信選[M]//黃晉凱,張秉真.象征主義·意象派.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12]William Carlos Williams.The Collected Poem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1909-1939(Vol.1)[M].New York:New Directions,1986.
[13]鄭敏.英美詩歌戲劇研究[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3.
[14](法)保羅·利科.活的隱喻[M].汪堂家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15]William Carlos Williams.The Collected Poem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1939-1962(Vol.2)[M].Ed.Mac Gowan, Christopher.New York:New Directions,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