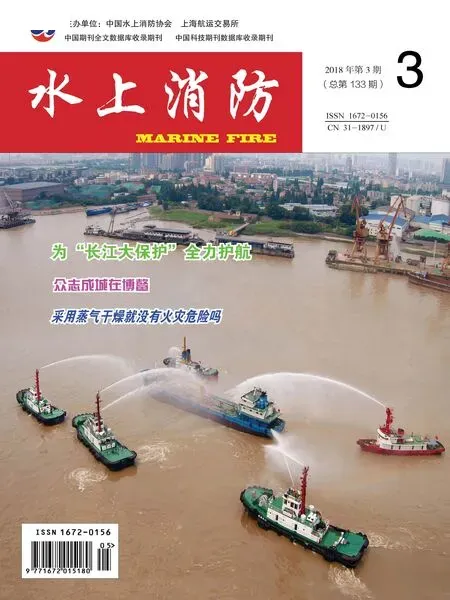危險貨物法律定義的發展及思考
■蔣文青
(上海市碼頭管理中心,上海 200120)
0 引言
隨著化工產業、材料科學和農業技術的發展,商品種類也在不斷增多,其中不乏具有危險性質的貨物。危險貨物運輸是國際貨物運輸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調整因海上危險貨物運輸的各種法律關系,保護海上運輸過程中的人身、財產和環境安全,國際公約和國內法律對危險貨物運輸作出了相應規定。危險貨物應該如何界定?這不僅屬于法律解釋問題,也是一個專業技術問題,不但如此,受制于人們認識的局限性,還會涉及運輸實踐中的具體情況。以英國的The Giannis NK [1998]案為例,該案中,“The Giannis NK”輪裝載了花生和麥子。在海上運輸過程中,花生被發現感染了谷斑皮蠹。在兩次熏蒸仍不能消滅谷斑皮蠹情況下,船長將貨物傾倒入大海。該案中,花生本身并非通常理解的易燃、易爆或具有危險性質的物品,但由于其感染了害蟲,而該等害蟲感染會傳染給同航次的麥子,因此花生可能對船載其它貨物造成實際損害,法院據此認定涉案花生為危險貨物。于是,不同于危險貨物是指易燃易爆物品的一般社會觀念,花生在特定情形下,也可能是危險貨物。
1 法律淵源
一直以來,有關危險物質、危險物品、危險品、危險化學品和危險貨物等概念不斷出現在國內立法中,給國內相關“危險品”的法律體系帶來一定的混淆,加之“危險品”涵蓋的專業技術性較強,也給司法實踐中對貨物性質的認定帶來一定的困難。《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中對重點管理對象的提法是“危險物品”,其定義涵蓋了運輸領域的危險貨物。相應的,不同管理部門在各自的管理職責范圍內立法,根據不同的管理對象,產生了不同的“危險品”概念。港口危險貨物安全管理中,危險貨物的認定是最基本的法律問題。認清其法律定義的發展與實際司法實踐中的運用對在行政管理與經營活動中的正確適用具有積極意義。危險貨物的法律界定早在海牙規則中既已出現,長期以來受國際法影響,并逐步轉化為國內立法。
1.1 國際公約
1.1.1 海牙規則
早在1875年,英國的《商船法》就區分了普通貨物與危險貨物,但其中并未對“危險貨物”進行定義。最早給出“危險貨物”定義的是在《統一提單的若干法律規則的國際公約》(海牙規則,1924年8月25日訂于布魯塞爾)第4條第6款:“具有易燃、爆炸或危險性的貨物”。不難看出,該定義側重對貨物理化特征的描述,即內在危險性而言,且對危險性的認識僅限于燃燒和爆炸性。受制于當時的科學技術水平與航海經驗,承運人對貨物性質的認定更多基于在承運過程中是否安全和穩定,是否可能發生難以控制的反應而給整個航程帶來潛在的危險。因此,考慮到海上運輸巨大的風險性,為了平衡托運人與承運人雙方的權利義務,同時保證航行安全,條約對雙方在因貨物危險導致的法律責任上有了傾斜,如該款規定了,承運人無論是否在事先知曉貨物的危險性質,均可在貨物對船舶或貨載發生危險時,亦得同樣將該項貨物卸在任何地點,或將其銷毀,或使之無害,而不負賠償責任(發生共同海損不在此限)。此外,提單背面的危險貨物條款還確定了托運人對貨物危險性質的正確申報和標明危險品標志和標簽并事先書面形式告知承運人的義務,否則,承運人享有拒裝或一經發現,為船貨安全有權將其變為無害、拋棄或卸船,或以其他方式予以處置,而相關損害責任由托運人或收貨人承擔。
1.1.2 漢堡規則
《1978年聯合國海上貨物運輸公約》(漢堡規則)(1978年3月31日頒布、 1992年11月1日生效)中沒有對危險貨物的明確定義,而是傾向于各國可以通過制定國內規定、簽訂雙邊條約等方式,自行定義“危險貨物”。漢堡規則生效后,截至1996年10月,共有成員國25個,其中絕大數為發展中國家,占全球外貿船舶噸位數90%的國家都未承認該規則。因此,對于國際海運而言,漢堡規則沒有被廣泛接受,但其中包括和危險貨物運輸有關的一些條文和理念被我國之后制定的《海商法》等國內規定中援引。例如:托運人在危險貨物運輸中對危險貨物加以妥善包裝、作出妥善標志、向承運人如實告知貨物危險性質以及預防措施的義務等。
1.1.3 鹿特丹規則
2009年9月23日于荷蘭鹿特丹簽署公布的《聯合國全程或部分海上國際貨物運輸合同公約》(鹿特丹規則)中將“危險貨物”定義為:“貨物因本身性質或特性而可能對人身、財產或環境形成實際危險的貨物。”從文字表述的變化可以看出,《鹿特丹規則》不僅以貨物自身屬性作為“危險貨物”認定標準,而且通過考察貨物是否會對其自身以外的人身、財產或環境形成實際危險來確定是否屬于危險貨物。我國雖尚未加入《鹿特丹規則》,不直接受其約束,但《鹿特丹規則》的規定援引了《聯合國關于危險貨物運輸的建議書》(TDG,2017年7月正式發布第20修訂版,俗稱《橙皮書》)和《全球化學品統一分類和標簽制度》(GHS,2017年7月正式發布第7修訂版,俗稱《紫皮書》)等相關規范標準,也體現了國際物流行業對于“危險貨物”定義的新發展。
1.2 國際國內規范標準
危險貨物的規范標準以《聯合國關于危險貨物運輸的建議書》為最基礎的國際標準和行動框架,可以結合不同的運輸形式定期進行統一的修改。同時,《橙皮書》還為一些特殊情況提供了可以參照的詳細信息框架。在此基礎上,國際相關組織根據運輸特點的不同,相應制定了不同運輸形式下的危險貨物規定,如:
1)國際海事組織(IMO)制定的《國際海運危險貨物規則》(IMDG code)、《國際海運固體散裝貨物規則》(IMSBC code)、《國際散裝危險化學品船舶構造和設備規則》(IBC code)和《國際散裝液化氣體船舶構造和設備規則》(IGC code)等;
2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制定的《危險貨物規則》(DGR);
3)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ECE)制定的《國際公路運輸危險貨物協定》(ADR);
4)歐洲鐵路運輸中心局(OCTI)制定的《國際鐵路運輸危險貨物規則》(RID);
5)國際民航組織(ICAO)制定的《航空危險貨物無風險運輸的技術指導》。
《紫皮書》從人體健康與環境安全的角度,為貨物的分類、包裝、運輸以及安全劃定了新的標準,目前也成為我國危險化學品登記制度的主要依據。
參照上述國際運輸規則,國內主管部門交通運輸部在各主要運輸領域也分別制定了相關規定:
1)《港口危險貨物安全管理規定》;
2)《船舶載運危險貨物安全監督管理規定》;
3)《道路危險貨物運輸管理規定》;
4)《鐵路危險貨物運輸安全監督管理規定》;
5)《民用航空危險品運輸管理規定》。
絕大多數的危險貨物通過海上運輸,受海上危險貨物相關規則調整。以《國際海運危險貨物規則》(簡稱《國際危規》)為例,國際海事組織的海上安全委員會(MSC)指派在海運危險貨物方面有豐富經驗的國家組成了一個專家工作組,根據《1960 年海上人命安全公約》(SOLAS)第七章的規定與聯合國危險貨物運輸專家委員會緊密合作編寫,并于1965年9月27日由國際海事組織以A.81(IV)決議通過產生了著名的《國際海運危險貨物規則》。作為全球海洋運輸包裝危險貨物的指導規則,其制定原則是除非符合規則的要求,否則禁止裝運危險貨物。其目的是:保障船舶載運危險貨物和人命財產安全、防止事故發生和海洋污染、維護航行安全與海洋清潔。《國際危規》自實施以來,由國際海事組織統一進行定期修正,目前是每2年更新一次。近期的修改主要體現在:明確了危險貨物運輸從業人員的強制培訓要求;對第9類雜類危險貨物進行了進一步細分;調整了危險貨物一覽表的結構;總結了近年海上運輸實踐,特別是吸取了事故經驗教訓,在一覽表中列明或新增了部分的危險貨物;在第4.1類中新增聚合物質;新增鋰電池的專用標簽等。《國際危規》在2004年1月1日起成為SOLAS公約下的強制性實施規則,成為指導海上危險貨物運輸的全球唯一有效規則,但仍有部分內容是建議性的。 自1982年10月起,我國已開始執行《國際危規》。《國際危規》當前的最版是第38—16版,2018年1月1日起強制實施。
1.3 國內立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港口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上交通安全法》等均提及但都未對“危險貨物”進行定義,《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中也沒有“危險貨物”的提法;但前述幾部法律中有關于運輸危險貨物的原則性規定。危險貨物作為運輸領域的專門概念,其嚴格的法律定義主要出現在交通運輸主管部門頒布的規章中,并且在近十余年結合國際立法和國內實踐不斷修改和完善。
在《港口危險貨物管理規定》(2003 年版)中,危險貨物是指“列入國家標準GB 12268《危險貨物品名表》和國際海事組織制定的《國際海運危險貨物運輸規則》,具有爆炸、易燃、毒害、腐蝕、放射性等特性,在水路運輸、港口裝卸和儲存等過程中,容易造成人身傷亡和財產毀損而需要特別防護的貨物。”概括而言,危險貨物應同時具備列名,危險性和需要特別防護三個特征。
2004年交通部制定的《船舶載運危險貨物安全監督管理規定》,對“危險貨物”的定義借鑒了聯合國最新的規章范本和船舶載運危險貨物可能對水體造成的潛在危害性,其定義的寬度與廣度也有所發展,規定了“危險貨物系指具有爆炸、易燃、毒害、腐蝕、放射性、污染危害性等特性,在船舶載運過程中,容易造成人身傷害、財產損失或者環境污染而需要特別防護的物品。”根據此規定,“危險貨物”除了在自身屬性上具有危險性外,還應滿足對其它人身、財產、環境容易造成實際危害的特征。
2012年版的《港口危險貨物安全管理規定》(2012年版)順應了此變化,并未作調整:“第三條 本規定所稱‘危險貨物’,是指列入國際海事組織制定的《國際海運危險貨物規則》和國家標準《危險貨物品名表》(GB 12268),具有爆炸、易燃、毒害、感染、腐蝕、放射性等特性,容易造成人身傷亡、財產毀損或者對環境造成危害而需要特別防護的貨物。”由于該定義未嚴格區分不同物理狀態和包裝形式的危險貨物,缺少對散裝類危險貨物的明確界定,在實踐中帶來一定混淆。為了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上述問題,2017年9月發布的《港口危險貨物安全管理規定》對危險貨物的定義作了較大調整。在保留援引《國際海運危險貨物規則》和國家標準有關內容的基礎上,具體新增或明確了:
1)《國際海運固體散裝貨物規則》(IMSBC code)附錄一B組中含有聯合國危險貨物編號的固體散裝貨物,以及經評估具有安全危險的其他固體散裝貨物。
2)《經1978年議定書修訂的1973年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MARPOL73/78公約)附則I附錄1中列明的散裝油類。
3)《國際散裝危險化學品船舶構造和設備規則》(IBC code)第17章中列明的散裝液體化學品,以及未列明但經評估具有安全危險的其他散裝液體化學品。但在港口儲存環節中,僅包含上述具有安全危害性的散裝液體化學品。
4)《國際散裝液化氣體船舶構造和設備規則》(IGC code)第19章列明的散裝液化氣體,以及未列明但經評估具有安全危險的其他散裝液化氣體。
5)我國加入或者締結的國際條約、國家標準規定的其他危險貨物。
6)《危險化學品目錄》中列明的危險化學品。
2 司法實踐
在2004年以前的司法實踐中,我國海事法院多以貨物自身屬性作為認定“危險貨物”的標準,通過審查涉案貨物是否列入《國際海運危險貨物規則》或《危險貨物品名表》(GB 12268),判斷涉案貨物是否屬于危險貨物。比如,(2003)粵高法民四終字第55號、(2003)滬海法商初字第485號、(2003)廣海法初字第296號、(2004)滬海法商初字第492號等案例都采用了這種認定方式。
2004年之后對危險貨物的認定方式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已不僅僅是簡單的考察貨物的自身屬性。以上海海事法院“泛亞—吉與寶”案 為例:
原告(反訴被告):連云港泛亞物流有限公司。
被告(反訴原告):瑞士吉與寶有限公司(GEARBULK AG, SEITZERLAND)。
泛亞公司訴稱,2007年4月29日,當事人雙方訂立航次租船合同,約定由吉與寶公司所屬船舶運輸泛亞公司約900 t鋼管從中國連云港到美國休斯敦。裝載期間,共87捆重約193.3 t貨物遭吉與寶公司拒裝,致使泛亞公司不得不另行安排上述貨物的運輸,遭受經濟損失。請求法院判令吉與寶公司賠償經濟損失人民幣401 381元及利息。法院在考察受海水污染鋼管是否屬于危險貨物時,除了考慮貨物是否具有易燃、易爆等自身屬性外,還重點考察了貨物是否會對船舶或船載其它貨物造成損害。
法院認定:1)吉與寶公司未能充分舉證證明,涉案鋼管會對船舶或船艙中何種貨物造成損害,以及船舶及其它貨物會受到何種程度的損害。由于吉與寶公司未能證明涉案鋼管是否達到危險貨物標準,被拒載鋼管不能被認定為危險貨物,吉與寶公司的拒裝行為缺少法律依據。2)吉與寶公司的拒裝行為沒有合同依據。3)對于海上運輸貨物而言,僅因貨物表面存在含鹽水分即斷定其將對同船其它貨物造成損害,尚缺乏足夠依據。據此,法院認定吉與寶公司的拒裝行為違反航次租船合同約定,判決吉與寶公司賠償泛亞公司運費等損失33 450.68美元和人民幣16 000元及其利息。吉與寶公司在反訴中提出的虧艙費和船舶滯期費損失系由其自身違約行為所致,不應由泛亞公司承擔,反訴請求不予支持。一審判決后,原、被告均沒有提起上訴。
3 港口危險貨物的認定問題
3.1 危險貨物的定義逐漸作寬泛解釋
從上述“危險貨物”的法律定義和司法裁判的發展來看,對“危險貨物”的認定標準作相對寬泛的解釋是國際航運界和海商法領域所共同的價值取向。之所以有這種發展:1)基于海上運輸的高風險性,尤其是隨著船舶大型化的趨勢,一個航次運載大量不同性質類別的貨物,即使是普通的貨物在特定環境或條件下也可能會對其他貨物產生影響。但在司法實踐上應以現實存在的危險性為前提條件。比如上述“泛亞—吉與寶”案糾紛中,對鋼管進行淡水清洗后可以正常運輸,雖然清洗可能增加了費用、延誤了開航時間,但不足以構成現實的危險。2)人們對貨物認識的發展,從關注貨物的自身特性轉而兼顧貨物在運輸過程中對航行安全和自然環境的影響。3)隨著化工、材料及農業技術的發展,新的具有上述危險性的物質不斷產生并進入運輸領域。
縱觀國內立法中危險貨物法律定義的發展,其指向性逐漸明確和具體(2017版《港口危險貨物安全管理規定》中對危險貨物的定義細分為7個子項),不僅體現了危險貨物管理的技術性和科學性,而且在日常管理和運輸實踐中的實用性不斷增強。港航行政管理部門,危險貨物運輸經營人、合同履約人等,都應及時了解國際國內相關運輸規則的修訂,適時關注仲裁及司法判例,把握危險貨物法律界定的變化和發展,合法依規運輸危險貨物,預防和減少可能造成的人身、財產和環境的損害,同時避免在經營活動中因違法認識性不足而導致的法律風險。
3.2 港口監管中對危險貨物認定的一般原則
行政法以合法與合理行政為基本原則。區別于民事領域的法無明文禁止即可行,政府行政行為以法律授權為合法有效依據。這就要求各級港口行政管理部門在對危險貨物的日常行政監管中,應以交通運輸部《港口危險貨物安全管理規定》(2017版)第八十七條中危險貨物的定義確定具體的管理對象,在行政和執法過程中保持政令的穩定性,各級港口行政管理部門不得對危險貨物的范圍作擴大解釋。同時,對于屬于危險化學品的港口危險貨物,港口行政部門還應注意相關上位法的有關規范要求(如:《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對屬于煙花爆竹、民用爆炸品、放射性物品的危險貨物還應當按照有關特別法進行管理。
3.3 港口船供物料的監管問題
2017版《港口危險貨物安全管理規定》實施以來,港口危險貨物的定義已和海上運輸立法相一致。兩者適用同一認定范圍,便于港航立法的統一管理。但由于《國際危規》等的主要立法目的在于保障海上運輸過程中的安全,對于相對靜態的港口作業形式完全適用同一標準不盡合理。例如船供物料的港口作業管理問題。相關法規中并未明確:在港口裝卸屬于危險貨物范圍的船供物料是否屬于港口危險貨物作業,以及該類作業的具體管理要求。筆者認為,規范此類業務需考慮以下三方面的問題:
1)船供物料與危險貨物海上運輸的本質區別。即使作業物料“具有爆炸、易燃、毒害、腐蝕、放射性等危險特性,在港口作業過程中容易造成人身傷亡、財產毀損或者環境污染而需要特別防護的物質、材料或者物品”的定義特征,但其并非作業委托人交付的貨物,不具有以海上運輸為目的的本質特征。類似的經營種類還有港口水上供油、油污水接收等業務,盡管油品和油污水均具有危險貨物的特征,但都不屬于貨物。
2)風險和危險性相對較低。通常情況下,和危險貨物的單艘次作業量相比,船供物料的作業量較小,作業品種也相對固定(較常見的有:桶裝油漆、機械設備用潤滑油、清洗夾板艙的鹽酸等,屬于航行過程中的生產生活必須品)。
3)船供業務的經營者規模大小不一。對于大量規模較小的船供單位,如果一律按照危險貨物港口經營的許可條件,將有相當數量的經營者無法達到資質要求,無益于規范市場經營秩序。
因此,如何設定此類經營的市場準入條件,如何加強對該類單位的日常監管,對于維護港口經營秩序和公共安全,以及防止港口水域污染尤為重要。
筆者認為,對于船供(按性質屬于危險貨物)物料,因其不具有以海上運輸為目的的本質特征,不宜將其認定為港口危險貨物作業。但考慮到物料自身固有的危險性,應較船供普通貨物的管理有更高要求。具體措施可以借鑒港口危險貨物作業的日常安全管理制度,如作業申報制度、劃定封閉作業區域、加強作業現場監護,配備個體防護措施,針對物料的種類和危險特性落實相應安全操作規程和應急防范措施等,確保港口作業安全。
4 結語
一個多世紀以來,危險貨物的法律定義已經從最初的直觀危險性,逐漸發展至如今的兼顧本質與潛在的危害性質、區分不同的運輸形態和危險類別。危險貨物的范疇在未來仍將隨著社會經濟技術水平發展,人們認識與科技水平的進步,運輸實踐經驗的積累而變化。理解和掌握的它的發展及內涵,對于采取適當措施、科學和立法規范管理、確保港口作業和貨物海上運輸的安全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