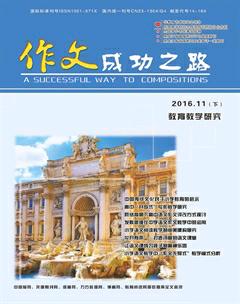古典詩詞中的實景與虛景
劉慧敏
【摘 要】虛實相生是中國繪畫運用的傳統技法,也是古典詩詞中重要的表現手法。在日常教學中,很多學生并不能準確的辨識虛景與實景,理清兩者的關系。本文分別從兩個角度,厘清了實景與虛景的概念與關系。
【關鍵詞】實景 虛景 實景與虛景的關系
“孤舟微月對楓林,分付鳴箏與客心。嶺色千重萬重雨,斷弦收與淚痕深。” (王昌齡《聽流人水調子》)。這首詩中第三句“寫嶺色,兼寫箏聲”時很有特色,實寫一彎微月之下一葉孤舟之上所見層層山嶺雨霧籠罩的迷蒙景象,想象(虛寫)樂音的繁促凝重,虛實結合,牽惹客子的愁情。虛實結合這一考點在歷年全國高考試題中都有所涉及,2016年江蘇高考考試說明關于古代詩文閱讀的鑒賞評價中也有藝術技巧的鑒賞這一依據。但是在完成詩歌鑒賞題時,很多學生都不能從虛實的角度去分析。所以筆者認為,很有必要在此厘清古典詩詞中的實景與虛景的概念與關系。
一、何為實景,何為虛景
所謂“實景”,是指眼前所見的實象、實事、實境。所謂“虛景”,是指并非眼前所見,而是回憶、想象或是夢境中的景物。實景比較容易辨別出,而虛景往往不易一眼看出。那我們做題時,如何準確的辨識出虛景與實景呢?
(一)關注詩句中的標志性詞語,辨識虛景
不少詩詞中,有很明顯的標志性詞語,能夠幫助我們迅速而準確的找出虛景的句子。如:(1)胡曾的《詠史詩·江夏》:“黃祖才非長者儔,禰衡珠碎此江頭。今來鸚鵡洲邊過,惟有無情碧水流。”抓住第三句中的“今來”就能夠辨識出前兩句是對過去之事的描繪。(2)皇甫冉的《送魏十六還蘇州》:“秋夜沉沉此送君,陰蟲切切不堪聞。歸舟明日毗陵道,回首姑蘇是白云。” 抓住第三句中的“明日”就能夠辨識出后兩句是對未來之景的描繪。(3)黃庭堅的《題陽關圖》:“斷腸聲里無形影,畫出無聲亦斷腸。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從第三句中的“想得”二字可以看出后兩句是對異地之景的描繪。(4)皇甫松的《夢江南》:“蘭燼落,屏上暗紅蕉。閑夢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蕭蕭。人語驛邊橋。”抓住第三句中的“夢”就能夠辨識出后三句是對夢中之景的描繪。
(二)關注詩句下的注解,分清實景與虛景
如果詩句中沒有標志性的詞語,我們還可以通過關注注解來分清實景與虛景。如:(1)皇甫曾的《送人還荊州》:“草色隨驄馬,悠悠同出秦。水傳云夢曉,山接洞庭春①。帆影連三峽,猿聲近四鄰。青門②一分手,難見杜陵人”。【注:①云夢、洞庭都指古代楚地,荊湘一帶。②青門:長安東南門,古屬秦地。】從注解中,我們不難看出,作者與友人此時在秦地青門,那么詩中的中間四句就是想象與別后友人將去之處的風光和途中的情景,流露出對友人一路山高水長、孤獨寂寞的關切。(2)杜甫的《月夜》:“今夜鄜州①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云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注:①鄜(fū)州:今陜西省富縣。當時杜甫的家屬在鄜州的羌村,杜甫在長安。】這首詩則是從對方著筆手法,全篇虛寫,抒寫了妻子對自己的思念,也寫出自己對妻子的思念。
二、實景與實景關系如何
分清詩句中的實景、虛景,這還只是淺層次的,我們還需要弄清虛景在詩詞中的作用,這就要把虛景和實景兩者結合起來,具體分析一下兩者之間的關系。一般而言有以下兩種關系:
(一)相輔相成,渲染烘托,突出中心。如皇甫冉的《送魏十六還蘇州》中,秋夜沉沉,蟋蟀鳴叫,友人即將遠行,詩人心情無比沉重。而別后呢,見到的唯有滿天白云,到那時,孤獨惆悵之情定會比今夜更深。虛實相生中難分難舍之意躍然紙上。黃庭堅的《題陽關圖》中,斷腸的離歌聲中,征人啟程,漸行漸遠,依依惜別之情溢于言表,再一想,征人去處又是一個絕城窮荒之地。離別之悲滲出畫面,感人至深。
(二)相反相成,對比反襯,突出中心。如:李白的《越中覽古》用昔時歌舞升平的繁盛反襯眼前的凄涼,表現了人事變化和盛衰無常的主題。李商隱的《夜雨寄北》用來日聚首之時的幸福歡樂反襯此刻身處巴山傾聽秋雨時的寂寥之苦。
據此,虛實結合這類藝術技巧題型也就有了一套答題程式:(1)虛實相生,某種虛景與某種實景相融合、相映襯,烘托出某種氣氛,渲染出某種情感。(2)虛景與實景相對照,使某地和某地的景形成鮮明的對比,突出(反襯出)了某種景的特點,表達了詩人某種感慨。
我國的古典詩詞,語言精練,意蘊豐富。許多詩詞中運用虛實結合的藝術手法,特別是以白描手法寫景敘事的詩詞。虛景的呈現極大地豐富了詩詞的意蘊,開拓了深遠的意境,給讀者無盡的想象空間,真境逼而神境生。掌握了虛景實景的概念,理清了兩者的關系,相信很多學生從此面對這一題型時不會再是束手無策。
【參考文獻】
【1】吳曉鳳.略談古典詩歌中的虛與實【J】.現代語文(文學研究),2010(4)
【2】王波平.李白詩歌四大吟詠范疇淺析【J】.文教資料,2015(12)
【3】黃俊娟.格式塔心理學對詩詞翻譯的影響【J】.中國農業銀行武漢培訓學院學報,2010(4)
【4】李剛.古典詩詞中的虛實【J】.考試.高考語文版,2011(7)
【5】唐宋詞鑒賞辭典【M】.上海辭書出版社第2版,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