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慣例研究演進與熱點:WOS的文獻計量分析
鐘耕深 周 憲 蘇錢宏
(山東大學 管理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組織慣例是理解組織變革和學習、創新、戰略柔性、知識轉移等一系列組織現象的核心,也是當前許多被廣泛接受的組織和戰略理論的重要解釋機制。[注]Pentland Brian T., Martha S. Feldman,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s a unit of analysis", in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14 (2005).然而,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于組織慣例本身的研究卻處于概念模糊、莫衷一是的尷尬境地。面對這一局面,該領域學者曾專門就組織慣例的概念、內涵等相關問題在美國新墨西哥州圣菲研究所召開過專題研討會,從認知實在論的視角將組織慣例定義為組織成員之間反復出現、可以選擇的行動模式。盡管這一定義并沒有完全消除學術界對于“什么是組織慣例”的爭論,但也奠定了近20年組織慣例研究的基礎。
為了幫助對組織慣例的理解,學者們從其概念特征、研究范式和研究視角等方面對已有研究進行了梳理。如Becker(2004)總結了組織慣例所具有的特性,并歸納了其對組織的影響;又如Pentland et al.(2005)將組織慣例作為基本分析單位的三種研究策略,即視組織慣例為無差異“黑箱”、單獨研究組織慣例內部結構的不同部分、考慮不同部分及其變化過程的關系;再如Parmigiani et al.(2011)從能力視角和實踐視角審視組織慣例,前者側重于組織慣例形成能力進而影響企業績效的過程,后者則關注慣例內部的微觀結構特征。[注]Parmigiani Anne, Jennifer Howard-Grenville, "Routines revisited: Exploring the capabilities and practice perspectives", in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Vol.5(2011), p.413.但是,對于組織慣例這一問題涉及面廣、研究群體目標不一的研究領域來說,單純依賴研究者的主觀歸納和經驗總結,恐怕難以全面把握這一領域已達成的共識和研究進展。而運用文獻計量的方法或可全面、客觀乃至可視化的展現組織慣例領域的演進歷程及其發展現狀。[注]李杰、陳超美:《CiteSpace: 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視化》,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本文以1996-2017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數據庫中有關組織慣例研究的文獻作為分析樣本,綜合運用HistCite、Citespace和SPSS三種分析工具對組織慣例研究的外部統計特征進行分析,抽取和提煉構成組織慣例研究的知識基礎和研究熱點,并對已有研究進展進行初步總結和展望,以期為組織慣例研究領域在未來的理論探索提供參考。
一、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文計量分析的文獻來源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數據庫,具體檢索方法:以“routine”為主題詞進行檢索,選取SCI-EXPANDED、SSCI兩大引文數據庫來源。由于本文關注的是組織慣例在管理學領域中的主流學術研究進展,所以類別選擇設定為management,文獻類型為article和review,語種為English。參照Parmigiani et al.(2011)的做法,將時間跨度設定為1996-2017年。經過幾次預測試之后,最終確定1333篇文獻,總被引頻次為67160次,共有參考文獻51398篇。
(二)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引文分析法對組織慣例研究領域的外部統計特征進行分析,從宏觀上對這一領域的研究現狀和發展趨勢進行描述和評價。其次,綜合運用共被引分析法和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抽取并提煉構成組織慣例研究領域的知識基礎。最后,運用關鍵詞共現分析和聚類分析,對這一領域的研究熱點進行主題聚類。在分析過程中,本文主要運用HistCite、Citespace和SPSS三種分析工具。通過HistCite最重要的兩個參數之一,即本地引用次數,更加精確地定位本領域研究成果;[注]董坤祥等:《國內外眾包研究演化路徑與未來展望》,《科技進步與對策》2016年第8期。通過Citespace進行機構和作者科研合作網絡分析、關鍵詞共現分析和聚類分析,繪制科學知識圖譜;SPSS軟件則主要用以因子分析。
二、統計特征分析
(一)發文數量趨勢
從既有文獻的數量來看,組織慣例研究領域整體上呈現出波動性上升的趨勢。具體來說,1996-2009年間,這一研究領域論文發表數量增長較平穩,平均每年發表論文數量只有41篇。2009年,Feldman et al.(2003)的研究論文創造性地將組織慣例進一步區分為明示面和實行面,并指出組織慣例既是穩定性又是變革性來源。之后的8年間,這一領域發表論文數量急劇增長,從62篇迅速攀升至123篇,平均每年發表論文達到94篇。與此同時,組織慣例研究領域文獻被引頻次呈現出“指數型”增長趨勢。在2004年之前,這一領域文獻的被引頻次增長較為平緩,此后的十幾年間平均每年的總被引頻次達到588次。在本文進行計量分析的1333篇文獻中,Feldman et al.(2003)的經典論述就有260篇文章被引用,而且Feldman(2000)還首次論述了組織慣例內部動態性的文章。[注]Feldman, Martha S,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s a source of continuous change", in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11(2000), p.611.本地引用次數也達到了204次,這足以說明組織慣例研究的重要地位。
(二)核心作者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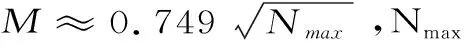
從表1可知,Feldman和Pentland是目前組織慣例研究領域絕對的權威學者。Feldman雖然發表論文數量略少于Pentland,但是其在本地引用次數達到936次,而且70%以上的文獻被她有所提及。這二人在組織慣例研究領域中形成了緊密的合作關系,許多經典論文都是由他們合作完成。作為演化經濟學的奠基者,Winter與Nelson合作撰寫的《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著作,在Google Scholar上的引用次數已達36299次(截至2017年12月5日),本地引用也有339次。另外,作為動態能力理論過程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Winter認為動態能力是高水平組織慣例(元慣例)聚合而形成的高階能力,從而搭建了組織慣例與動態能力理論研究之間的橋梁。總的來說,雖然引用次數大于50的核心作者發表論文數量只占7.5%,但其引用次數卻占到了全部本地引用次數的87%,足見這一領域已經形成了絕對的學術權威,若要在此領域開展研究,就必須深刻了解這些核心作者,特別是Feldman、Pentland和Winter這幾位學者的基本思想。

表1 核心作者統計信息
說明:核心作者研究方向信息系本文作者手工摘自作者所在研究機構網站及其最新論文
(三)核心研究機構
運用HistCite軟件進行統計發現,共有1071家研究機構參與到組織慣例的研究中。其中,發表論文的數量上,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38篇),University of Michigan(24篇)、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23篇)、Harvard University(22篇)、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篇)。本地引用次數上,Feldman所在的University of California(620次)和Pentland所在的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578次)最多,是這一領域的權威重鎮。然而,不管是數量上還是本地引用次數上,這一領域中來自中國研究機構發表的文章不多,只有46篇,發文數量排名稍微靠前的是香港理工大學(5篇)和香港城市大學(4篇)。
(四)核心期刊來源
運用HistCite軟件統計發現,共有179種專業期刊發表了組織慣例相關的研究成果,本文首先根據引用次數選取排名前10的期刊,確定組織慣例研究領域核心期刊的基本框架;其次,綜合刊載這一領域論文數量,本文最終確定了10種核心期刊。其中,側重于組織基礎性研究的期刊ORGANIZATION SCIENCE在這一領域不僅發表論文數量最多(93篇),而且其引用次數也是絕對地領先于其他核心期刊(1091次),是該領域學者進行學術爭鳴的主陣地。此外,該領域的核心期刊還有:ORGANIZATION STUDIES(48篇;188次)、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41篇;254次)、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39篇;427次)、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37篇;374次)、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7篇;133次)、MANAGEMENT SCIENCE(17篇;60次)、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6篇;114次)、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4篇;421次)等。
(五)高被引文獻
對高被引文獻進行分析,有利于研究者把握該領域的經典文獻,從中汲取知識并形成對該領域的基礎性認識。參照張惠琴等(2017)的做法,[注]張惠琴、侯艷君:《基于知識圖譜的國內員工創新行為研究綜述》,《科技進步與對策》2017年第11期。本文選取了LCS排名前10的文獻進行分析。分析結果表明,組織慣例研究領域至少存在三個特點:第一,高被引文獻出版時間均較為久遠,距今都在10年以上,但其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第二,高被引文獻當中出現了兩篇動態能力理論方面的經典論文,它們是Zollo et al.(2002)的《Deliberate Learn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Dynamic Capabilities》,和Eisenhardt et al.(2000)的《Dynamic Capabilities:What Are They?》。前者從組織學習的角度闡述了動態能力的演化過程,后者則將看似玄幻的動態能力視為組織和管理過程的“最佳實踐”,代表著動態能力理論過程學派的重要觀點。這也說明,組織慣例的研究與動態能力理論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若要領悟動態能力理論的深刻內涵,也必須了解組織慣例的基本特征和復雜結構。第三,這一領域的經典文獻無一例外全是質性研究類的論文,充滿思辨色彩、難以開展大樣本實證研究或許是這一領域進一步發展的最大阻礙因素。[注]Pentland Brian T., Thorvald Hrem, Derek Hillison, "Comparing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s recurrent patterns of action", in Organization Studies, Vol.31(2010), p.917.
三、組織慣例知識基礎
本文參照李杰、陳超美(2016)的做法,將高被引文獻的原始引證網絡手工轉化為矩陣P(r),再通過矩陣運算得到文獻的共被引矩陣C,運算規則為C=PT(r)*P(r);[注]限于篇幅,共被引矩陣表從略,感興趣的讀者可聯系作者索取。并借助SPSS21.0軟件,運用Correlations程序,選擇度量標準Pearson的相關系數,將共被引矩陣C轉換為相關系數矩陣,然后進行主成分因子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法進行正交旋轉,經過篩選之后,最終提取了4個因子,累計解釋率為92%,并將這4個因子命名為:經典組織慣例理論、組織學習與知識創造理論、資源基礎觀與動態能力理論、管理認知與戰略微觀基礎的相關研究。
(一)經典組織慣例理論
組織慣例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卡內基學派關于組織決策的研究和演化經濟學的企業適應性觀點。在March et al.《Organization》和Cyert et al.《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的著作中,作者將慣例視為個體相對無意識的、重復的行為模式和標準化的操作程序,能夠有效地協調組織內部沖突,從而提高組織內部決策效率。Weick在其《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ing》(1979)著作中,促使組織慣例的研究吸納了很多社會心理學的內容,并開始關注個體的認知因素。而Nelson et al.(1982)則打破了傳統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以適應行為(包括慣例的變異、選擇和保留)替代了理性行為,使得組織慣例研究更富有經濟學的理論邏輯。此外,Giddens的《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1984)也成為Feldman和Pentland等學者后續關注組織慣例內部動態性研究的重要思想源泉。
(二)組織學習、吸收能力與知識創造理論
組織學習理論與組織慣例研究之間本就存在著天然的聯系。如Argyris于1978年出版的《Organizational Learning:a Theory of Action Perspective》一書,既是組織學習理論的奠基之作,也對組織慣例的研究影響深遠。然而,通過學習而獲取的新知識,并不一定能夠完全地被轉化和利用。同樣,作為知識在企業的沉淀,組織慣例的復制和轉移也不可能完全如愿以償。Cohen和Levinthal在1990年從技術創新角度提出的“吸收能力”為強化知識轉移和共享提供了新的思路。而Nonaka和Takeuchi在1995年合著的《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至今仍影響很大,作者在書中提出知識是在組織內部顯性知識和隱形知識的不斷交互和轉換中創造的,而組織慣例恰恰就是企業歷史經驗積累而沉淀下來的重要隱性知識。這一知識創造的觀點有益地啟發了組織慣例變異和重構的研究。這些研究有別于經典組織慣例理論主要從社會學和演化經濟學角度的思考,豐富了組織慣例研究的知識視角。
(三)資源基礎觀與動態能力理論
不同于組織理論視角下組織慣例研究關注個體之間的互動,基于組織經濟學視角的組織慣例研究更多地關注其作為一項重要資源或是能力與企業競爭優勢之間的關系。整體而言,組織慣例是資源基礎觀乃至動態能力理論的重要解釋機制,如Teece等(1997)指出,企業競爭優勢來源于嵌入在組織協調和整合資源、學習、重新配置資源的過程及過程中形成的難以復制或模仿的組織慣例,其與企業所控制或者擁有的資源以及企業演化路徑共同塑造和提升動態能力。Eisenhardt et al.(2000)則認為,動態能力本身就是一種戰略慣例,就是企業在新產品開發、資源配置和知識轉移過程中形成的“最佳實踐”。組織慣例研究與資源基礎觀,特別是與動態能力理論之間建立起聯系,使得組織慣例的研究更富有戰略內涵,也促使其成為解釋戰略管理領域諸多理論的核心。
(四)管理認知與戰略微觀基礎的相關研究
受卡內基學派和演化經濟學的影響,組織慣例的研究一貫遵循的是行為模式的思路,而從認知角度進行的研究相對比較欠缺。[注]Eggers Jamie P., Sarah Kaplan, "Cognition and capabilities: A multi-level perspective", in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Vol.7 (2013), p.295;陳彥亮、高闖:《物質情境、分布式認知與組織慣例復制研究》,《科技進步與對策》2014年第14期。組織慣例到底是個體無意識、重復的行為模式,還是個體主觀上“努力成就”的結果,這也是學者們在很長時間內所爭論的問題。要揭示組織慣例內部復雜的動態性,就必須充分理解組織慣例的微觀構成要素及其認知基礎。近年來戰略管理認知學派的興起,特別是在組織和戰略管理領域掀起的微觀基礎運動(Felin等,2015),將認知科學甚至于神經科學應用到戰略研究當中,為打開組織慣例的微觀基礎和認知機制提供了有力的理論視角。
四、組織慣例研究熱點
本文運用Citespace軟件,將“Timeslicing”設置為“1996-2017”,以2年作為一個時間切片,選擇每個時間切片前100的關鍵詞,在對表述意義相同的關鍵詞進行合并之后,采用LLR算法進行聚類分析,并以時間線視圖方式呈現,生成關鍵詞共現聚類圖譜。[注]限于篇幅,關鍵詞共現聚類圖譜從略,感興趣的讀者可聯系作者索取。衡量聚類效果的Q值為0.407、S值為0.5023,表明這一聚類結構顯著且較為合理。[注]陳悅等:《CiteSpace 知識圖譜的方法論功能》,《科學學研究》2015年第2期。由于在LLR算法之下自動生成的聚類名稱依然帶有一定的隨機性,故本文又對每一個聚類中所包含的關鍵詞進行了分析和提煉,并將意義相同且關系緊密的聚類進行合并、對不能準確反映研究內容和熱點方向的聚類進行了剔除,最終形成了組織慣例的三大研究熱點主題。
(一)慣例內部動態性與參與者行動模式
組織慣例為什么會發生變異?傳統觀點認為,慣例變革性主要來源于外部環境的沖擊,而現在學者們基本達成共識的是,組織慣例內部復雜動態性也是其發生變異的緣由,由此引起學術界對慣例內生性變革的研究(Parmigiani et al.2011)。如Feldman(2000)首次將“能動性”視角引入到組織慣例的研究中,他通過對大學生公寓辦理入住、設備運營維護的預算、雇傭和培訓公寓管理員、辦理退宿等一系列慣例的參與式觀察和訪談,認為慣例內部動態性源自慣例參與者基于遵循先前慣例產生的行為結果與預期之間的差異,而對慣例進行“修復”、“擴展”和“持續改進”的反思和迭代。在此基礎上,Feldman et al.(2003)根據拉圖爾(Latour)關于明示和實行的區分,進一步將構成組織慣例的微觀結構分為明示面和實行面(前者是指組織成員對慣例的抽象理解、后者是指組織成員在具體情境中的實際執行),并指出慣例的內部動態性其實就是慣例明示面和實行面相互建構的結果;慣例明示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慣例參與者的實行行為,但慣例參與者在理解和解釋慣例明示面的時候會發生偏差,在慣例實行過程中也會不斷修正慣例明示面,從而導致慣例變異。
另外,作為一個動態的生成系統,組織慣例的內部結構不僅包括抽象的明示面和具體的實行面,還包括與之相聯系的物理載體。這些物理載體表現形式可能是組織的成文規則和標準化運營程序,也可能是工作流程表單和數據庫,這些與慣例參與者及其能動性共同塑造了慣例的動態性(Parmigiani et al.2011)。
參與者能動性和物理載體是慣例內部動態性研究的重要視角,但是,拘泥于這一視角在一定程度上也忽略了慣例實行面的行動序列,而直接將參與者行動視作研究對象則能夠有效地解決組織慣例操作化的問題,從而更好地開展量化研究。因此,慣例作為行動模式的研究也備受關注。如Pentland等(2010)對挪威四家不同類型組織發票處理慣例進行了分析,運用馬爾科夫模型佐證了相同慣例可能產生不同行動模式的觀點,并指出將慣例視為復現的行動模式是促使其進行實證研究的基礎。Pentland等(2017)倡導以行動為中心的研究視角,提出將行動模式作為組織慣例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透過不同行動類別及其順序而構筑的行動網絡,追蹤慣例參與者的行動序列特征,從而預測其未來的行動趨向。[注]Pentland Brian T., Alex P. Pentland, Roger J. Calantone, "Bracketing off the actors: Towards an action-centric research agenda", in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 Vol.27(2017), p.137.為此,他們還專門開發了一款能夠將慣例參與者行動模式可視化的軟件——ThreadNet。大數據時代所承載的海量行動數據應用于組織慣例的研究,為這一領域的定量研究創造了良好條件。
(二)慣例復制與雙元能力
慣例復制涉及跨國公司的地理擴張、卓越企業“最佳實踐”和知識的跨邊界轉移等,是企業價值創造的重要戰略選擇。[注]Friesl Martin, Joanne Larty, "Replication of routines in organizations: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new perspective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Vol.15(2013), p.106.比如麥當勞憑借著“在全球范圍內提供有限系列的、美味的快餐食品”,成功地推廣了它的商業運營體系。基于組織慣例復制的復制戰略不僅能夠促使企業不斷深化對自身商業模式核心要素的認知,也能夠幫助企業充分撬動已有知識資產,從而實現地理擴張和知識轉移(Parmigiani et al.2011)。基于此,現有研究圍繞如何復制企業“最佳實踐”?如何有效地解決復制過程中的悖論困境等相關問題展開了研究。如Winter et al.(2001)建立了復制戰略的兩階段模型,認為復制不是簡單地應用原有知識和經驗,企業必須花氣力和資源探索慣例的“阿羅核心”,即獲取關于企業可復制、有復制價值以及如何復制的知識,塑造和提煉其商業模式的模板,然后大規模地復制和轉移其業務活動;他們還指出,由于組織慣例所具有的情境依賴性特征,在復制過程中企業往往會擔心模板與新環境難以匹配適應,以致面臨“精準復制”還是“當地適應”的兩難選擇,進而產生所謂的“復制困境”。
以Winter為代表的學者認為,一旦復制的模板形成了,任何形式的修改都是徒勞無益的,任何組織的復制戰略都應該建立在固定模板的基礎上,并通過“精準復制”促進企業知識的有效轉移。這是因為,復制過程本身就具有因果關系的模糊性和復雜性特征,嵌入在組織進行的重復性、模式化活動當中的知識資產,通過組織慣例將其連接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行動鏈條,脫離或者修改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可能偏離原有的行動邏輯,從而扭曲對“阿羅核心”的認識。而Gupta等(2015)則認為,復制的模板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最佳實踐”也會遭遇水土不服而需要做出重新設計。[注]Gupta Anuja, David G. Hoopes, Anne Marie Knott,"Redesigning routines for replication",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36(2015), p.851.D'Adderio(2014)也認為,復制戰略并不是簡單地由探索而后轉向開發的線性序列過程,在慣例轉移的過程中,探索和開發活動往往交織在一起,企業可以通過不同目標之間連續地、動態地“選擇性實行”,利用物理載體和溝通社區來建立慣例明示面和實行面相互建構的行動模式,通過培育組織雙元能力實現復制與適應之間的動態平衡。[注]D’Adderio Luciana, "The replication dilemma unravelled: How organizations enact multiple goals in routine transfer", in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25(2014), p.1325;陳彥亮、高闖:《基于組織雙元能力的慣例復制機制研究》,《中國工業經濟》2014年第10期。
(三)慣例與能力的微觀基礎
“微觀基礎”這個概念在過去的十幾年間引起了戰略和組織領域學者們的極大興趣。從已有研究來看,能力微觀基礎研究呈現出個體管理者、組織過程和結構三個視角,[注]Felin Teppo, et al, "Microfoundations of routines and capabilities: Individuals, processes, and structure", in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49(2012), p.1351.學者們圍繞能力,特別是動態能力如何產生和變化的問題,展開了富有真知灼見的研究。從個體管理者角度看,有學者指出相較于企業一般的運營能力而言,動態能力并不是完全嵌入在組織運營慣例之中,而是與管理者搜尋和選擇、配置與部署企業協同專業化資產所形成的動態慣例有關,由此而提出了資源編排理論;[注]Sirmon David G., et al,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o cre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 Breadth, depth, and life cycle effects", in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37(2011), p.1390.而且企業對先前歷史經驗、知識編碼形成組織慣例繼而演化塑造動態能力的過程也不是完全無意識的,而是管理者主觀能動性“努力成就”的結果,其設定、發展和修正組織慣例的不同心理和認知過程會顯著地影響動態能力的產生和發展(Eggers et al.2013)。從組織過程角度看,Zollo et al.(2002)提出動態能力源于企業內部經驗積累、知識銜接和知識編碼三個組織學習過程,這一過程中組織慣例的變異、選擇、復制和保留機制決定著動態能力的演化。從組織結構角度看,現有研究主要關注組織結構的形式和復雜程度如何影響組織慣例和能力的形成和變化。總而言之,運營慣例聚合形成普通能力,而高水平組織慣例則聚合形成高階的動態能力(Zollo et al.2002),能力的微觀基礎離不開組織慣例內部明示面和實行面之間深刻而復雜的二元互動關系。
五、基本結論與未來研究重點
本文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數據庫中發表在1996-2017年間的1333篇組織慣例研究文獻為樣本,運用文獻計量學的分析方法,力圖全面梳理組織慣例領域已有研究的知識基礎和研究熱點,從而為今后的研究提供參考。
研究發現,組織慣例研究領域的發文數量呈現出波動上升的趨勢,特別是從2009年以來,受Feldman和Pentland(2003)獲獎論文的影響,這一研究受到更多學者的廣泛關注,形成了以Pentlend、Feldman和Winter等為代表的核心作者群,以University of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和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等為代表的核心研究機構,而且作者與研究機構之間形成了緊密的科研合作網絡。在主流期刊當中,ORGANIZATION SCIENCE成為這一領域中發文數量最多、影響力最廣的核心期刊。此外,本文識別了構成組織慣例研究的四大知識基礎,包括經典組織慣例理論、組織學習與知識創造理論、資源基礎觀與動態能力理論、管理認知與戰略微觀基礎的相關研究;并總結和提煉了三大研究熱點,包括慣例內部動態性與參與者行動模式、慣例復制與雙元能力、慣例與能力的微觀基礎。
本文的不足之處。其一,并未對國內組織慣例的研究進行文獻計量分析。一是國內組織慣例研究相對不足,只有少數學者如黨興華和孫永磊(主要關注網絡慣例)、高闖和陳彥亮(主要關注慣例復制)等對這方面的研究比較深入,也只有《管理世界》、《科研管理》、《科學學研究》、《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科技進步與對策》等少數國內期刊對此有所涉及,而文獻計量的方法比較適用于分析相對比較成熟的學科或者研究領域。二是國內已有研究成果引用文獻主要是英文文獻,對此進行共被引分析并不能增加現有知識基礎的累計解釋率;而且,國內研究所關注的話題相對集中于將慣例視為一個“實體”,探討其對組織能力的影響,不會影響本文所歸納的基本研究熱點。其二,由于本文主要目的是對已有研究成果進行文獻計量分析,從而從宏觀上梳理這一研究領域的演進脈絡和研究熱點,故在具體內容和理論細節上相對比較粗略。其三,盡管對文獻計量和知識圖譜的解讀本身就是一項兼具科學性和建構性的工作,得出的結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本文也遵循一定的規則和程序,力求通過多種分析方法和工具的綜合運用來客觀地呈現分析結果,但是在Citespace的參數設置、因子命名和主題聚類上仍然帶有一定的主觀性。
針對以上基本結論和不足,我們認為未來可以重點開展以下研究:第一,對近年國內組織慣例的相關研究進行定性梳理,總結國內開展組織慣例研究所具備的獨特優勢條件,以此推動國內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展。第二,隨著中國互聯網行業的快速發展,商業模式創新正在從“copy to China”向“copy from China”轉變,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向國外輸出商業模式,也有越來越多的海外企業來中國尋求商業模式創新的秘訣;而“阿羅核心”是商業模式輸出成功的核心要素,在此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是,本土企業商業模式如何通過慣例復制和復制戰略進行模式輸出?管理者在這個過程中應當扮演什么角色?第三,以行動為中心的研究視角增加了組織慣例定量研究的機會,未來可以憑借企業積累的海量數據資源開展行動研究,揭示組織慣例的微觀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