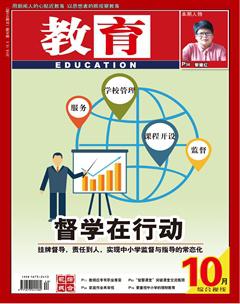家庭作業再審視
陳健
2018年7月,教育部基礎教育質量監測中心發布我國首份《中國義務教育質量監測報告》顯示:“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家庭作業時間過長,參加校外學業類輔導班比例較高,學習壓力較大。”有研究指出:家庭作業具有兩面性,既能提高學習成績,也能降低學習興趣,家庭作業一旦過量,便會侵占生活、愛好、健康、娛樂的時間,因而不是多多益善。當前,學校把家庭作業這種輔助性教學手段當成了主要的教育手段,用到了極致。
家長談“家庭作業”
今天的教師和家長都不同程度地有了家庭作業依賴:很多“主科”教師,如果沒有家庭作業作為最后的一道“防線”,他們會對自己的教學效果感到不踏實,不管什么內容,一定要課下多練幾遍才放心;同樣的心理,家長也會有,他們中有的還會在學校作業之外再給自己的孩子增加一些作業和測驗。
近年來,雖然不乏教育專家、學者主張減少或取消家庭作業,但是我國孩子的作業負擔似乎并未減少。“學生家庭作業時間過長”屢受詬病。
《中國義務教育質量監測報告》對學生課業負擔監測結果顯示:四年級學生數學、語文單科平均每天作業時間在30分鐘以上的比例分別為33.6%、40.4%,在60分鐘以上的比例分別為14.7%、21.5%,在2小時以上的比例分別為4.4%、8.7%;八年級學生數學、語文單科平均每天作業時間在30分鐘以上的比例分別為50.2%、45.5%,在60分鐘以上的比例分別為19.2%、15.1%,在2小時以上的比例分別為4.6%、3.4%。
監測報告指出:我國四年級學生參加數學和語文校外輔導班的比例分別為43.8%、37.4%,八年級學生參加數學和語文校外輔導班的比例分別為23.4%、17.1%。此外,三成以上學生感到很有學習壓力。以數學學習為例,四年級學生表示在數學學習上感到很有壓力的人數比例為30.7%,八年級學生表示在數學學習上感到很有壓力的人數比例為49.4%。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指出:“對義務教育的監測,只有各級政府重視監測反映的問題,才能達到監測的目的。所以,各級政府主管教育部門需要讀懂義務教育質量監測報告,并用好監測報告。”
檢查孩子作業,讓許多家長不堪重負。安徽合肥一位“80后”母親楊女士說:“家長給孩子的作業簽字看似簡單,想要達到老師的要求,卻并不容易。孩子上了小學,寫作業的事情常把我們折騰得筋疲力盡。老師說孩子的作業里有錯題,建議我們以后認真檢查再簽字,不要出錯了。我認為孩子寫作業錯一兩道題很正常,在老師訂正講解時就可以加深印象。”一項調查顯示:79%的家長反對孩子作業由家長簽字。主要原因在于反對課業過量,反對強行增加難度、脫離實際的作業,反對老師教育職能的“缺位”。
對于家長的抱怨,教師的解釋似乎也站得住腳。合肥市淮河路第三小學英語教師張蓮娣說:“孩子的教育需要家庭、學校相互配合,特別是低年級的孩子,更需要家長擔起責任督促他們學習,幫助他們打好基礎,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讓家長簽字是希望家長重視孩子的學習,督促孩子保質保量完成作業,因為老師不可能面面俱到、照顧到每一個孩子。”從她多年的教學實踐看,家長重視孩子的作業,認真檢查簽字,孩子的作業和學習成績相對會比較好;相反,如果家長對孩子的作業不重視,一些孩子可能幾天都不做作業、不交作業,有的孩子雖然寫了作業,也字跡潦草,敷衍了事。
“讓家長告別檢查作業”呼聲漸起
前不久,網上關于“小學生作業家長要不要簽字”一事,網友的討論各執一詞,十分熱烈。
2017年9日,浙江省金華市金東區實驗小學發出兩份公約:《讓家長告別檢查作業——實驗小學教師公約之作業篇》和《讓家長告別檢查作業——實驗小學學生公約之作業篇》。前者提出:“認真批改作業,是每一位老師的基本職責!我們希望學生這樣認識:檢查作業是我自己的事,不是媽媽的事;從今天起,我們想改變‘家庭作業變成‘家長作業的現狀,取消規定家長為孩子家庭作業簽字的要求……”后者提出:“認真完成作業,是每一位同學的基本職責!我們想改變這樣的作業場景:媽媽在身邊嘮叨不停,爸爸在桌旁眉頭緊鎖;從今天起,給我一方書桌,給我一份安靜,我會成為作業的主人……”
“現在,有些家長接送、陪做作業、陪吃飯、陪玩耍,一切以孩子為中心。這樣子,孩子缺少了很多獨立生活、獨立學習的機會,會讓他們養成依賴性。我做了校長之后也經常會和家長聊天,發現大家都有同樣的焦慮:要檢查作業、要糾錯、要批改,學生作業演變成了家長作業,無形中增加了家長的壓力。所以,我覺得學校有必要科學引導,倡導家長不參與作業檢查,提倡學生獨立完成作業,由老師承擔起應盡的責任。”金東區實驗小學校長方青指出:家長要為孩子做的,是營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和氛圍,幫助和引導孩子正確地思考和解決問題,而不是跟孩子去完成作業;要讓孩子認識到,學習是自己的事情,只有讓孩子明確了學習的目的,提高了認識,端正了學習態度,孩子才會努力認真地對待學習和作業。
無獨有偶,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陶藝藝術大師徐安碧曾攜帶8份提案參加兩會,其中一份提案就是專門討論“家長批改作業”的。徐安碧認為:教師堂而皇之地要求家長批閱家庭作業和周末試卷等,是教師轉移教學責任的表現。家長應盡責任是督查孩子完成作業,督促其專注,督促其書寫認真之類,豈能將批閱的責任也推到家長身上?教師要求家長批閱作業,如發現未曾批閱或者批閱有誤,便會批評孩子,或批評家長。而教師批閱作業是天經地義,假如連作業都可以不批閱了,豈不是“不務正業”嗎?為此,徐安碧建議教育主管部門重申或出臺有關教師教學工作職責規范,盡快制止“家長批閱”的行為。
如何治理“家長作業”?2018年7月12日,在四川省政協召開的“治理‘家長作業促進義務教育健康發展的建議”重點提案辦理協商會上,四川省教育廳答復:“我廳正在廣泛開展中小學減負大調研。我們將在調研的基礎上,聯合相關部門制定措施,切實推進課后服務。”針對近年來一些中小學生家庭作業異化為“家長作業”這一社會熱點問題,與會的四川省政協委員和四川省教育廳相關負責人,從“家長作業”的成因、對策及其落實等方面展開深入探討,就厘清家校職責邊界、規范教學要求、建立良好家校溝通機制和督查機制等達成了基本共識。
控制作業量和作業時間
一項調查數據顯示:中國上海青少年每周寫作業花時間最多的約14小時,其次是俄羅斯、新加坡,而芬蘭每周是3小時,雖然韓國的學生也是3個小時,但是他們平均每周請1.4小時家教,上3.6小時課外補習班。另外,調查還發現學生用在作業上的時間與家庭經濟條件關系密切,富裕家庭比貧困家庭的學生每周多1.6個小時用在寫作業上。
“家庭作業”是老師和家長檢驗孩子學習效果的輔助性教學手段。近年來“減負”呼聲居高不下,但不少老師和家長依然把家庭作業當成了主要的教育手段,用到了極致。家庭作業是不是越多越好?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目前,我國有一些地方把初中生的作業量限定在兩小時以內,小學五、六年級限定在一小時以內,而小學三、四年級限定在半小時以內……作業量以時間計量會遇到一個老大難問題:以誰的能力來定時間,因而可操作性不強。另外,這兩年有更多的地方加入了小學一、二年級不留書面家庭作業的行列。這項措施有可操作性,也很容易檢查。小學一、二年級不留家庭作業,是否有根據?是否會影響孩子的學業成績?三、四年級甚至小學全學段是否也可以不留作業呢?這需要有切實的研究來支持,也需要對家庭作業這種教學手段的作用進行再審視。
2018年6月,重慶市教委下發《關于做好2018年中小學暑假工作的通知》,要求遵守減輕學生課業負擔的規定,嚴格控制學生假期作業量,小學一、二年級不布置書面作業,其他年級可根據學生實際布置適量假期作業。同時還要求,各中小學在暑假期間不得以任何名義和形式組織學生集體上課、補課,不得動員、組織或誘導學生到社會培訓機構補課,嚴禁學校將校舍、設施設備等提供(租、借)給社會機構、學術團體和個人舉辦各類補習班、培訓班、競賽輔導班。
家庭作業形式應豐富有效
學生的家庭作業除了課本知識作業,應該還有勞動技能作業,甚至包括洗衣、掃地等日常家務勞動。2018年7月,由浙江省教育廳、團省委、省少工委聯合出臺的《關于加強中小學勞動實踐教育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要加強勞動實踐教育,以改變一些學生勞動觀念差、輕視勞動實踐、不珍惜勞動成果的現象。
《教育》記者了解到,當前許多中小學生不會做家務,基本上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有的住校生甚至每周把臟衣服打包帶回家,讓父母洗。追根究底,主要是勞動教育在學校被弱化,在家庭中被淡化,導致中小學生勞動實踐機會少,勞動觀念淡薄,不會勞動,不珍惜勞動成果。同時,在應試教育的指揮棒下,中小學生的書包越背越重,作業越來越多,補習培訓有增無減,甚至暑假成了“第三學期”,學生沒有時間與機會參加勞動實踐,接受勞動教育。
這種問題,早就引起了政府關注。2015年,教育部聯合共青團中央、全國少工委印發《關于加強中小學勞動教育的意見》,要求對中小學生開展勞動教育,提高廣大中小學生的勞動素養;要求學校安排適量的勞動家庭作業,鼓勵學生參加力所能及的家務勞動。而今,浙江省把家務納入家庭作業,是舊話重提,是對素質教育的重申。浙江省要求,用3年左右時間,推動建立課程完善、資源豐富、模式多樣、機制健全的勞動實踐教育體系,形成普遍重視勞動實踐教育的氛圍。一方面,在學校中設置各種勞動課程,給學生創造各種勞動機會;另一方面,讓洗衣、掃地成為學生的家庭作業。這一政策在獲得各方支持的同時,也讓一些學校和家長犯了愁。在他們看來,操作起來有難度。
根據隨機的采訪調查,多數家長對浙江的這一政策表示支持:“孩子的素質由多方面決定,光是學習成績好顯然不夠,假如學校和家庭形成合力推動勞動教育,培育孩子的勞動意識,對孩子的幫助肯定很大。”不過,也有個別家長持謹慎和懷疑的態度,他們認為現在孩子每天做完作業睡覺都是在晚上9點以后,怎么忍心再讓他們做家務,因此,堅持做這個家庭作業有點難。
如何真正體現家庭作業的價值,需要我們再審視,從根本上找出解決辦法。有專家觀點:教師不應用作業“綁架”家長。《人民教育》2018年第6期刊登程路文章指出:“沒有多少老師和家長會特別顧及家庭作業的負面屬性;除了教育行政部門的減負文件和一些地區性法規外,似乎也沒有多少人會注意家庭作業的學段、學科效果區別;最重要的是,我們把家庭作業這種輔助性教學手段當成了主流的教育手段,用到了極致。在解決這個問題上,一是化解社會焦慮;二是在控制作業總量的前提下,盡可能把學業內容在校內消化解決;再有就是加強家庭作業方面的研究。找到適合我國實際的家庭作業規律并進行推廣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