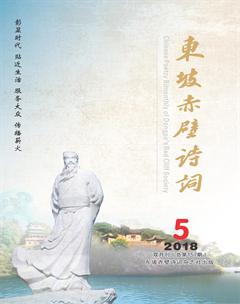詩的正氣,詩的美韻,詩的啟迪
周光輝
我和紹祥先生相識已十年了。那還是我剛任麻城師范學校校長時。記得當時有一個班的學生,要舉辦畢業30周年紀念活動,邀我參加,我十分高興應邀前往。也就是通過那次活動,我結識了一批在麻城政界及教育界十分活躍的人士,并通過亊后他們所做的畫冊,認知和記住了能夠創作格律詩詞的紹祥先生。由于我們有共同的愛好,從那時起,我們便一路互幫互學走到今天。紹祥先生的人生歷經了多個崗位,不管在哪兒,除了做好本職工作外,一直在自覺堅持詩詞創作,一直在自覺傳承和弘揚古典詩詞這一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這在眾多的麻城師范學子中,是十分突出的。僅這一點,就讓人十分欽佩。今天,他要呈現給人們的這部《勁草臨風》詩集,就是他多年創作成果的集成和展示。這部詩集共分六個部分,內容豐富,選材多樣,有記述,有想象,有抒懷,記錄了他不同時期的工作經歷、友情交往和心路歷程。認真拜讀后,覺得此集具有三個鮮明特點。
一、思想上是昂揚向上的,詩具正氣
思想性是詩的靈魂。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今天,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過程中,衡量一部文學作品的首要標準,是看其是否具有鮮明的思想性。作者是否堅持做到了“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作品是否反映了人世間真的善的美的情愫,是否能引領讀者向上向善,引導人們在正確的人生道路上闊步前行,這是當今時代必須首先關注的課題。我認為,紹祥先生在創作實踐中,很好地把握住了這一點。
他是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在履職盡責的同時,利用業余時間,創作了大量謳歌公安干警英雄形象的詩詞作品。如《冬夜勇救投河女》中寫道:“鈴聲嘀嘀響三更,少婦投河噩夢驚。勇士飛車驅夜霧,男兒躍水破寒冰。”
一個舍已救人的英雄群體躍然詩中,一幅警民和諧的溫馨畫面盡展眼前。其另一首《情系農家》更加精彩:“晨沐朝陽晚沐霞,走村入戶訪農家。噓寒問暖人人樂,濟困扶貧處處夸。一聲老哥情似海,三聲大嬸淚如花。圍爐促膝心相印,手捧香茶話稻麻。”此作有情景記述,沐浴著朝陽晩霞走進農戶;有溫情承接,噓寒問暖濟困扶貧;有高潮迭起,老哥情似海,大嬸淚如花;有裊裊余音,心相印,話稻麻。這首詩通過對公安干警入戶扶貧這一細節的記敘,反映了人民警察為人民服務的初心,反映的是他們不僅僅只是把人民的安危擔在肩上,更重要的是,時時刻刻把人民的冷暖總記心頭。
紹祥先生在頌贊人間正氣的同時,自已的人生態度也堪稱昂揚向上,充滿著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我選取他《五十八歲生日感懷》為證:“遙看秋日近山前,歲月如歌又一年。茶遇知音神亦爽,人逢盛世志尤堅。東隅雖已成佳話,余熱還當著美篇。云卷云舒皆任意,但求康健伴詩眠。”作者雖已年近甲子,但思盛世人歌;雖有東隅佳話,仍思余熱生輝。期望在云卷云舒之下,與友品茗,與詩為伴,與詩共眠,詩意僅僅反映的是飲茶吟詩么?恐怕還不是,這給人們留下了無限的想象空間。
二、藝術上是可圈可點的,詩具美韻
藝術性是詩詞的肉體,是詩詞質量的重要構成,如果撇開詩詞的藝術質量,單純追求詩詞的思想性和教育作用,詩詞同樣沒有生命力。猶如一個人一樣,如果只具備完備的思維系統,而沒有強壯的體格、淵搏的學識和優雅的儀態,同樣不是完整的人生。紹祥先生在把握詩詞思想教化的同時,在追求詩詞的藝術完美上,也作了探討和追求,并有明顯成效。
可先從一首小令《十六字令·秋》說起:“秋,云淡天高景色幽。風霜染,紅葉漫山丘。”說這是一首詞么,無疑是的;說這是一幅畫么,我覺得也是的。說這是麻城東山的秋景,像;說是北京西山的秋景,也行;總之是用精準的語言,寫出了中華大地秋天獨有的詩情畫意。說到秋天,詩人們多用蕭瑟來形容,故有秋風秋雨秋意濃和秋風秋雨愁煞人之說,而紹祥先生不是這樣。他從蕭瑟的秋風中獲取靈感,把秋景寫得這般美好,這般曼妙,這般多姿多彩。這就不由使我聯想到陳毅元帥的那首著名的《題西山紅葉》:“西山紅葉好,霜摧色愈濃。革命亦如此,斗爭見英雄。”進而又聯想到了共和國的開國太祖、詩詞大家的那首《沁園春·長沙》“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我不知道,紹祥先生在創作那首小令的時候,是否受到過偉人們的啟發。我猜想再少是熟知開國太祖的那首詞吧。他的另一首絕句《河邊散步》,也頗具趣味:“天邊日出水中霞,路上行人霧里花。兩岸風光依舊在,歌聲飛去卻無她。”朝陽灑在水面上,泛出道道霞光,河岸兩邊散步的男男女女,在朝霧中若隱若現,朦朧中還不時飄來幾聲悅耳的歌聲。是誰在漫步?是誰在放歌?是他否,是她否,還是真有花否?不得而知,給人聯想并帶著期待。待到晨風吹散朝霧,陽光灑滿大地時,看到的是廬山真面貌,是大河兩岸依舊的風光。不知歌聲從哪兒飛出,不見霧里花紅,幾分失望,幾分迷茫,幾分惆悵凝聚筆端,讓人忍俊不禁,浮想聯篇。
三、思想性藝術性是高度統一的,詩具啟迪
詩的最高境界是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高度統一和完美結合,只有這樣的詩作,才能夠啟迪人,教化人,并給人們以美的享受。自古以來,中華民族的文人墨客創作了大量的詩詞作品,不少精品流傳至今,并為人們津津樂道,供我們學習,鑒賞,品味。我們在閱賞精品詩詞時,常常感受到在與古人進行近距離的對話和交流,精神得到洗禮,境界得到升華,感受到了無窮無盡的樂趣。我想這就是文學的教育和啟發作用吧。當然,要使詩詞的兩性統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亊情。它是廣大詩詞愛好者共同追求的目標。有的人奮斗不止也無法達到目的,但卻又為此癡迷和努力。我觀紹祥先生的詩作,覺得他在追尋這一目標上,作了可喜的探索并為之稱道。如《秋游龜山》:“牯嶺凌空起,神龜矯鄂東。云低猶壓頂,樹直且招風。干老枝尤勁,秋深葉自紅。迎難攀峭壁,步步震蒼穹。”《望鄉》:“月朗星稀夜,魂牽夢繞時。南游懷別意,北望寄相思。一掬憂傷淚,幾行眷戀詩。伊人身影遠,日日盼歸期。”他的這兩首五律,堪為思想性與藝術性高度統一的典型佳作。《秋游龜山》是歌頌家鄉的,是歌頌家鄉勝景龜峰山的,他為此肯定傾注了無限的熱愛和溢美之情。其思想性是勿容置疑的。與開國元勛董必武的那首頌龜峰山的五律一樣,飽含著黃麻赤子對家鄉山水的深情厚意和對家鄉熱土的深深感激。人們讀詩以后,龜峰山的形象在心目中更加高大和完美起來。與此同時,由于有了情感和熱愛作為依托,詩的藝術成就也更為豐滿。云低猶壓頂,樹直且招風。干老枝尤勁,秋深葉自紅。這兩聯遣詞造句自然,形象準確,既是詩,又是畫,又是照,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并且對仗工整,一氣呵成,反復吟誦后,會口留余香。詩的最后是詩的高峰,反映出麻城兒女的奮斗精神,即不管在血雨腥風的戰爭年代里,還是在實踐中國夢的征程中,都會向著更高目標奮力攀登。
《望鄉》同樣值得一讀。望鄉思鄉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中華兒女不管走到何處,不管走向七大洲還是五大洋,家鄉總是我們魂牽夢繞的地方。這種思念還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對家人的思念,而要更深層次地理解為對親人,對故土,對祖國的熱愛和眷戀。我們的先賢尤為如此,曾留下很多膾炙人口的鄉思詩詞,其中我最喜歡的是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如果我們把這兩首詩比較一下,是不是感覺到異曲同工?一個是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一個是月朗星稀夜,魂牽夢繞時。表現的都是對家鄉對親人的思念之情,并且其思念都十分地強烈。“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與“伊人身影遠,日日盼歸期”比較起來也十分相似,一是家人團聚唯缺一,一是伊人天天盼郎歸。我不敢說,紹祥先生已熟讀唐詩三百首,但起碼是讀過許多唐詩的。《望鄉》一詩的感情色彩還十分濃郁,不管是南游還是北望,每逢佳節,都向著家的方向或注目或鞠躬并流下思鄉熱淚,我認為這首詩藝術上最大的成功,就是全詩處處自然流露的思鄉情懷。
誠然,這部詩集也有瑕疵,首先是詩風上可能是效仿白居易先生的,顯得過于平實,如果在堅持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基礎上,學學太白詩風,做到浪漫與現實結合,那詩集或許就更加完美了。其次是在煉字上仍需用功。但這兩點瑕疵,并不影響詩集總體的成功。我覺得,這部詩集《勁草臨風》的名字取得很好,勁草就必須臨風,而臨風的勁草,才能生長得更加茂盛。我衷心祝愿紹祥先生如臨風沐雨的勁草,在今后的詩詞創作過程中,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我也愿與他一起攜手并肩,共同邁向詩的遠方。
(作者系東坡赤壁詩社常務理事、麻城杏花詩社社長、校園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