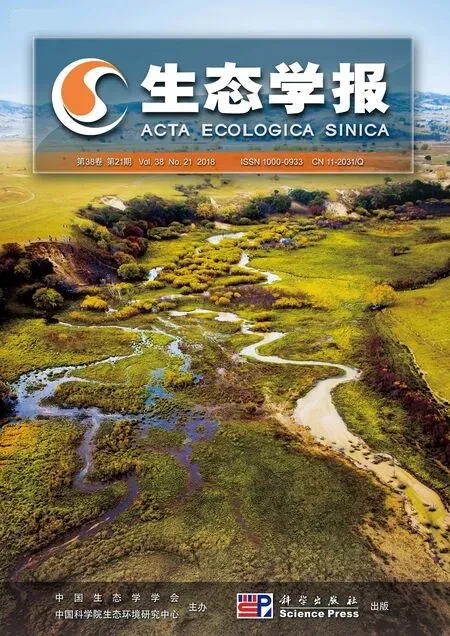鄱陽湖水體淹沒頻率變化及其濕地植被的響應
谷 娟,秦 怡,王 鑫,馬靜宇,郭仲皓,鄒樂君,沈曉華
浙江大學地球科學學院,杭州 310025
在湖泊生態系統中,水文特征的變化顯著推動著濕地植被的形成和變遷,進而影響魚類和野生動物棲息地乃至整個湖泊生態系統的質量[1- 3]。其中,湖水淹沒頻率反應了水體淹沒時間的長短和次數,被認為是影響濕地植被生態系統的最重要的一種水文因素[4]。因此綜合分析湖泊淹沒范圍內淹沒頻率的空間分布和時間變化特征,進而揭示其對湖泊植被分布及演替的影響,對改善湖泊季節性淹沒區域資源的養護和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遙感技術在湖泊生態系統時空變化監測上具有獨特的作用。MODIS數據由于具有高時間分辨率和多光譜特性,已被廣泛運用于湖泊變化監測中。由于水體幾乎吸收了近紅外和中紅外波段的全部能量,而植被、土壤等對這兩個波段的吸收量非常少,目前通過遙感技術提取水體大多都是基于水體的這個特性實現的[5]。常見的MODIS水體提取方法主要有單波段閾值法[6- 7]、水體指數模型[8- 10]和混合像元分解模型[11- 14]3種。其中混合像元分解模型是對MODIS中混雜有陸地信息的混合像元進行分解,通過定標獲得接近實際覆蓋情況的水體豐度,解析每個像元內水體的所占比例,較前兩種經驗方法在精確估算水域參數方面更具優勢[15- 16],對于河流和湖泊的局部細節以及小型水體的面積提取可以獲得更高的精度[5,17],更適用于水陸變化復雜情況下的湖泊水體提取。
鄱陽湖作為中國第一大淡水湖,其形態與面積的季節性波動很大,豐水期的水域面積往往可達枯水期面積的四倍以上[18],并且由于受湖底地形地貌特征影響[19],在枯水期鄱陽湖被分割成了眾多的子湖泊,使得枯水期與豐水期的水體表面的空間分布有較大的差異,基于水位數據的水淹過程評價精度相對洪水季節較低[20- 22],這個時期水體淹沒過程的評價以及給植被帶來的影響仍需要進一步研究。近年來很多學者使用遙感數據對鄱陽湖變化進行監測,但他們更注重于對湖區面積的時間序列變化或者影響因素的探討[7,23- 24]。劉元波等利用淹沒頻率分析了鄱陽湖近年來的空間變化和變化速率[25- 26],但尚未深入分析淹沒頻率對湖泊生態帶來的影響。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多時相MODIS遙感圖像數據和混合像元分解模型為基礎,分析了退水期鄱陽湖水體淹沒頻率的時空變化規律,并討論了淹沒頻率和植被分布的關系,以期對鄱陽湖的生態環境變化影響以及周邊水利工程的建設提供一些科學依據。
1 研究區概況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概況
鄱陽湖位于江西省北部(圖1),長江中下游南岸,115°47′—116°45′E,28°22′—29°45′N,是一個十分典型的季節性、過水性和吞吐型淺水湖泊,湖水平均深度為8.4m。鄱陽湖形似葫蘆,湖盆主要由河道和洲灘組成,以都昌和吳城間的松門山為界限,鄱陽湖可分為南北兩部分:南部是寬廣、較淺的主湖區,北部則為狹長、較深的入長江河道。鄱陽湖受季風影響,水域面積變化明顯,在洪水期時湖水面積可達4000余km2,枯水期時僅1000多km2。河道和洲灘在洪水期時均被淹沒,退水期則廣泛出露,伴有植被、泥灘以及水域等濕地景觀類型。在本研究中,根據混合像元分解模型獲取的15年間鄱陽湖9月淹沒面積的最大值作為研究區邊界。
1.2 數據獲取和預處理
MODIS數據
遙感數據來源于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免費提供的MODIS數據產品(http://modis.gsfc.nasa.gov),MODIS數據集包含多個數據產品,本文使用的MODIS產品為1B級數據MOD021KM,它含有36個離散波段,最高空間分辨率達250m,且每天在不同時間過境4次。在本研究中利用ENVI 5.1圖像處理軟件對圖像進行了輻射定標、大氣校正、系統幾何校正等預處理工作。考慮到MODIS和Landsat影像空間分辨率的差異,以Landsat影像為基準對MODIS影像進行了幾何精校正處理,保證了MODIS影像0.1像元的幾何精度。考慮到MODIS影像中云對混合像元分解的影響,研究中用波譜面積比值法[27]做了去云處理,經上述預處理工作后選取了2000年到2015年的220期影像。由于MODIS數據不同波段的空間分辨率不同,研究中將所用波段全部重采樣為250m,重采樣后按湖區邊界進行統一裁剪。
Landsat數據
Landsat- 8發射于2013年,每16天一景數據,分辨率為30m,對LC8遙感數據進行最大似然法分類,將分類的結果作為MODIS數據定標的參考值。
2 方法
2.1 水體提取
混合像元分解模型所獲取的豐度反應了某一像元內相應地物類型所占的比例,其技術難點在于影像純端元的選取,而對于MODIS這類低空間分辨率影像數據通常難以獲得足夠的純端元用于分解混合像元。郭峰博士[14]在其論文中曾詳細介紹了基于地物波譜特征的混合像元分解模型,該模型在進行線性混合像元分解前,先采用最大似然法對Landsat ETM+數據進行分類,獲得參考豐度,再對MODIS影像進行定標,獲得水體、植被和裸地3種豐度,該方法利用相對高分辨率影像分類的結果代替了影像純端元的選擇,提取結果在水陸交互區更具優勢,更符合鄱陽湖區的實際情況。在本文中根據水體豐度在圖像像素中累積分布產生的直方圖,確定了水體淹沒與否的最佳閾值。對鄱陽湖的北部河道和中部洲灘地區的水體提取結果的檢驗表明,提取精度達97.45%。
2.2 淹沒頻率變化分析
淹沒頻率是指一個區域在一定時間內被水體淹沒的次數占總淹沒次數的比例[26],在本文中,通過對水體/非水體二值影像的空間疊加運算,獲得影像各像元的淹沒頻率。
鄱陽湖每年自4月進入雨季,湖水上漲,一般從8—9月開始水位逐漸下降,進入退水期[28],當鄱陽湖水開始消退時濕地植被開始生長。因此湖水的漲退過程對鄱陽湖洲灘出露分布影響最顯著的時段為8—11月[29],并且由于16周是包含植被生長節律的很大一部分而又能使植物種間競爭效應最小化的一個時間周期[4],因此我們選擇8—11月(退水期)水體進行淹沒頻率分析。同時,根據鄱陽湖水面面積的變化過程和特征,以及三峽工程建成蓄水的時間節點[30],將2000至2015年期間鄱陽湖的水面變化分為3個時間段:2000—2005年、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對每個時間段分別計算8—11月的淹沒頻率,來分析湖區的演化特征。
2.3 淹沒頻率與植被分布響應

圖2 數據處理流程圖Fig.2 The flowchart of data processing
水文過程制約著濕地的生物、物理和化學過程,是濕地植物群落形成和演變最重要的驅動因素[31],每年的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鄱陽湖洲灘濕地植被生長狀況達到最好。植被生物量可用植被分布面積和總生物量來表示,在本研究中用混合像元分解模型獲取的植被豐度來表示像元內植被覆蓋面積占比。考慮到濕地植被的生長除了受到水體淹沒的影響還受自身季節生長節律的控制[28],這里以8—11月的淹沒頻率代表鄱陽湖在退水期間的淹沒過程差異、選取11月植被豐度的最大值代表11月植被生長所能達到的最旺盛狀態的區域分布,通過分析兩者之間的關系來評估退水期水淹過程對濕地植被生長的影響。
考慮到MODIS數據的分辨率,把整個研究區劃分為69319個250m×250m的網格,按網格將淹沒頻率信息和植被豐度信息對應起來,通過繪制淹沒頻率和植被豐度的二維散點圖分析植被對淹沒頻率的響應關系。
數據處理流程圖如圖2所示。
3 結果與討論
3.1 淹沒頻率變化分析
3.1.1 淹沒頻率時間變化分析

圖3 2000—2015年期間鄱陽湖退水期淹沒頻率變化Fig.3 Inundation frequency of Poyang Lake during receding period from 2000 to 2015

圖4 2000—2015年期間退水期淹沒頻率分布 Fig.4 Inundation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Poyang Lake during receding period from 2000 to 2015
圖3表示了3個時期鄱陽湖的淹沒頻率空間分布變化,其中藍色越深代表著淹沒頻率越高,紅色越深則代表著淹沒頻率越低。整體上從2000—2005年到2006—2010年鄱陽湖的平均淹沒頻率由57.07%降到了40.07%,然后在2011—2015年平均淹沒頻率小幅度回升到46.34%。從淹沒頻率的空間變化以看出不同的區域的淹沒頻率變化程度不同:北部河道段從2000—2005年到2006—2010年的過程中淹沒頻率明顯下降,低淹沒頻率區顯著增加,但2011—2015年淹沒頻率又回升到較高的水平;中部洲灘段在2000年到2010年淹沒頻率下降明顯,2011年到2015年則變化不大,15年間的變化程度不如北部河道段,但由于洲灘地勢通常較低平坦,變化的區域更加廣泛;南部的子湖泊在2000年到2015年的淹沒頻率則基本無變化。
統計不同淹沒頻率下像元的個數,計算出不同淹沒頻率的面積及其比例(表1),總體而言鄱陽湖的低淹沒頻率區(淹沒頻率<20%)淹沒面積持續增加,面積占比由18.21%上升到22.34%再到22.56%,但增加的速度由快變緩。中等淹沒頻率區(20%<淹沒頻率<60%)則經歷了面積先增大后減少的趨勢,其中淹沒頻率為20%—40%的面積最終由914.19km2降到882.53km2,而淹沒頻率為40%—60%的區域面積由636.29km2升到731.83km2。高淹沒頻率區(淹沒頻率>60%)的面積變化趨勢則與中等淹沒頻率區相反,淹沒頻率為60%—80%的面積占比先降低后回升,最終從16.5%略有上升到17.02%,而常年水域區(淹沒頻率>80%)面積雖然是先降低后回升,但15年間的面積還是由1273.05km2大幅降到了998.15km2。

表1 淹沒頻率變化統計表
淹沒頻率的普遍降低預示著湖泊向陸地的轉變,低淹沒區域的增加、高淹沒區域的減少,退水期鄱陽湖的變化既反應了近些年的氣候異常,更是反應了人類活動的影響。自2003年三峽工程調節蓄水以來,長江干流入鄱陽的水量大大減少;近年來鄱陽湖周邊建立了許多人工灌溉渠道和水庫,用于防洪、灌溉和供水方面;再加上不同區域的采砂活動導致的地勢差別進一步擴大,這些因素都可能是造成鄱陽湖不同區域的湖水面積衰退不等的原因。淹沒頻率的變化會誘發一系列的生態環境問題:低淹沒頻率區域的持續增加會對越冬鳥類造成不利的影響;洲灘顯露時間的延長也會影響到濕地植被的種類數量和生長狀況;高淹沒頻率區域的變化則使得濕地植被呈現正向演化趨勢。
3.1.2 淹沒頻率空間格局分析
圖4顯示了2000—2015年鄱陽湖退水期間水體的淹沒頻率分布,從整體淹沒頻率的空間分布來看,鄱陽湖的淹沒頻率總體上呈“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這種空間分布差異是鄱陽湖發展演變的結果,也是地貌特征的反映。鄱陽湖北部河道地區的淹沒頻率為60%—90%,中部因退水期間洲灘廣泛出露、植被生長而淹沒頻率相對較低。鄱陽湖邊緣的自然小湖泊群,在豐水期時水體會越過堤壩連成一片水域,在枯水期時則因天然堤壩與湖泊主體隔離而成為獨立封閉的小湖泊[20]。在圖4中表現為中部洲灘區域的淹沒頻率從子湖湖心往四周逐漸降低,呈“島嶼式分布”。距離各子湖泊湖心越遠,對應的高程逐漸增加,水體被淹沒的頻率相應下降,在圖4呈現出似伴隨著大小不均的斑塊式空間分布特征。此外,鄱陽湖南部一些水體區域(如軍山湖、青嵐湖和金溪湖)接近永久淹沒,比北部河道的淹沒頻率空間分布更加穩定,這是因為這些湖泊均屬人為湖泊,因此在退水期時期,它們的面積往往與季節變化關系不大。
從鄱陽湖淹沒頻率的空間分布格局和時間變化,可以清晰的分辨鄱陽湖湖內不同地區被水淹沒的空間差異以及變化的趨勢。淹沒頻率的差異性分布也顯示出了湖區不同地段蓄水量和湖底特征的差異,低淹沒頻率區主要分布在鄱陽湖的湖岸線、松門山等高地勢區域以及五河入湖河道,一半以上鄱陽湖面積淹沒頻率低于60%。研究這些不同淹沒頻率區域的植被生長情況,探究淹沒頻率的變化是促進了濕地植被的發育還是導致濕地植被豐富度的下降,有利于洲灘植被的發展和植被多樣性的保護。
3.2 植被對淹沒頻率的響應

圖5 2000—2015年期間11月植被豐度最大值分布 Fig.5 Mean maximum value distribution of the vegetation abundance in November from 2000 to 2015

圖6 淹沒頻率與植被豐度散點圖Fig.6 Inundation frequency versus vegetation abundance diagram背景色為交點處的像素數目,紅色越深代表該處像素數目越多

圖7 植被豐度對淹沒頻率的響應空間分布 Fig.7 Distribution of response of vegetation abundance to inundation frequencyIF:淹沒頻率 inundation frequency; VA:植被豐度 vegetation abundance
圖5展示了2000—2015年期間平均的11月植被豐度的最大值分布,和圖4對比,植被豐度的空間形態和淹沒頻率的空間形態具有較高的相似性。淹沒頻率>80%的區域的植被豐度普遍偏低,平均豐度值在27.66以下,其中,軍山湖和青嵐湖的平均豐度值更是低至11.12,這些區域常年被水淹沒,是湖泊中心區。在北部河道段,受科里奧利力的影響,來自長江干流的泥沙淤積在左側,凹岸三角洲的植被豐度較高。鄱陽湖中部的低淹沒頻率區(淹沒頻率<20%)植被豐度較高,但植被豐度也不是和淹沒頻率完全呈負相關關系;中部洲灘處越靠近岸邊的湖水淹沒頻率就越低,植被豐度最高值的區域卻并不是分布于最靠近岸邊的區域。為了更好的探究植被與淹沒頻率在空間分布的聯系,分析了植被豐度和淹沒頻率的二維散點圖以及兩者的空間響應關系,來探討淹沒頻率對植被覆蓋的影響。
圖6為淹沒頻率和植被豐度的二維散點圖,其中的背景顏色代表的是相應淹沒頻率和植被豐度在圖像中的像素數目,紅色越深代表相應的像素數目越多。圖6中,淹沒頻率和植被豐度的散點圖呈中間高兩邊低的“n”形分布:當淹沒頻率達60%—70%時,植被豐度急劇下降,意味著水體的高頻淹沒使植被的生長受到限制,只有部分沉水植被生長,當淹沒頻率>80%時,植被豐度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在低淹沒區域,以淹沒頻率20%為界,植被豐度也出現了明顯的界限:當淹沒頻率<20%時,植被豐度處于中等偏低水平。這主要是兩個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因為淹沒頻率偏低的區域多為地勢較高的灘涂裸地,不利于植被的生長;另一方面是因為最靠近岸邊的濕地樹林在11月時已經到了落葉季節,因此植被的生長程度沒有隨著退水期冒出來的濕地植被群落旺盛。當淹沒頻率為20%—70%時,植被豐度整體處于一個較高的水平,意味著此區間的淹沒頻率有利于退水期植被的生長。并且,當淹沒頻率為40%左右時到達二維散點圖“n”形的頂點,即以16周為植被生長周期,退水期植被最旺盛的區域位于淹沒頻率為40%左右。
為了更清楚反應植被豐度對淹沒頻率的響應,根據兩者的二維散點圖選擇4個區域進一步分析其空間特征,分別是淹沒頻率0—20%與植被豐度0—50(圖7選區1)、淹沒頻率20%—70%與植被豐度40—70(圖7選區2)、淹沒頻率20%—70%與植被豐度70—100(圖7選區3)、淹沒頻率70%—100%與植被豐度0—30(圖7選區4)。四個選區的空間特征分別指示著不同的植被類型。選區1主要分布于鄱陽湖的湖岸帶附近,淹沒頻率和植被豐度均偏低。從前人資料可知鄱陽湖湖岸帶的綠地景觀和水體景觀從1990—2010年在逐步萎縮,轉變為建設用地和裸地[32],選區1的空間分布有效的支持了這一理論,并且從圖7中可看出,北部河道的兩側具有明顯的差異。選區2主要分布于堤壩和蝶形坑群的較高平原上,在南磯山濕地的南部尤其廣泛。這些區域主要分布著以蘆葦群落為代表的半挺水植被[2]。選區3主要分布于鄱陽湖的濕地以及濕地底部邊緣的水域,面積占研究區域的19.92%。主要分布著以薹草群落為代表的濕生植被[20]。選區4為高淹沒頻率低植被豐度覆蓋的常年淹沒水體,但選區4排除了蝶形湖中蚌湖、大湖池、大汊湖和白沙湖等區域。這些區域受到了輕度到中度的富營養,水質較差,主要是因贛江和饒河輸入的工業廢水、生活污水影響所致[33]。
從散點圖選取不同的感興趣區域,將其與已知植被類型對應起來,可以運用到MODIS數據識別不同的植被類型中。也可以通過統計不同年限間的植被中感興趣區域所累積的背景像素數目的多少,而達到評判不同年限間的濕地植被生長情況好壞的目的:當選定區間的植被豐度的像素數目總和較高,則代表著當年的植被生長狀況良好,而植被生長狀態不好的年份散點圖中的像素總和較低。
將圖7和圖3對應起來,反映出水情變動導致的濕地植被的變化:選區3所代表的濕生植被在15年間的面積由343km2上升到736km2,增加了兩倍以上,其變化率遠大于相應淹沒頻率段的變化率。這說明了低淹沒頻率區域的增加,很大的促進了濕生植被的生長。從圖7選區3看出,退水期間薹草群落的分布最為廣泛,成為鄱陽湖的優勢物種。通過圖7選區2結合前人資料[2]知,蘆葦群落所代表的植被數量在2000—2010年下降了一半以上,南磯山濕地南邊水陸交界處以蘆葦為代表的群落明顯向下擴展,而底部灘地的薹草群落則遷入淺水區。這些結果表明:在干旱趨勢條件下地勢較高的半挺水植被(如:蘆葦、荻等)的生物量或密度下降;相對應的,由于底部濕生植被(如薹草屬和虉屬)發生了積極的植被演替,呈明顯上升的趨勢。
4 結論
本文利用MODIS混合像元分解技術獲取鄱陽湖水體分布信息,分析了2000—2015年的鄱陽湖退水期的湖水淹沒頻率時空變化,并討論了淹沒頻率對植被豐度的響應分布,得到了以下結論:
(1)淹沒頻率的空間分布較好的反映了鄱陽湖在退水期湖水淹沒過程的空間差異,其空間格局同高程相關,反映了不同水域被淹沒的概率性高低。淹沒頻率的時間變化則反映出15年間鄱陽湖退水期的空間淹沒范圍經歷了先急劇下降后回升但總體呈下降的趨勢。
(2)通過將淹沒頻率的空間變化規律和植被豐度的空間分布規律對應起來,在淹沒頻率過高(>70%)或者過低(<20%)的區域植被分布普遍偏低,植被與淹沒頻率呈中間高兩邊低的“n”形分布關系,當淹沒頻率為40%時最適宜濕地植被的生長。當鄱陽湖的淹沒頻率普遍降低時,鄱陽湖的濕生植被呈向下擴展的積極演變趨勢。
研究認為,這項研究采用的方法在時空尺度上分析了植被覆蓋面積與水體淹沒過程之間的聯系,所得研究結果有助于我們認識鄱陽湖在退水期的水淹過程與植被生長變化的規律,既可以作為分析鄱陽湖水淹變化對植被分布的空間基礎,也可以進一步研究植被豐度和淹沒頻率的關系而運用到對濕地植被類型的劃分及其長勢優劣的評判,從而為鄱陽湖的資源管理以及環境變化檢測提供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