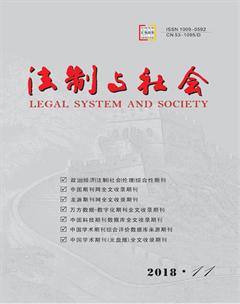對尋釁滋事中毆打、毀損行為主觀目的的認識
李維維 高迪
摘 要 尋釁滋事罪是指恣意挑釁,橫行霸道,隨意毆打、滋擾他人,或者強拿硬要、任意毀損、占用公共財物,情節惡劣,或者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行為。其客觀方面表現為恣意挑釁,橫行霸道,破壞社會管理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本罪在客觀方面最典型的特征,包括兩種類型:第一,無事生非型,即毫無緣由,逢人便打,見物就砸;第二,借故生非型,即有一定事由,多為日常生活中的摩擦或瑣事,但這些事由被行為人借題發揮,夸大并加以利用。而本案行為方式表現為借故生非。
關鍵詞 尋釁滋事 隨意毆打 情節惡劣
作者簡介:李維維、高迪,天津市靜海區人民檢察院。
中圖分類號:D920.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11.029
一、基本案情
2016年11月28日許,犯罪嫌疑人崔某某、李某某、王某某、王某某及崔某某(另案處理)五人酒后駕車到天津市某區設備租賃有限公司向該公司原承租人崔某某索要欠款。崔某某等人在明知該公司已更換其他承租人,該公司門衛人員張某某告知其該公司實際控制人為沈某某等人的情況下,強制翻墻入院,無故踢踹該公司辦公樓房門,將其中25個房門踹壞,并將該公司值班人員周某某、張某某打傷。在現場,崔某某、李某某、王某某、王某某被民警抓獲。崔某某逃離現場。經鑒定,被損毀木門價值人民幣4550元;周某某、張某某身體所受損傷均為輕微傷。
二、爭議問題
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尋釁滋事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的規定,行為人因婚戀、家庭、鄰里、債務等糾紛,實施毆打、辱罵、恐嚇他人或者損毀、占用他人財物等行為的,一般不認定為“尋釁滋事”,但經有關部門批評制止或者處理處罰后,繼續實施前列行為,破壞社會秩序的除外。
對崔某某等人實施毆打、損毀行為主觀目的的認識存在分歧,形成兩種不同意見:
一是崔峻豪等人為討要債務而實施毆打、損毀行為,符合司法解釋的要求,不認定為尋釁滋事。
二是被害人方與崔峻豪等人無債務關系,崔峻豪等人在明知公司老板不是肖長華的情況下,仍實施毆打、損毀行為,系借故生非,不符合司法解釋中的要求,應認定構成尋釁滋事罪。現有證據能夠證實崔某某等人去同創同德工廠的主觀目的是為了找肖某某要賬,但崔某某明知肖某某將該廠轉給他人,且在門衛張某某告訴其該廠老板不是肖某某后,崔某某等人在未核實該信息的情況下,仍繼續實施毀壞財物、打傷他人的行為。故崔某某等人的行為不符合司法解釋中“行為人因債務糾紛,實施毆打他人或者損毀財物的行為,一般不認定為‘尋釁滋事”的規定,其主觀上具有借故生非的故意。崔某某等人客觀上實施了隨意毆打他人致兩人輕微傷、任意毀損財物的行為,財物價值4550元,造成了同創同德工廠的損失,擾亂了社會公共秩序。故犯罪嫌疑人崔某某、王某某、王某某、李某某之行為符合尋釁滋事罪的構成要件,涉嫌尋釁滋事罪,系共同犯罪。
三、評析意見
從尋釁滋事罪的犯罪構成上看,包括無故生非與借故生非兩種類型,而前因行為是判定無故生非或借故生非的重要依據。綜合上述證據,盡管肖某某證實該公司尚屬于其個人所有,但馬某某等三人的證言及相關書證足以證實肖某某向公安機關做出了虛假證言,現有證據證實,案發當時,同創同德公司已經另租他人,崔某某一方實施的踹門與毆打行為可以認定為是尋釁滋事主觀故意中的借故生非。因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尋釁滋事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足以證實崔某某、李某某、王某某、王某某有借故生非,任意損毀公私財物、情節嚴重,又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犯罪事實存在。尋釁滋事罪客觀行為之一,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行為。所謂“隨意毆打他人”,是指出于耍威風、取樂等目的,無緣無故或者小題大做,毆打他人的行為。有的是毫無緣由的,有的是有一定理由的,但行為人自以為是的理由,作為毆打他人的借口,是不被一般社會公眾所承認的。毆打他人的手段,既可以是赤手空拳的毆打,也可以使用棍棒、磚塊等器物毆打。作為隨意毆打他人的一種體現,行為人很少使用特定犯罪工具,徒手作案多,即使使用工具也多是現場找取,毆打他人的強度一般不大,打擊的部位大多不是要害部位,往往是能打哪兒就打哪兒,并且一般還伴有叫囂、辱罵、示威等言辭或行為。本案中崔某某等人主要用木條、拳頭、巴掌打門衛,用腳踹門。王某某隨手用現場木條打人。其行為符合尋釁滋事罪的客觀行為。
情節惡劣,是指隨意毆打他人造成身體傷害的;持械隨意毆打他人;隨意毆打他人手段惡劣的;多次隨意毆打他人的;造成被毆打人精神失常或者自殺等嚴重后果的;造成社會秩序嚴重混亂等惡劣情節的。這里的造成他人身體傷害,應以造成輕傷為限,如果造成他人重傷、死亡的,則超出了尋釁滋事罪的范圍。本案中兩名被害人均構成輕傷,并未超過釁滋事罪的犯罪構成。
四、處理結果
法院經審理認為,對四被告人的行為是否符合尋釁滋事的法律特征,應否作為犯罪處理的問題。經查,四被告人于當日晚間來案發地點,因未找到實際債務人,為發泄不良情緒,憑借已方人多勢眾、身強力壯,在被明確告知涉案單位已更換實際經營人的情況下,仍翻墻入院并公然毀損財物,后又就地取材,恃強凌弱,對與涉案債物毫無關系的兩名當班值守人員就地實行毆打并致傷的行為,屬于典型的“無事生非”的表現,足以表明四被告人具有較大的主觀任意性和隨意性。同時也是對他人的身體安全和健康安全欠缺尊重,對依據法律和社會公德所確立的社會公共生活的正常秩序的嚴重破壞,對調整社會管理秩序的國家禁止性規范的肆意踐踏。
關于本案案發屬于“事出有因”中“因”的理解,按照社會一般人的主觀評價,此“因”不足以引發毆打和毀財的行為,實施毆打和毀財的行為與該事件的起因之間不具有對稱性,因果關系不成比例,且被害人對事件的發生并無過錯,其原因內容荒唐、邏輯混亂,不能為一般社會公共所承認和接受,辯護人提出的所謂的“事出有因”是一種違背常理、常情和社會公序良俗的“借口”,不具有正當性。
縱觀全案,從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出發,結合四被告人行為實施時間的隨時性,地點的不區分性,犯罪對象選擇的臨時性、隨機性和擴大性,以及犯罪動機的無視法律性,并綜合考慮該案的社會危害性和四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經全面分析評價,四被告人的行為具有可罰性。
法院認為,被告人崔某某等人任意毀壞公私財物,破壞社會秩序,情節嚴重;又隨意毆打他人,破壞社會秩序,情節惡劣,其行為均構成尋釁滋事罪。關于四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問題,在案證據表明,被告人崔某某、王某某、李某某基于同一犯意,積極參與,分別實施不同程度的打砸行為,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王某某雖未直接實施打砸行為,但其在現場對其他同案人的打砸行為在精神上予以壯勢,行為上予以配合,其行為是本案尋釁滋事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他三被告人的作用相當,亦為主犯,應當按照其參與的全部犯罪予以處罰。根據本案的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及對社會的危害程度,經審委會討論決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六十七條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尋釁滋事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判決被告人崔某某、王某某、李某某、王某某犯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兩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