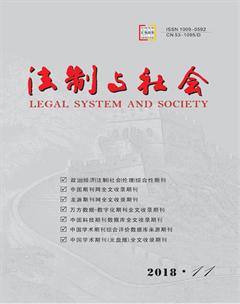略論公民教育權義觀
摘 要 “權利優先”抑或“義務優先”是公民教育在權義觀上的兩大分野,由此產生了權利論公民教育和義務論公民教育。權利論公民教育堅持“權利優先”原則,強調公民個體的權利,將權利作為公民教育的第一要義;義務論公民教育堅持“義務優先”原則,強調公民個體對共同體的義務,將義務作為公民教育的核心內容。本文嘗試從公民身份的法哲學視角對公民教育權義觀進行論證,為權利論公民教育正名。
關鍵詞 公民教育 權義觀 公民身份 法哲學
作者簡介:劉杰,西安航空學院助教,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與實踐。
中圖分類號:D9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11.116
公民教育如何在權利和義務之間選擇,這始終是公民教育理論研究領域的一大議題。本文嘗試從公民教育的對象——公民著手,從法哲學視角對公民身份進行解讀,以期為公民教育的“權利優先”原則辯護,為權利論公民教育正名。
一、公民身份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公民身份”是一個頗具爭議的復雜概念,從不同視角對其內涵進行解讀,其特殊性和普遍性的涵義也不盡相同,從公民所指的對象這一視角出發去揭示公民身份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不失為一個很好的嘗試。
(一)公民身份的特殊性
“公民”被認為是由古希臘時期的“城邦”衍生而來的 ,公民是構成城邦的基本元素,是“屬于城邦的人”,這是“公民”一詞最原始的內涵。
城邦源于血緣關系,希臘時期的城邦僅僅代表城邦中的特定群體,即具有本邦血統的成年男子。隨著城邦的不斷演變,公民身份也隨之變化。起初,只有貴族和具有一定財產的人才有資格成為公民。到了城邦民主較為發達的時代,底層平民也有機會被納入公民范疇。當戰爭來臨時,則會進一步擴大城邦公民范疇,以抵御外邦侵略。 然而,無論怎樣變化,城邦時期公民的本質始終沒有改變,即由血緣關系決定社會地位。因此,希臘時期城邦的公民人數普遍較少,這一時期的公民身份只是一種特權的象征,并不具備普遍意義上的權利內涵。
(二)公民身份的普遍性
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發展,羅馬時期公民的外延有了極大的擴展。羅馬共和國時期,平民大眾在與上層貴族的激烈斗爭中逐漸獲得了與貴族同等的公民資格,這種平民化的公民資格伴隨著帝國的擴張逐漸遍及整個羅馬帝國。 相比之下,羅馬帝國在公民權利的問題上超越了希臘城邦的狹隘性,賦予了公民身份權利的內涵。這一切都要歸功于羅馬法,羅馬法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賦予了平民大眾以公民權利,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將其確定下來。隨著羅馬法在西方世界的普及和發展,法律作為一種維護社會秩序的權威準則被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采用,以權利為象征的公民身份也由此走向了大眾化。
“毫無疑問,羅馬法是古羅馬對西方文明做出的最偉大的貢獻。” 羅馬法被認為是現代法治的起源,它是現代訴訟制度的起源,它奠定了現代憲政文明的基礎,確立了現代法治的根本。 羅馬法是古代西方政治和法律文明的重要標志,為人類社會的法治發展和民主進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公民身份被明確的法律條文確定下來,法律規定國家的所有居民依法享有同等的公民權利,“公民”自此成為一個法律名詞并真正走向大眾化成為普遍意義的平等身份。
二、公民身份的法哲學闡釋
如前所述,公民身份由古希臘時期的特權地位發展到近代普遍的平等身份,法在其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法對公民身份由特權身份發展到普遍身份具有旅程碑的意義。那么,法發展到當代,它對公民身份的影響和意義發生了哪些變化,或者說當代公民身份從法中獲得了哪些益處?這是一個涉及面極廣、見仁見智的問題。筆者從法哲學視角出發,從法的真、善、美層面闡述法和公民身份之間的緊密聯系。
(一)法之“真”賦予了公民身份不可侵犯的權威性
從客體哲學角度看,“真”是人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是人把握客觀世界的基礎,人的認知活動的目標是探尋事物的“真”。從主體哲學角度看,“真”是客觀事物在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特點,是客觀事物的本質屬性。 因此,若把法看作主體,從主體哲學角度來理解的話,法之“真”便是指法的本質屬性,包括法的邏輯性和確定性,法的普遍性、穩定性和公開性,法的巨大權威性和強制性, 法的正當程序性和可訴性等。
當代公民身份是具有法律權威的一種普遍性的身份認同,具有不可侵犯的權威性,這源于法自身的穩定性、巨大權威性和強制性。準確的說,法的穩定性是相對穩定性,是指法必須在一定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不得隨意更改、中斷或廢止,以保持法的權威性。穩定性是法作為一種社會準則的內在屬性,是法之“真”的具體體現。 法的權威性是指法的效力的至上性,其意義在于保障法所體現的人民意志被暢通地執行,保證公民的法定權利得到切實維護,保證違法行為被依法追究。法的強制性與法的權威性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一方面,沒有法的強制性作保障,很難樹立法的權威;另一方面,法的強制性又不能和法的權威性相并重,即不能簡單地通過法的強制力來達到樹立法的權威性的目的,法的強制性必須以法的正當性為前提。法的巨大權威性和強制性是法在控制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法之“真”。 正是法的穩定性、巨大權威性和強制性融合在一起的法之“真”,才保障了公民不可侵犯的法定權利和法律地位。
(二)法之“善”賦予了公民身份無差別的平等性
“善”通常是被看作倫理學的概念,不僅用于評價人的主觀行為,還用于評價客觀事物和現象。從認識論的角度看,“善”主要被用于反映人和客觀世界的價值關系。物質世界里的一切事物客觀上都存在對人的有用性,這些有用性能否成為現實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人對客觀事物的認識程度;二是人的實踐水平所能達到的對客觀事物的利用程度。因此,所謂“善”即主體把自身的價值尺度觀念地、實踐地運用到實踐對象上去,賦予實踐對象應然意義的活動。 主體對“善”的追求是無止境的,“只有把現有的東西提升為某種自己創造的東西……才會產生善的更高境界” ,客觀事物“善”的程度正是在人們的這種不斷對理想境界的追求中得以提高的。法的“善”正是人們在自身價值尺度的框架內對法的認識和改造中賦予它的合乎人們價值標準的準則。
法之“善”是法所蘊含的符合人們價值標準的正面價值,法之“善”有眾多的具體表現形式和現實形態,大體包括:正義、公平、平等、自由、權利、民主、效率等。 一部法是否是善法,就取決于它是否體現了這些價值標準。若一部法體現了公平正義等原則,保證了人們能夠享受到法律所規定的無差別的平等權利和自由,那么它就是一部善法;反之,則是惡法。法的這種無差別的“善”保障了公民法定權利被無差別的共享。這就使得公民身份無差別的平等性在法理上得以確立,從而最大限度上保證了社會的公平正義。
(三)法之“美”確立了好公民的標準
對于什么是“美”,“美”的本質是什么這一問題,自從柏拉圖說“美是難的”以來,對“什么是美”的問題出現了各種解釋。其中,英國美學家阿諾理德對“美”的界定得到了學界的廣泛認同,“關于審美價值有三種可能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審美價值是物的一種重要特質,它獨立于主體之外,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種觀點認為審美價值是一種精神特質,是有個體差異的;第三種觀點認為審美價值是由精神與客觀對象二者之間的關系組成的” 。這三種觀點就是所謂美的客觀說、主觀說和主客觀關系說。對于法來說,法是“人為”的,同時法又是“為人”的。就是說法是由人創造的,同時也是為人服務的。因此,在理解法之“美”的時候,理應將法的客觀“美”和人的主觀審美聯系在一起,在主客觀的統一中理解法之“美”。
法是否可以成為審美的客體,法是否有客觀的“美”?對此一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法之美,美在何處?在法中,處處有美” 。對公民身份來說,法客觀上的“美”,是指法在對公民身份進行規定和描述時所使用的文字的簡練、精確與嚴密;法主觀上的“美”,是指法通過優美的法律條文,形象地描繪出符合人們審美觀的好公民的具體標準。由此可見,在區分公民“美”與“丑”的時候,人們依據的是法所確立的好公民的標準。好公民即依法行使公民權利且不對他人造成權利侵害的公民。
法之“真”,在于法自身的穩定性、巨大權威性和強制性,并以此確立滿足特定社會和歷史時期所需要的社會準則;法之“善”在于法對公平、正義、權利等的維護,并以此促進社會的和諧;法之“美”在于法律語言的簡練、精確與嚴密,在于通過美的文字為社會確立一個“美”的標準。 法之“真”賦予了公民身份不可侵犯的權威性,法之“善”賦予了公民身份無差別的平等性,法之“美”確立了好公民的標準。
三、權利論公民教育是公民身份得以實現的有力保障
通過對公民身份進行法哲學剖析,法對公民身份的意義可見一斑。但并非有了法律的保障,公民的權利就會真正被公民切實享有,法律只能保證公民權利法理上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性,卻不能保證所有公民實踐地對自身權利的享有和行使。公民對自身權利行使和享有的程度取決于他們對權利的主觀認知水平和實踐能力,而這正是權利論公民教育的題中之義。
(一)權利是公民身份的象征
權利是公民身份的第一要義,把公民與私民、臣民進行對比,有利于更深刻地理解公民身份的權利內涵。“公”對“私”,一個是“私有”的“私”,是一種所屬關系,這層含義上的“私民”意為“為別人所有的人”,最主要的形式便是封建專制時期的“臣民”;另一個是“私人”的“私”,這層含義上的“私民”便是現實社會中備受批判的自私自利的人。權利是公民身份的第一要義,“臣民與公民最本質的區別,反映在其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上。作為自然經濟、宗法社會和專制政治的產物,臣民是君主的附庸,臣民無我。而作為市場經濟、現代社會和民主政治的產物,公民是自由民、主體、主人,是有主體意識和自由權利的人” 。相應的,公民意識的核心便是權利意識,臣民意識的核心則是義務意識。臣民意識有三個主要特征:一是在“朕即國家”的皇權至上的集權統治下,臣民只有忠君的義務而無任何權利的自覺;二是在泯滅主體意識的“修身”觀念束縛下,臣民缺乏基本的主體意識;三是在嚴苛的等級制度壓制下,形成了“盡人皆奴仆”的政治心態。 通過與私民、臣民進行對比,不難看出公民區別于私民和臣民的最主要標志在于公民有權利意識并依法享有公民權利。因此,從某種程度上看,權利就是公民身份的代名詞。
(二)公民權利的三種形態
權利有眾多類型,根據權利由產生到發展的過程,可將權利分為“應有權利”、“法定權利”和“實有權利”三種形態。“應有權利”是主體基于社會物質生活條件而產生的權利訴求,是主體自身利益和需要的自發反映,是權利的最初形態,是“自在”的權利;“法定權利”是通過立法對“應有權利”的進一步確認,是權利的發展形態,是“自為”的權利;“實有權利”是主體對“法定權利”的現實享有以及對相應義務的確實承擔,是權利的實現形態,是“自在自為”的權利。
公民權利也具有以上三種形態,這三種形態分別與公民權利的產生、發展和實現三個階段相對應。公民的“應有權利”是“自在”權利,它不以法的變更為轉移,它在內容和范圍上是三種形態中最廣的。“權利不以法律的存在為前提,但是以法律的保護為最佳方式。” 公民雖然擁有廣泛的“應有權利”,但要想使這些權利免于侵害,就必須依賴于法律的保護,通過法律的保護賦予公民權利以不可侵犯的權威,這便是公民的“法定權利”。但由于每個人的物質生活水平不盡相同,因而每個人對權利的訴求也不相同,即每個公民的“應有權利”在內容和范圍上存在差異。法律很難實現對每個公民的全部“應有權利”予以保障,法律只能盡可能給予全部公民以最大范圍的權利保障。因此,較之公民的“應有權利”而言,公民的“法定權利”在內容和范圍上有很大縮減。現實生活中,公民“法定權利”所能實現的程度取決于其自身對其“法定權利”的認知水平和實踐能力。因此,對公民進行權利的認知和實踐教育就顯得尤為重要。
(三)權利論公民教育是公民權利得以實現的現實途徑
如前所述,法律雖然在法理上保障了公民權利的不可侵犯性,但卻很難在現實生活中保障公民的各項“法定權利”被公民切實享有。唯有公民對其依法享有的“法定權利”的行使和維護有了充分的認知,并積極進行權利實踐,公民的“法定權利”才能被切實享有從而轉化為公民的“實有權利”,但這卻是法律條文力不能及的。法律只能為公民權利提供法律保障,卻無助于提升公民對其自身權利的認知水平和實踐能力,提升公民對權利的認知水平和實踐能力要靠教育。作為一種教育實踐活動,以“權利優先”為基本原則的權利論公民教育恰好彌補了法律的這一缺憾,為公民權利認知水平和權利實踐能力的提升提供了現實途徑。
權利是公民身份的象征,公民教育理應把權利教育放在尤為突出的位置,堅持“權利優先”原則,這不僅符合公民身份的基本理論,也有利于提升公民對權利的認知水平,強化公民的權利意識,促使其在反復的實踐中把權利意識內化為自身的內在人格,以促進整個人類社會的民主進程,促進人類民主文明不斷發展前進。
注釋: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著.吳壽彭譯.政治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109.
叢日云.古代希臘的公民觀念.政治學研究.1997(3).
張博穎、陳菊.西方公民觀與公民道德觀的歷史演變——從古希臘羅馬時期至17、18世紀.倫理學研究.2004(6).
[英]F·H·勞森著.黃炎譯.羅馬法對西方文明的貢獻(上).比較法研究.1988(1).
許中緣、蔣海松.羅馬法的傳統與現代價值——“羅馬法傳統與現代中國:回顧與前瞻”國際研討會綜述.光明日報.2011-07-05.
劉志山.真善美的哲學與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55-57,61-62.
呂世倫.法的真善美——法美學初探.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14-115,125-145,265-267.
[德]黑格爾著.范揚、張企泰譯.法哲學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66.
阿諾·理德.美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117.
Desmond Manderson. Songs Without Music: Aesthetics Dimensions of Law and Justice. California.2000.201.
喻中.法的真善美三維透視.社會科學報.2001-01-18.
藍維.公民教育:理論、歷史與實踐探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3.
劉澤華.中國政治思想史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61-268.
文正邦.法哲學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92-93.
何志鵬.權利基本理論:反思與構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