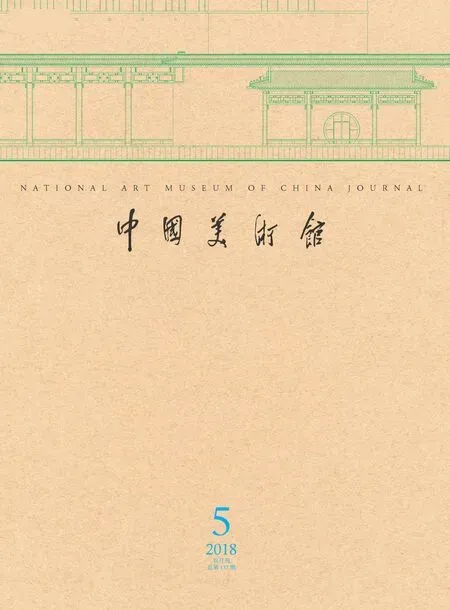“藝道尋真
——張安治的藝術(shù)人生”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綜述
吉仁(整理)
2018年7月26日下午,“藝道尋真——張安治的藝術(shù)人生”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在中國美術(shù)館七層學(xué)術(shù)報(bào)告廳舉行。張安治先生的哲嗣、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張晨,張安治先生的學(xué)生、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編審劉龍庭,張安治先生的學(xué)生、上海博物館研究員李維琨,中國國家博物館原副館長陳履生,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鄧嘉德,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教授邵彥,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教授曹慶暉,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研究員華天雪,中國美術(shù)館展覽部主任裔萼,中國美術(shù)館公教部主任徐沛君,中國美術(shù)館收藏部副主任王雪峰,中國美術(shù)館藝術(shù)品修復(fù)中心副研究館員鄧鋒參加了本次活動(dòng),該研討會(huì)由中國美術(shù)館副館長安遠(yuǎn)遠(yuǎn)主持。筆者現(xiàn)將參加研討會(huì)的各位專家發(fā)言摘錄如下,以饗讀者。
安遠(yuǎn)遠(yuǎn):作為國家捐贈(zèng)與收藏項(xiàng)目的“藝道尋真——張安治的藝術(shù)人生”展既是文化和旅游部2018年的重要項(xiàng)目之一,也是中國美術(shù)館捐贈(zèng)與收藏系列展覽的一部分。我們在做這個(gè)展覽的過程中,特別榮幸地得到了張安治先生親屬對中國美術(shù)館的大力捐贈(zèng)。“藝道尋真——張安治的藝術(shù)人生”展之目的在于通過對張安治先生的藝術(shù)人生研究和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展示,來回看20世紀(jì)中國美術(shù)的發(fā)展歷程及我國老一輩藝術(shù)家對這個(gè)時(shí)代的貢獻(xiàn)。所以,我們要特別感謝家屬的大力支持。中國美術(shù)館之所以能夠不斷地將精彩的展覽呈現(xiàn)給大家,就是得益于社會(huì)各界藝術(shù)家對我們的鼎力相助。現(xiàn)在先請這個(gè)展覽的策展人之一鄧鋒講一下展覽的總體構(gòu)思和策展理念,并對本次展覽的一些亮點(diǎn)作一些介紹。
鄧鋒:謝謝安館長。我很榮幸地受張晨先生邀請,參與了此次展覽的策劃。的確,能夠參與本次展覽的策劃,既是義不容辭,也是一次難得的學(xué)習(xí)機(jī)會(huì)。我在此就先簡要介紹一下參與此次展覽策劃的大體情況和基本想法。
首先,我得感謝張晨老師。張晨老師作為張安治先生的兒子,是一位資深的美術(shù)史研究者。他對父親遺存的畫作和文獻(xiàn)進(jìn)行了系統(tǒng)而完整的梳理,這也成為此展一個(gè)極為重要的學(xué)術(shù)基礎(chǔ)。薛永年先生曾這樣概括張安治先生:“三絕詩書畫,兩美史與論”,這就指出張安治先生藝術(shù)成就不僅全面,而且都達(dá)到相當(dāng)?shù)母叨取H绾文芡ㄟ^一個(gè)展覽來呈現(xiàn)張安治先生如此全面的成就呢?難度非常大。我和張晨老師反復(fù)討論,認(rèn)為一方面普通觀眾可能對張先生了解不多,另一方面大多研究者也未曾較為全面看過張先生這些作品和文獻(xiàn)。因此,我們商定此展的基本定位就是盡可能客觀地梳理其藝術(shù)人生、全面展示其學(xué)術(shù)成就。此次展覽囊括了張安治先生創(chuàng)作的各種藝術(shù)形式和各個(gè)創(chuàng)作時(shí)期的作品,包括油畫、水彩、粉畫、素描、速寫、中國畫、書法,甚至還有幾張版畫,這些作品涵蓋了他各個(gè)創(chuàng)作時(shí)期,最早的作品有其15歲隨謝公展所習(xí)寫意花卉,最晚的作品有其去世前夕的書法和國畫。當(dāng)然,主體可分為中西藝術(shù)兩大板塊。同時(shí),展出其一定數(shù)量的書信、手稿,手稿包括畫史專題、個(gè)案研究、畫學(xué)理論研究、畫評、雜文,甚至還有他20世紀(jì)40年代所作歌曲以及其著述、畫冊等書籍。本展總計(jì)展出其作品及文獻(xiàn)兩百余件,我們試圖以點(diǎn)帶面,相對全面地展現(xiàn)張安治先生融書畫家、學(xué)者、詩人、美術(shù)教育家等多重身份為一體的全能、通才面貌。我們也希望通過這樣的全面展示,讓觀者近距離、多維度地走近其藝術(shù)人生,為研究者提供更多的觀察視角和思考路徑。
但伴隨而來的問題是,該以怎樣的展題來概括如此眾多的展品和維度呢?這既要相對客觀、準(zhǔn)確,又要能體現(xiàn)出我們對于張安治先生的學(xué)術(shù)理解。在翻看張先生作品時(shí),我和張晨老師發(fā)現(xiàn)有一枚“真中之夢、夢中之真”的鈐印,張安治先生使用它頗為頻繁,而且在不少作品的詩句題跋中也常有論及。我們的理解是:張安治先生的藝術(shù)人生正是處在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民生關(guān)切與民族文脈、藝術(shù)理想之間,處在普及推廣西法寫實(shí)與探尋深挖傳統(tǒng)寫意之間,處在個(gè)人追求與時(shí)代進(jìn)程之間,最終形成了在“真”與“夢”之間既潛隱起伏又極富張力的獨(dú)特道路。沿著這一理解向度,我們反復(fù)考量,最終確定以“藝道尋真”為展題。為了對應(yīng)其藝術(shù)人生,我們又將其細(xì)化為“真中之夢”(西畫部分)、“夢中之真”(中國書畫部分)兩大板塊,并輔以“學(xué)人·詩心”的文獻(xiàn)資料板塊。我個(gè)人認(rèn)為,這里的“真”可作多方面理解:它既可指其追隨徐悲鴻先生探尋藝術(shù)真諦,尤其是在引入西方寫實(shí)造型之“真似”方面的研習(xí);也可指其面對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和感受自然造化之真;還可指其受傳統(tǒng)君子文化熏染,在真性和真情中追求完美人格和完善自身的內(nèi)在心路歷程……
因?yàn)樵谥袊佬g(shù)史研究方面,我是張安治先生的再傳弟子,所以在參與策劃的過程中,令我感受最深的是如何以展覽的方式呈現(xiàn)作為美術(shù)史論家的張安治先生?從20世紀(jì)30年代開始,張先生便開始撰寫美術(shù)評論文章。他于1946年赴英游學(xué)期間主攻藝術(shù)史,并大力推動(dòng)中國文化藝術(shù)的宣講介紹;他在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教授創(chuàng)作實(shí)踐的同時(shí),主要精力已轉(zhuǎn)向?qū)χ袊媽W(xué)和畫史的研究;其在20世紀(jì)80年代更是成為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中國美術(shù)史論研究的一面旗幟,著力培養(yǎng)碩士研究生與博士研究生。他的學(xué)術(shù)研究范圍極廣,進(jìn)而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和方法,如史論結(jié)合、以“史”帶論、風(fēng)格與意蘊(yùn)并重、重視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與理性思辨的結(jié)合等,這些都成為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美術(shù)史論教學(xué)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尤為值得關(guān)注的是,他的史論研究既有與時(shí)代的對應(yīng)與合拍,也有著超越時(shí)代的傳統(tǒng)文脈承續(xù)。在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的抗戰(zhàn)環(huán)境中,他強(qiáng)調(diào)藝術(shù)參與社會(huì)的功能;在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的潮流中,他冷靜思考中國畫傳統(tǒng)的價(jià)值和轉(zhuǎn)化;在改革開放初期,針對中國畫再次陷入危機(jī)的爭論以及求變求新的思潮,他撰寫了《論文人畫》一文,辯證分析其利弊,并撰寫多篇反思創(chuàng)新與繼承關(guān)系的文章。這些研究文章中均有關(guān)于時(shí)代性與永恒性、個(gè)性與普及性的辯證思考,顯示出其既有開闊的比較研究視野,又有別具立定本根的自信。本次展覽中所呈現(xiàn)的研究文獻(xiàn)和手稿僅是“冰山一角”,由于籌展時(shí)間的關(guān)系,也沒有尋找到最為合適的展現(xiàn)手段。我想,如果我們能夠以“講課”或“課堂”的方式再現(xiàn)與梳理其史論研究的時(shí)代背景、研究初衷或研究方法等,或許會(huì)讓展覽更有意思。當(dāng)然,這還需要我們做大量的工作。
最后,回到此展中特別強(qiáng)調(diào)的張安治先生座右銘:崇剛健之德,尚樸素之美,依自然之理,寄浩蕩之思。(其早年所書的后兩句為:習(xí)精嚴(yán)之法,依自然之理。)這既是其藝術(shù)觀的寫照,也是其人生觀的寫照。通過其由早年到晚年的局部改寫,我們不僅可以管窺其文化心理的微妙變化,更可感受到一位既有傳統(tǒng)風(fēng)骨、又與時(shí)俱進(jìn)的藝術(shù)大家風(fēng)范——回到“心正藝正”“治藝以誠”的文人之本。展覽的基本情況我就介紹到這,謝謝大家!真誠期待各位專家和前輩對本次展覽提出寶貴意見。
安遠(yuǎn)遠(yuǎn):正如吳為山館長在序言里面所說:“在20世紀(jì)中國美術(shù)史的發(fā)展歷程中,張安治先生是一位集書畫創(chuàng)作、詩詞寫作與美術(shù)史論研究于一身的學(xué)者型藝術(shù)家”。面對這樣的藝術(shù)家,觀者想通過幾張作品了解他是很難的,想要通過他的作品、著述、立論來全面地理解他也是有局限的。現(xiàn)在我們請劉龍庭先生發(fā)言,他可能有比較生動(dòng)的課堂直接授業(yè)的經(jīng)歷。
劉龍庭:我在張先生的課上斷斷續(xù)續(xù)地聽了《畫論》提要,張先生當(dāng)時(shí)住在西單,我去的比較少,所以,對于課堂的情況,我談不了多少。
但是,我跟張先生有點(diǎn)緣分,我在山東師范學(xué)院學(xué)習(xí)一年,在山東藝專學(xué)習(xí)四年。后來一個(gè)偶然的機(jī)會(huì),我又見到了張先生。我們班在1962年快畢業(yè)的時(shí)候,去泰山管理處臨摹天王殿壁畫時(shí)遇到了張先生。張安治先生當(dāng)時(shí)大概51歲,他帶劉炳森、杜鐵寶、張雪茹到泰安寫生。我印象中的張先生非常魁梧,相貌堂堂,很是英俊。當(dāng)時(shí)泰山管理處收藏了一些鄭板橋的竹子、書法以及一些中國畫,張先生就此給我們講了一次課。張先生白天寫生,我們也是跟著看和觀摩,也不臨摹壁畫了。那個(gè)時(shí)候生活條件不是太好,張先生住在泰山賓館,泰山管理處為了讓我們臨摹壁畫的師生吃好,搞了一些食物,劉炳森他們也跟著我們吃,當(dāng)時(shí)他們就說,將來到了北京的話,招待我們。到了1978年報(bào)考研究生的時(shí)候,我準(zhǔn)備報(bào)考張先生的研究生,就給張安治先生寫了一封信。那時(shí),我不太敢報(bào)考張先生的研究生,因?yàn)楸本┎佚埮P虎、人才輩出,所以就很矛盾,最后實(shí)在憋不住,我就給張先生寫了封信。我說,“提前祝賀你出山”并寫上了我的名字和當(dāng)時(shí)的情況,結(jié)果在第三天就收到了張先生的回信,他讓我不要有顧慮,大膽報(bào)考,積極準(zhǔn)備。那可是一封關(guān)鍵的信,要沒有這封信我就不敢考,要是不考研究生也就沒有什么出路了。收到張先生的信后,我就想起了一次電視節(jié)目里所說的話:第一要有專業(yè)基礎(chǔ),要有天分;第二,要有貴人提攜。我這一輩子要感謝的貴人就是張先生,是他改變了我的命運(yùn)。
師生如父子,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張先生1990年去世的時(shí)候,我磕了三個(gè)頭,有人還拉了我一下,別人都是鞠躬,我沒有辦法表達(dá)對老師的感情,所以就磕了頭。
我今天看了張先生的藝術(shù)展,作為張先生的老學(xué)生,我感謝安副館長以及徐沛君主任、鄧鋒先生能給我的恩師舉辦這么大規(guī)模的一個(gè)展覽。張先生本身也是中國美術(shù)史專家,他早期跟著徐悲鴻先生學(xué)習(xí)藝術(shù)。我剛才看到張先生的油畫、水彩和素描作品,他的作品和徐悲鴻先生的作品相比,簡直可以亂真了。另外,他在中國畫、詩詞、書法、美學(xué)諸領(lǐng)域造詣都很全面。如果沒有這個(gè)展覽,大家(尤其是廣大的觀眾)對張先生就不可能有深入的了解。他不只是一個(gè)畫家,更是一個(gè)大藝術(shù)家、大文學(xué)家、大詩人,我對有這么一個(gè)老師感到無比的光榮,我對受教于張先生感到非常的榮幸。在先生面前我太渺小了、太沒有作為了,現(xiàn)在已經(jīng)悔之晚矣,因?yàn)槟芰τ邢蕖?/p>
看了這個(gè)展覽之后,凡是搞藝術(shù)的人都會(huì)受到很大的教育,什么叫做水平,什么叫做藝術(shù)的高峰,什么叫做藝術(shù)的修養(yǎng)?張安治先生的素描跟徐悲鴻先生毫無二致,幾乎能夠亂真,張先生的筆法特別神似。藝術(shù)能夠到達(dá)到這個(gè)程度,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另外,徐悲鴻先生在抗戰(zhàn)時(shí),張安治先生、劉汝醴先生是徐悲鴻先生的左膀右臂,徐悲鴻先生走到哪兒,張先生就跟在哪兒,他不簡簡單單是助教,徐悲鴻先生的藝術(shù)和生活都由張先生來協(xié)助料理,徐悲鴻先生有苦惱時(shí)也跟他說。張安治先生的朋友很多都在南方,張先生到了南方以后比北方游刃有余,他的南方老朋友特別多。
中國美術(shù)史不僅僅體現(xiàn)在畫上,還體現(xiàn)在人們的心中和社會(huì)生活當(dāng)中,張先生方方面面的成就可以說是體現(xiàn)在藝術(shù)夢中,張先生的藝術(shù)夢是一個(gè)大的夢想,我希望我們每個(gè)搞藝術(shù)的人都能從這個(gè)展覽中得到啟迪。
張晨先生在張先生去世之后籌辦了張安治美術(shù)獎(jiǎng)學(xué)金,這件事很有意義。張晨先生一個(gè)人做了很多事情。張晨的能力還沒有全部被大家認(rèn)識(shí),通過這個(gè)展覽我們可以深入思考這個(gè)問題。
安遠(yuǎn)遠(yuǎn):劉龍庭先生作為親歷者,其感情很真摯,雖然沒有講得很多,但是非常生動(dòng)。張安治先生確實(shí)具有中國古典君子的修養(yǎng),琴棋書畫他都會(huì),他還有現(xiàn)代藝術(shù)教育和身體力行參與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的實(shí)踐行為。另外,他還曾是南京籃球隊(duì)的主力隊(duì)員,參加過全國比賽,他英俊瀟灑、才華橫溢、風(fēng)流倜儻,在很多領(lǐng)域都很出色,這才是中國文化最根本、最精深的一個(gè)特點(diǎn)。
今天上午,吳為山館長特別向張安治的子女頒發(fā)了捐贈(zèng)證書,表達(dá)了中國美術(shù)館對張安治家屬的感謝。通過一個(gè)展覽,我們可以看到一個(gè)人和一個(gè)時(shí)代,這是我們特別要關(guān)注張安治先生的一個(gè)重要原因。我們今天在研討的時(shí)候,也是基于這樣的一個(gè)主題,張安治先生以多面的才華和成就給我們呈現(xiàn)了他個(gè)人在那個(gè)時(shí)代的奮斗過程。下面,我們請李維琨先生來發(fā)言,因?yàn)樗呛笃诟S張安治先生的唯一一位博士生。
李維琨:張先生是文化部批準(zhǔn)的第一批美術(shù)界四位博士生導(dǎo)師之一,這四位博士生導(dǎo)師包括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美術(shù)研究所的王朝聞先生和溫廷寬先生、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的金維諾先生和張安治先生。張先生的博導(dǎo)任職資格在1987年的時(shí)候就作為正式文件下達(dá)。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美術(shù)研究所的兩位導(dǎo)師比較快地就招到了博士研究生,就是鄧福星先生那一批博士研究生。但是,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的兩位博導(dǎo)可能要求比較高,所以一直遲遲沒有招到他們感到滿意的博士研究生。
當(dāng)時(shí)還蠻有趣的,兩位研究中國美術(shù)史的博導(dǎo)找到兩位西洋美術(shù)史專業(yè)的碩士畢業(yè)生,希望我們改行。我和師兄羅世平當(dāng)時(shí)都是學(xué)西洋美術(shù)史的碩士畢業(yè)生,面臨著繼續(xù)升學(xué)和繼續(xù)工作的情況,后來就在這么一種情形之下轉(zhuǎn)行了。老羅跟了金先生,我跟了張先生。說老實(shí)話,在報(bào)考博士研究生之前我對自己的導(dǎo)師知之甚少,不太了解,因?qū)I(yè)不對口,原來關(guān)心的都是西洋美術(shù)史,一下子轉(zhuǎn)過來,就感覺步伐蠻大。張先生第一次跟我本人面對面談話時(shí)是在他家里,他讓我還是要加強(qiáng)基礎(chǔ)知識(shí)學(xué)習(xí),要多讀書,盡快地在讀書中找到自己所感興趣的問題,然后展開研究。在三年的學(xué)習(xí)時(shí)間里,我在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上課的機(jī)會(huì)是不多的,實(shí)際上的耳提面命也很有限,畢竟張先生已經(jīng)七十多歲了,本科生、研究生的一些大課基本上都停了,我們上畫論課時(shí)也是到先生府上學(xué)習(xí)。雖然課不太多,但是總體和系統(tǒng)的學(xué)習(xí),先生早期所發(fā)表和出版的東西確實(shí)非常驚人。今天我們的展覽里面有相當(dāng)一部分內(nèi)容反映了他在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在中國美術(shù)史方面的個(gè)案以及專題研究。
先生越到給我們上課時(shí),他思考的問題越細(xì),其比較重要的內(nèi)容就是對于中國畫論的系統(tǒng)研究。張先生在前人的基礎(chǔ)上,在自己的著述中對中國文人畫史的基本特征做出了非常好的闡釋和發(fā)揮。比較可貴的是,先生不是一個(gè)書齋學(xué)者,非常關(guān)心整個(gè)文化界的一些情形,比如說西洋的油畫到了中國后如何發(fā)展等,先生對這些都有比較獨(dú)特而精到的見解。
我看了這個(gè)展覽后很驚訝,中國美術(shù)館的朋友們確實(shí)做了非常好的工作,這個(gè)展覽不是純粹局限在他的書畫方面,而是通過不同的展陳方式將張先生的西洋畫、中國畫和許多相關(guān)的文獻(xiàn)、手稿、草圖加以展示,特別是在一些作品成品和草圖之間予以了對照展示。上海博物館做展覽的一些朋友看完展覽后說對自己有很多啟示。通過這樣一種并置陳放布展方式,觀者對原來的文本會(huì)升發(fā)出新的見解和想法。
我們以前通過很多文字已經(jīng)了解了張先生,但是我們看完美術(shù)館展覽的這些作品后,效果會(huì)大有不同,這些作品要比文字的含量和內(nèi)涵多很多,非常精彩。
張先生自己收藏了一件古代作品——閔貞的《醉酒圖》,策展者也動(dòng)了腦筋,把閔貞的這件揚(yáng)州畫派作品和張先生在1946年臨摹學(xué)習(xí)的作品并置在一起,非常好,張先生在這件作品中的題跋給了我們非常重要的啟示。這件作品也不是他自己的收藏,是他舅舅轉(zhuǎn)給他的。他1946年臨摹這件作品并寫題跋的時(shí)候,舅舅已經(jīng)去世。通過繪畫所傳遞給我們的信息遠(yuǎn)遠(yuǎn)大于我們通過文字所了解的內(nèi)容。諸如此類的還有很多出版物、非常珍貴的手稿以及用鋼筆寫的格子字。文獻(xiàn)確實(shí)是近年來展覽中越來越為大家所吸取的一種形式,深刻了解一個(gè)人(不管他是文學(xué)家、大畫家,還是大書法家),只有通過多個(gè)領(lǐng)域,才能夠更完整地看到一個(gè)人之所以為人,一個(gè)藝術(shù)家之所以為藝術(shù)家,一個(gè)學(xué)者之所以為學(xué)者所包含的所有素養(yǎng)——這才是一個(gè)人的全部。
我寫過一篇回憶老師的文章,就是關(guān)于一個(gè)學(xué)者、一個(gè)藝術(shù)家的素質(zhì)問題,我覺得這個(gè)展覽充分體現(xiàn)出張先生本人多方面的素養(yǎng),這種素養(yǎng)是由他自己所經(jīng)歷的時(shí)代而鍛造出來的。那個(gè)時(shí)代過去以后,再出這樣的人不可能,因?yàn)槲覀儾皇悄莻€(gè)時(shí)代的人,但向那個(gè)時(shí)代著名的人物學(xué)習(xí)什么以及如何來學(xué)?這個(gè)我們可以做到。作為弟子,我覺得我所做的工作非常慚愧,我本身的基本素養(yǎng)、水準(zhǔn)和見識(shí)遠(yuǎn)遠(yuǎn)不能夠和老師那一輩人相比。但是,我們還是可以通過他的經(jīng)歷和展覽了解其所思、所想、所行、所言,從中可以看出他待人接物以及對待學(xué)術(shù)、藝術(shù)的境界,他在這條道路上所做出的成就,我們可以學(xué)習(xí)一輩子。
這個(gè)展覽在某些方面做得還是不夠。今年6月,我參加華東師范大學(xué)藝術(shù)教育專業(yè)的博士論文答辯,有一個(gè)博士研究生的學(xué)位論文寫的是抗戰(zhàn)時(shí)期的中國美術(shù)教育,非常專業(yè),他找到了很多張先生當(dāng)時(shí)在廣西辦訓(xùn)練班的教材、講義和教學(xué)大綱。在抗戰(zhàn)的大背景之下,先生作大畫或者創(chuàng)作巨幅作品都很難完成,但是,張先生在向全民族來傳播我們的藝術(shù)之美以及培養(yǎng)美術(shù)教師方面做了非常多的貢獻(xiàn)。張先生的人緣在南方要?jiǎng)龠^北方,他在南京、桂林等地有非常多的學(xué)生。我今天感慨很多,暫時(shí)先講這些,謝謝大家。
安遠(yuǎn)遠(yuǎn):張先生確實(shí)是一個(gè)多面手,他的人緣特別廣。我記得我還是本科生的時(shí)候,特別喜歡到畫室串門,我跟張先生在42教室門口聊過天。我在寫畢業(yè)論文的時(shí)候還請教過他。我從小接觸到特別多的青銅器,所以就開始研究青銅器。在這個(gè)研究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玉器在中國文化精神里更有代表性和精神性。我在這方面還跟張先生交流過。“君子比德以玉”,那個(gè)時(shí)候我就覺得此話用到張安治先生身上特別貼切,他雖然外表溫文爾雅,但是,他的內(nèi)心激情澎湃,對社會(huì)的責(zé)任感特別強(qiáng)烈,這在他的作品里面我們都能感受到。但是,他還是非常克制,他在用筆、用墨處理畫面的時(shí)候很有節(jié)制。這樣的人文情懷和經(jīng)歷也許陳履生先生能給我們解讀和闡釋得更好,下面有請陳副館長發(fā)言。
陳履生:我對上面兩位學(xué)兄的發(fā)言感慨良多,非常羨慕他們一生中能有張安治先生這樣的老師。確實(shí),我認(rèn)為在這樣老師的輔導(dǎo)下成長是非常榮幸的。我在展廳里面看到一張照片,是張安治先生于1984年在南京舉辦展覽和我的導(dǎo)師劉汝醴先生的合影照片。因此,剛才龍庭兄說劉汝醴先生和張安治先生是徐悲鴻先生的左膀右臂非常有道理,我非常有幸成為劉汝醴先生的研究生。
我在劉汝醴先生身邊學(xué)習(xí)了三年之后,即將到北京工作之際,我記得非常清楚,在劉汝醴先生家里,他就跟我講,你到北京之后要好好向張安治先生學(xué)習(xí),多請教。雖然我沒有太多請教的機(jī)會(huì),但是我后來有幸跟張先生的公子張晨先生成為同事,所以從他那里偷學(xué)了一些東西。
我還要回到那張照片上來說一下。張安治先生當(dāng)時(shí)穿了毛氏的中山裝,我的幾位南京老師都是西裝革履打著領(lǐng)帶,這幾位老師有謝海燕教授、陳大羽教授和劉汝醴教授。我們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這三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對于張安治先生的友情是超于一般的,從他們的衣服和著裝上就能說明三位先生對張安治先生的尊敬,這個(gè)合影里面還有幾位徐悲鴻先生的學(xué)生,當(dāng)他們處在這樣一個(gè)特殊的氛圍之中時(shí),我就感受到他們好像又回到了徐悲鴻先生身邊一樣。
另外,我非常榮幸成為“張安治教授美術(shù)史獎(jiǎng)學(xué)金”的首屆獲得者。張安治教授的獎(jiǎng)學(xué)金在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設(shè)立之后,經(jīng)過審核,我成為首屆獎(jiǎng)學(xué)金的獲得者,我一直以此為榮,因?yàn)樵诿佬g(shù)史專業(yè)還不是很發(fā)達(dá)的年代,張晨兄能夠捐出獎(jiǎng)學(xué)金來弘揚(yáng)張安治先生的藝術(shù)與學(xué)術(shù),推動(dòng)中國美術(shù)史的研究和教學(xué),這對于中國美術(shù)史論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貢獻(xiàn)。我想,并不在于是因?yàn)槲业玫搅霜?jiǎng)學(xué)金,或者是其他人得到了獎(jiǎng)學(xué)金,這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一種社會(huì)風(fēng)氣,是一種方向,使得后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投入到美術(shù)史的研究中,以至于美術(shù)史學(xué)科成為好多院校中非常熱門的專業(yè)。由此我想到了1978年,今年正好是我們?nèi)雽W(xué)40周年,謝海燕教授在1978年開學(xué)典禮上作報(bào)告時(shí),就講到現(xiàn)在的敦煌在中國,敦煌研究在國外。1978年時(shí),全國院校中的美術(shù)史論老師加到一起不足40人,那個(gè)時(shí)候是非常的少。我聽了謝海燕教授的報(bào)告之后,決定轉(zhuǎn)向美術(shù)史論的研究,這些老師和前輩的指引,有時(shí)候是一句話,有時(shí)候是稍微點(diǎn)撥一下,但可能都會(huì)產(chǎn)生很大的影響,這是我今天要講的開場白。
我今天看了這個(gè)展覽之后,確實(shí)對策展人鄧鋒深表敬意。因?yàn)槲铱催^他們策劃的很多展覽,我認(rèn)為這個(gè)展覽策劃得最好,或許是基于個(gè)人感情的原因,鄧鋒花了很多的心力,使這個(gè)展覽整體的策劃思路非常明晰,運(yùn)用的手法非常多樣,在布展上非常下功夫,使得這個(gè)展覽呈現(xiàn)出了一個(gè)關(guān)于張安治先生個(gè)案研究的完整風(fēng)貌,讓我們了解到張安治先生的方方面面,了解到過去我們所不知道的張安治先生。這個(gè)展覽的多方面呈現(xiàn)方式以及在個(gè)案研究方面所下的心力,突破了一般性展覽的慣例。當(dāng)然這里面應(yīng)該得益于張晨兄及其家屬對于這個(gè)展覽提供的很多資料,包括維琨兄說的那件閔貞的《醉酒圖》和張安治先生臨摹的那件作品。這些都說明張安治先生對繪畫方面的認(rèn)真態(tài)度以及他當(dāng)時(shí)為什么要臨摹這件作品,這些問題都非常值得研究。
這個(gè)展覽呈現(xiàn)出一個(gè)多才多藝的張安治先生,而且,只有在這個(gè)展廳中完整呈現(xiàn)張安治先生的時(shí)候,我們才能夠感受到其中的精彩,感受到那個(gè)時(shí)代的氛圍,感受到他作為徐悲鴻水墨畫派重要的捍衛(wèi)者和傳承人在臨摹方面所作的種種努力,這里面有很多個(gè)案值得進(jìn)一步研究。
從整體上來看,張安治先生藝術(shù)的發(fā)展經(jīng)歷了多個(gè)時(shí)期,在每一個(gè)時(shí)期中,我們都能看到他關(guān)注身邊生活,從生活入手去發(fā)現(xiàn)、研究身邊很多的內(nèi)容,包括他早期的那幅油畫《漁民》,這就是在江南地區(qū)農(nóng)村里經(jīng)常看到的打漁景象,類似這樣題材的作品,他畫了很多,而且這種畫法以及這種藝術(shù)的態(tài)度正反映了民國時(shí)期——實(shí)際上是40年代中國畫壇整體的走向,那就是用自己的藝術(shù)表現(xiàn)自己的人生,表現(xiàn)家國的災(zāi)難等等。因此,新中國成立之后,張安治先生也和同時(shí)期的很多畫家一樣,努力去適應(yīng)新的時(shí)代,他畫了很多新的作品和新的題材,比如說我們看到的都江堰工地寫生,還有1964年畫的井岡山,還有1965年畫的《賀核試驗(yàn)成功》。通過一系列的作品,我們發(fā)現(xiàn)一個(gè)問題,即為什么張安治先生1949年以后的作品非常努力融入到新中國的體系之中?新中國成立后,并不是每一位畫家都能夠得到機(jī)遇和新時(shí)代的厚愛,今天來看張安治教授和同時(shí)期的任何一件作品,我們可以看出他恪守了徐悲鴻的水墨體系,放棄了時(shí)代所要求的裝飾性內(nèi)容,在他不改變自己以及時(shí)代不能改變他的情況下,他只能被時(shí)代邊緣化。所以,他畫了很多革命圣地題材的作品,包括和傅抱石一起在江西創(chuàng)作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他這個(gè)時(shí)代的作品缺少時(shí)代裝飾要求,但當(dāng)他仍然不能為時(shí)代所接受的時(shí)候,張安治先生沒有放棄,他仍然去努力創(chuàng)作,正如他畫都江堰的作品那樣,他仍然和民國時(shí)期的畫法一樣,非常散亂地畫一些人物,并不是非常有組織和非常有時(shí)代感。所以在這個(gè)特殊時(shí)期之內(nèi),不管是革命圣地題材還是建設(shè)題材,他都沒有得到重視,這使得他的水墨畫在新中國被邊緣化,當(dāng)然這對于他來說并不是很重要,因?yàn)樗牟拍茉诙喾矫娴玫搅吮憩F(xiàn)。因此,他在美術(shù)史論學(xué)科的建樹可以填補(bǔ)歷史空間,在這個(gè)空間的填補(bǔ)過程中,張安治先生非常努力地研究了很多美術(shù)史問題,這也使他成為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第一批博士生導(dǎo)師,培養(yǎng)出了薛永年、劉龍庭這樣一批美術(shù)史家,我想這是他的歷史性貢獻(xiàn)。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這次展覽中很難得的幾張粉畫。對于粉畫,現(xiàn)在包括專業(yè)人都不是太了解,但像張安治先生、劉汝醴先生那一代畫家,都用粉畫去創(chuàng)作作品。我記得80年代初期的時(shí)候,我在南京看過我導(dǎo)師策劃的一個(gè)全國粉畫展,作為愛好粉畫的小眾人群,用粉筆表現(xiàn)細(xì)膩的色彩變化以及造型中若干的趣味,我在這次展覽的幾件粉畫作品中看到了很親切的筆法。在越來越成為一種歷史稀缺的當(dāng)下,粉畫的失傳以及張安治先生這樣一位值得尊敬的藝術(shù)家的為人為藝方法在今天都成為稀缺的時(shí)候,這個(gè)展覽更成為我們今天所有藝術(shù)家都值得去觀摩、學(xué)習(xí)的一個(gè)人生榜樣。
正因?yàn)榇耍弦惠吽囆g(shù)家對我們的影響正成為今天努力的方向。因此,我認(rèn)為這個(gè)展覽非常重要。我們剛剛也翻了畫冊,里面有很多的史料成為我們今天研究20世紀(jì)美術(shù)史重要的補(bǔ)充。客觀來說,隨著個(gè)案研究越來越深入,20世紀(jì)中國美術(shù)史的研究也越來越深入,也越來越讓人看到一種發(fā)展前景。我也特別感謝鄧鋒和張晨兄。和其他名家后代有所不同,張晨兄幾十年來不遺余力在學(xué)術(shù)角度上梳理他父親多方面的資料,使得我們看到完整的發(fā)展脈絡(luò),在這方面我覺得張晨兄值得大家尊敬,謝謝。
安遠(yuǎn)遠(yuǎn):謝謝陳履生先生從多方面對張安治先生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考和角度,也對20世紀(jì)美術(shù)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佐證。下面我們先請邵彥教授來談一談。
邵彥:謝謝安館長。我今天有幸來參加這個(gè)研討會(huì),因?yàn)橐灿袃芍厣矸荨N业牡谝恢厣矸菔菑埌仓蜗壬脑賯鞯茏樱胰雽W(xué)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讀研究生時(shí),招生制度是教研組集體指導(dǎo),薄松年先生、薛永年先生、尹吉男先生指導(dǎo)過我,最后論文是在薛先生和尹先生的指導(dǎo)下完成的,后來又跟薛先生讀了博士。我到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是1993年,雖沒有接受過張安治的親臨教誨,但我現(xiàn)在體會(huì)到薛先生在教學(xué)中很注意把張安治先生的治學(xué)思想和方法傳授給我們;另外一重身份是1995年(我還是碩士研究生的時(shí)候)也獲得了張安治獎(jiǎng)學(xué)金。陳履生先生是作為學(xué)者獲得的張安治獎(jiǎng)學(xué)金,我是作為在讀研究生獲得的張安治獎(jiǎng)學(xué)金,這個(gè)獎(jiǎng)學(xué)金對研究生也有獎(jiǎng)助制度。我現(xiàn)在做這個(gè)行業(yè)也已經(jīng)幾十年了,人到中年,也不可能再改行了,也說不上有什么教學(xué)和科研的成績,但是一路走下來,我覺得這兩重身份對我的學(xué)術(shù)發(fā)展都具有非常深遠(yuǎn)的影響。
先說作為張先生的再傳弟子這一方面。薛先生在教學(xué)當(dāng)中就很注意把張安治先生的兩個(gè)特點(diǎn)告訴我們,并讓我們傳承下去。一個(gè)是史論結(jié)合,不但要研究藝術(shù)史,也要研究古代的藝術(shù)理論。張先生早期帶過的碩士研究生遠(yuǎn)小近先生后來幾十年在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教授《中國古代畫論和藝術(shù)理論》課程。在指導(dǎo)我們這些偏重于藝術(shù)史個(gè)案研究的學(xué)生中,薛先生也是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對藝術(shù)理論要重視,不只是研究古代的藝術(shù)理論,你自己在自學(xué)中也要不斷地加強(qiáng)理論修養(yǎng),史論不分家,而且強(qiáng)調(diào)論從史出,不要以論帶史。這種教誨對我后來學(xué)術(shù)方向的取向和研究影響非常深遠(yuǎn);第二點(diǎn),薛先生強(qiáng)調(diào)過很多次,藝術(shù)史論家要有一些實(shí)踐動(dòng)手的經(jīng)歷和能力。不是為了把自己變成一個(gè)藝術(shù)創(chuàng)作者,但是,你一定要有實(shí)踐動(dòng)手的經(jīng)驗(yàn)和感覺,這樣在藝術(shù)史論研究上才能不說外行話。這一點(diǎn)也是從張安治先生那里傳承下來的一個(gè)非常優(yōu)秀的傳統(tǒng)。
我們回溯新中國藝術(shù)史論學(xué)科建設(shè)時(shí)不能回避的是,第一個(gè)美術(shù)史論系建在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第二個(gè)建在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中國一開始就把史論系放在美術(shù)學(xué)院,這和西方把藝術(shù)史學(xué)科放在綜合性大學(xué),和考古系、建筑系并置于一起的傳統(tǒng)非常不一樣。這樣一種傳統(tǒng)的建立,看起來雖是有當(dāng)時(shí)人事方面的偶然性,但是,現(xiàn)在有了一定的歷史距離時(shí)回頭來看也不偶然。因?yàn)橐詮埌仓蜗壬鸀榇淼睦弦惠吽囆g(shù)史家都有非常深厚的創(chuàng)作功底,可以說是一身兼二任,既是非常出色的藝術(shù)家,也是非常專精的史論家。我們在國外的同行身上是看不到這個(gè)特點(diǎn)的,國外的藝術(shù)史家是一種人文學(xué)者,不是藝術(shù)家。雖然有的綜合性大學(xué)里面也會(huì)涉及到藝術(shù)創(chuàng)作專業(yè),但是人文學(xué)者和藝術(shù)家是完全分開的。中國自古以來(包括民國時(shí)期)的知識(shí)傳統(tǒng)是人文學(xué)者和藝術(shù)家不分家,這奠定了我們現(xiàn)在的學(xué)科面貌。我的本科是在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讀的,我讀本科的時(shí)候,浙江美術(shù)學(xué)院史論學(xué)科的帶頭人當(dāng)時(shí)還是王伯敏先生,現(xiàn)在是范景中先生,我在那兒讀書時(shí),范先生因病沒有在一線工作。王伯敏先生也具有這樣一個(gè)特點(diǎn)——藝術(shù)家兼史論家,也兼詩人。王先生和張先生很像,既有共同的特點(diǎn),也有很大的差別,王先生是傳統(tǒng)的書法家,所以,王先生做中國書畫史很自然,他搞的創(chuàng)作也是傳統(tǒng)書畫,后來我了解到王先生并不傳統(tǒng),他的學(xué)術(shù)視野和方法架構(gòu)很前沿。張安治先生是一個(gè)很深入的西畫學(xué)者和實(shí)踐者,但為什么后來慢慢又回到中國傳統(tǒng)書畫研究并為文人畫辯護(hù)?因?yàn)槲覀冎溃瑢π毂櫹壬缒暧绊憳O深的康有為最早提出了對中國傳統(tǒng)文人畫的批判。后來張先生在英國的時(shí)候,徐悲鴻又跟幾位傳統(tǒng)書畫教授有過一次關(guān)于中國書畫史的爭鳴,徐悲鴻還和徐志摩有過論爭,徐先生的觀念對于張先生會(huì)有一些影響。為什么在徐先生去世以后,張先生就慢慢轉(zhuǎn)向?qū)ξ娜水嫷难芯坎槲娜水嫷牡匚贿M(jìn)行呼吁?我現(xiàn)在的體會(huì)是張先生有非常寬闊的國際視野。他是在抗戰(zhàn)之后、解放前以及在改革開放初期比較早地到國外訪學(xué)、講學(xué)的一位學(xué)者,而且,他的出國不像我們現(xiàn)在這樣出國半年或一年,他是住下來,語言過關(guān),在當(dāng)?shù)赝度虢虒W(xué)、科研工作,也辦畫展,對于國外的藝術(shù)體系運(yùn)作、包括國外當(dāng)代畫家動(dòng)態(tài)、國外收藏資料的了解和思考是非常深入的,我想這個(gè)經(jīng)歷是張先生后來最終肯定中國傳統(tǒng)繪畫(尤其是文人畫)的重要原因。這具有獨(dú)特的價(jià)值,其影響非常深遠(yuǎn)。
他不是一個(gè)喜歡爭論的人,之前康有為關(guān)于中國繪畫價(jià)值論爭以及徐先生參加過的兩次論爭,他都沒有參與。到80年代中期,李小山還有一次非常有名的對于中國畫價(jià)值和前途再次質(zhì)疑,這幾次張先生都沒有發(fā)聲,他沒有參與很熱鬧的論爭,其實(shí)他用行動(dòng)表明了態(tài)度。中年以后,他把越來越多的精力投入到中國傳統(tǒng)繪畫的研究當(dāng)中,他的寫作確實(shí)在傳統(tǒng)史論和學(xué)科架構(gòu)問題上做出了貢獻(xiàn)。他傾注大量的心力培養(yǎng)學(xué)生,要把史論的血脈傳下去,后來,他確實(shí)通過史論方面的教學(xué)和著作使得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在傳統(tǒng)繪畫史研究上至今在國內(nèi)乃至全世界也是第一流的水平,這都依賴于從張先生那里傳下來的血脈。他對于傳統(tǒng)繪畫和文人畫所做的工作遠(yuǎn)遠(yuǎn)超過了簡單地參加論爭或撰寫兩篇文章。所以,張先生留學(xué)和訪學(xué)的經(jīng)歷對于他最后做出學(xué)術(shù)選擇的影響是非常深遠(yuǎn)的。隨著對他的作品和著述的閱讀理解以及我自己人生閱歷、學(xué)術(shù)經(jīng)歷的積累,我現(xiàn)在形成了這樣一個(gè)認(rèn)識(shí),可能不太成熟,請大家指正。
我的另外一重身份是首屆張安治獎(jiǎng)學(xué)金的獲得者。當(dāng)時(shí)美術(shù)史學(xué)科還是非常冷門,研究條件也很差,我們看不到多少繪畫原作。大概是1994年的時(shí)候,故宮博物院西門建了一個(gè)書畫館,該館有沒有展覽要看運(yùn)氣,它斷斷續(xù)續(xù)辦過幾次展覽,差不多十年功夫好像有過四五次比較重要的展覽。真正的轉(zhuǎn)機(jī)出現(xiàn)于2008年,為了喜迎奧運(yùn)會(huì),故宮武英殿開始有固定的中國書畫通史陳列。2008年時(shí),中國美術(shù)館也把館藏的歷代繪畫拿出來作展覽。從那兒以后,就有比較多的原作展出,整個(gè)國家的條件都不一樣了,較多原作展出對研究條件和研究風(fēng)氣有非常大的影響。在這之前十多年,我覺得是比較難熬的,因?yàn)榭床坏蕉嗌僭鳎菚r(shí)出版條件也不如現(xiàn)在。1995年獲得張安治獎(jiǎng)學(xué)金的經(jīng)歷對于我把藝術(shù)史論這一最初的選擇堅(jiān)持下來以及把科研工作、教學(xué)工作做下去,是一個(gè)非常大的支持。雖然這是很早年的一件事情,錢不是特別多,但是,這種心靈上的支持和溫暖對我持久地產(chǎn)生作用。我現(xiàn)在自己也帶學(xué)生,有時(shí)候也蠻心灰意冷,因?yàn)槲野l(fā)現(xiàn)畢業(yè)生的轉(zhuǎn)行率非常高,轉(zhuǎn)行是客觀條件所致,因?yàn)椴荒苷业綄I(yè)比較對口的工作,所以改行。但是,學(xué)生自己內(nèi)心的堅(jiān)持其實(shí)也很重要,不是每一個(gè)人都能做到,我算是蠻軟弱的人,當(dāng)時(shí)獎(jiǎng)學(xué)金支持我這么多年一直做下去,現(xiàn)在不能說做得多好,但是,也成了行業(yè)的中年骨干,這只是因?yàn)閳?jiān)持的年頭多,并不是因?yàn)槲宜礁摺.?dāng)時(shí)大家都說張安治獎(jiǎng)學(xué)金的設(shè)立體現(xiàn)了張先生的高風(fēng)亮節(jié),因?yàn)閺埌仓渭覍僖彩亲隽艘患浅3绺叩氖虑椤N蚁脒@對于一個(gè)受助者后來的學(xué)術(shù)之路來說,真是具有重要的后續(xù)影響,也許我很平庸,但是畢竟堅(jiān)持下來了,這是張安治獎(jiǎng)學(xué)金起到的長久作用。我就說這些,謝謝。
安遠(yuǎn)遠(yuǎn):謝謝,滴水之恩當(dāng)涌泉相報(bào),因?yàn)橛幸粋€(gè)前輩的榜樣給你了巨大的支撐。邵彥現(xiàn)在也是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中國美術(shù)史專業(yè)的骨干。總之,在前仆后繼的道路上,一代又一代人的堅(jiān)持總會(huì)結(jié)出碩果。我們是比較幸運(yùn)的,我們當(dāng)年在北京時(shí),每逢故宮晾畫的時(shí)候,都可以看到原作,在這個(gè)過程中我們經(jīng)常去故宮上課,我跟華天雪是上下屆,我比她早一年。張安治先生于1973年還在故宮書畫組工作過一年。我想華天雪對中國書畫的理解和她親身的經(jīng)歷也是有關(guān)系的,下面我們請華天雪發(fā)言。
華天雪:前面幾位有學(xué)長、學(xué)姐、學(xué)妹,都跟張安治先生有各種各樣的關(guān)聯(lián),我沒有任何類似的經(jīng)歷。
安遠(yuǎn)遠(yuǎn):我們今天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的前半部分差不多都有關(guān)于張安治生平的回憶和關(guān)聯(lián)性的解讀,這有助于學(xué)術(shù)判斷。
華天雪:希望我們這種沒有類似經(jīng)歷的人說話不會(huì)太冒昧。我是第一次比較全地看張安治的畫展,在此之前我有一點(diǎn)準(zhǔn)備,所以就翻了一篇《藝為人生》的文章和《張安治美術(shù)文集》,今天我想從徐悲鴻學(xué)派的角度聊聊張安治先生。如果從張安治先生的作品出發(fā)考察徐悲鴻學(xué)派的話,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原本在學(xué)校里一直擔(dān)任西畫教授、曾經(jīng)主持過中大西畫組的徐悲鴻先生的教學(xué)中,中國畫占據(jù)了半壁江山,從他個(gè)人來說是這樣。張安治先生畫展中有一半中國畫作品,另一半是西畫作品,從整體上來講,所有的學(xué)生當(dāng)時(shí)也處在這樣的狀態(tài)。這個(gè)群體的中國畫作品絕對少有中規(guī)中矩、氣息很純正的傳統(tǒng)面貌,應(yīng)該是一種改良中國畫的面貌,而且他們的改良思路基本上可以統(tǒng)一地歸于徐悲鴻體系。我認(rèn)為將寫實(shí)造型植入到中國畫的方式落實(shí)到他們彼此之間的創(chuàng)作方法上沒有什么太大的差別。
張晨:那是早期,晚期就不是了。
華天雪:他們的差別其實(shí)主要體現(xiàn)在題材上,藝術(shù)水準(zhǔn)的高下主要取決于他們各自寫實(shí)造型能力的高低。這種趨同性同樣反映在他們的西畫創(chuàng)作方面。無論中國畫還是西畫的趨同性,說到底是由徐悲鴻的教學(xué)方式?jīng)Q定的。因?yàn)椋谛毂櫟慕虒W(xué)當(dāng)中通常就是通過一兩年的寫實(shí)造型訓(xùn)練,獲得得心應(yīng)手表現(xiàn)物象的基本能力之后,選擇怎樣的工具、材料乃至于創(chuàng)作什么作品,都沒有界限,就是要像,只要像就行。徐悲鴻歷來所痛恨的是通過《芥子園》和臨摹的方式學(xué)習(xí)中國畫的方式。他自己找到了可以替代這種方式的方式,主要就是寫生——即對著真東西來寫生,唯一看中的就是寫實(shí)能力。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一言以蔽之,師法造化而已”,沒有別的,就是無所謂中西。在徐悲鴻執(zhí)掌北平國立藝專之前,他的這套辦法并不體現(xiàn)在課程設(shè)置當(dāng)中,主要靠他自己的創(chuàng)作做出示范性的影響。張安治先生因?yàn)楦S徐先生太密切,所以才有這樣的影響,這種影響屬于身教加言教。有研究者在研究中大中國畫教學(xué)的時(shí)候,曾經(jīng)說徐悲鴻的這套模式在中大的中國畫教學(xué)當(dāng)中幾乎沒有發(fā)生過作用,中國畫教學(xué)從呂鳳子、汪采白到張書旂,之后到張大千、高劍父、傅抱石都處于很多元的狀態(tài),沒有哪種方法可以成為這個(gè)學(xué)校的統(tǒng)一方法,這是一個(gè)現(xiàn)實(shí)。當(dāng)徐悲鴻有了執(zhí)掌學(xué)校的權(quán)利之后,這個(gè)方法才在全學(xué)校得以實(shí)施,并覆蓋到任何一個(gè)系科,當(dāng)他正式地把這套教學(xué)方法納入到課程規(guī)定當(dāng)中去的時(shí)候,就出現(xiàn)了“三教授罷教事件”,我認(rèn)為這個(gè)沖突是必然現(xiàn)象。雖然說徐悲鴻學(xué)派的提出一直以來存在爭議,但如果從徐悲鴻的教學(xué)主張、教學(xué)方法使得整個(gè)創(chuàng)作的集體風(fēng)格與面貌趨同性角度來講,這個(gè)提法是可以成立的。徐悲鴻學(xué)派的本質(zhì)核心就是通過一到兩年寫實(shí)造型訓(xùn)練加兩三年分科學(xué)習(xí),從三年到四年制再到五年制來回地變,達(dá)到能夠自如地畫出客觀物象的程度之后,幾乎沒有畫科的界限,同時(shí)覆蓋了各科。徐悲鴻學(xué)派就是源自法國學(xué)派,法國學(xué)派對于西方各個(gè)系,無論是油畫還是雕刻、版畫,這套體系都是很適用的,唯獨(dú)對于中國畫是利弊參半,好處在于造型能力得到增強(qiáng),尤其為人物畫的發(fā)展提供了保障,使得題材的擴(kuò)展有了無限的可能性,什么都可以畫。弊端在于語言的獨(dú)特性遭到很大程度的損失。事實(shí)上就是憑借普遍造型水平比較好的這個(gè)能力,使得這個(gè)學(xué)派在民國時(shí)期的確在現(xiàn)實(shí)題材和人物畫方面有非常突出的表現(xiàn),有著比國內(nèi)任何私立美術(shù)學(xué)校和社團(tuán)群體更豐富的表現(xiàn)力,包括張安治先生在內(nèi)的很多學(xué)生在畢業(yè)創(chuàng)作或者畢業(yè)之后都有過現(xiàn)實(shí)主義追求,他們普遍對現(xiàn)實(shí)人生有比較敏銳的關(guān)注,具有迫切想去表達(dá)現(xiàn)實(shí)人生的熱情,這絕不是對意識(shí)形態(tài)的迎合,也不是對于政治圖解式的表達(dá),他們要體現(xiàn)所謂的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讓人覺得是一個(gè)很自覺的追求或者是一個(gè)更樸素的追求。但是在我們梳理曾經(jīng)有過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脈絡(luò)時(shí),始終忽略了徐悲鴻和徐悲鴻學(xué)派的整個(gè)成績,這是很遺憾的。
作為徐悲鴻學(xué)派很重要的一個(gè)代表性人物就是張安治先生。他在建國之后,對徐悲鴻學(xué)派的中國畫教學(xué)主張有相當(dāng)?shù)陌l(fā)展或者校正,我發(fā)現(xiàn)他在20世紀(jì)50年代后期到20世紀(jì)60年代前期不到10年的時(shí)間里面,對中國畫的筆法、墨法、透視法、空間觀、意境、形神問題等都分別撰寫過很專門的文章,說得很具體,而且都是行家的話,說得很到位,集中呈現(xiàn)了他這么多年來認(rèn)識(shí)上的一個(gè)變化——他多年來對于傳統(tǒng)予以了深入的思考和領(lǐng)會(huì),因?yàn)樗羞@樣的認(rèn)知基礎(chǔ)。張安治先生于1959年撰寫的名為《關(guān)于中國畫教學(xué)問題的一點(diǎn)體會(huì)》這篇文章尤其重要,這篇文章的寫就在那個(gè)時(shí)代肯定是師徒授受式的教學(xué)方法所致,肯定了以臨摹為主要學(xué)習(xí)手段的傳統(tǒng)技法訓(xùn)練方法,肯定了傳統(tǒng)技法訓(xùn)練中對形神較為本質(zhì)的理解以及對于表現(xiàn)神氣特征的重視,肯定了始建于畫理互相參證的學(xué)習(xí)方法等,該文認(rèn)為這些優(yōu)長都應(yīng)該結(jié)合到中國畫教學(xué)中,與源于西畫的教學(xué)法互相補(bǔ)充,這些建議在當(dāng)時(shí)很難被采納,但是即便跨越了整整一個(gè)甲子,在今天我認(rèn)為仍然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稱得上是真知灼見,這個(gè)觀點(diǎn)非常之超前,這樣的認(rèn)識(shí)跟徐悲鴻具有特別大的距離和跨越,但是我個(gè)人認(rèn)為即便是跟徐悲鴻有如此大的不同,但是這種發(fā)展和變化本身也應(yīng)該被當(dāng)作這個(gè)學(xué)派一個(gè)部分,這個(gè)學(xué)派不是固定不變的,它也是要靠這個(gè)學(xué)派當(dāng)中一代又一代人不斷地完善和發(fā)展。
最后我想提一個(gè)建議,我個(gè)人認(rèn)為缺少一個(gè)更詳盡的張安治年譜長編,我剛才給張晨先生發(fā)微信,就是前幾天翻報(bào)紙看到關(guān)于張安治辦畫展的消息。1934年,徐悲鴻從歐洲巡展剛回來,就參加了他和陸其清在南京民教館辦的展覽。我的意思就是說,對于南京、廣西還有重慶的各種報(bào)紙上的信息還需要再去挖掘,這么一個(gè)有如此豐富經(jīng)歷的人,他的意義不僅僅局限于家屬和個(gè)人,他對中國近現(xiàn)代美術(shù)史具有重要的意義。
安遠(yuǎn)遠(yuǎn):謝謝華天雪,她的研究非常專業(yè),而且提出來的問題也很有價(jià)值,對我們以后怎樣看待徐悲鴻學(xué)派里的人物以及學(xué)派的發(fā)展都有價(jià)值,對20世紀(jì)美術(shù)事業(yè)的發(fā)展也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下面我們請曹慶暉教授發(fā)言,曹慶暉教授是研究近現(xiàn)代美術(shù)史和近現(xiàn)代美術(shù)家的專家。
曹慶暉:我在上大學(xué)的時(shí)候跟張安治老師就見過一面,但是這件事總能想起來,為什么這件事印象特別深呢?那一次是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美術(shù)史系舉辦元旦活動(dòng)請來了張安治先生和許幸之先生。我知道這兩位先生,但從來沒有見過。張安治先生先進(jìn)來,許幸之老師后進(jìn)來,一進(jìn)來我們班所有的女生都爆發(fā)出尖叫聲!張安治先生長得特別帥,用今天的詞匯無法形容。那是第一次見到張先生,雖然不知道他當(dāng)時(shí)多大年紀(jì),但印象極深。張安治先生一頭銀發(fā),頭發(fā)很白,但腰板筆直。那次讓我知道什么是紳士風(fēng)度,我從來沒有這種感覺,他有那種紳士范,人的氣場帶著一種紳士范。
邵彥:那是因?yàn)閺埌仓蜗壬谟盍?年。
曹慶暉:張晨老師為了給張安治先生辦這個(gè)展覽做了很多工作,做了中大弟子的調(diào)查,每次取得的成果我們都有溝通。之前,我能夠看見的就是張晨老師編的兩本書。這兩本書當(dāng)中所提供的方方面面的信息量,讓我們覺得張安治老師是一個(gè)特別有厚度的人,不是所有的學(xué)生都有他的厚度,這里面有高有低。如果做張安治先生這一個(gè)案研究,你能夠通過張安治先生走入中國近現(xiàn)代美術(shù)史,因?yàn)樗婕暗拿鎸挕⒚娑唷⒚嫔睢=F(xiàn)代美術(shù)這一領(lǐng)域?qū)ρ芯空叩囊蠓浅8撸覀兏咀霾坏剑覀冎荒茏鲆恍\表的研究。
如果換成我做這個(gè)展覽,無非是梳理已有的關(guān)于張安治先生的材料,而這些材料張晨老師都會(huì)提供。但是張晨老師編的那兩本書是十幾年前,我可以非常公正地說,十幾年來厚度沒有“長”。我們今天通過家屬找各種各樣的材料、文獻(xiàn)相對來說比較方便,但是,你會(huì)看到這里面寫文章的仍是薛永年先生、郎紹君先生等,還是這些內(nèi)容。我們無非是把這些東西整合起來,以一種非常漂亮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而已,這還談得上研究嗎?這確實(shí)沒有長進(jìn)。但是你發(fā)現(xiàn),你要研究進(jìn)去你就別做展覽,因?yàn)檎褂[是有時(shí)間要求的,中國美術(shù)館不可能給你一年的時(shí)間去研究。因?yàn)槟阋怯虚L進(jìn)的話,真得把他那些從來沒有被人看過的寫得“亂七八糟”的手稿看一遍,你看一遍,才能把他那些閃光的東西或者是打動(dòng)人的東西摘出來,否則的話就是貌似很有研究,實(shí)則是粗暴拿來式的擺放。我個(gè)人在做展覽時(shí)面對的問題就在于此,家屬很熱情,但是,我們時(shí)間上的投入受制于美術(shù)館檔期的安排,它不給你這個(gè)時(shí)間。因?yàn)槲覀儾豢赡茉趲讉€(gè)月的時(shí)間當(dāng)中單獨(dú)干這一件事情,同時(shí)還有很多事要做。我們要把它們消化掉,這是一個(gè)很大的問題。借助于今天的這種電子化手段,圖像材料的消化相對來說比較快,但是對那些不是圖像的東西怎么消化呢?就憑我們這三斤半兩的水平,不太可能,把它讀一遍,讀順之后整理成電子文檔,就不錯(cuò)了,研究生干不了這個(gè)事情,這是一個(gè)很現(xiàn)實(shí)的問題。
其實(shí)能夠比較完整地呈現(xiàn)張安治先生的成果那都是十幾年前的了,我剛才翻了一下這本書,內(nèi)容差不多,編排結(jié)構(gòu)差不多,也就是在這十幾年的過程當(dāng)中,我們形成了一套怎么應(yīng)對畫家個(gè)案的一些經(jīng)驗(yàn),而且,這個(gè)經(jīng)驗(yàn)很容易程式化。我們也很容易拿這個(gè)東西來擋一擋,其實(shí)沒有太多的長進(jìn),這里面很多基礎(chǔ)的東西可以再討論,這些都沒有做得太深。
張晨:還是長進(jìn)了一點(diǎn),我加了點(diǎn)題跋的釋文、印章的釋文,還加了一篇比較重要的文章——薛先生給古代畫論寫的那篇序。另外,更改了年表里面發(fā)現(xiàn)的一些錯(cuò)誤。總之,比原來看的要稍微舒服一點(diǎn)。
曹慶暉:我剛才說的基本上是在做編輯工作,只能是這樣。深入地討論張安治先生必須在中國一個(gè)大的環(huán)境當(dāng)中進(jìn)行,而且這個(gè)環(huán)境離不開徐悲鴻學(xué)派。其實(shí)在這十幾年當(dāng)中,跟徐悲鴻有關(guān)系的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老師都紛紛做過展覽,比如吳作人、戴澤。要是把他們這些人的展覽通過高科技的手段并置在一起的話,你會(huì)發(fā)現(xiàn)這里面很有意思,為什么能夠成為一個(gè)學(xué)派?這里面確實(shí)有一個(gè)趨同現(xiàn)象,特別是早期,大家對此都有共識(shí)。
徐悲鴻學(xué)派比較顯性的邏輯就是關(guān)注民生問題。在整個(gè)20世紀(jì),關(guān)注民生問題對于徐悲鴻學(xué)派來說表現(xiàn)得比較耀眼,而且也比較自覺,他們在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的學(xué)生就能拿出像張安治的《群力》、宗其香的《嘉陵江上》這樣的大畫,時(shí)間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晚,它很早。我們今天看了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的作品為什么會(huì)比較吸引我們的目光,而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的作品基本上整個(gè)水平下降了呢?當(dāng)然,可以從不同的方面討論到底是什么樣的原因,或者水平是降了還是沒降?但是,從我自己來說,我還是覺得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的作品有意思。相對來說,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的作品沒有受到太多的束縛,那種民生關(guān)注直接落地;而建國以后對民生的關(guān)注有各種各樣的要求。在某種程度上,不能說是偽表達(dá),但意識(shí)形態(tài)太強(qiáng),不自然,他們拼命地想自然,但是沒有自我。我們觀看早年的作品,你發(fā)現(xiàn)像張安治和李斛這些人畫得也有蠻像的那種感覺,但是每個(gè)人有每個(gè)人的觀察視點(diǎn),他的早年作品里面具有樸素之美,而且早年關(guān)注民生的作品里面帶有一種自然的批判現(xiàn)實(shí)的東西,建國以后,批判現(xiàn)實(shí)主義就被扼殺了。到今天為止,主題性創(chuàng)作面對這個(gè)問題基本上是歌頌題材。
我比較注意從教學(xué)的層面討論問題,而且也寫過一些文章,教學(xué)層面的研究有一些很困難,你不要覺得你拿到了課程表、教案、材料就能說清楚,因?yàn)檫@些教案、材料、課表很雷同,這都是綱,綱的東西沒有什么太大的差異。對于如何畫速寫這樣的事情誰講都一樣。問題就是他怎么講?個(gè)體的經(jīng)驗(yàn)把握對于我們研究學(xué)派來說至關(guān)重要,但是特別難的一件事情,這是我們討論徐悲鴻教育學(xué)派時(shí)很難抓到的地方。
教學(xué)做展覽怎么做?我現(xiàn)在一直懷疑一個(gè)問題,展覽只是若干回答問題的方式之一,而且有可能是一個(gè)最簡單的方式。但是,今天又處在一個(gè)美術(shù)館蓬勃發(fā)展時(shí)期以及展覽、策展人不斷涌現(xiàn)的時(shí)間段。我們覺得好像展覽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其實(shí)展覽解決不了什么問題,展覽只是一個(gè)悅目形式。占據(jù)材料了,怎么解讀呢?如果我們今天換一個(gè)題目,作為教師的張安治來做展覽,這個(gè)怎么展呢?你會(huì)發(fā)現(xiàn)這個(gè)要求會(huì)更高,整個(gè)展覽的方式、空間都要變化。
另外,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從來不做這樣的工作,也沒有人做這樣的工作,這種工作我也做不了,那就是對于20世紀(jì)七八十年代來華的外籍留學(xué)生方面的情況,我們始終沒有掌握住,而且,對于這些來華留學(xué)生后來回國以后的一些情況,我們也是模棱兩可,除非他后來成為在美術(shù)史界或者創(chuàng)作實(shí)踐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我們可能關(guān)注一下。20世紀(jì)七八十年代,張安治老師培養(yǎng)的這些學(xué)生里面有日本人,也有美國人,如果說能夠在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會(huì)更好,換句話說它是相對國際化的課題,這個(gè)是要改變的地方,或者是以后能落實(shí)的地方。
安遠(yuǎn)遠(yuǎn):謝謝曹慶暉教授,他經(jīng)常提出一些非常尖銳和深刻的問題讓我們思考。我們現(xiàn)在做任何工作,都很有意義,我們美術(shù)館呈現(xiàn)的展覽雖然不夠深入,但我總希望通過這樣的一個(gè)展覽,讓更多的人能夠參與其中,也許在看展覽的過程中,就有產(chǎn)生做更深入挖掘的后來研究者,也期待著你給我們提供更多的研究資源。下面我們請鄧嘉德先生發(fā)言。
鄧嘉德:前面發(fā)言的各位都跟張安治先生多多少少有一些文墨的關(guān)系,我也挺羨慕。我今天能夠參加這個(gè)會(huì)議,是因?yàn)槲腋鷱埑客铝?4年,我在2004年調(diào)到中國畫院理論部跟張晨先生一塊工作,當(dāng)時(shí)陳履生是我的領(lǐng)導(dǎo)。我跟張晨老師接觸比較多,和他在一起的時(shí)候,我能感受到很多張安治先生留給張晨先生的優(yōu)秀品質(zhì)。
張安治先生給我的第一個(gè)印象是人長得玉樹臨風(fēng),中西繪畫都精通,書法也算得上是高手,詩詞歌賦、美術(shù)理論都很全面,是非常完美的一個(gè)人。
第一,張安治先生是20世紀(jì)中西繪畫兼學(xué)的一個(gè)典型代表。20世紀(jì)中國繪畫有兩個(gè)體系:一個(gè)是沿著國畫自身發(fā)展的體系;一個(gè)是中西繪畫兼學(xué)體系。張安治先生是中西繪畫兼學(xué)體系里面非常典型的人物,通過他我們可以提出來很多問題討論。所以說,中國美術(shù)館收藏張安治先生的作品是非常有價(jià)值的。
第二,書法在中國畫中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徐悲鴻是書法高手。我從張安治出版的這些東西以及平時(shí)張晨老師的言談之中,得知張安治先生一輩子都在研究書法。不管你怎么融合,你不能抹掉中西繪畫里面的界限、本質(zhì)。中國畫離不開線,將經(jīng)過書法訓(xùn)練的線條和對書法有一定造詣的線條用在繪畫之中,帶給你的氣質(zhì)、氣息是絕對不一樣的。這是張安治先生給我們后輩人的一個(gè)啟示。
第三,繪畫說到底是一種術(shù),它建立在術(shù)的基礎(chǔ)之上。如果畫家要止于一個(gè)術(shù),跟一個(gè)木匠、一個(gè)賣油翁或跟一個(gè)做任何手藝的人沒有區(qū)別。畫家之所以是畫家,他在術(shù)上、術(shù)外有很多的綜合修養(yǎng),這是一個(gè)藝術(shù)家必須具備的,藝術(shù)家除了應(yīng)具備很多畫外功夫之外,還應(yīng)該具有一定的品質(zhì),人品即畫品,就和這個(gè)展覽的名字“藝道尋真”一樣,繪畫是一個(gè)人最真實(shí)的心靈反映,大家都是內(nèi)行,你是騙不了人的。我通過這次展覽得到了這三點(diǎn)啟示。
現(xiàn)在加一點(diǎn),張晨先生為了整理他父親的資料,10多年以來付出了很大的心力,如果沒有張晨先生在背后做的大量工作,這個(gè)展覽無法舉辦。因?yàn)楹芏嗖牧先绻悴皇羌覍倌愀咀霾坏剑驗(yàn)槟銢]有這個(gè)條件,如果家屬不做,很多事情就被淹沒了。從這一點(diǎn)來說,張晨先生也是繼承了他父親非常優(yōu)秀的品質(zhì)。
安遠(yuǎn)遠(yuǎn):謝謝鄧嘉德先生的總結(jié),下面有請裔萼主任發(fā)言。
裔萼:接觸張安治先生的藝術(shù)作品之前,我一直以為他僅僅是一位美術(shù)史論家。的確,他的畫名、詩名長期被美術(shù)史家之名所掩。后來我在做20世紀(jì)中國人物畫研究時(shí),發(fā)現(xiàn)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張安治先生有一批特別突出的水墨人物畫作品,我認(rèn)為這批作品是張安治先生創(chuàng)作歷程中最為重要的作品。縱觀他一生的創(chuàng)作,他是位全才型的藝術(shù)家,涉獵多個(gè)畫種,包括中國畫、油畫、素描、水彩、水粉、版畫等,但是他著力最多的還是中國畫,我覺得他真正能夠進(jìn)入美術(shù)史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就是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的這批以《避難群》 《劫后孤女》《擔(dān)草婦》為代表的水墨人物畫作品。我在梳理這段歷史的時(shí)候,張安治先生就自然進(jìn)入了我的研究視野。作為徐悲鴻先生的學(xué)生,他實(shí)踐著徐悲鴻的寫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理念,無論是對現(xiàn)實(shí)表現(xiàn)的力度,還是對人物表現(xiàn)的深度,他的現(xiàn)實(shí)題材人物畫都比他的老師更為深入。張安治先生三四十年代的現(xiàn)實(shí)題材人物畫和李斛、宗其香先生同時(shí)期的作品一起書寫了寫實(shí)水墨人物畫開創(chuàng)時(shí)期的重要篇章,也在中國現(xiàn)代美術(shù)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頁。
我們特別感謝以張晨老師為代表的張安治先生家屬慷慨捐贈(zèng)給國家美術(shù)館50件藝術(shù)精品,這不僅給我們研究者提供了特別豐富的研究素材,也給觀眾提供了特別好的藝術(shù)享受。我認(rèn)識(shí)張晨老師很多年,他的淡泊平和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為人之誠懇與治學(xué)之嚴(yán)謹(jǐn)令人欽佩。通過張晨先生,我們也能夠追想張安治先生的謙謙君子之風(fēng)。
張晨:謝謝,我沒有那么高的境界,我是想讓展覽的效果好一些。
安遠(yuǎn)遠(yuǎn):感謝,下面有請徐沛君主任發(fā)言。
徐沛君:張安治先生無疑是一位很偉大的藝術(shù)家,他偉大之處首先在于他秉持“藝為人生”的理念。在他成長的年代,當(dāng)時(shí)的藝術(shù)家按取向來說可以分為三類:比如像吳昌碩這種類型的藝術(shù)家堅(jiān)持傳統(tǒng)道路,雖然也收學(xué)生,也賣畫,但這也是一種藝術(shù)人生的方式;再比如在延安魯藝,是用一種貼近土地、貼近最下層民眾的最樸實(shí)方式(比如說木刻)來傳達(dá)喚醒民眾的藝術(shù)理念;另外就是像張安治先生那樣,以一種“藝為人生”的方式來貫徹、實(shí)現(xiàn)自己的藝術(shù)理想。
張安治先生的作品區(qū)別于他人之處在于,它帶有一種很明顯的沙龍氣,他的格調(diào)非常高,有一種很高的追求,畫面里有一種對古典主義的向往,具有很特殊的氣質(zhì),他的水墨畫、油畫、水彩都是如此。他涉獵非常廣泛,一方面他想傳承傳統(tǒng)的薪火,另一方面也想把國外優(yōu)秀的文化引進(jìn)來,以促進(jìn)中國藝術(shù)的發(fā)展,這種全球性的眼光以及前瞻性的實(shí)踐成果在他所處的年代呈現(xiàn)得可能還不是很明顯,但在他之后就非常明顯了。
以徐悲鴻先生、張安治先生為代表的那一批藝術(shù)家開創(chuàng)了一種獨(dú)特的藝術(shù)教育之路,在解放之后這種藝術(shù)教育之路已經(jīng)是遍地開花,繼承最明顯的應(yīng)該是像南京師范大學(xué)這樣一些高校,要求學(xué)生對中國畫、油畫、版畫、雕塑乃至?xí)ā⑺囆g(shù)史都要懂一點(diǎn),雖然在藝術(shù)實(shí)踐上可能還不夠深入,但是一定要有全局性的視野。可能他們中沒有人能像吳昌碩那樣成為畫壇明星,但是整體修養(yǎng)很高。在我看來,最近有人把吳昌碩抬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如果按照我的劃分,吳昌碩應(yīng)該被劃分到傳統(tǒng)的藝學(xué),如果再極端一點(diǎn),應(yīng)叫“遺老遺少”,他是很偉大,但是沒有必要把他抬到這么高的一種地位。從這個(gè)角度來說,以張安治先生為代表的藝術(shù)家,在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的節(jié)點(diǎn)上起到了一個(gè)非常好的作用,是一位繼往開來的藝術(shù)家。
張安治先生雖然涉獵很廣泛,但藝術(shù)成就最高的仍然是他的水彩畫,水彩以水作為色彩的調(diào)和劑,和中國的水墨用水作為調(diào)和劑在物理層面上是一樣的,從藝術(shù)的格調(diào)來講,也有相通之處,但是,又有本質(zhì)上的不同,比如在構(gòu)圖、審美上就有不同之處。張安治的水彩畫面貌可能和張先生留學(xué)英國的經(jīng)歷有關(guān),因?yàn)橛撬十嫷墓枢l(xiāng)。張安治先生畫的水彩畫,不管是風(fēng)景,還是人物,都既有水的趣味,也有色彩的和諧關(guān)系,同時(shí)筆法簡潔、概括,非常傳神,這體現(xiàn)出他很高的藝術(shù)修養(yǎng)。再有一個(gè),有些風(fēng)景畫能把中國傳統(tǒng)山水畫的魅力和水彩畫的特色在有意、無意之間達(dá)成一種天成趣味,他對水的濃、淡、干、濕、枯、潤等把握得非常好,他的水彩成就非常高,值得我們深入的研究。
安遠(yuǎn)遠(yuǎn):謝謝徐沛君主任。每一個(gè)人都不能脫離時(shí)代,而且從一個(gè)時(shí)代往前看的時(shí)候,都會(huì)有時(shí)代的精神和時(shí)代的價(jià)值,剛才徐沛君說,要有全局觀,這個(gè)非常重要。下面有請美術(shù)館收藏部的王雪峰副主任發(fā)言。
王雪峰:我非常認(rèn)同曹慶暉老師對現(xiàn)在展覽的看法,現(xiàn)在每年都要在美術(shù)館里面舉辦很多展覽,展覽舉辦得也非常豐富,但是展覽辦完之后,對于展覽中的一些知識(shí)生成或者美術(shù)史的總結(jié)往往做得很不夠。我們前幾年在策劃王臨乙、王合內(nèi)展覽時(shí),曹老師也提出了這樣的看法,我也是很認(rèn)同的。后來我思考了這個(gè)問題,中國的美術(shù)館發(fā)展應(yīng)該會(huì)有三個(gè)階段:第一個(gè)階段是現(xiàn)代美術(shù)館的建立階段。這個(gè)階段從民國開始一直到20世紀(jì)末,比如張安治時(shí)代,他于民國時(shí)代在廣西或者在英國的時(shí)候,我們從照片中看到他在做展覽的時(shí)候就是把畫一掛,展覽就形成了,即使到了20世紀(jì)80年代,張安治先生在江蘇美術(shù)館舉辦展覽時(shí),變化也不算大,我認(rèn)為這個(gè)階段屬于中國的美術(shù)館的初創(chuàng)期,是一個(gè)展覽館的時(shí)期,這個(gè)過程一直持續(xù)到21世紀(jì)初;第二個(gè)階段,就是我們現(xiàn)在這個(gè)階段,隨著國家經(jīng)濟(jì)與文化的發(fā)展以及國際交流的深入,越來越多的美術(shù)史專業(yè)畢業(yè)生成為美術(shù)館工作人員的主體,展覽中的學(xué)術(shù)性得以加強(qiáng),并在設(shè)計(jì)師的設(shè)計(jì)下,藝術(shù)家作品與文獻(xiàn)資料在展覽中得以全面呈現(xiàn),我們目前屬于這樣的一個(gè)階段;第三個(gè)階段就是美術(shù)館除了呈現(xiàn)作品和資料之外,也是美術(shù)史知識(shí)與美學(xué)思想形成的地方,這種美術(shù)史知識(shí)和美學(xué)思想的形成將為未來美術(shù)史和美學(xué)史的書寫提供內(nèi)容,美術(shù)館會(huì)真正成為一個(gè)人類美學(xué)思想產(chǎn)生和聚集的地方,每一個(gè)來到美術(shù)館的人將會(huì)在思想和知識(shí)兩個(gè)層面得以提升,這是我們將來美術(shù)館發(fā)展的一個(gè)方向,同時(shí)也是一個(gè)理想,這需要中國的美術(shù)館在辦館理念與機(jī)制運(yùn)行上真正以學(xué)術(shù)為核心才能向前推進(jìn),曹老師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個(gè)問題。
其實(shí)做展覽就是做一道大菜,我們今天呈現(xiàn)了一道大菜,館領(lǐng)導(dǎo)就是點(diǎn)菜的人,我們收藏部人員就是統(tǒng)籌的人,張老師就是提供材料的人,設(shè)計(jì)師就是負(fù)責(zé)視覺傳達(dá)的人,在策劃小組的群策群力下,這道美餐才能呈現(xiàn)在大家面前。這個(gè)展覽在籌劃的時(shí)候感覺非常輕松,張晨先生是一個(gè)非常好的供貨源,以往我們做展覽的時(shí)候,就好像買個(gè)“蘿卜”一樣,而張晨提供的這個(gè)“蘿卜”是從田里洗干凈,皮也削完,切成絲給我們。過去做展覽很麻煩,我們找“蘿卜”的時(shí)候要去田里拔,有了張晨先生的大力協(xié)助,我們省去了很多麻煩。
我在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做博士后的時(shí)候,看到人文學(xué)院墻上掛著張安治先生和許幸之先生的像,寫著江蘇揚(yáng)州人,我看了之后非常激動(dòng),因?yàn)槲乙彩菗P(yáng)州人,這兩個(gè)人跟我是老鄉(xiāng),我心里面自然有親近感。沒有想到今天機(jī)緣巧合能夠參與到張安治先生的展覽策劃當(dāng)中來。張安治是一位非常有情義、有教養(yǎng)的文人,他對家鄉(xiāng)很有感情,他雖然從小離開母親到南京,但母親是他一直的牽掛,母親在,他的心一直惦念著揚(yáng)州,無論在何地,他的心里都有那個(gè)城市的位置,我從他的畫和詩里面能夠感受到他對揚(yáng)州的感情。而且,我有很多相似的內(nèi)心感受。過去如果想從揚(yáng)州出來,必須要經(jīng)過瓜州,坐船過江到鎮(zhèn)江,從鎮(zhèn)江再坐火車到北京、上海乃至世界各地。張安治每次回家的時(shí)候,必然也經(jīng)過鎮(zhèn)江、瓜州再回?fù)P州,他的詩里面就多次寫到“過金山”和“過瓜州”。我對他當(dāng)時(shí)的情景描寫和近鄉(xiāng)情切的心情感同身受。同樣,他對南京也有很深的感情,他從小在南京長大,他的畫表現(xiàn)了南京的玄武湖和南京中央大學(xué)時(shí)期朋友、同學(xué)的交往情形,他對家鄉(xiāng)的情誼洋溢在他的藝術(shù)作品里面。這一點(diǎn)我作為揚(yáng)州的老鄉(xiāng)是有切身感悟的。
張安治時(shí)代的揚(yáng)州和我生活時(shí)代的揚(yáng)州是不一樣的,他生活時(shí)代的揚(yáng)州是沒落的貴族聚集之地,清中葉揚(yáng)州鹽商經(jīng)濟(jì)很發(fā)達(dá),所造就的文化影響也很大,揚(yáng)州人是見過世面的,張安治先生雖然沒有在揚(yáng)州成長,但是那種文化在他身上是有所顯現(xiàn)的,這種文化內(nèi)涵在他身上形成了文化自信,這種精神狀態(tài)一直貫穿他的一生。他到了南京之后,所接受的教育是當(dāng)時(shí)最好的教育,因?yàn)樗木司恕⑼夤际乔扒宓男悴牛木烁纲芎闶莾山瓗煼秾W(xué)堂的老師,和李瑞清經(jīng)常一塊交流。張安治先生從小看他們的雅集,也就接受了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對詩和傳統(tǒng)文人畫的喜好在那個(gè)時(shí)候就播下了種子。后來,他考上了江蘇省立第四師范學(xué)校,開始學(xué)習(xí)受揚(yáng)州畫派、海派影響的謝公展的花鳥畫,張安治最初的繪畫學(xué)習(xí)是從傳統(tǒng)繪畫訓(xùn)練開始的。薛永年先生在一篇文章里面提過,張安治的中國畫創(chuàng)作有兩條線:一條是融合性的線,就是徐悲鴻的體系;還有一條是傳統(tǒng)的線,這兩條線不斷地產(chǎn)生呼應(yīng)。張安治上了中央大學(xué)之后,開始接受了西方油畫體系訓(xùn)練,完全是徐悲鴻所倡導(dǎo)的路子。在中央大學(xué)的時(shí)候,他在詩詞和美學(xué)上也受到了國內(nèi)一流人才的培育,所以張安治在文化上很自信,我們看他的照片發(fā)現(xiàn)他的雙眼非常有神,自信的氣質(zhì)顯現(xiàn)于他的精神狀態(tài)上。中央大學(xué)畢業(yè)之后,受“藝術(shù)為人生”口號的影響,張安治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更多地和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結(jié)合在一起。張安治先生于1946年寫了一篇題為《論文人畫和畫工畫》的文章。徐悲鴻一直是揚(yáng)畫工畫、貶文人畫的,我估計(jì)張安治那時(shí)在思想上是追隨徐悲鴻的,張安治年輕時(shí)創(chuàng)作的水墨畫屬于徐悲鴻體系,多表現(xiàn)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更多的是從“像”上著眼,表現(xiàn)人物苦難的狀態(tài),這是他水墨畫創(chuàng)作的第一個(gè)階段。到了解放之后,他受新中國文藝路線的影響,繪畫創(chuàng)作是徐悲鴻體系的新發(fā)展,和宗其香等人的風(fēng)格很像,他的畫里面有水彩和西畫的因素,那個(gè)時(shí)候被稱作彩墨畫。但到了60年代,我發(fā)現(xiàn)他的畫風(fēng)開始發(fā)生變化,這是他水墨畫創(chuàng)作的第二個(gè)階段。為什么會(huì)產(chǎn)生變化呢?因?yàn)樗接螅诙嗄昝佬g(shù)史研究的過程中,他對中國的傳統(tǒng)畫論做了梳理,對中國傳統(tǒng)畫論梳理的過程實(shí)際上就是對于文人畫理論的認(rèn)同過程。他在60年代的畫風(fēng)變化體現(xiàn)在從“狀物寫象”的表現(xiàn)轉(zhuǎn)向?qū)Α耙庀蟆钡氖惆l(fā);80年代是張安治中國畫創(chuàng)作的第三個(gè)階段,這個(gè)階段他完全把所見之“象”減弱了,更多的是抒發(fā)自己的胸臆,以草書筆法書寫胸中之“象”,把對黃山等景物的內(nèi)心感受完全用半抽象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這就和文人畫的意象表現(xiàn)在理論和實(shí)踐上完全趨同了。
這三個(gè)階段的水墨畫實(shí)踐是非常有意思的,在徐悲鴻體系里能夠達(dá)到第三個(gè)階段的畫家其實(shí)是不多的,什么原因呢?就在于這需要畫家的文學(xué)修養(yǎng)和對藝術(shù)史(特別是文人畫史)的梳理與積累。這是徐悲鴻系統(tǒng)里的一般畫家所不具備的。張安治先生水墨畫的三個(gè)創(chuàng)作階段是非常有意思的藝術(shù)史現(xiàn)象。在20世紀(jì)中國美術(shù)史上很難找到第二個(gè)像張安治先生這么全面的藝術(shù)家,我們透過張安治可以進(jìn)入20世紀(jì)廣闊的社會(huì)空間。
美術(shù)史的形成是有偶然性的,后世美術(shù)史的書寫一般是由作品累積而成,如果說張安治先生當(dāng)年畫10張類似《群力》這樣的畫,張安治的美術(shù)史形象可能又是另外一個(gè)面貌。所以,由于他涉及的面太廣,有時(shí)遮蔽了他作為畫家的才華和形象。
安遠(yuǎn)遠(yuǎn):謝謝王雪峰從文人畫和中西融合兩個(gè)方面的論述,還是挺有想法的,因?yàn)橥跹┓迨沁@個(gè)展覽的統(tǒng)籌,他在這個(gè)過程中跟張晨老師和鄧鋒一直在溝通。
李維琨:張先生在理論方面以及在中國畫、西洋畫的實(shí)踐上沒有被限制住,他實(shí)際上一直在突破這種局限,希望成為比較全能的一個(gè)人,這是我們今天看完展覽或者回顧先生一生得到的一個(gè)比較大的啟示。一個(gè)人能夠突破一種局限,達(dá)到一種自由,當(dāng)然是一種理想,但是在實(shí)踐當(dāng)中有些實(shí)際是能夠做到的。跨界也好,突破局限也罷,這是張安治先生一生求藝、求真、學(xué)道、得道這一過程所帶給我們的啟示。
曹慶暉:我們在20世紀(jì)中國美術(shù)史的研究當(dāng)中,往往有大家公認(rèn)的說法,比如說中西融合。在我看來這些教給本科生是可以的,因?yàn)橐⑾鄬Φ囊粋€(gè)維度和框架。但是,進(jìn)入到研究層面的時(shí)候,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這樣的概括和歷史的發(fā)生之間太過于簡單了。我們今天還在強(qiáng)調(diào)張安治先生的人生圖景由兩條線構(gòu)成,但在我看來,和張先生人生圖景的復(fù)雜性和生成過程相比,這種概括還是有些簡單。一個(gè)人在成長過程當(dāng)中有什么樣的機(jī)遇,碰到什么樣的人,這不是設(shè)定好的,這跟我們今天處在社會(huì)當(dāng)中認(rèn)識(shí)誰或不認(rèn)識(shí)誰一樣都不是安排好的,不要以這種方式做特別簡單的切分。
我回應(yīng)一下李維琨老師提到的問題。我們今天有個(gè)詞叫做“跨界”,他們以前沒有“跨界”,我們今天是因?yàn)閷I(yè)區(qū)分越來越細(xì)了,才開始覺得不能這樣做了,才討論“跨界”的問題。舉一個(gè)簡單的例子,80年代我在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讀書時(shí)和高等院校師生的交往談不到跨界的問題,本來就在一塊兒玩兒,現(xiàn)在是不在一塊玩了,才想到我怎么去跟戲劇學(xué)院的聯(lián)系聯(lián)系。我們不能老是以一種概念模式看待一個(gè)人,這樣自然就終結(jié)了,就無法討論了。
再補(bǔ)充一點(diǎn),我沒有把自己僅僅當(dāng)成教師來看,因?yàn)槲乙沧鲆恍┱褂[,在策劃展覽的過程當(dāng)中,我意識(shí)到問題后,有時(shí)候也在想辦法突破,但是有時(shí)想要突破,卻一點(diǎn)辦法都沒有。我說的沒有長進(jìn),不是指對于基礎(chǔ)材料的挖掘,也不是冒犯張晨老師。我是說我們的研究到今天為止,如果還未達(dá)到薛永年先生和郎紹君先生的水平,你就沒有長進(jìn),如果我們達(dá)到他們的水平,甚至超越他們,能發(fā)現(xiàn)一些新的問題,那就是有長進(jìn)了,其實(shí)“有長進(jìn)”不在于材料本身,當(dāng)然對于材料本身的進(jìn)一步挖掘也是“長進(jìn)”的一個(gè)量化指標(biāo),我想說的是研究問題的方式與方法,似乎在今天捋起來還是我們先生輩的思路,我們自己沒有拿出來新方法和新方式。
李維琨:展覽是讓作品說話,策展人要讓它說什么和觀眾能否接受你所說的,這又是一回事情。剛才我提出做10件像《群力》這樣作品的設(shè)想,在張安治先生這樣一個(gè)具體情境之下,不管是1949年以前,還是1949年以后,是不為?還是不能?這個(gè)問題要有一個(gè)基本的構(gòu)架才行,他有沒有這種能力做?還是根本沒有條件做這個(gè)事情?
曹慶暉:我們平時(shí)看了很多展覽,對我有很大的啟發(fā),今天中國目前的展覽形式是什么呢?并不是說我們要求所有的展覽都有主題,有些確實(shí)沒有主題,作為策展人來說,一定要有所超越。
邵彥:我說一下我的體會(huì),曹老師從近現(xiàn)代美術(shù)史研究專家的角度對自己和策展團(tuán)隊(duì)的要求都很高。我雖然也算美術(shù)史家,但是我做的美術(shù)史研究是辛亥革命以前的時(shí)段,在這之后我就不了解,每次觀看這種大規(guī)模的展覽,我覺得收獲都很大,包括以前鄧鋒策劃的陳師曾展覽,也許他自己要求很高,但是我看了以后就有很多收獲,真正關(guān)注策展那一領(lǐng)域的專家是少數(shù)人,而普通觀眾更多。
曹慶暉:不是所有的展覽都要求一天進(jìn)來幾千觀眾,這個(gè)我們太清楚了。你剛才把展覽分為學(xué)術(shù)的和大眾的兩類。今天中國的現(xiàn)實(shí)是中國美術(shù)館做展覽肯定還是面對大眾,專家思考的量度在哪里?要有量度自我的要求,這個(gè)量度高,對于普及來說更有好處。不要把展覽劃分為學(xué)術(shù)的和大眾的兩類,這沒多大意義。你今天要做展覽,肯定要面對一個(gè)為誰做展覽、做多長時(shí)間、后面誰買單的問題,這些我們都會(huì)考慮。
鄧鋒:剛才曹老師說每個(gè)展覽都想要去突破。我們作為真正的策劃者,感覺現(xiàn)在有一種突破的焦慮癥。說到張安治先生的展覽,我們的確還是沒有辦法超越水天中先生、薛永年先生、郎紹君先生對于張先生整體而宏觀的把握能力,所有的材料我都看了,的確很難找到一個(gè)特別適合的角度加以突破。我之前甚至想過就把張安治先生的課搬到美術(shù)館來,我們請?jiān)?jīng)受過張安治先生教誨的薛永年先生、李維琨老師用另外一種方式講出來。我覺得展覽的確還應(yīng)考慮到每一個(gè)對象,即做過幾次展覽,想解決什么問題,這可能得一步一步地慢慢來。
張晨:這的確需要時(shí)間,一個(gè)是準(zhǔn)備展覽需要很長時(shí)間,還有要讀那些材料,包括薛永年先生、郎紹君先生也是看看片子,有些東西可能也說得不準(zhǔn)確,但是作為家屬,他們能為先生寫點(diǎn)東西,我就已經(jīng)感激不盡了。由于種種原因,我不能要求人家太多,人家也很忙,還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我知道像王雪峰寫段首語也是看了很多東西,翻來覆去地想怎么寫,怎么才能說得準(zhǔn)確,首先得我認(rèn)可了才行,不說別的了,確實(shí)挺難做的。
我說說我的感受。安館長以及朋友們和我們都是同行。父親一生從事美術(shù)教育、美術(shù)創(chuàng)作、詩歌創(chuàng)作和史論研究,從1921年在江蘇省立第四師范兼課至1990年11月去世,共65年。他15歲就開始在那兒一邊念書一邊兼課,因?yàn)樗酿B(yǎng)在舅父家,也并不是那么愉快。他的各類藝術(shù)創(chuàng)作與時(shí)代變遷、社會(huì)生活、個(gè)人生活軌跡以及感情緊密相關(guān),你無法界定他是山水畫家、還是人物畫家,是西畫家,還是中國畫家,其藝術(shù)門類、題材、內(nèi)容、風(fēng)格十分豐富,反映了他的真性情,我在策展初期無從下手,多虧了鄧鋒、雪峰和修復(fù)師孔妍,通過大家的策劃、溝通、協(xié)調(diào)、幫助才得以形成現(xiàn)在的面貌并最終呈現(xiàn)給觀眾。
父親從事藝術(shù)創(chuàng)作是從內(nèi)容和主題入手,他運(yùn)用了自己掌握的古今中外各門類的藝術(shù)技法和手段抒發(fā)自己的情懷,對各種技能和材料做到了“為我所用”,他可能畫兒童就用素描,其他作品有的用中國畫或水彩的方法,他的作品中交織著中國畫、詩歌、書法、西洋繪畫的形式特點(diǎn),蘊(yùn)含了東西方藝術(shù)的意境和主題要求,表現(xiàn)了他的個(gè)性和情懷。
父親一生參與了大量的行政事務(wù)工作,他于1964年調(diào)到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也是因?yàn)槿~先生想畫畫,行政的事情和教學(xué)的事情都交給我父親了,他參與了大量的行政事務(wù)工作,也經(jīng)歷了多次政治運(yùn)動(dòng),但是,他始終遵從自己的內(nèi)心,遵從一名教師的職業(yè)操守,遵從一個(gè)藝術(shù)家的良知。他始終認(rèn)為他所選擇的藝術(shù)教育、藝術(shù)創(chuàng)作是最幸福的職業(yè)。他實(shí)際在我上中學(xué)的時(shí)候,就灌輸我以后當(dāng)老師,因?yàn)槔蠋熡泻罴伲鎸Φ亩际菍W(xué)生——年輕人,你自己也不老。為什么他說藝術(shù)教育、藝術(shù)創(chuàng)作是最幸福的職業(yè)呢?因?yàn)樗囆g(shù)滿足人類的精神愿望和追求,他是我們子女的榜樣和驕傲,我唯一能比較欣慰的就是,我從1990年父親去世到現(xiàn)在,用了很長時(shí)間,慢慢地通過閱讀、整理父親的詩詞集、畫集之類的資料,讀懂了他對祖國、對自然、對藝術(shù)、對家人、對朋友、對學(xué)生的愛。
作為子女,我想通過舉辦此次展覽使自己與父親的靈魂更近,父親的所思、所想、所念、所憂全都在他的詩歌、繪畫和文章之中。
最后,我代表我們?nèi)w家屬感謝中國美術(shù)館的朋友們,也感謝薛永年先生給我們的幫助,盡管他今天沒有來,但給我出了不少主意,感謝在座的各位女士們、先生們,謝謝大家。
安遠(yuǎn)遠(yuǎn):謝謝張安治先生所有的家屬對于中國美術(shù)館的支持和貢獻(xiàn)。我和張安治先生在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聊天的那個(gè)印象和最后在醫(yī)院告別的那個(gè)印象一直印在我的腦海里。我經(jīng)常在我館六樓藏寶閣介紹展覽時(shí)看到許幸之的作品《柿子》,就會(huì)告訴大家他當(dāng)年一頭白發(fā)在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圖書館煤堆前打太極拳的印象。那個(gè)時(shí)候我們對這些老師都不是很了解,我在學(xué)校的時(shí)候,不知道許幸之先生就是《風(fēng)云兒女》的導(dǎo)演,我也不知道當(dāng)時(shí)這些人和那個(gè)時(shí)代的關(guān)系。所以,我們就是通過展覽把前人呈現(xiàn)出來,讓更多的人了解一個(gè)藝術(shù)家和他的時(shí)代、他的思想、他的創(chuàng)作、他的成果,因?yàn)橹挥型ㄟ^這些作品才能讓我們認(rèn)識(shí)到當(dāng)時(shí)發(fā)生了什么,那些人做了什么、想了什么,我們沒有辦法還原歷史,我們也沒有辦法把有血有肉、生動(dòng)快活的景象永遠(yuǎn)呈現(xiàn)給大家,熟悉的人看這些藝術(shù)家及其生活時(shí)都是活生生的、鮮亮的,但是,作為后來者觀看的時(shí)候都是無聲的默片。我們怎么樣通過這些作品讓藝術(shù)家的靈魂和思想再一次活靈活現(xiàn)的呈現(xiàn)出來?這就是美術(shù)館在不斷地做展覽呈現(xiàn)時(shí)首要的一個(gè)義務(wù)。
今天大家從各個(gè)方面討論了張安治先生作為一個(gè)教育家、藝術(shù)家、史論家、詩人、書法家等全面的成就和影響,但是,這只是一個(gè)開始,也給我們提出了美術(shù)史研究、美術(shù)史教學(xué)和人才培養(yǎng)方面的一些新課題和新要求。
通過這樣的討論,也對美術(shù)館的策展工作和學(xué)術(shù)視野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議,這樣的討論對我們來講也是很受惠的,因?yàn)槲覀兠佬g(shù)館人希望在學(xué)術(shù)方面和展覽等專業(yè)服務(wù)方面做得更好。因?yàn)橹袊恕⒅袊?jīng)驗(yàn)貫穿著中國所有的文化和社會(huì)發(fā)展進(jìn)程。這些藝術(shù)品所寄托的人文精神就是我們中國經(jīng)驗(yàn)和中國未來發(fā)展的最主要支撐。
將美術(shù)館從一個(gè)中央美術(shù)展覽館變成中國美術(shù)館這樣的一個(gè)建館策略是當(dāng)時(shí)毛主席最后確認(rèn)的。我們曾經(jīng)也走過很多彎路,最終從一個(gè)藝術(shù)家的作品展示場所轉(zhuǎn)變成今天的公共文化服務(wù)機(jī)構(gòu)。我們今天所有的努力都會(huì)為未來種下一顆發(fā)展的種子。
我希望這個(gè)僅僅是開始,因?yàn)楹芸炀鸵_始建設(shè)新的國家美術(shù)館了,那個(gè)時(shí)候我們會(huì)有非常好的美術(shù)史陳列館,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人才加入到我們美術(shù)史研究的隊(duì)伍里,希望更多的人把作品拿到中國美術(shù)館展示,也希望更多的人通過中國美術(shù)館的作品研究呈現(xiàn)更好的學(xué)術(shù)成果。對于未來,我們希望依然要保有良好的熱切希望。我們希望大家更多地幫助我們,使我們不斷地成長,進(jìn)而做出更好的業(yè)績。
今天我特別代表吳為山館長感謝出席此次研討會(huì)的各位專家和學(xué)者,也特別再次感謝張安治先生全家對中國美術(shù)館的貢獻(xiàn),謝謝各位!
作品在,人就在,作品中的靈魂一直與我們同在。我們看展覽的時(shí)候會(huì)有一種藝術(shù)家跟我們在一起的感覺,這反而可以更直接的去審視藝術(shù)家的本質(zhì)和他的精神世界。我們這個(gè)展覽雖然很快地結(jié)束了,但是會(huì)有影像資料和更多的學(xué)術(shù)記錄不斷地呈現(xiàn)出來,以后這些研討會(huì)的發(fā)言和展覽的影像都會(huì)在中國美術(shù)館的官網(wǎng)上發(fā)布,這可以讓更多的人通過不同的方式來了解展覽,通過展覽來理解藝術(shù)家、時(shí)代精神和他的創(chuàng)作成果,這些工作我們以后會(huì)更多地做下去,謝謝各位。今天的研討會(huì)到此結(jié)束,感謝各位,祝大家一切如意、平安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