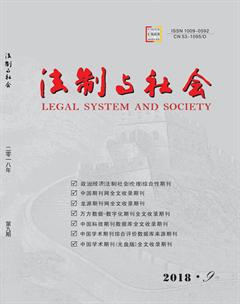信訪法治化的現實困境與路徑選擇
摘 要 信訪是作為國家核心制度的補充而存在的,且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轉型,大量的社會沖突、矛盾等現象往往會通過信訪渠道而體現出來。目前,我國現行的信訪制度與大量的信訪境象相比,則存在滯后問題,且弊端叢生。由于我國司法體系尚不夠完善,各種權力制衡與社會正文的維護尚存在諸多問題。本文就信訪法治的現實困境與路徑選擇進行系統闡述,以期為實現信訪法治化提供更多的參考與借鑒。
關鍵詞 信訪 信訪制度 法治化 政府 公民
作者簡介:林華東,淮陰師范學院法律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中國礦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2017級行政管理專業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法學、行政法治。
中圖分類號:D63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9.304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經濟社會的轉型,促使我國社會逐步進入了一個人民內部矛盾的凸顯期,同時也加劇了信訪“洪峰”的出現。雖然,我國在國家層面上不斷地出臺各種信訪條例、規定,但目前的信訪“洪峰”問題卻未得到根本性變化與解決,且信訪機構仍處于高負荷運行狀態。因此,加強對信訪、信訪制度建設的研究,則成為了當前學界所關注的焦點問題。本文認為:欲完善我國信訪制度須從制度內部的體制關系著手,通過信訪法治化之路才能真正進一步規范信訪法律援助制度、信訪處理聽證制度等,最終實現高效保障信訪制度的時代性,滿足人民需求。本文就信訪法治的現實困境與路徑選擇進行系統闡述。
一、信訪的概念梳理與歷史沿革
(一)信訪概念的厘定
信訪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依法、依規通過書信、現代通信平臺、電話以及走訪等形式向各級國家權力機關反映當前社會情況或個人生活(或工作)情況等,或提出自己投訴請求,或提出相關的意見、建議等行為。因此,信訪即是公民向各級行政主體表述意愿的一種活動,也是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
信訪制度則是以信訪活動為核心設計的相關制度。廣義的信訪制度:是由國家層面設計、確定的,并對信訪人、被信訪對象產生高度的規范、約束作用;狹義的信訪制度:自建國以來的相關信訪制度性安排。因此,信訪制度具有高度的政治民主性、人民維權性以及“半司法性”的特點。
(二)信訪制度的歷史沿革
1951年,我國信訪制度與組織體系的逐步完善,但在文革期間則一度處于“癱瘓”或“半癱瘓狀態”。直至1995年時,國務院頒布《信訪條例》,這也標志著我國信訪工作真正邁向法制化。2014年時,國家信訪局頒布《關于進一步規范信訪事項受理辦理程序引導來訪人依法逐級走訪的辦法》,同時明確提出:要通過改革信訪工作制度,逐步健全、及時就地解決群眾合理訴求機制。同時,也再一次加快了信訪法治化的進程。
二、信訪法治的現實困境分析
(一)多元組織體系,削弱了政治權威性
目前,我國信訪制度是一個多元組織體系,其機構重疊、歸口不一,在各級黨委、人大、政府機構以及相關職能部門均設有信訪機構(或信訪窗口)。雖然,各不同機構受理的信訪側重點不同,其性質卻是相同的,但是受多元化信訪組織體系的影響,既造成了各機構的信訪工作效率卻極為低下,也導致很多案件在各部門之間進行著“流轉”即無法找到真正的相關責任部門。正是這種多元組織體系造成了各信訪機構缺乏管制協調,加之信訪信息不共享而造成了信訪者的不認同,甚至導致大量信訪不斷升級現象的發生。長久下去,必然會導致黨政機關政治權威性被削弱。
(二)剛性責任機制,萌發了基層激進主義
為了切實將矛盾解決在基層,實現確保社會穩定的目的,中央就信訪工作責任制進行了強化,甚至將信訪工作納入到地方政績考核體系之中。雖然,在剛性責任機制下,各地政府均對信訪工作予以了高度重視,但因一些信訪案件本身就針對當地政府,這也導致個別地方政府在無法解決群眾上訪問題時,也采用了過激、錯誤的“堵”、“抓”、“黑名單”等手段,在無法有效解決上訪問題時,越級上訪事件也隨之增加,這也促使基層激進主義顯現萌發、發展,甚至造成了不良的社會輿情。
(三)權利救濟功能,弱化了國家治理基礎
法治社會中解決矛盾糾紛、實現權利救濟的基本途徑就是司法途徑。但是,當前的信訪制度卻更多的是借助行政權威來執行,進而導致行政權威承擔公民權利救濟功能。盡管,信訪制度下的行政權威幫助了很多公民實現了實質正義,但這種依靠上級行政主體的介入實現信訪、救濟途徑的同時,即使矯正了司法不公,但也存在個別權力機關、高層黨政領導“過度”替代了司法救濟功能,甚至一些基層群眾將信訪視為是優于司法救濟的“特殊權利”,既造成信訪功能出現錯位,也消解、沖擊了各級司法機關的權威性,從另一角度來看,這是對國家治理基礎的一種弱化。
三、信訪法治化的路徑選擇
信訪應是柔性扶助制度,但事實上卻逐步成為了另一種救濟方式,并與其他主要救濟制度出現了“抗衡”,甚至被基層群眾視為一種“優于”,甚至是超越國家司法救濟或其他行政救濟的重要救濟形式,并出現了一股“信訪不信法”、“有事就信訪”的錯誤思想,并在潛移默化之中弱化了國家治理的基礎。
(一)改變多元組織體系下的信訪困境
首先,從各級行政機關(或相關職能部門)將信訪機構分離出來,僅在人大建立信訪機構。調查發現:爭議解決機構的權威性、獨立性是絕大多數的訪民訴求。因此,我國信訪法治化路徑的選擇過程中,既要避免因各級行政機關信訪機構在處理大量信訪案件過程中效率低問題,也要確保信訪機構的相對獨立性,這就需要將信訪機構從行政機關予以脫離,并通過單獨設立來提高信訪機構的公信力,這對提升信訪案件處理的高效性、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有機地將信訪與人大制度結合,既可以避免“向上負責”現象的出現,還有利于促進信訪制度逐步由原來的“向上負責”轉向“向下負責”。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人大,其在法理上具有超越司法、行政機關的效力;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人大代表是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代言人”,其可以有效地對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予以維護。因此,應在人大常委會增設信訪工作委員會,其職責就是指導、監督其他國家機關的信訪工作。同時,還需在市縣兩級設立專門的信訪協調委員會,負責協調、組織各責任部門共同地、集中地接待上訪群眾,真正實現“一站式接訪、一條龍辦理”,在提高信訪工作效率的同時,也能夠全面降低群眾信訪成本。
其次,完善行政權力監督,完善行政監察專員制度。由古至今,一切有權力的人都有可能出現覽勝權力的問題,因此,行政權力也需要被監督。雖然,在國務院層面已設置了監察部,但行政監察效力卻出現了相對缺失現象,其行政監察制度的不完善性也被“放大”。因此,可以將行政檢察權直接交予人大,并在法律層面上對紀檢部門、行政監察專員的權力加以明確、并在其權力運作程序予以規范,以提高行政監察專員工作效力。
(二)從運行機制上摒棄傳統信訪工作模式
十八大以后,中央已經就信訪工作機制效能低下問題進行著不斷的嘗試與改革,如改變了原有信訪排名通報制度等,且將更多的精力放在的信訪源頭治理問題上。本文認為:欲推進信訪法治化,還需要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首先,全面推進信訪信息化建設。通過建立、完善信訪信息化制度,既可以利用網絡優勢拓寬信訪渠道,也促進了信訪的便捷化、公開化、高效化。同時,網上受理信訪制度,還可以引導群眾“多上網、少走訪”;并將受理、辦理、結果等重要環節通過網絡予以公開,最終實現信訪事項的溯源,即“可查詢、可追溯、可督辦、可評價”,這對提高信訪受理效率及訪民滿意度均具重要意義。
其次,依法規范信訪工作及相關流程。一是要嚴格按相關法定權限、程序對信訪機構的職責、工作流程等進行規范,同時還要不斷提高信訪工作人員的職業素養,提高其為人民服務意識與能力,使之能夠依法、依規為訪民辦實事,更要依法、依規去維護訪民的合法權益,最大程度地解決訪民訴求。二是要規范內容,即按當前《信訪條例》規定以及涉法、涉訴信訪工作改革要求,最大程度地發揮法定訴求表達渠道的各項功能、作用;同時,還要徹底將信訪、訴訟予以分離,真正將涉法、涉訴信訪納入到法治軌道之中,最大程度地維護司法權威。三是規范秩序,既要嚴格按照《信訪條例》中的相關規定、原則,及時、就地解決訪民合理訴求,并在完成、強化屬地責任的基礎上,積極引導訪民能夠自主地通過合法的、理性的信訪渠道、信訪方式逐級去表達自己的訴求或意見等。
第三,完善信訪事項公開聽證制度。信訪機構必須健全信訪事項公開、“陽光信訪”、“陽光查證”機制,利用信訪聽證為訪民釋疑、解惑。這樣一來,既可以提高訪民及一些不明事情(或事件)真相群眾的“知情權”。同時,公開聽證制度,還可以將更多群眾關心的問題擺在明處,讓群眾能夠清楚事件的真相,避免出現群體性治安事件等。另外,為了確保聽證會的嚴肅性、公正性及聽證意見的法律效力,須將聽證意見作為終結意見,并為依法打擊處理提供有力證據,避免上訪人出現無理纏訪等事件的發生。
(三)引導信訪人依法、有序上訪,將涉法、涉訴信訪納入到司法軌道中
首先,將涉法、涉訴信訪納入司法軌道。受信訪門檻低、走司法程序費用高、耗時長、基層信訪機構不作為等因素影響,導致很多上訪人對政法部門出現了不信任現象,甚至出現了“信訪不信法”的怪象。因此,必須不斷提高司法公信力,讓更多的信訪案件理性地回歸到司法程序之中,逐步在全體公民心中樹立起“信法不信訪”的法治理念,并加以踐行。由于,信訪與司法均為法律規定的救濟渠道,因此,必須逐步將涉法、涉訴信訪納入到司法軌道中來,在有效提升法律地位、司法公信力的同時,也能夠充分發揮司法機構的重要作用。
其次,建立信訪法律援助制度。信訪法治化之路,既要設計出與信訪制度相匹配的制度,還要確保相關制度的有效運行。因此,建立信訪法律援助制度,既可以發揮出法制在解決信訪問題中的重要作用,還可以發揮出提高社會管理水平、高效化解矛盾的協作機制;同時,在為訪民、群眾提供更多法律幫助的基礎上,還能夠讓訪民能夠遵循法律渠道來解決矛盾、糾紛,并通過理性、法律維權來降低上訪率。
綜上所述,信訪法治化的路徑選擇,既需要為信訪制度走向法治化創造良好的政治環境、司法環境,還需要地方政府成為信訪制度法治化的引領者。同時,也需要信訪部門積極掌握各種群眾訴求的信息與動態,爭取將任何影響社會穩定的隱患、事件消除在萌芽狀態,避免事態走向極端化。
參考文獻:
[1]宋瑤.信訪法治化的路徑選擇.中國海洋大學.2015.
[2]秦小建.信訪納入憲法監督體制的證成與路徑.法商研究.2016(3).
[3]王藝穎.涉訴信訪法治化研究——以華北Q縣為例.燕山大學.2016.
[4]楊祝琦.信訪工作法治化對策研究——以Z省為例.華東政法大學.2015.
[5]曾遠根.信訪法治化的可能路徑:政治功能的剝離與紓解.云南大學.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