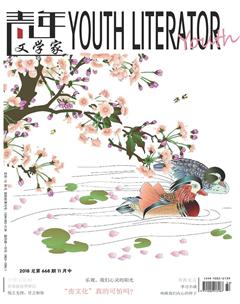理性與感性的多重故鄉
摘 要:很多研究都是關注魯迅《故鄉》中的思想,情感,但為了更加全面地認識魯迅的《故鄉》,我們要在反常規的進行文本細讀,《故鄉》中的故鄉其實是多重的,它是現實故鄉,過去的故鄉,既有真實的,也有記憶中的,以及理想故鄉的綜合體。我們要發現多重故鄉背后的意義,情感,思考,既要看到魯迅的悲觀絕望,更要看到魯迅的對希望的信仰。
關鍵詞:多重故鄉;魯迅;《故鄉》;理性;感性
作者簡介:李楓(1992.11-),男,安徽宿州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小說。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32-0-02
眾所周知,魯迅在他的小說中有很多深刻的思考,如對國民性的批判等,在對《故鄉》的研究中,很多學者都是關注《故鄉》中的哲學思考,如茍泉所寫的<覺醒與抗爭之路——魯迅《故鄉》對精神家園的追尋>,認為《故鄉》是魯迅追尋精神家園中覺醒和抗爭的希望之路[1]。又如劉俐俐所寫的<永遠的故鄉與魯迅的返鄉之路——魯迅《故鄉》的文本分析>[2],認為魯迅的《故鄉》中的情感包含了魯迅對于人生等問題的哲學思考。當然也有部分作品關注《故鄉》中魯迅所表達的故鄉情結,如劉思源所寫的《魯迅的故鄉情結》[3]。分析小說中的情感、思想是現代文學研究中常規研究方法,大部分學者從這些角度進行文本閱讀和研究。但是,我們要在魯迅的常規之中發現“反常規”,那就是故鄉并不是一個,而是有多個,而多重故鄉的背后是魯迅對于個人經歷、情感和歷史使命的思考。
一、現實的故鄉
魯迅對現實的故鄉的第一次敘述是在開頭部分,故鄉是嚴寒的,多年未回。“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不禁的悲涼起來了。啊!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4]”,敘述帶有很強的主觀情感:悲涼和不敢相信。由于長時間和遠距離的疏遠故鄉,自身對故鄉的期待和現實故鄉之間產生的心理落差,對故鄉的情感寄托沒有實現;同時,由于魯迅自身經歷產生的消極情緒,對待消極的事物,魯迅很容易產生這種悲觀情緒。
第二次對現實故鄉的敘述是見到老屋,作為故鄉的物質載體的老屋“瓦楞上許多的斷莖當風抖著”,“幾房的本家大約已經搬走了,所以很寂靜”,“我的母親早已迎著出來了,接著便飛出了八歲的侄兒宏兒”[4]。這里將魯迅內心的情感用比較客觀的敘述表現出來,破敗寂靜的老屋和幾房本家搬走,母親和侄兒的出現寫出了家族人丁的稀少,家族的衰敗,傳統宗法制度在逐漸解體,故鄉在不斷變化;魯迅還寫到母親很高興,也藏著許多凄涼的神情,不談搬家的事情,宏兒遠遠的站著只是看。雖是寫母親和侄兒,但對于魯迅來說,故鄉是承載兒時記憶和父親的地方,這里有很多親友,老屋即將被賣掉,魯迅將永遠的失去這些記憶的載體,魯迅和他的母親侄兒一樣都是充滿凄涼之感和陌生感的。
第三次關于現實故鄉的敘述是見到豆腐西施,對豆腐西施樣貌的描寫,還有豆腐西施所說的話語,看出魯迅在面對豆腐西施是處于一個無語的狀態,這也可以看作是一個從大城市來的現代知識分子對于愚昧物質的鄉村的無奈,被現實故鄉所壓制和排斥。同時,過去的豆腐西施與現實故鄉中對比,豆腐西施往日坐在店里生意就可以很好,如今卻出門了,這是因為她無法坐著做生意了,她的豆腐店生意可能破產或者慘淡,生活的艱辛使得她變得愛占便宜,不斷變得刻薄,這只是一個縮影,它的背后實際上整個中國鄉鎮的衰落和頹敗。
第四次關于現實故鄉的敘述就是見到閏土,詳細描寫閏土的樣貌變化,閏土叫出的一聲“老爺”,以及閏土對自身生活狀況的敘述。少年閏土代表著過去的故鄉的面貌,現實故鄉的閏土相貌可以作為現實故鄉的參照物。紫色的圓臉變成灰黃,滿臉皺紋;戴著的小氈帽也變成了破氈帽;頸上的明晃晃的銀項圈取而代之的是極薄的棉衣;紅活圓實的手變得粗笨開裂。過去的少年閏土經過艱辛的生活已經變成了麻木的窮苦人。可以看出現實故鄉的破敗,中國鄉村的破敗。
第五次關于現實故鄉的描寫是魯迅在離開的時候對故鄉環境的描寫:“我們的船向前走,兩岸的青山在黃昏中,都裝成了深黛顏色”,這里的景物色彩大都屬于暗色,并不是想魯迅記憶中過去的故鄉那樣充滿明亮的色彩。二者對比,可以看出對于這兩種故鄉的感情,熱愛和絕望。
第六次對于現實故鄉的描寫是“碗碟事件”,它更多的是作為一種補充,一個插曲,看似無關緊要,卻又意味深長。小說中說到豆腐西施發現灰堆中藏有十多個碗碟,并認為是閏土所藏,當然這一事件中成年閏土嫌疑的確最大,用警察常用的術語來說就是“第一嫌疑人”,這一段描寫,魯迅和母親對待這一事件的態度是“惘然”,惘然的意思在我看來最貼切的就是若有所失的樣子,所以在這里,魯迅的情感是持懷疑態度,但又不想相信自己認識的那個閏土會做這種事情。閏土在這里是作為一個記憶中過去故鄉美好化身,同時也是現實故鄉破敗混亂情況的敘述者和展現者,魯迅對于“碗碟事件”的態度也正是魯迅對于故鄉情感復雜性的表現,這一不起眼的事件也正是魯迅委婉表達自我情感的手段,以小見大,手法不可謂不高明。
二、過去的故鄉
魯迅過去的故鄉有兩種,一種是真實的記憶中的故鄉,那就是過去的故鄉,還有一種就是魯迅自己主觀情感影響下的過去故鄉,它是美好的,是記憶的故鄉。
關于過去的故鄉的敘述是我家那一年是大祭祀的值年,人手不夠,便讓閏土來我家管祭器。以及后邊的捕鳥,海邊撿貝殼,看西瓜。這點我把它放在過去的故鄉中,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有人物原型,杜撰程度并不高,少年閏土與少年魯迅的友誼之間發生這些事情是極其有可能的,所以我把他放在過去的故鄉這部分里。除了描寫魯迅對過去故鄉的美好回憶之外,也側面表現出故鄉的變化,通過現實我與閏土的關系對比,會有很多個少年如同少年閏土和少年魯迅一樣在這樣的變化中,走上不同的路,逐漸變得隔膜。
記憶的故鄉魯迅在小說中提到有兩次。第一次是見到現實故鄉后的感慨:“我是所記得的故鄉全部如此。我的故鄉好的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可以看出魯迅這里說的是記憶的故鄉是美好的;第二次敘述是在魯迅母親提到閏土以后,魯迅腦中忽然閃出的那幅神異的圖畫:閏土手捏鋼叉在金黃的圓月下的西瓜沙地上向猹刺去。這幅神異的圖畫是魯迅自身記憶的故鄉的樣子。這里的故鄉帶有魯迅自身的主觀色彩,這點可以從敘述帶有很多明亮色彩的詞語中可看出端倪,比如天空是深藍的,圓月是金黃的,西瓜地是碧綠的,這些明亮的色彩我們也可以看出魯迅對記憶中過去的故鄉的喜愛和懷念。記憶中過去的故鄉是與現實的故鄉產生強烈對立的,對記憶中過去的故鄉的熱愛和贊美,對現實故鄉的悲觀和失望。
三、理想的故鄉
小說中對理想故鄉的描寫有兩處。第一處,魯迅希望侄兒宏兒和水生應該有新的生活,為他和閏土這輩人所未經生活過的。在魯迅看來,理想中的那個故鄉下一輩們應該會過著一種不同于現在或者過去的生活,生活幸福快樂。第二處,是魯迅描寫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幅熟悉的畫面,這個場景在前邊魯迅回憶與閏土的友誼出現過:“這時候,我的腦里忽然閃出一幅神異的圖畫來: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猹盡力的刺去,那猹卻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4]沒變的是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但是又有所不同,西瓜,項帶銀圈手拿鋼叉的少年,還有猹都已消失不見,原本屬于記憶的故鄉的具體內容消失了。一方面,在經歷現實的故鄉后,過去和記憶的故鄉的美好,都被現實的故鄉打破,絕望和悲涼使魯迅放下了對故鄉執著熱愛的情感,放下了對記憶中過去的故鄉的懷念。另一方面,魯迅的深刻之處在于絕望中的反抗,雖然失去了具體的內容,但是海邊無邊無際的碧綠沙地和深藍天空中的金黃圓月還在,它們依舊帶著明亮的色彩,依然存在于魯迅的心中。“我想: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4]理想故鄉的具體內容需要現在人和后來人共同腳踏實地的走出來。這種理想故鄉可以擴展為整個國家,當時中國多災多難,不知何去何從,急需要一條可行的道路。魯迅堅信有這樣的一條路,它需要我們共同努力。魯迅雖身處絕望,卻依舊懷有希望,看似矛盾,但卻寫出了那個時代大多數人的現狀,魯迅是一個先行者,是一位未來的思考者,是一個國家的脊梁和魂魄所在。
四、結語
魯迅在小說中將多重故鄉放在一起寫,這里的故鄉是多重故鄉的綜合體,不論是過去的故鄉的美好回憶,還是記憶中過去的故鄉的美麗和佳處,都不能滿足魯迅對于理想故鄉的期望,它們最終都被現實的故鄉的所打敗和取代,這使得魯迅陷入一種絕望。但魯迅并沒有深陷這種絕望,而是反抗這種絕望,一直懷有一種希望。這種希望魯迅也有一定的論述,如“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來了。閏土要香爐和燭臺的時候,我還暗地里笑他,以為他總是崇拜偶像,什么時候都不忘卻。現在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遠罷了。”[4],在提到這種希望的時候,魯迅將它與閏土的求神拜佛進行對比,最后得出的結論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希望,不論是閏土的崇拜偶像,還是自己的希望,總的來說,都不失為一種信仰。這是魯迅對于信仰宗教和懷有希望的理性思考,這種希望并不只是魯迅的,魯迅認為這種希望應該讓更多的人所信仰,那個混亂的年代,整個國家都在頹敗,每天都有人失去希望,絕望的死去,魯迅期望人們信仰和堅信這股希望,沿著這條希望之路走下路,走出一條充滿希望的路。
參考文獻:
[1]荀泉.覺醒與抗爭的希望之路——魯迅《故鄉》對精神家園的追尋[J].雞西大學學報,2013(02),124-126.
[2]劉俐俐.永遠的故鄉與魯迅的返鄉之路——魯迅《故鄉》的文本分析[J].中南大學學報,2006(01),81-85.
[3]劉思源.魯迅的故鄉情結[J].魯迅研究月刊,2002(08),78-79.
[4]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