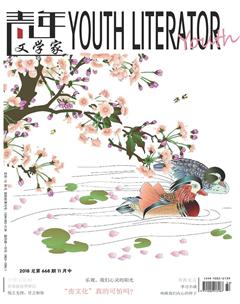唐詩對日本漢詩文產(chǎn)生的影響
劉彥汝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32-0-02
日本漢詩文,即日本人創(chuàng)作的漢詩和具有文學(xué)性的漢文。日本漢詩文是日本文學(xué)的一種樣式和組成部分,是日本人民的精神財富,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日本漢詩文興起于公元七世紀中葉的近江時代,在開始學(xué)習(xí)西方的明治維新時代開始走向衰落。
唐代是中國古代悠久歷史上一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詩的黃金時代。盛唐時期成熟的文字、發(fā)達完善的思想體系、開放的對外政策,使得其在文化上對周邊地域具有強勁的輻射力。日本漢詩文就是其對唐詩進行充分受容的產(chǎn)物。唐詩作為唐代文學(xué)甚至是中國古代文學(xué)的典型代表,其對日本漢詩文的影響不容小覷,具體體現(xiàn)在“形式”“內(nèi)容”“情感”等多個方面。
一、日本漢詩文在形式上對唐詩的模仿
唐詩的興盛并不僅僅源于社會環(huán)境的開放和內(nèi)容情感的豐沛,其形式的多樣化和嚴謹也是鑄就其成為中國古代詩歌巔峰的重要原因。唐代的古體詩分為五言和七言兩種,近體詩則由絕句和律詩組成,唐詩的創(chuàng)作在形式上不僅要符合各自字數(shù)的規(guī)定,句與句之間的格律、韻腳、平仄等也要求嚴格。唐朝詩人通過廣泛地繼承樂府傳統(tǒng),吸收漢魏民歌,不僅沒有使這種嚴謹清晰的詩歌形式導(dǎo)致唐詩樣式上的古板僵化,反而鑄造了唐詩豐富多彩、推陳出新的風(fēng)格。
與盛唐同時期的是日本的奈良時代,此時的日本經(jīng)過了大化改新,社會經(jīng)濟得到了迅速地恢復(fù)和發(fā)展,在文化上也急需復(fù)興。因為強大,所以才被世人仰慕。因此唐詩的流光溢彩在此時很快地吸引了日本的目光。在奈良時代,出現(xiàn)了第一部日本最早的漢詩集《懷風(fēng)藻》,此書中收錄的64名詩人的120首作品多以五言八句為主,在押韻、對仗、格式等方面都能明顯看出模仿唐詩形式的痕跡。例如猿丸大夫的《深山紅葉》:“深山紅葉滿地飄,足踏紅葉路迢迢。聞道鹿鳴聲哀苦,悲感風(fēng)寒秋氣高。”,全詩以七律為框架,嚴合韻律規(guī)則,是日本漢詩借鑒唐詩進行創(chuàng)作的典范。
早期的日本漢詩人在不熟悉唐詩文化內(nèi)涵的情況下從模仿唐詩形式入手,雖不免造成作品缺乏新意、風(fēng)格古板,但形式的嚴格依然是日本漢詩文此后迅速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基礎(chǔ),比起文學(xué)本身,在文學(xué)史上更具有價值。
二、日本漢詩文在內(nèi)容上對唐詩的借鑒
處在中國古代文化發(fā)展巔峰時期之一的唐代,社會開放、文化包容性強。社會環(huán)境的穩(wěn)定與富足,使得唐詩的著眼之處自然而然地富有一種雍容氣象。內(nèi)容上的豐富是時代特點的彰顯,李白“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的狂放灑脫、王灣“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的博大之美、杜甫“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大氣開闊都是盛唐氣象的體現(xiàn)。
而在日本漢詩發(fā)軔期的奈良、平安時代,漢詩仍屬于高雅文化的范疇,能夠接觸并學(xué)習(xí)到漢詩文化的漢詩作者局限于宮廷貴族。唐詩豐饒的意象,給這些囿于宮廷、見聞難廣的詩人們以極大的魅惑,他們紛紛起而仿效,盡情想象那彼岸廣袤原野的風(fēng)光人情。例如嵯峨天皇的《江上船》:“一道長江通千里,漫漫流水漾行船。風(fēng)帆遠沒虛無里 疑是仙查欲上天。”日本其實并沒有這樣煙波千里的大江,詩中描寫的應(yīng)就是中國長江的景色,模仿的痕跡十分明顯。其他如寫閨怨、征戍等題材的作品,也都集思于唐詩,再運用想象之筆,描繪未曾親見的世界,內(nèi)容開闊,與唐詩一脈相承。
另一方面,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也使得唐朝詩人在選材和描寫上更有閑情逸趣來關(guān)注生活上的細節(jié),也更有充分的時間細致地觀覽山川風(fēng)物。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描寫美麗的山光水色和田園情趣,以高適、岑參為代表的邊塞詩派描繪邊疆的奇麗風(fēng)光和風(fēng)土人情,在日本漢詩文中地位最高、最受尊崇的白居易在作詩的選擇上也多取材于生活。
日本的漢詩人敏銳地察覺到了唐詩這一內(nèi)容選材角度,他們學(xué)而升華,與唐詩人一樣,往往從生活自然入手進行創(chuàng)作。奈良朝詩集《懷風(fēng)藻》中所收的117首漢詩中,吟誦四季花鳥風(fēng)月的不在少數(shù);平安朝時代的“敕撰三詩集”(《凌云集》、《文華秀麗集》、《經(jīng)國集》)和《和漢朗詠集》的漢詩中,對節(jié)序景觀的描寫內(nèi)容大增;《和漢朗詠集》卷上的目錄就直接按照春夏秋冬四季順序來排列,其中對春秋兩季的題詠對象尤為豐富,這都是日本漢詩人在廣泛接受唐詩影響進行升華創(chuàng)作而成的。
三、日本漢詩文在情感上對唐詩的吸收
唐詩作為詩史上那顆最璀璨的明珠,其閃耀歷朝歷代甚至遠傳海外的內(nèi)在動力絕不僅僅是華麗的外表和多變的內(nèi)容,其詩中蘊涵著的豐富深沉的情感才是使之經(jīng)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唐朝詩人多為仕途失利之人,政治及生活上的失意往往會使得詩人在情感表達上更趨于細膩和深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在創(chuàng)作中常常注入自己內(nèi)心真實的感受,使得以他們?yōu)榇淼奶瞥妷A麗下不掩失落,壯闊后藏有哀情,平淡中透出傷感,種種感受構(gòu)成了唐詩在情感上耐人尋味的特點。
唐詩復(fù)雜的情感寄托也直接影響到日本的漢詩文創(chuàng)作。日本著名漢詩人清少納言精通漢學(xué)、才思敏銳,由于她十分崇奉《白氏文集》,因此她在《枕草子》一書中所描寫的自然風(fēng)光以及對愛情等人生的感想都鮮明地貫穿了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的自然觀,全書中體現(xiàn)的敏銳纖細的女性感覺以及日本文化中獨特的“物哀之美”也與唐代詩人普遍存有的“感懷傷春”的情感不謀而合。
唐詩廣泛傳入日本后,最受日本人歡迎的詩人是白居易,但日本人最喜歡的一首唐詩,令他們癡迷不已,激動到涕零的,卻是在一個深秋,張繼在蘇州寒山寺寫的《楓橋夜泊》。從這首詩在日本的流行中也可以窺得唐詩與日本漢詩文在情感上的共通。《楓橋夜泊》詩中凄涼、憂傷、略帶著淡淡失落感的美學(xué),正符合日本人對于美的理解。感性文化發(fā)達的日本漢詩人將從唐詩中吸收的淡淡愁緒與本國文化中重要的“物哀之美”和細節(jié)美學(xué)結(jié)合升華,創(chuàng)作出帶有獨特感情的日本漢詩文。例如龍湫周澤的《夜泛湖見月》中的“扣舷一曲無人會,唯有秋風(fēng)入棹歌”一句中那種隱于景物中表達、讀之飽滿立體的“悵然失意”的情感就是詩人接受唐詩情感影響后的產(chǎn)物。
唐詩是中國古代文化中一顆獨特又璀璨的明珠,日本漢詩文是日本漢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兩者的交融共通是在特定歷史時期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chǎn)物。公元7到9世紀,是中國古代的盛唐時代,國家綜合實力的強盛也使得其在文化上的實力邁上新的高峰。強實力帶來的文化自信使得整個唐代文化社會保持著一種積極的開放形態(tài),同時,處于改革維新階段的日本,對文化知識的渴求使得他們廣闊地將眼光放眼世界,這為中日文化的交流創(chuàng)造了外部條件。
這種交流使得日本漢詩文對唐詩的借鑒吸收擺脫了形式的禁錮,也使得唐詩對漢詩文從多方面而非片面的角度產(chǎn)生了影響。回顧整個交互影響的歷程,我們也應(yīng)看到的是:文化的輸出和吸收是不可分割的兩面,永遠抬頭看天時,就看不到自己的不足,當收支不能平衡時,屬于自己的獨特文化就會逐漸被侵蝕。
中日文化背景不同,再之山川阻隔,風(fēng)云異向,中國文學(xué)對日本漢文學(xué)的影響并不是直接、對應(yīng)、平衡、全面的。日本漢詩文文化在其發(fā)展中,也形成了自己鮮明的民族性,這表現(xiàn)在民族意識、民族文化的浸透以及對文體文風(fēng)獨特的選擇等各方面,有著豐富的民族文化內(nèi)蘊。
千百年前,唐詩漂洋過海,漂到了隔著海灣的這個國家。日本漢詩人謙卑地學(xué)習(xí)與改變,吸收與升華,讓烙著唐詩烙印的日本漢詩文發(fā)展成為世界漢學(xué)中的一個重要部分,而在千百年后的現(xiàn)在,這個與當時的世界已滄海桑田的時代,我們冷靜觀之,回顧唐詩,還會是什么呢?是鳳凰臺上呼嘯的風(fēng)聲,是寒山寺里悠悠的鐘音,是那段怎么樣也走不完的行路難,還是月下獨酌時那杯孤獨的將進酒呢?不敢說斯人已逝,只是我們都知道,大和民族俯首低眉請來的唐詩,那段詩意的黃金歲月,早已悠悠地飄走,難以再來了。
真正的謙和,源于真正的自信,希望在不久以后的將來,能再看到唐詩與漢詩文的再興,再看到那個文化取長補短、互通有無的盛況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