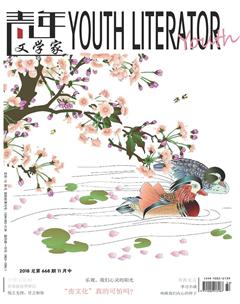嘉慶《溧陽(yáng)縣志》文學(xué)史料價(jià)值淺論
萬(wàn)海娟
摘 要:嘉慶《溧陽(yáng)縣志》是在承繼前代縣志的基礎(chǔ)上編纂的一部通志,搜采精博,體例謹(jǐn)嚴(yán),為邑志中之佳作。地方志作為一個(gè)地區(qū)文化基因的儲(chǔ)存庫(kù),這部志書(shū)不僅具有重要的史料價(jià)值,而且對(duì)于保存地方文化有重要貢獻(xiàn)。
關(guān)鍵詞:嘉慶《溧陽(yáng)縣志》;文學(xué)價(jià)值;史料價(jià)值
[中圖分類號(hào)]:K29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139(2018)-32--02
中國(guó)素來(lái)就有修史的傳統(tǒng),國(guó)有史傳,地有方志,族有族譜。古代地方志的編纂流傳至今,保存了相當(dāng)豐富的文獻(xiàn)資料,具有很高的史料文獻(xiàn)價(jià)值。清朝統(tǒng)治者非常重視地方志的編纂,地方志大部分屬于官修,其主持修纂的往往是本地的長(zhǎng)官和名望紳士,嘉慶《溧陽(yáng)縣志》便是由溧陽(yáng)知縣陳鴻壽和李景嶧主修、史津和史炳編纂的。陳鴻壽是清代著名篆刻家、西冷八家之一,清嘉慶辛未年,聘史炳、史津等纂修邑志,在延用《江南通志》體例的基礎(chǔ)上,廣泛采用舊有志書(shū)的文獻(xiàn)史料,訂舛正訛,于嘉慶十八年付梓刊行。
溧陽(yáng)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邑,文化底蘊(yùn)深厚。早在東周列國(guó)時(shí)就已有“溧陽(yáng)”之名,至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guó),始設(shè)溧陽(yáng)縣。嘉慶《溧陽(yáng)縣志》共計(jì)十六卷。前有序、舊序、銜名、凡例、目錄,以及15幅溧陽(yáng)縣志圖,并附萬(wàn)歷至清乾隆間縣志《敘》8篇、跋1篇。后分輿地志四卷,河渠志、食貨志、學(xué)校志、武備志、職官志、選舉志各一卷,人物志四卷,藝文志一卷以及雜類志一卷,具有豐富的歷史文獻(xiàn)價(jià)值。
一、《嘉慶溧陽(yáng)縣志》的文學(xué)價(jià)值
《嘉慶溧陽(yáng)縣志》并沒(méi)有獨(dú)立設(shè)卷收錄詩(shī)歌,但是在《輿地志》《職官志》等其他卷記載溧陽(yáng)風(fēng)情、名宦時(shí)將有關(guān)文學(xué)記錄了下來(lái)。僅《輿地志》之“寺”“觀”這兩節(jié)便保存了近60首詩(shī)詞,如孟郊的《唐興寺觀薔薇花,同諸公餞陳明府》,董正域《勝因寺》,張孝祥《三塔寺阻雨》《過(guò)三塔寺》,虞謙《大環(huán)山寺》,陳名夏《西寺坐贈(zèng)宋介卿》《泰安寺》《泰虛觀記略》,吳穎《西寺老梅》,馬世俊《東寺訪源公》《湖庵西禪堂題詞》,許堅(jiān)《游下山凈上院》,釋行鑒《過(guò)優(yōu)云禪院》,狄沖《屏風(fēng)山寺》,史徐《龍興寺》,蔣珙《山前寺》,周絳《太虛觀詩(shī)》等。一些詩(shī)人并沒(méi)有獨(dú)立的詩(shī)文集流傳于世,后人考證這些詩(shī)人時(shí),往往缺乏文獻(xiàn)資料的支持,通過(guò)縣志中保存下來(lái)的文學(xué)史料,為考證研究工作提供了真實(shí)的記錄。
(一)孟郊《游子吟》
《游子吟》是孟郊的名篇,題下自注“迎母溧上作”。在嘉慶《溧陽(yáng)縣志.職官志》中記載:“貞元末年任見(jiàn)名宦”。[1]孟郊一生顛沛流離,41歲才中進(jìn)士,50歲才銓選,分配九品溧陽(yáng)縣尉,便將老母親裴氏接到溧陽(yáng)。但孟郊并不能適應(yīng)官場(chǎng)的來(lái)往應(yīng)酬,只能寄情山水。于是他常帶小吏騎著毛驢,去投金瀨射鴨吟詩(shī)以解悶,或帶著隨從到平陵遺址悠游。這引起了縣令的不滿,孟郊的俸祿被扣了一半。他因此灰心喪氣而辭職歸鄉(xiāng)。清嘉慶《溧陽(yáng)縣志》中,平陵城及射鴨堂被列為溧陽(yáng)名勝,由蕪湖汪鴻繪圖,史炳題詞:“射虎家兒,勲封六縣,如何竹弓,笑彼浪戰(zhàn)。”[2]明弘治《溧陽(yáng)縣志》在“名宦”篇中已經(jīng)收錄了孟郊的簡(jiǎn)介,清嘉慶《溧陽(yáng)縣志》在“名宦”“文題名”中也有孟郊的條目介紹,并收錄了五首詩(shī)作,在“輿地志”之寺一節(jié)中記載勝因寺時(shí),還收錄了孟郊的《唐興寺觀薔薇花,同諸公餞陳明府》:
忽驚紅琉璃,千艷萬(wàn)艷開(kāi)。佛火不燒物,凈香空徘徊。花下印文字,林間詠觴杯。群官餞宰官,此地車(chē)馬來(lái)。[3]
孟郊雖官場(chǎng)不順,但溧陽(yáng)這片美麗的土地給予了孟郊以安慰。在縱情山水間,徘徊賦詩(shī),留下了膾炙人口的名篇佳作。
(二)李白三到溧陽(yáng)
詩(shī)仙李白與溧陽(yáng)也有不解之緣,曾多次來(lái)到溧陽(yáng),留下10余首不朽的名篇。公元747年的秋天,李白第一次來(lái)到溧陽(yáng),在郊外寫(xiě)下了《游溧陽(yáng)登北山望瓦屋山懷古贈(zèng)同旅》。公元754年,李白二到溧陽(yáng),縣令鄭晏宴請(qǐng)李白,李白以《戲贈(zèng)鄭溧陽(yáng)》詩(shī)答謝: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無(wú)弦,漉酒用葛巾。
清風(fēng)北窗下,自謂羲皇人。何時(shí)到栗里,一見(jiàn)平生親。[4]
詩(shī)人借陶淵明自喻以表明與其一樣的高風(fēng)亮節(jié),心態(tài)怡然自得。鄭晏還邀請(qǐng)李白為史貞女撰寫(xiě)碑文《溧陽(yáng)瀨水貞女碑銘并序》。第三次來(lái)溧陽(yáng)是在公元756年的春天,嘉慶《溧陽(yáng)縣志》記載:“天寶十五載之春,太白與張旭相遇于溧陽(yáng),而太白又將邀游東越與張旭登樓宴別,乃作《猛虎行》詩(shī)云: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腸斷非關(guān)隴頭水,淚下不為雍門(mén)琴……溧陽(yáng)酒樓三月春,楊花漠漠愁殺人。胡人綠眼吹玉笛,吳歌白纻飛梁塵。丈夫相見(jiàn)且為樂(lè),槌牛撾鼓會(huì)眾賓。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yú)笑寄情相親。
此詩(shī)又名《宴別張旭于溧陽(yáng)樓》,敘述安祿山攻占東都洛陽(yáng)造成的生靈涂炭。借張良、韓信以抒發(fā)身處亂世,卻報(bào)國(guó)無(wú)門(mén)的憂愁。嘉慶《溧陽(yáng)縣志》記載:“(太白樓)元時(shí)猶有登臨懷古之作而莫詳其處。”除此以外,嘉慶《溧陽(yáng)縣志.職官志》中還記載了《贈(zèng)溧陽(yáng)宋少府陟》、《登黃山凌 臺(tái)送族弟溧陽(yáng)縣尉濟(jì)充泛舟赴華陰》、《李白酒樓歌》[5]等詩(shī),反映了安史之亂后,李白為派遣心中煩悶而再游溧陽(yáng),借與故友重聚排遣憂思愁緒。
二、《藝文志》的史料價(jià)值
藝文志發(fā)軔于東漢班固的《漢書(shū)》,目是為了整理文獻(xiàn),考訂學(xué)術(shù)源流。方志藝文志不僅具有正史藝文志中“辯章學(xué)術(shù),考訂源流”的作用,而且更傾向于保存地方文獻(xiàn),嘉許鄉(xiāng)賢文采,進(jìn)行道德教化。我國(guó)地方志書(shū)最早有“藝文”內(nèi)容的是北齊宋孝王《關(guān)東風(fēng)俗傳》,被認(rèn)為“無(wú)疑開(kāi)了后世地方志中載藝文的先河”[6]。方志藝文志因時(shí)因地而異,一般有兩種基本體例:其一是記當(dāng)?shù)卦?shī)詞文賦,是文選式的詩(shī)文總集;其二是記典籍著述,是目錄式的文獻(xiàn)匯編。嘉慶《溧陽(yáng)縣志》采用的即是目錄學(xué)形式,按照經(jīng)史子集分類并按年代編排。由于很多古籍文獻(xiàn)不能留存下來(lái),后人只能在“藝文志”中看到前人著作的目錄和內(nèi)容。利用縣志所提供的史料可以對(duì)溧陽(yáng)文學(xué)家的身世研究作進(jìn)一步補(bǔ)充,并加深溧陽(yáng)名門(mén)家族文學(xué)的研究。
“彭馬史狄周,吃穿不用愁”,這五大姓氏是溧陽(yáng)鉅族,清人劉獻(xiàn)廷《廣陽(yáng)雜記》中也有記載:“東吳尤重世家。宜興推徐吳曹萬(wàn),溧陽(yáng)推彭馬史狄,皆數(shù)百年舊家也。”[7]在藝文志主中可以看出,明清時(shí)期五大家族的文化崛起。溧陽(yáng)狄氏之祖,是南宋狄英,《溧陽(yáng)縣志.始遷》中記載:“狄英,字天秀,天水人。隨宋高宗南渡,舉賢良方正,任江浙省副使,開(kāi)府溧陽(yáng)。致仕,遂居胥渚里,今狄氏祖也。”[8]狄氏在與江南文化的碰撞融合之中,逐漸成為名門(mén)望族。在嘉靖萬(wàn)歷年間狄氏崛起,狄氏子孫由祖上隱德不仕而涉足仕途,這是江南文風(fēng)轉(zhuǎn)變的反映。狄斯彬《山居野志》實(shí)際上就是他獨(dú)立編寫(xiě)的《溧陽(yáng)縣志》,其中很多素材被后世編溧陽(yáng)縣志者所采納。《藝文志》中收錄了狄敬撰《尚書(shū)蔡傳衍義》《潼關(guān)志》《治河紀(jì)畧》,狄恂《禮記家訓(xùn)》,狄字《禹貢傳》,狄咸《三傳分國(guó)》,狄斯彬《山居野志》《地理正傳》《稽命集》《明律詩(shī)鈔》《竹湖遺稿》《玉華子游藝集》,狄寬《史學(xué)提要輯注》。溧陽(yáng)彭氏在江南歷史悠久,江南遷徙各地奉溧陽(yáng)彭氏為“正溯”。彭顯后又過(guò)了五代孫名彭效,始遷居溧陽(yáng)南門(mén),為溧陽(yáng)南門(mén)始祖,這一支世稱“溧陽(yáng)南門(mén)彭氏”。《藝文志》收錄彭光斗《檀弓序木》《三國(guó)志校本》《瀨上遺間》,彭謙《菱東詩(shī)集》,彭若龍《少白詩(shī)集》,彭九齡《西嚴(yán)詩(shī)集》。不僅保存了當(dāng)?shù)剜l(xiāng)賢的重要文獻(xiàn),也為日后做進(jìn)一步的考證梳理做了基礎(chǔ)工作。
地方志作為我國(guó)獨(dú)有的文化傳承方式,其價(jià)值歷來(lái)受到重視。嘉慶《溧陽(yáng)縣志》體例比較完備,內(nèi)容鮮明,條理清晰,比現(xiàn)存溧陽(yáng)縣其它舊志略好。不只簡(jiǎn)單的提供了文獻(xiàn)資料,也是對(duì)前代或同代縣志的補(bǔ)充和完善,還為后世編纂江南地方志書(shū)提供了寶貴資料,具有較高的文學(xué)價(jià)值、史料價(jià)值。地方志是連接國(guó)家與地方的重要紐帶,從地方志中可以窺見(jiàn)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發(fā)展的整個(gè)面貌,對(duì)于研究家族文學(xué)、地方文學(xué)和時(shí)代文學(xué)而言具有相當(dāng)重要的意義,因此我們應(yīng)該更加重視地方志,使之物盡其用。
注釋:
[1]李景嶧、陳鴻壽:《嘉慶溧陽(yáng)縣志.職官志》,第192頁(yè)。
[2]李景嶧、陳鴻壽:《嘉慶溧陽(yáng)縣志》,第19頁(yè)。
[3]李景嶧、陳鴻壽:《嘉慶溧陽(yáng)縣志.輿地志》,第107頁(yè)。
[4]李景嶧、陳鴻壽:《嘉慶溧陽(yáng)縣志.職官志》,第192頁(yè)。
[5]李景嶧、陳鴻壽:《嘉慶溧陽(yáng)縣志.職官志》,第192頁(yè)。
[6]倉(cāng)修良:《新修方志中藝文志不可少》,《中國(guó)地方志》1992年4月。
[7]劉獻(xiàn)廷:《廣陽(yáng)雜記》,光緒刻《功順堂叢書(shū)》本,卷1,第54-55頁(yè)。
[8]李景嶧、陳鴻壽:《嘉慶溧陽(yáng)縣志.人物志.始遷》。
參考文獻(xiàn):
[1]倉(cāng)修良.新修方志中藝文志不可少[J].中國(guó)地方志,1992,(4).
[2]李景嶧、陳鴻壽.嘉慶溧陽(yáng)縣志.
[3]詹锳.李白詩(shī)論叢[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08.
[4]郭沫若.李白與杜甫[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71.10.
[5](清)劉獻(xiàn)廷著.廣陽(yáng)雜記[M].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5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