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歐洲建筑“留改拆”看城市更新
一座城市或一片建筑,是社會歷史文化的構成部分,它們帶有明顯的地域特征,豐富多彩,各具特色。
社會發展越是現代化,人們就越珍視自己的歷史文化。面對精美但失修的老舊建筑、熱鬧卻殘損的街區,是拆是留,是棄是珍,考量著現代人在文化與經濟、公平與效率、溫情與欲望之間取舍的智慧。
縱觀世界各地,法國、德國、意大利、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都十分重視和保護自己的城市、建筑及景觀遺產,建立了完善的保護制度。回望當下,從 “拆改留”到 “留改拆”,不僅僅是文字的變化,更是一種態度的轉變:一座城市如何看待歷史、如何處理遺存,將影響她的未來。
對老舊建筑和城市風貌進行保留和保護,國際上有很多成功案例。盡管因為每座城市、各個地區的歷史文化背景、發展動力各不相同,對城市的保護并無固定規章可循,但從以下三個案例可以看出,保護與發展并非一對矛盾,文化遺產實則可以撬動城市可持續發展。
通過歷史建筑的保護與利用、歷史街區的保護與再生、歷史城鎮的保護與復興等等這些具體而富有實效的行動,歐洲國家將文化遺產保護與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緊密結合起來,讓文化遺產充分發揮其社會、經濟、文化和環境的效益。

德國案例
柏林國會大廈:歷史建筑串起城市過去與未來
一座歷史建筑往往具有不同的藝術、歷史、科學價值,從而具有社會和文化的意義。因此,歷史建筑的保留保護就不僅僅是簡單的物質遺存,還應充分發揮其價值,這就是再利用。好的再利用的前提,是尊重歷史建筑的文脈,從而將城市的過去和未來串聯起來。
柏林國會大廈建成于1894年,由德國建筑師保羅·瓦洛特設計,呈現出鮮明的古典主義風格。1933年,著名的“國會大廈縱火案”燒毀了國會大廈的中央穹頂,毀壞了議會全體會議大廳。簡陋修復后的國會大廈隨之成為納粹德國宣傳部的活動中心,并在“二戰”開始后成為希特勒的軍事堡壘。1945年4月30日,蘇聯紅軍攻占柏林,把紅旗插上國會大廈的屋頂,宣告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但同時,該歷史建筑也遭到了嚴重的損毀。
1990年德國統一后,人們開始討論這幢具有象征意義的歷史建筑的保護、修復和再利用的問題。首先,確定其功能為“ 德國聯邦議院”,以更好地承襲之前的建筑功能;其次,面對在“二戰”中損毀嚴重的建筑內部和中央穹頂,德國政府于1992年組織了國際設計競賽。1994年至1999年,中標建筑師福斯特通過修復立面、替換內部結構體系的方式解決遺產本體保護與內部功能的關系。而在最有象征意義的中央穹頂的設計中,設計師并沒有去仿造一個一模一樣的古典穹頂,而是采用裸露全鋼結構,支撐起一個全新的玻璃穹頂。

這個方案一方面體現了遺產保護的真實性原則,沒有 “以假亂真”,另一方面藝術性地將古典風格、被炸毀的歷史和當前的功能需求進行了巧妙結合。如今,無論柏林市民還是參觀者,通過這樣的保留保護,都能夠深深感知歷史的厚重、對過去的反思和對未來的期許,這是對文化的尊重,也是對歷史的敬畏。
點評:這一案例非常值得我們在歷史建筑的保留保護過程中借鑒。無論是標志性的文物建筑,還是比較普通的民居院落、巷弄宅里,都需要在研究分析建筑特征及其價值的基礎上,進行尊重歷史文脈的保留保護和活化利用。
法國案例
巴黎市中心馬萊區:歷史街區價值重現
“遺產保護與價值重現”是法國遺產保護的雙重目標。政府通過強有力的全國性政策平衡遺產的公私屬性,由此構建兼具文化多元性和社會包容性、歷史與現代并存、宜居而充滿活力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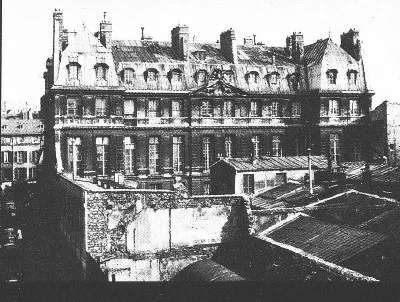

現在已經很難想象20世紀50年代的法國:城市中心被戰爭毀壞,街區殘破骯臟,大量城市中心區、尤其是歷史地區,被劃定為“不衛生街區”。當時最有誘惑力的城市問題根治方案是像許多衛生專家主張的那樣:拆除重建。然而人們很快發現,伴隨著這些整體改造方案,城市的特色風貌景觀也在快速消失。而巴黎之所以是巴黎,里昂之所以是里昂,并不是因為其郊區景觀有所差別,而在于其歷史悠久的城市中心,在于其不同時代所形成的歷史街區。
1962年頒布的 《馬羅爾法令》,第一次將城市發展和建筑及遺產保護聯系起來。根據該法令,巴黎劃定了馬萊區和第七區兩個保護區。
馬萊區是巴黎市中心一個非常獨特的街區,又是法國現有保護區中最復雜的一個。它既集中了很多16世紀和17世紀的豪宅,同時又集中了一大批特色手工業作坊和商店。但在19世紀,這個地區逐漸衰敗成一個貧窮的手工業區。1960年代初期,這里居住擁擠,衛生條件差,曾被劃定為巴黎市中心“不健康”的街區。

1965年,馬萊區被指定為法國的保護區,面積為120公頃。保護區 《保護和價值重現規劃》規定:在保護區內所有新的建設和改變都必須得到準許。國家被賦予了絕對的權力來執行規劃所確定的保留保護措施,同時國家和城市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來鼓勵業主積極參與自己所有的遺產的保護。
對于列級保護的歷史建筑,國家與業主達成協議:業主在沒有獲得有關部門同意的情況下,不能對自己的保護建筑進行任何變動,而若進行必要的修繕則可申請獲得維修成本25%至50%的國家補助。國家還鼓勵業主將自己的產業向公眾開放,并根據參觀者的數量,在剩余成本的 50%至75%之間可減免稅收。對于注冊登記的歷史建筑補助相對少一些,同時保護的要求也較為簡單。
根據規劃,保護區內176幢列級保護的歷史建筑和526幢登記保護的歷史建筑得到了修繕,其中有一些成為了重要的文化空間,比如畢加索美術館、巴黎歷史博物館等等。盡管物質性的保護和修復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客觀上卻導致了租金的上漲和街區紳士化傾向。大量居民外遷,工人、小業主逐漸被自由職業者和從事高級職業的人群所取代。為緩和這種變化,巴黎市政府將保護區中的一些街區改造為社會住宅區,低租金出租給中下層收入的居民。馬萊區的一部分被列為巴黎市八個 “住宅改善實施計劃”之一。這一計劃通過政府補貼,幫助業主自行對房屋進行維修,并鼓勵他們以低租金出租房屋,租金越低補貼越高。這種政策有利于保持原有的社會結構,緩和過度劇烈的居民結構變化,使城市中的中下層居民能夠繼續生活在被保護和改善了的巴黎城市中心。 (圖①為改造后優雅而充滿活力的馬萊區街景。)
點評:如何讓生活、工作在歷史街區里的人們能夠體面、舒適,甚至優雅地生活,是城市更新中不可回避的現實。面對同樣寸土寸金的歷史街區,巴黎更強調歷史、文化、社會和環境效益的協調,以公私合作的方式鼓勵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積極參與歷史建筑的修繕改造,讓風貌區褪去逼仄、還原風情。
意大利案例
熱那亞老城:歷史城鎮植入新功能
和一座歷史建筑、一片歷史街區相對有限的范圍相比,一座歷史城鎮的保護與復興更需要有強烈的政治意愿、明確的工作目標、強大的統籌能力和有效的實施機制。


意大利熱那亞老城在20世紀80年代因為港口和工業的危機,出現了衰敗的現象:日益惡化的建筑遺產,不斷加劇的社會沖突,愈加嚴重的邊緣化等問題明顯。自20世紀80年代末至2000年初,熱那亞大都市區范圍內開展了大規模的城市更新實踐,老城的保護與復興是其中重要一環,其根本目的是通過物質空間品質提升、功能調整和公共活動植入,來激發老城的活力。
老城復興的觸發點是1989年當地政府決定將熱那亞大學建筑學院植入到圣·西維斯托修道院遺址。這一舉措既很好地尊重了古代遺址的歷史,同時也使得老城區因為年輕人的加入而充滿活力:他們在此學習和生活,租用學校周邊經過保護修繕的歷史建筑,促進了當地零售批發產業的復興,而這又進一步吸引了其他社會群體的融入,為城市重新注入了生機。
接著,1992年,為了紀念哥倫布到達美洲500周年,熱那亞舉辦了盛況空前的哥倫布世界博覽會。雖然在城市濱水公共空間興建了一些休閑娛樂設施,也吸引了大量游客,但未能將這個文化大事件與老城的持續發展結合起來。
在深刻反思后,熱那亞充分利用了2001年G8峰會和 2004年歐洲文化之都這兩次城市大事件,爭取并獲得了從歐盟至地方政府各層面公共財政的支持,并制定了具有前瞻性的戰略和系統性的公共政策,進行了一系列的城市復興項目,從而轉變老城物理的、經濟的和社會的衰敗,達到了城市整體復興的目標。

首先是老港口的復興。港口的最南端碼頭利用老的倉儲建筑改造成了博覽會場館。其北側的碼頭則建造了水族館,如今每年有120萬游客參觀,成為濱水區域吸引游客的主要場所。港口最北部幾乎被廢棄的碼頭則植入了經濟商業學院,帶動了新的居住和商業功能。2004年還設置了一個航海高等學校和海洋航海博物館。老港口區域通過旅游、文化和老港口記憶保護的有機融合,重新成為城市富有活力的一部分。(圖②為更新后的老港口海濱。)
其次是在老城中心進行 “針灸式”功能植入。如圣阿戈斯蒂莫博物館綜合體的修繕、托塞劇場的開放、公爵宮殿文化中心和卡洛·費利切劇場的開放等。
第三是將老港口與老城中心重新聯系起來,并對串聯重要文化節點的公共空間進行品質提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老城道路系統和沿街歷史建筑的修繕,其中的 “新街和羅利宮殿群”在2006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遺產名錄》。
在熱那亞整個城市復興過程中,地方政府并未直接介入具體實施工作,而是承擔了管理與推動、協調與整合各類項目的職責。通過公共財政的投入帶動大量公有企業、私有企業、各類機構和組織以及個人的投資,并通過多個政府部門共同制定策略和長期行動框架,包括改善物質和生態環境、改善通達性、完善社會服務體系和發展經濟產業等。看得出,熱那亞各個城市更新項目形成了城市整體復興的一盤棋。
點評:從熱那亞的成功經驗我們可以看到,老港口濱水區的更新和整個老城的復興計劃不是將歷史區域看成一個旅游中心或主題公園,而是積極探索如何將其改造成為永久居民和臨時人口服務的綜合性場所。由此,熱那亞老城重新成為了一個富有吸引力的居住、工作和休閑場所,舒適、溫馨、宜居,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新居民和新的城市用戶 (包括學生、游客、夜間休閑者等)的進入,帶動了整個老城的復興。
(摘自9月9日《文匯報》。作者為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