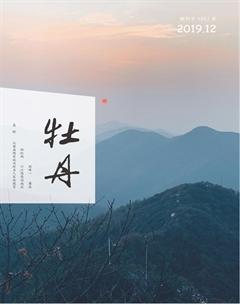《行行重行行》詩意解讀

《古詩十九首》中第一首為《行行重行行》,追本溯源,這首詩作于漢代,此時天下分崩,社會動蕩不安,詩人觸景生情,借物言志,通過纏綿相思的離亂之歌,表達自己心中的孤苦和惆悵之情。讀者在對其進行詩意解讀時,需要結合時代背景和當時的民俗風情,并與漢代文學創作特點聯系在一起,加深理解,做到入心、入情、入理,為學習古代詩詞提供有力支持。
我國歷史文化底蘊深厚,在詩詞歌賦方面成就顯著,一些膾炙人口的詩文經久傳誦,內涵豐富,讀之令人感慨良深。尤其是漢代詩詞,具有較強的代表性,能夠體現漢文化、風俗和社會背景。一些詩詞不僅文辭華美,還蘊含真摯的情感,通俗易懂,又令人回味悠長。因此,讀者需要對其深入剖析,拓展性思考,增強理解,這有利于傳承和發揚中華傳統文化。
一、從古典文學角度進行詩意賞析
(一)天涯路遠,相見無期
《行行重行行》前六句為“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主要進行情境描述與回憶,流露出路遠難見的無奈,預示相見無期。
“行行重行行”,簡單的描述,卻飽含真情。不知女子送丈夫遠行的腳步走了多久還未停下來,這每一步都飽含深切的不忍分別之情。“與君生別離”,意思為女子與丈夫活生生地別離,帶有幾多不舍之情,更多一些無奈。“相去萬余里”,是說女子與丈夫從此相距萬里,預示相見無期,這既是對追憶的一種描述,又為后面的相思之苦提供了鋪墊,無法相見,才更加相思。“各在天一涯”,女子與丈夫天各一方,依然表達彼此之間相距遙遠,如何才能長相廝守,只能通過精神寄托,聊以自慰。“道路阻且長”,路途那樣艱險又那樣遙遠,雖然是描述路途,但表現出思婦想要去尋找自己的夫君的愿望。“會面安可知”,不知道見面是在什么時候,表現出難以相見,卻又期盼相見,雖然希望渺茫,但依然不放棄的相思之情。這種別離是讓人難以忍受的,雖然相見希望渺茫,但從未割舍這種相思之情。
(二)滿心愁情,更傷別離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顧反,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表現了思婦內心的愁苦、傷情,并因這種思念而日漸憔悴。“胡馬依北風”,北馬南來依然留戀著北風,無論走到哪里,都會思戀自己的家鄉。詩中通過北馬這個意象,表現思婦對丈夫的一種理解,同時又表現出一種疑問:丈夫是否還在思戀著自己?“越鳥巢南枝”,南鳥北飛筑巢依然在南枝頭,表現思婦對丈夫無論走到哪里,都時刻惦念自己的期盼,更表達一種期望,期望丈夫回到自己的身邊。“相去日已遠”,彼此分離的時間長久,表明思婦已經與丈夫很久沒有聯系,更添牽掛之情,更說明相見無期。“衣帶日已緩”,衣服越發寬大,人越發消瘦,這是因思念丈夫而產生的一種悲情,日日思念,導致寢食難安,令人為之動容。“浮云蔽白日”,思婦注視著遠方等待丈夫的歸來,但見浮云遮住太陽,難以看得更遠。同時,云遮日還表達一種在逆境中目標難以實現的涵義,表達思婦處境艱辛。“游子不顧反”,遠在他鄉的游子卻并不想回返,這是轉折之筆,思婦此時認為丈夫不回返,并不是因為天涯路遠,而是丈夫心中沒有回返之意,帶有一種哀怨之情。“思君令人老”,因思婦想念丈夫而加劇日漸衰老,表達一種相思帶來的感傷,又流露出時光易逝,歲月無情的感慨,如果不能及早相見,恐怕沒有相見的機會。“歲月忽已晚”,又是很快到了一年的年關,說明歲月不知不覺中逝去,這種思念使人忘記了一切,生無所戀。在這一部分內容中,著重寫思婦因與丈夫難以相見所產生的悲苦之情,帶有些許的哀怨,但這種哀怨并沒有影響她對丈夫的思戀。
(三)幾多無奈,真情遙寄
“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這部分表達思婦的無奈,只能通過這樣的祝愿,排遣自己內心對丈夫的牽掛。雖然只有一句,卻屬于整首詩的轉折之筆。“棄捐勿復道”,還有許多心里話都不說了,為什么不說,因為說不盡,因為越說心里越苦,思念之情越濃,使自己無法自拔,所以不說。“努力加餐飯”,只愿你自己多保重切莫受饑寒。無法與丈夫相見,只能送去祝福,這種祝福雖然簡單,但卻飽含真情。從這一句話之中,可以體會到思婦在傾訴自己內心的痛楚之后,對其與丈夫之間的別離又多了幾分感悟,雖然不能忘卻,但逐漸使自己超脫痛苦,增加了幾分理性的認識,通過祝福表達情感,而不是期盼丈夫回歸。可見,原有的思念哀怨之情已經得到升華,女子認為彼此之間只要真心相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雖然天各一方,只要丈夫過得好,那么自己就安心了。此外,這里還有一層含義值得討論,即努力加餐飯也是指自己要如此,不僅僅指丈夫,一語雙關。
二、從歷史背景角度進行詩意賞析
(一)世事離亂,民生多艱
漢朝末年,社會分崩離析,動蕩不安,民生多艱。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的《行行重行行》,不僅表達男女之間的思念之情,還表達社會帶給人們的傷痛。為什么思婦與丈夫天各一方且路途艱難,是否是因為這種社會形勢,使其不得不如此呢,這值得反思。這首詩雖然注重愛情方面的表白、思念和感悟,但卻較為悲苦。與只表達一種炙熱的思戀之情的情詩相比,這種悲苦情調的體現,與當時的社會背景相契合。除此之外,文中還寫到“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以“胡馬”和“越鳥”為起筆更說明這一問題。當時為東漢末年,三國鼎立,后為魏晉南北朝,這一階段戰亂頻仍,百姓流離失所,且胡人內遷現象嚴重,政權更迭較快,并存在一些少數民族政權。在這一歷史環境下,思婦需要一種依托,所以更加思念自己的丈夫。因此,這首詩描述的情感也代表了當時所有家庭分離人們的心聲,表達了對社會現狀的一種無奈和情感的發泄,而最后一句對丈夫的祝福,也可以引申為對國家發展的期望,期盼國家能夠早日統一,長治久安,減少這樣的人生別離。
動亂時期,民眾生活在饑寒交迫之中,往往衣食難以保障,生命難以保全。所以,思婦對丈夫的這種情感是一種傾訴,并帶有強烈的想象意味。既然已經天涯相隔,丈夫是否依然活在人世,難以預知。且結尾之處,思婦希望丈夫莫饑寒即可,可以認同為一種祝福,也可以拓展為一種擔憂,這種較為簡單的訴求可以表達情感的真摯,也多了幾分動亂時期的無奈,民眾的愿望較為簡單。
(二)期盼團圓,穩定安樂
整首詩在結尾處,可以說是一種大轉折,將原有的愁情化作了一種期盼,不僅僅是期盼丈夫,也是在解脫自己。在這樣的年代下,坐愁相思了無益,如果不能自拔,整日愁苦不堪,那么不但人顏憔悴,且心也隨之老去,即使有相見之日,恐怕也難以留得健康之身,那么這時的別離后的期盼便不只是早日相見,還需要學會自我解脫。詩文講述了思婦對分離的回憶,思念過程的波動與悲傷以及真情的寄托,流露出思婦希望團圓、穩定、安樂的心愿。以詩文首句“行行重行行”而言,送別之路越走越遠,也表達出思婦與丈夫之間的距離也就越來越遠,如果腳步永不停歇,那么相見更無從談起,所以,詩文也表達出在這一社會背景下的求穩之心。
我國古典文化中,文人以家國天下安定為己任,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最早來自于《大學》,而無國何談家的思想在當時根深蒂固。詩文中家庭破碎,且相見無望,表達的也是對社會現狀的一種痛心,女子希望國家穩定,希望與丈夫相見。家是國的小單元,如果每個家庭都支離破碎,國家何談強大、何談穩定。民為邦本,民眾的這種疾苦是時弊的表現,并非是個人獨有的。因此,詩文在結尾處一改感傷之調,而是有了一種坦然,心在即可,莫要自傷,事實無法改變的時候,則要面對,不能自損其身,更要懷有希望。
三、從世風民俗角度進行詩意賞析
(一)綱常倫理,夫唱婦隨
漢朝尊崇儒術,且無論官民皆對儒家思想較為重視,三綱五常,不可有違。整首詩字里行間流露出思婦對丈夫的遠行的不舍與思念,可以感受到思婦對丈夫的遠行,情緒幾經起伏,思婦對于丈夫的遠行并不是支持和認同的態度。但是,思婦依然表露一種強烈的思念,而不是明顯的不滿。這與當時的文化息息相關。從愛情觀的角度分析,思婦對于丈夫感情至深,即使天各一方,相見無期,這種情感也不能使她放棄。從道德觀的角度分析,當時婦女的地位低于男子,不能對丈夫隨意指責,所以文中多有疑問,卻又比較隱晦地表達,并未直接說出思婦心中的想法。除此以外,“行行重行行”,除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發人深省以外,更值得討論的是為什么思婦沒有和丈夫一起遠行。這可能原因較多,但不能排除丈夫不想帶領妻子一起走,如果原因如此,那么整篇文章在離別之苦的格調上將會增加幾分怨懟之苦,更多的將是表達自己對曾經情感的追溯,對美麗愛情的一種憧憬。與此同時,思婦在對丈夫思念過程中,也表露出自己急切想要知道丈夫內心所想的強烈意愿,千里之遙,相隔日遠,丈夫是否還像從前一樣對自己這樣思戀。思婦想要見到丈夫并不僅僅是因為相思,還有重要一點,則是想要了解現在丈夫是否依然初心不改。總體而言,這首詩中表達的情感較為復雜,思念之情只是其中之一,還有思婦內心對丈夫的一種不解。
(二)情理并重,通俗純樸
漢時受當時文化背景的影響,民眾普遍文化素質較低,詩詞曲賦的含義只有較為容易理解,才能夠廣為傳誦。本文研究的《行行重行行》,屬于當時廣為流傳的詩詞之一,具體由何人所做,未可得知。多數評價皆注重于情感基調,關于文章所表達的道理則研究較少,有失偏頗。其中“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一句,表達的不僅是一種思念家鄉之情,更有深層含義,即飛禽走獸尚且眷顧家鄉,更何況是人呢,作為遠在外地的丈夫,是否應該想想回轉之事呢。“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一句,蘊含深刻的人生哲理,即:在思念之中,人容易老去,已然忘卻了周圍的事物,轉眼之間一年便過去,“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這樣快的時光不會給人過多等待的機會,思念之情越強烈,人老卻越快,人老卻越快,相見機會越渺茫,包含一種辯證的關系,引申出這一無法解決矛盾,所以在后一句提出“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表達自己的真心,想念依然如故,但少了些許傷痛,自己需要面對現實,不能過于執著,“努力”加餐飯,并不是“多”加餐飯,則可以側面反映出丈夫并不容易,這可以理解為對丈夫的一種勉勵。
四、結語
本論文首先對《行行重行行》的詩意進行解讀,然后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文化背景展開分析。整首詩情感基調以悲苦為主,滿懷相思與牽掛之情,并流露出些許哀怨和懷疑,但最終依然通過思婦表達的祝福,表達出發自內心的牽掛之情,表現出思婦經過回憶與傾訴思念之后,實現感性向理性的轉變。
(江蘇安全技術職業學院)
作者簡介:張永影(1981-),女,安徽阜南人,講師,研究方向:語文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