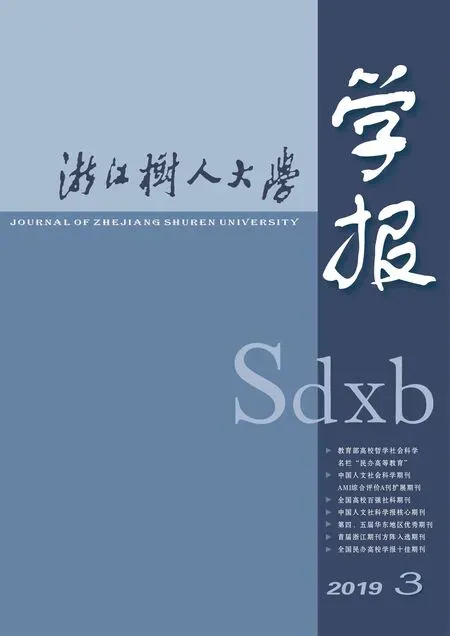元稹墓志銘節度使官職考辨
金沛晨
(廈門大學 中文系, 福建 廈門 361005)
節度最早并不是官職名,唐長孺云:“考都督本兼制數州軍事,而節度之稱乃除所管州之外兼施之于不屬州郡之‘軍’‘城’等。”[注]唐長孺:《唐書兵志箋證》,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76頁。又《舊唐書·太宗紀》載:“(武德元年)拜太尉、陜東道行臺尚書令,鎮長春宮,關東兵馬并受節度。”[注]劉昫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4頁;第1385頁;第1918頁;第535頁。可知節度最開始是差遣性質,意為關節調度。而節度成為官職最初出于中央掌控邊境的需要:“于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注]劉昫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4頁;第1385頁;第1918頁;第535頁。安史之亂后,地方勢力威脅君權,原先僅用于鎮守邊境的節度使制度逐漸蔓延到內地:“至德之后,中原用兵,大將為刺史者,兼治軍旅,遂依天寶邊將故事,加節度使之號,連制數郡。”[注]劉昫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4頁;第1385頁;第1918頁;第535頁。由此,節度使的設立與裁撤,成為唐王朝必須面對的棘手問題。
《元稹志》載,元稹曾任武昌軍節度使。今考各版本《元稹志》標題,均有武昌軍節度使一職[注]詳見謝思煒《元稹志》所附校記。,便知武昌軍節度使確為墓志原題。然白居易在墓志正文中作如下記載:“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度使。”[注]謝思煒:《白居易文集校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929頁;第1907頁。各版本《元稹志》正文亦記“鄂岳節度使”,白居易《祭微之文》也沿襲《元稹志》正文的說法,稱元稹的官職為“鄂岳節度使”[注]謝思煒:《白居易文集校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929頁;第1907頁。。正文中的鄂岳節度使與標題中的武昌軍節度使兩種叫法截然不同,令人費解。史書的說法也較蕪雜,如《舊唐書·元稹傳》記載元稹晚年官職為:“(太和)四年(830年)正月,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注]劉昫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336頁。此處出現鄂州刺史與武昌軍節度使兩官職并列。然據《舊唐書·文宗紀下》:“(太和四年正月春)以尚書左丞元稹檢校戶部尚書,充武昌軍節度、鄂岳蘄黃安申等州觀察使。”[注]劉昫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4頁;第1385頁;第1918頁;第535頁。提到元稹任武昌軍節度使和鄂岳觀察使,未提鄂州刺史。《新唐書·元稹傳》同《舊唐書·元稹傳》,亦記為武昌軍節度使,不過未提及元稹擔任過鄂州刺史與鄂岳觀察使。趙令畤《微之年譜》則給出了不同的記載,“乙巳敬宗寶歷元年(825年),丁未文宗太和元年,乙酉三年”條云:“是歲召為尚書右丞,旋改鄂岳節度使。”[注]趙令畤:《侯鯖錄》,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5頁。然而,卞孝萱《元稹年譜》、周相錄《元稹年譜新編》直接沿襲兩《唐書》,記元稹為武昌軍節度使,沒有對《侯鯖錄》所言“鄂岳節度使”加以辨證。
一、“鄂岳”地方軍政長官的官職兼帶現象
鄂州刺史與鄂岳觀察使本就與“鄂岳”關系緊密,而武昌軍節度使則為鄂岳地區的最高長官:“武昌軍節度使。治鄂州,管鄂、岳、蘄、黃、安、申、光等州。”[注]⑥⑨劉昫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391頁;第1389頁;第519頁。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和武昌軍節度使三個職位都與鄂岳地區有關,帶有濃重的地域色彩。但以上史料并沒有將這三種官職同時記載。若要對“鄂岳節度使”之稱進行考辨,應先說明這幾種職位與“鄂岳”的內在關聯。“節度使例兼觀察之職,故或稱節度或稱觀察”[注]錢大昕著,方詩銘、周殿杰校點:《廿二史考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89頁。,說明唐代節度使兼觀察使較普遍。節度使亦多兼州刺史,如《職官分紀》“都督”條下注:“大率節度、觀察、防御、團練皆兼所治州刺史。”[注]孫逢吉:《職官分紀》,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703頁。此種兼帶關系在鄂岳地區亦然,如“武昌軍節度、鄂岳觀察處置等使、兼鄂州刺史”[注]吳廷燮:《唐方鎮年表》,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879頁。。
由此可知,元稹實際兼任鄂岳觀察使、鄂州刺史和武昌軍節度使三職,故這三種官職不應被孤立看待。且觀察使有時與節度使并無嚴格區分,兩者的區別一般以時局決定。如《舊唐書·地理一》:“至德(756—757年)之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軍戎,遂有防御、團練、制置之名。要沖大郡,皆有節度之額;寇盜稍息,則易以觀察之號。”[注]⑥官職邊界的模糊加強了彼此的聯系,也促使地方軍政官職兼帶現象的出現。雖鄂岳觀察使與武昌軍節度使可為兼帶關系,但這種兼帶關系建立在“代替”的基礎上。據《讀史方輿紀要》“武昌”條:“治鄂州。元和初置鄂岳觀察使,十二年(817年)平淮西,以申州來屬,寶應初升為武昌軍節度,太和中仍為觀察使,領鄂、岳、蘄、黃、安、申、光七州,尋復曰武昌軍節度。”[注]顧祖禹著,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56頁。
既然兩種官職存在興廢替代關系,若同兼于一人身上,官職名便易因襲。武昌軍節度使替代鄂岳觀察使并不意味著后者被廢,而是部分職能發生了轉變,節度、觀察彼此仍為兼帶關系,如《順宗實錄》云:“五月乙酉,以尚書左丞韓皋為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注]⑩董誥、阮元、徐松等:《全唐文》,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666頁;第4653頁;第5675頁。這說明觀察使升為節度使后,觀察和節度兼行于一人身上。
兼帶關系為官職的省略提供了可能。牛僧孺任武昌軍節度使時,史料有時只以觀察稱之:“鄂岳觀察使牛僧孺奏:‘當道沔州與鄂州隔江相對,才一里余,其州請并省,其漢陽、汊川兩縣隸鄂州。’”[注]⑨節度使掌軍權,觀察使側重行政。這種叫法不僅突出了牛僧孺的行政職能,也不會因為官職省略而引起誤解。兼帶將觀察使的“鄂岳”冠名與節度使聯系在一起,節度使兼觀察使、刺史,加上武昌軍所在地武昌其實就是鄂州,這些均隱隱指明鄂岳節度使就是武昌軍節度使。
二、“鄂岳”并置的地理原因
鄂、岳因緊密的地理聯系而經常并列。《鄂州新廳記》載:“國家故務省官息人,而終慮咽喉襟帶之地,思典守者既輕其權矣,復欲俾任重,尤難其選。”⑩當時淮西叛亂,鄂岳地區由于接近淮西,所以戰略地位較重要。韓愈《平淮西碑》便云:“蔡帥(州)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是以朝廷對該地的政治考量,是“鄂岳”統稱形成的重要推動力。此外,鄂、岳兩州在該地區亦最有淵源。據《中國行政區劃通史》載:“(貞觀)十年(636年)……并割山南道直屬蘄、黃、申、光四州為淮南道直屬地區,十三年,淮南道直屬地區有壽、濠、楚、廬、舒、蘄、黃、申、光九州。”[注]郭聲波著,周振鶴編:《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唐代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頁;第424-425頁;第438、441頁。直到天寶十三載(754年),黃、蘄、申、光四州仍屬淮南道。天寶十五載后格局才漸有變化,四州各自隸屬于其他道。其中,蘄、黃從永泰元年(765年)后才受鄂岳長官管轄。安州于元和元年(806年),申州大概在元和十三年以后才隸屬鄂岳地區[注]②③郭聲波著,周振鶴編:《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唐代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43、449-450頁;第444-445頁;第565-568頁。。光州在大多數時間里都屬于淮南道或者河南道的節度使管轄[注]②。而鄂、岳兩州早在景云二年(711年)便已同屬江南西道,乾元二年(759年)后被并列稱為“鄂岳”,已基本組成新的行政區域[注]③。可見,在武昌軍節度使管轄的州境內,只有鄂、岳地理淵源緊密,故兩者并置出于政府考量無疑。安史之亂后,天下十五道被進一步分割,原屬于江南西道的鄂州、岳州以及原屬于淮南道的蘄、黃等組成新區域“鄂岳道”。《舊唐書·德宗紀》云:“命宰臣蕭復往山南、荊南、湖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等道宣慰。”[注]⑤⑩劉昫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40頁;第424頁;第414頁。可知,該區域長官之所以叫鄂岳觀察使或鄂岳節度使,就是由其所轄“鄂岳道”的區域得名。
又《舊唐書·憲宗紀》載:“(元和二年)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每歲賦入倚辦,止于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注]⑤安史之亂后,唐王朝主要以東南八道的財賦收入來支持中央機構的運作,這點早在肅宗朝便已現端倪,如杜甫詩云:“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索漢水清,緬通淮湖稅。”[注]杜甫著,蕭滌非編:《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833-844頁。該詩為《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鄂岳”為東南八道之一的“鄂岳道”,說明鄂、岳兩州并稱有其復雜的社會背景,是當時官方對鄂岳觀察使或節度使管轄區域約定俗成的地理名稱。元和二年正是武昌軍節度使鎮守“鄂岳”的時期,那時就已稱“鄂岳”區域為鄂岳道,反之亦可理解成鄂岳道的節度使就是武昌軍節度使。
鄂岳道的成立與中央政府減弱藩鎮實力的意圖有關。所謂“大者連州十數,小者猶兼三四”[注]趙翼著,王樹民校正:《廿二史札記校正》,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430頁。。小者之所以能兼三四州的緣故,未嘗不是地方權力細分的結果。如《資治通鑒》“元和十四年二月己巳”條云:“上命楊于陵分李師道地,于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寡眾,校倉庫虛實,分為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為一道;緇、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上從之。”[注]司馬光著,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7765頁。在這樣的背景下,“鄂岳”從鄂州、岳州的并稱走向以鄂州、岳州為主,包涵其他州的大地理概念——鄂岳道,故鄂岳節度使就是鄂岳道的節度使。此外,雖武昌軍節度使與鄂岳節度使的名字不同,但不代表管轄范圍有差異。據《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永貞元年(805年),升為武昌軍節度使。元和元年,以淮南道廢奉義軍節度使之安、黃二州來屬。三年,降為鄂岳都團練觀察使……寶歷元年,升鄂岳都團練觀察使為武昌軍節度使。二年,廢沔州。太和五年,降為鄂岳都團練觀察使。”[注]周振鶴編:《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唐代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70頁。可見,鄂岳都團練觀察使與武昌軍節度使的興廢替代,并不涉及管轄范圍的變更。武昌軍節度使既是地方節度使長官,那么該官職也可理解為“鄂岳道”的節度使。這種以地域冠名節度使的叫法已有先例,如《舊唐書》便說:“以鄂岳沔觀察使韓皋為鄂、岳、蘄、安、黃等州節度使。”⑩史書稱鄂、岳、蘄、安、黃等州節度使,是指管理鄂、岳等州的節度使。從此前該區域長期將“鄂岳”并列稱呼的習慣看,政府顯然將官職前長串的地域冠名盡量縮減,以最重要的兩州并列作為區域統稱。故相對于武昌軍節度使,鄂岳節度使這個名字更多強調區域地理概念。
三、武昌軍——鄂岳節度使官職的“特例”
元稹卒前,鄂岳地區軍政長官被稱為武昌軍節度使的時間約七年[注]參見吳廷燮:《唐方鎮年表》,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879-891頁。,可知鄂岳地區并沒有稱呼該地軍政長官為武昌軍節度使的傳統。鄂岳地區在太和五年之前,其軍政長官基本是鄂岳觀察使、防御使等官職。防御、團練使跟節度使關聯性較強。如《通典·都督》云:“自至德以來,天下多難,諸道皆聚兵,增節度使為二十余道。其非節度使者,謂之防御使……上元末,省都統,后又改防御使為都團練守捉使,皆主兵事,而無旌節,寮屬亦減。”[注]杜佑著,王文錦等點校:《通典》,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895-896頁。可見,防御、團練使與節度使的區別只是名字不同,地位有高下,但差異不算太大。而鄂岳節度使既與武昌軍節度使同名“節度”,其內在差別只會更小。更何況鄂岳觀察使等官職早就冠以了“鄂岳”兩字。歷史上岳州雖曾被裁撤出鄂岳地區,但隸屬他道的時間不長。既然“鄂岳”地區軍政長官長時間頂著鄂岳頭銜,那么當該地長官的職位變為節度使時稱其為鄂岳節度使也順理成章。
此外,判定節度使的冠名是否為某某軍,則視該地節度使是否有軍額而定。《舊唐書·伊慎傳》云:“貞元十五年(799年),以慎為安黃等州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察等使……二十一年,于安黃置奉義軍額,以為奉義軍節度使、檢校右仆射。”[注]②劉昫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055-4056頁;第513頁。這提供了兩個信息:一是重要州名之間的并置以泛指一個大地區,如安、黃并稱類似鄂、岳并稱;二是安黃節度使變為奉義軍節度使是因為安黃地區設置了奉義軍軍額,同理,鄂岳節度使被稱為武昌軍節度使是因為該地設置了武昌軍軍額,從而使稱呼側重點轉移到軍額上。《舊唐書·敬宗紀》載:“以僧孺檢校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鄂州刺史,充武昌軍節度、鄂岳觀察使。淮南節度使王播兼諸道鹽鐵轉運使。于鄂州特置武昌軍額,寵僧孺也。”[注]②雖然史書沒有對軍額作專門的解釋,但能從史料中有所窺探,如《唐會要》“京城諸軍”條云:“廣德二年正月敕。左右神武等軍,各一千五百人為定額。”[注]王溥:《唐會要》,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1293頁。它可以理解為軍隊人員的名額,與人頭數密切相關,而且有數量限制,不能超過政府設定的上限。敬宗于鄂州置軍額,實際上就是在鄂州放置了一支新軍隊。此外,軍額往往使軍隊帶有軍號,帶軍號的軍隊與一般軍隊分屬兩種不同體系。因此,只有鄂岳地區獲得了武昌軍軍額,地區長官才能被稱為武昌軍節度使。武昌軍節度使比鄂岳節度使多了一支軍號為“武昌軍”的軍隊,這是最根本的不同。一旦軍額被撤銷,節度使的名稱便會改變。如《停忠義軍額敕》云:“襄州近因趙匡凝作帥,請別立忠義軍額,既非往制,固是從權。忠義軍額宜停廢,依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注]⑦⑨董誥、阮元、徐松等:《全唐文》,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977-978頁;第881頁;第5666頁。因為忠義軍軍額被撤銷,該地長官便不再是忠義軍節度使,而是循舊名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據此,武昌軍節度使與鄂岳節度使大有不同,鄂岳節度使的概念大于武昌軍節度使的概念,前者可以包含后者。《新唐書·兵》載:“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注]宋祁、歐陽修、范鎮等:《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329頁。軍的概念顯然比道小,而此前提到的鄂岳道兵,顯然是對道內所有兵力的總稱。鄂岳地區在不設節度前,長官多以觀察使兼團練使或防御使,團練、防御等使麾下兵力多稱守捉而非軍。如《冊府元龜·將帥部》載:“柳公綽元和中為鄂岳都團練觀察使。”[注]王欽若等著,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鳳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4792頁。《授問俗鄂岳等州團練使制》載:“充鄂岳沔三州都團練守捉使。”[注]⑦可見,鄂岳地區在置軍額前,其長官所帶兵力一般稱為守捉。守捉與軍的區別不在于數量,可能取決于鎮守者的地位,如《唐書兵志箋證》記載:“軍與守捉雖有高卑之別,然守捉統軍亦有多于軍者”[注]唐長孺:《唐書兵志箋證》,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頁。;《順宗實錄》記載:“乙酉以尚書左丞韓皋為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初皋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簡倨自高,嫉叔文之黨。”[注]⑨牛僧孺任武昌軍節度使前為宰相,且史書載明他是因為備受寵遇所以鄂州才被放置了軍額。元稹與韓皋一樣為尚書左丞,又是先帝宰相,所以他鎮守鄂州時軍額也沒有取消。可見,軍額設置亦與鎮守者地位相關。
武昌軍節度使強調“軍”,側重規格,而鄂岳節度使則為地理意義的總稱,故前者可被后者囊括。如《新五代史·職方考》曾云:“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于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后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注]歐陽修著,徐無黨注:《新五代史》,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45頁。武昌軍節度使正是一個典型。
四、奏疏中的“鄂岳”節度使
從奏疏看,鄂岳節度使與武昌軍節度使兩種稱呼在當時都屬于官方稱呼。《唐方鎮年表》云:“元年,復置武昌軍節度使。二年,罷。四年,復置。六年,復罷”[注]吳廷燮:《唐方鎮年表》,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894頁。,說明大中元年(847年)至二年時鄂岳地區長官為武昌軍節度使。然《進海潮賦狀》卻記:“臣會昌三年(843年)舉進士……故鄂岳節度使盧商自中書出鎮,辟臣為從事。”[注]董誥、阮元、徐松等:《全唐文》,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8001頁。可知,大中元年鄂岳地區設立了武昌軍節度使,盧商接替鄭朗任此職,但稱盧商為鄂岳節度使,說明鄂岳節度使與武昌軍節度使兩稱并行。《進海潮賦狀》屬于官方應用文書,用詞務求準確。在官方文書中以鄂岳節度使代替武昌軍節度使,說明鄂岳節度使亦是官方稱呼,與武昌軍節度使互不矛盾。郁賢皓考證盧肇任歙州刺史為咸通四年(863年)至咸通七年,而《進海潮賦狀》云:“去年五月,又蒙恩除歙州刺史”[注]董誥、阮元、徐松等:《全唐文》,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8001頁。,則知該狀寫于咸通五年。自元稹卒年(太和五年)至咸通五年,已過去30年之久,正可說明鄂岳節度使之“鄂岳”是官方認可的長久襲用的地理區域大概念。
這種一官兩稱的現象在白居易文集中并不是孤例,如《與恒州節度下將士書》載:“充恒冀深趙徳棣六州觀察使,成徳軍節度使。”[注]③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059頁;第1302頁。題目稱恒州節度,正文稱為成德軍節度。又《論行營狀》載:“今李光顏既除陳許節度,盡領本軍。”[注]③該文作于長慶二年(822年),考《舊唐書·穆宗紀》:“癸未,以深冀行營諸軍節度、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顏為滄州刺史、橫海軍節度使,兼忠武軍節度、深冀行營并如故。”[注]⑤劉昫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95頁;第1611頁。李光顏時為忠武軍節度使,而白居易在文中則稱其為陳許節度使,可見當時對于某一官職的確有兩種稱呼。因此,鄂岳節度使與武昌軍節度使一樣,為鄂岳地區節度使官方的一種稱呼。另據《舊唐書·地理三》:“鄂岳節度使牛僧孺奏”[注]⑤,稱呼牛僧孺為“鄂岳節度使”,表明在白居易寫墓志之前,鄂岳節度使已與武昌軍節度使一樣,成為鄂岳地區最高軍事長官的稱呼。而武昌軍節度使這個稱呼出現的頻率高于約定俗成的鄂岳節度使的原因,大概是因為鄂岳節度使是以道為單位的地理概念,不管是鄂岳等州的節度使還是鄂岳道節度使,總體上屬于地理上的泛稱。武昌軍節度使則因為強調了軍額和軍號,帶有特指意味。安史之亂后藩鎮勢力強大,雖因唐憲宗出兵平叛一度重建了中央政權的威信,然唐穆宗時河朔三鎮再度叛亂,唐王朝風雨飄搖。在這樣的情況下,強調軍額的武昌軍節度使,應比泛稱地方節度長官的鄂岳節度使更能與當時的社會形勢相符。
綜上所述,鄂岳節度使是武昌軍節度使的另一種叫法,源于長久以來地方約定俗成的習慣,也與中央對鄂岳地區的行政區劃和軍政長官命名習慣密切相關。鄂岳節度使與武昌軍節度使為包含關系,但側重不同,前者側重地理意義的泛稱,后者側重軍額并具有特指意義,故兩者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