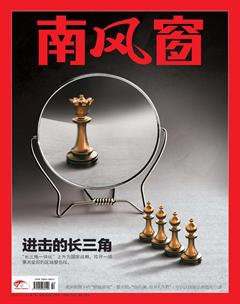基層政府的屬地管理之惑
曹檸

這兩年來,意外“躺槍”的基層干部越來越多了。
據新華社、半月談、法制日報等多家媒體報道,屬地管理原則被濫用正困擾著一些基層干部。市縣一級的個別職能部門把一些職責范圍內的“燙手山芋”,也打著屬地管理的旗號,下放到基層,自身則從責任主體搖身一變成為督查主體,出了問題便可以順理成章地追究事發地基層政府部門責任。
屬地管理的泛濫
屬地管理是我國行政管理體制的基本特征之一,所謂“條塊結合,以塊為主,分級管理”,屬地管理要求地方各級政府全面負責地方治理。
2016年的電影《我不是潘金蓮》讓信訪問題的屬地管理一時間引來熱議,片中李雪蓮作為一個農村婦女十年的上訪成了屬地領導揮之不去的痛,從鄉長到縣長、市長跟著她烏紗不保,甚至驚動了省長。片中的官員也許會叫屈,為什么明明跟自己沒直接關系的事也要負責?
原因就在于2005年信訪條例中將多年來實行的“分級負責、歸口辦理”信訪工作原則,修改為“屬地管理、分級負責”,強調了信訪事項屬地管理的優先原則,明確了地方各級政府在處理跨地信訪和越級信訪時的主導作用。
南通市臨江新區一位社區干部告訴《南風窗》記者,她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負責轄區內幾位老上訪戶的信息,但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已經不在本地居住,但她卻常常因為信訪戶又去了北京而“躺槍”。其中有一位死磕訪戶已經舉家搬遷到上海了,但是上級部門老是揪著不放,一出問題就怪到基層信訪辦頭上。
痛苦的還有鄉鎮干部,原本屬于垂直管理的市縣部門,如環保局、國土局、安監局,有的把難點工作打包往下分,自己則安心做起了“文件中轉站”,“誰主管、誰負責”成了擺設,屬地管理倒是成了怪罪下級的借口。
上面千把錘,下面一顆釘,鄉鎮政府壓力山大。據記者了解,在鄉鎮一級,一人負責3-4項工作任務的情況十分普遍,“鄉鎮街道一來人就那么幾個,分身乏術,二來沒有執法權,想管也管不了”。
山東省西部某市的一位鎮委副書記告訴記者,鎮內有一座國有礦區,但因為近年來區域規劃做過調整,礦區的經營權直接劃到了縣里的礦務局。2018年上半年礦區的安監檢查不合格,鎮上的領導因為監管不力被通報批評,“現在安全生產的要求很高,我們又沒有執法權,只靠鎮上現有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實現監管”,鎮上并沒有直接享受到礦區的任何好處,出了污染或安全事故卻成了責任人,這實在令他非常委屈。
沒有執法權不能辦,專業能力不足辦不了。基層政府目前的解決方法主要是尋求專業部門的協助,但是這種協助效率很低,一來在權責不明的狀況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都不想成為主要負責方;二來從下往上推太難,平級的都叫不動,上級更是別想了。“如果人家明明就是甩鍋,你還一個勁兒找人家幫忙,人家當然不會理你了。”
四川省通江縣的一位鄉長也告訴記者,在他看來,問題的關鍵在于屬地管理的適用范圍。因為“屬地管理”需要配備相應的行政執法職能部門和權力,而縣級職能齊全,還算是權責統一,若是再延伸到鄉鎮弊端就顯現出來了
屬地管理之殤有上級部門不作為造成的,屬于“背鍋”,也有責權劃分不清等歷史原因造成的,屬于“躺槍”。但無論是“背鍋”還是“躺槍”,反映出的治理轉型的困境是一致的:屬地政府的權責不統一。
“條條”與“塊塊”的博弈
所謂權責不統一,在基層政府那里就是一種吊詭的感覺:權力越來越小,責任卻越來越大了。
對于中國的行政體系稍加熟知,便知道組織網絡中有所謂“條條”和“塊塊”之分,前者指具有相同工作性質的機構和部門,例如國務院各部委,后者指地方各級政府。
而基層部門往往處于條塊關系的縫隙,接受雙重管理,既要接受上級部門的專業管理,又面臨地方政府的歸口管理。
這就有了屬地管理與垂直管理兩種不同管理模式的紛爭。實行垂直管理意味著直接由省級或者中央主管部門統籌管理人、財、物、事,不受地方政府監督機制約束。屬地管理則指地方監管部門的人、財、物、事,交由地方政府管理,同時地方政府對屬地內既有監管之權,也有監管之責。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實際的行政執法過程中,垂管部門的執法和管理力量是不夠的,一個縣的國土局分管到鄉鎮可能只有一兩個人,不可能有效治理。
改革開放初期以放權的改革為主,屬地管理責任和屬地的權力是同時增長的。但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很多領域權力下放后出現了各種問題,鄉鎮政府中稅費征收、計劃生育等政策執行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權力濫用等情況,導致權力又出現了向上集中的趨勢。
但垂直管理模式存在很多科層制的先天不足。首先,垂直部門習慣照章辦事,循規蹈矩,幾乎沒有突破創新的空間,也很難回應復雜的社會治理需求。其次,還存在根深蒂固的部門化利益,職責范圍之外的事務最好高高掛起,部門之間的合作成本過大。同時,屬地政府由于對屬地監管部門無力介入,也就失去了積極性,無權也無責,有事向上推,責任也上交,出現監管真空也就不足為奇了。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周黎安認為,“應對傳統屬地發包出現的地方治理問題一律采取垂直化改革的思路并非萬全之策。”因為權力的上收一方面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職權,限制了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和創新發展的空間,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增加政府部門的官僚主義和低效率。
很多垂管部門,比如國土、環保,出于專業化和高效管理的需要,把權力,尤其是執法權,收到“條條”里面去了。但在實際的行政執法過程中,垂管部門的執法和管理力量是不夠的,一個縣的國土局分管到鄉鎮可能只有一兩個人,不可能有效治理。屬地管理被濫用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
治理轉型中各有難處
管理的權力從屬地往上收到了垂管部門是一方面,還有一方面是上級考核的權力和能力都變強了,導致屬地政府的責任變大。
從改革開放到黨的十八大,政府在考核問責制度化方面并未形成嚴格的體系。周黎安認為,在錦標賽競爭和市場競爭的雙重壓力之下,地方官員大膽冒險與創新。只要結果被證明是成功的,即使創新實踐有可能違背了當時的規定和法律,地方官員的創新也可能得到首肯和獎勵。
這種格局下,地方政府間的治理整體上呈現出運動式治理的特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力求速戰速決。
黨的十八以后,改革進入“深水區”,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改革積累的社會矛盾頻繁爆發,政績考核開始呈現明顯的多元化,腐敗、安全生產、環境污染、群體性上訪被稱為基層政府新的“命門”,而且不止一處。“唯GDP論”受到批判,環保、民生以及反映經濟發展質量的指標逐步納入官員考核體系之中,甚至空氣質量、房價等指標被納入基層政府考核的“一票否決”范圍。隨著政府治理規范化和制度化,地方政府的決策和行動空間顯然在不斷縮小。
同時,行政體系內部監管、考核的效率也有了長足的進步。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通過調整紀檢監察組織領導體制,推行“大部制”和加強黨政合署辦公的機構改革,強化了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
這兩方面深刻的變化形成了一種新的央地關系。一方面下級面對的治理領域和考核指標變多了,另一方面是上級考核、控制的能力加強了,基層政府瞬間感到壓力陡增也不難理解了。
在過去的技術條件下,上級檢查時而演變為上下政府之間的“共謀”,中央和地方各層級政府之間存在著普遍的信息不對稱,上級政府也非常清楚它不可能有效監控基層政府行為。下級完成不了,上級盡管心知肚明,但是為了好交差便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現在信息化的行政方式則呈現出一邊倒的高壓督導,基層部門為了接待應接不暇的各類上級檢查,不得不花費巨大的精力和財力,甚至導致自身行政效率大幅下降。
問題在于,基層的許多工作需要耗費精力、人力,需要面對面,并不是說實現了事事留痕、無紙化辦公就意味著基層解決問題的水平就提高了。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員呂德文將此形容為“我們現在是用計算機的方式去治理一個算盤時代的社會問題”。他以自己做精準扶貧相關調研時的發現為例,基層干部要去扶貧的話,要反復入戶做調查,這都是手工操作的。但是對上級的計算機化的扶貧系統來說很簡單,數據一輸入進去很容易發現有沒有落實,比方說發現有兩個數據之間不匹配或邏輯關系不強,很容易發現基層做得不到位。但是如果從基層政府和扶貧干部的角度考慮, 為了完成上級精準的計算, 得反復做許多工作,編輯、錄入、核對,但這并不是他工作的重心。“現在很多形式主義泛濫和這套技術邏輯有很大關系。”
一位鄉鎮干部告訴記者,2018年下半年接待的上級檢查竟有150次以上,“巡視、環保督察、扶貧檢查、土地督查、安全生產檢查、審計、第三方評估……一天陪兩撥前來調研的上級領導,屬于家常便飯。”
北京市平谷區的例子就很值得借鑒。在縣域治理范圍內,賦予街道辦事處和鄉鎮政府的部門考核權和召集權。
最痛苦的就是“事必留痕”,“我就納了悶,基層的主要任務應該是把工作干好,怎么現在到頭來,都是在臨時抱佛腳,造各種材料,有的還是當天布置當天要。這樣下去,本職工作還怎么搞?”
權責再平衡
十九屆三中全會指出,機構改革的原則之一是 “堅持優化協同高效”。在此原則之下 ,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是精干設置各級政府部門其內設機構,科學配置權力,減少機構數量,簡化中間層次,推行扁平化管理,形成自上而下的高效率組織體系。
從功能上看,屬地責任和垂直管理都有合理性,也都有不足,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平衡。
屬地管理原則被濫用暴露出來的是條條專權,塊塊有責無權。條條既然有權力就得承擔責任,比如環保部門要環保執法權,就要分擔屬地的責任,要么就把執法權下放,或者通過運作模式創新,屬地能管的就管,確實管不了的就找職能部門,找了就得來,不然責任就是職能部門的。執法權還在職能部門,但是屬地有權要求職能部門來執法。
北京市平谷區的例子就很值得借鑒。在縣域治理范圍內,賦予街道辦事處和鄉鎮政府的部門考核權和召集權。面對一些需要部門協調及條塊合作的治理痼疾,街鄉可以“吹哨”召集各職能部門現場“報到”,參與聯合執法。運用這一機制,平谷區猖獗多年的沙石盜采、黃金盜挖等問題得到了有效控制。而部門因參與了治理過程,且治理目標亦“可見”,也就不存在隨意啟動督查檢查考核工作的問題,更不用啟動問責機制。
2018年11月中旬,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充分肯定了“街鄉吹哨、部門報到”在聚焦辦好群眾家門口事,打通抓落實“最后一公里”中的積極作用。
呂德文向記者表示,這一探索通過科學規劃各執法部門和屬地政府的權力和責任,賦予屬地政府執法召集權。這一方面給屬地政府賦權,改變了基層治理中的權責不一致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在無形中將屬地政府的治理行為納入到法治軌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