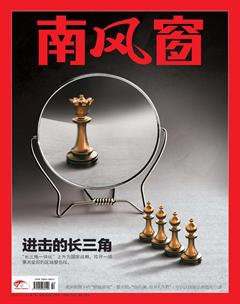長三角“醫保互通”之路
鄭嘉璐

2018年最后一個工作周,12月24日星期一,寧波市社會保障服務大廳,來報銷醫療費的人占滿了一排排長椅。辦事窗口全開放了,還是有許多人領號排隊。把一位顫顫巍巍的老太太扶到辦事窗口,祝紅亞給同事打去電話:“忙不過來了,再叫個人來!”
祝紅亞是寧波社保局費用審核處的副處長,她是來大廳維持秩序的。臨近年末,不少人把攢了一年的醫療費發票拿來報銷,祝紅亞和同事們到了一年里最忙的時候。不過,祝紅亞相信2019年底時不會這樣忙碌。寧波是長三角“異地門診就醫直接結算”的改革試點,新年里需要上門報銷醫療費的人會越來越少。
所謂“異地門診就醫直接結算”,解釋起來并不復雜:假設有人的醫保關系在寧波,卻在上海工作或生活,有了這項政策,他在上海看病時就可以直接刷寧波的社保卡付費,免去了自己墊錢和報銷發票的麻煩。
這項改革是長三角地區“醫保互通”的重要一部分。從區域視角來看,它是“長三角一體化”的一個縮影,從中可以看出區域一體化的迫切與困難;放眼全國,醫保互通改革還是中國醫療體制改革的關鍵,它有助于最終形成全國范圍內的社保“一卡通”。
異地的醫保
郭玲麗從挎包里取出一摞發票,這是她在上海做肺部手術時的票據,一共五萬多元。她估摸著,寧波醫保能給她報銷兩萬元。
郭玲麗55歲,過去是寧波一家企業的員工。幾年前企業改制,她被買斷了工齡,便到上海投奔姐姐,也定居在了那里。2018年5月,郭玲麗被確診為早期肺癌,在上海一家醫院接受了手術。這次回來寧波,她只為一件事:報銷醫療費。
在中國,醫保基金實行市級或縣級統籌,異地就醫是件麻煩事。不同統籌地區在醫保制度、資費標準、醫療待遇標準方面存在很大的差異,也不能統一調劑使用基金,所以人們在異地就醫看病時,往往需要自行墊付醫療費,再拿著發票回參保地報銷。
郭玲麗遇到的就是這種情況。由于一直在寧波繳納醫保,2017年以前,她在上海看病、手術都不能使用寧波的醫保卡,得自己出醫療費。對她來說,墊付幾萬元并不困難,但從上海跑來寧波報銷醫療費卻是件苦差事。
與郭玲麗正相反,64歲的章愛華持有上海醫保,卻在寧波生活。退休前,她是上海埃力生集團的員工,醫保關系也就留在了上海。由于女兒在寧波慈溪工作,章愛華在退休后搬回了慈溪老家。2014年,章愛華被查出了乳腺癌。手術后,她開始了在上海和寧波兩座城市之間的奔波。
兩地奔波是為了省錢。上海醫保有規定,像章愛華這樣的惡性腫瘤病人,在本地定點醫院就醫可以享受大病優惠政策:手術后五年內,患者使用中醫治療的費用可以由醫保報銷90%,而在參保地之外看病就沒有這么高的報銷比例。為了減少醫療費支出,章愛華沒有就近在寧波的醫院治療,而是選擇每月跑一次上海,使用中醫復查、拿藥。
但是,每月一次的往返占用了她巨大的精力。章愛華回憶,從家里出發,她要先坐50分鐘的公交,再乘三小時的大巴到上海南站,轉兩趟地鐵才到上海腫瘤醫院。一個來回,她要花十多個小時,早上五六點鐘起來,晚上回到家要十點左右。雖然在上海拿藥不僅可以直接刷社保卡,不用墊付醫療費,而且還能享受更高比例的報銷,但章愛華想一想還是劃不來,每月折騰一次不說,路費就要兩百多元。
這一年多內,僅到上海住院就醫直接刷卡的寧波參保人就有13990名,到寧波住院刷卡的上海參保人也有470人,這還不包括大量門診就醫和沒有刷卡的病例。
苦于異地就醫的人還有很多。近幾年,長三角一體化進程加快,區域內人員流動更加頻繁,異地安置、異地工作、轉移就醫等臨時性就診的情況更常見了。從2017年7月到2018年11月這一年多內,僅到上海住院就醫直接刷卡的寧波參保人就有13990名,到寧波住院刷卡的上海參保人也有470人,這還不包括大量門診就醫和沒有刷卡的病例。
寧波與上海之間異地就醫的人格外多,這與兩座城市的歷史淵源分不開。上海開埠前后,大量寧波人移民上海謀生,所以當前許多上海人都有寧波的親屬;上海又有許多知青在寧波插隊落戶,也在寧波享受醫保待遇,這些因素使兩座城市的聯系更加緊密。
十年前,兩地異地就醫的問題集中爆發出來。知青群體大多在出生于20世紀40、50年代,2008年前后正是他們集中退休的時間段,很多在寧波退休的上海知青選擇回家鄉養老。老年人群體使用醫保非常頻繁,他們在異地看病,卻還要跑回參保地報銷醫療費,費時費力。不少人像章愛華和郭玲麗一樣,苦于高額的醫療費墊付和兩地間的奔波。
采訪中,章愛華就向《南風窗》記者感嘆:如果能全國統一標準,無論哪個地方的老百姓都能使用一張社保卡在全國看病,那就好了!
政府的難處
章愛華的愿望恰恰是中國醫療體制改革的終極目標。醫保互通的最高層次是全國范圍內的醫保統籌,讓社保卡在所有城市實現“一卡通”。不過,推動醫保互通,地方政府有一系列的難處,從實際情況來看,距離這個目標的實現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這是由醫保制度本身決定的。中國城鄉與地域之間的經濟差距短期內難以改善,各地發展程度不同,醫保賬戶水平和醫保待遇也不同,這是地方政府從自身支付水平出發的必然選擇。但是,過低的統籌層次也使得中國的醫保制度形成了區域封閉、制度割據的特點,甚至同一個地級市下的縣市區之間都有各自的醫保系統,彼此不能互通。
在這個背景下,讓異地就醫人員直接異地參保、享受就醫地待遇是不現實的。對于那些在參保地繳納醫保卻在異地就醫的人,異地醫保機構肯定不愿意用自身統籌基金為其承擔費用。如果是外來人口聚集的大城市—比如上海,阻力就會更大。
類似的道理,醫保關系也不可能隨意轉移。章愛華曾想過將醫保轉移到杭州或寧波,這樣就能避免異地就醫的問題。但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女兒告訴她,退休職工沒有社保接收單位,遷入地不會接受她的申請。章愛華也想通了:“退休工人轉移到哪個地方,哪個地方就多一個負擔。人老了就是會帶來麻煩。”
盡管長三角地區各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差不算大,但差距仍然存在,尤其安徽省的幾個城市還與上海市有不小的差距。假如允許醫保隨意轉移,低繳費地區的參保人將會在退休前后涌入高繳費、高待遇地區。這樣一來,流入地醫保基金會面臨巨大的壓力,甚至會出現虧空,地方政府當然會出面阻止。
既然由就醫地承擔醫療費用不可行,那就只能仍然由參保地提供醫保,長三角地區的醫保互通就是在這個前提下開展的。但即便如此,政府依然會面臨很多困難。
最突出的是醫療資源的分配問題。在寧波,人們普遍相信上海的醫療水平更高,患上大病后往往選擇到上海確診和治療。但上海的醫療資源畢竟有限,外地人來的多了,本地人看病就會更困難。
醫保互通的另一個難處在于“反欺詐”。對于正常的、發生在參保地的就醫行為,社保部門比較容易有效監管;而異地就醫超出了社保部門的管轄范圍,患者的身份、病情、治療方案難以監控,異地醫院的醫療行為也不受約束。這就容易導致虛假票證、欺詐騙保、醫療費用高昂等現象。
服務的互通
醫保互通的困難的確有不少,不過陳英說,雖然醫保待遇暫時不能互通,但醫保服務可以。
寧波市實現醫保服務的互通過程有個明顯的特點:由市到省再到長三角地區,服務范圍逐步擴大。2011年以前,寧波市下轄的每個縣市各有一套獨立的醫保系統,寧波市民在不同縣市間看病都要自行墊付醫療費和報銷。2011年,寧波統一了全市職工醫療保險待遇政策,實現了寧波市范圍內的醫保結算“一卡通”。這相當于將醫保的統籌層級由縣提升到了市一級。
一年后,浙江省建立了省內異地就醫的直接結算平臺。寧波人在浙江省內的定點醫院看病,可以直接刷寧波市的醫保卡,由寧波醫保基金結算醫療費。2017年,國家級異地就醫結算平臺建立,跨省就醫也可以刷社保卡了。不過,由于不同省份門診報銷制度的差異非常大,跨省異地就醫只能實現住院醫療費用的直接結算,跨省的門診費用結算還是沒有打通。對于到異地出差和短期工作的人而言,門診支出占到醫療費的大頭,像郭玲麗這樣定期檢查和取藥產生的費用還是需要墊付和報銷。
雖然是異地刷卡,但并沒有提升醫保統籌的層次,只是通過打通信息平臺,把參保地的醫保基金拿到外地來付款。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醫保互通改革有一個共同點,即由參保地醫保基金結算醫療費。也就是說,雖然是異地刷卡,但并沒有提升醫保統籌的層次,只是通過打通信息平臺,把參保地的醫保基金拿到外地來付款。具體待遇標準則遵循“就醫地目錄、參保地待遇”的原則,也就是說藥物與醫療服務的價格,能報銷與否按照就醫地的規定;而報銷比例、最高支付限額等待遇則按照參保地的政策執行。這樣做避開了各地標準不同、醫保基金封閉等問題。
在醫保直接結算改革以前,寧波采取的異地就醫委托報銷的方式。寧波市與上海、杭州、舟山、臺州四地簽訂了服務協議,在這些城市看病的寧波參保人,雖然還是不能直接刷社保卡,但至少不再需要專門跑回寧波報銷發票,而可以在看病的城市就地報銷。當然了,出錢的還是寧波的醫保基金。
2018年,長三角地區開始試點異地就醫門診直接結算。包括寧波、嘉興、南通在內的八個統籌地區成為首批試點。
章愛華做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2018年10月,她在寧波第一醫院門診看病花費1300多元,個人只支付了240元,上海市醫保基金直接結算1100多元。這樣一來,她不再需要自己墊付看病的費用,也不用定期到社保局報銷發票了。截至2018年11月底,寧波參保人員在上海共發生2068筆門診直接刷卡就醫,費用總額64萬元。
不過,異地就醫門診直接結算改革還處在試點階段,并沒有解決全部問題。陳英坦言,上海只對寧波開通了15家三級醫院和8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試點的面還比較窄,對于在上海居住和工作的寧波人來說,這些醫院還遠遠不夠。
上海的醫療資源畢竟有限,改革如果一下子推開,涌進來看病的外地人太多,上海可能會吃不消。從試點的規模也能看出上海的謹慎:比如參與試點的嘉興,只有嘉興市區和下轄的嘉善縣納入試點;而杭州市只有省級單位大約20萬人參與試點。相對來說,寧波全市730萬人整體納入試點已經是不小的突破了。
醫保互通只是長三角一體化進程中的一個截面。由此既可以看出長三角一體化所面臨的許多挑戰,又顯示出區域整合的急迫性。如果一些制度壁壘還不能在短期內突破,怎樣盡可能地為要素的流動提供方便,降低企業和個人的成本,就成了長三角各地政府迫切需要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