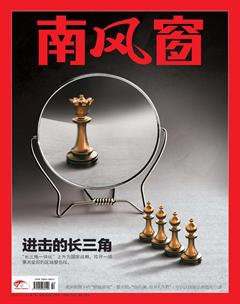浙商再闖大上海
何子維

杭州西湖東北角馬可·波羅塑像的底座上鐫刻著一句話,“杭州是世界上最美麗華貴之天城”。早在13世紀,杭州這座太平洋西岸的東方城市就進入了世界商業史的敘述之中。
現在,杭州和浙江又有了新的機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浙江要進一步發揮區位優勢,主動接軌上海、積極參與長江三角洲地區交流與合作,不斷提高對內對外開放水平。
杭州被稱為互聯網之都,浙江則是民營經濟大省,這兩大優勢也正是上海所需要的。無論是上海近代開埠,還是改革開放之后大浦東崛起,浙江人闖上海都是一種理所當然。
浙商嗅覺靈敏,總是能從某些變革中尋找機會,先人一步。那么,這一次呢?
上海互聯網的“杭州基因”
縱觀中國互聯網企業的排兵布陣,阿里兜兜轉轉定居杭州,騰訊駐扎深圳,北京更不乏驕子,比如百度、京東、小米、美團點評。當這些地方把互聯網玩得風生水起時,上海多少顯得有些落寞。
近年來,裹挾上海的話題是—上海出不了馬云、上海不相信互聯網、上海沒有BAT。上海仿佛一度被互聯網“拋棄”。但上海是不甘心的。
2015年,上海出了個拼多多。到2018年,拼多多GMV已經達到千億。達到這個數值,京東用了10年,唯品會用了8年,淘寶用了5年,而拼多多用了不到3年。
拼多多以這樣一種魔幻生長方式,賦予了上海一種新速度,也直接駁斥了上海沒有互聯網創業土壤的論斷。大家容易忽略的是,深埋在這家互聯網公司的兩個人,一個是拼多多CEO黃錚,一個是天使投資人孫彤宇,都是浙江人。
阿里2007年上市后,馬云讓孫彤宇“離崗進修”。十年后,孫彤宇帶著拼多多在上海崛起。
黃錚2001年在互聯網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受到了網易創始人、浙江寧波人丁磊的注意,因此與丁磊建立了聯系。這時候,黃錚還是一名浙江大學計算機學院的學生。等到黃錚赴美留學,丁磊將其推薦給了當時在美國的段永平—步步高集團董事長、后來OPPO、VIVO智能手機掌門人。黃錚不僅在做人做事方面得到了段永平的指導,在創建拼多多時,更得到了段永平的資金支持,做了他的天使投資人。
孫彤宇1996年追隨馬云,是阿里“十八羅漢”之一、原螞蟻金服的董事長彭蕾的丈夫、原淘寶總裁。阿里2007年上市后,馬云讓孫彤宇“離崗進修”。十年后,孫彤宇帶著拼多多在上海崛起。
商界風云變幻,奇人紛呈輩出。拼多多魔幻般出現,一直被八卦包圍,被“制造”質疑,但它的確是一個如假包換的“搏命少年”,更是浙江人、浙江企業、浙江資本的外流滬上的一個截面。
數據顯示,目前在滬浙商人數高達60萬。上海市浙江商會現有會員企業超過1.5萬家,有500多家海內外上市公司和行業龍頭企業,企業年利稅超過千億元。更令人驚喜的是,在上海2018年百強企業榜單中,入圍的浙江籍商人有14家,占比超過10%。在上海的外商中,浙商是實力最為強勁的一支。
浙商的自主流動和集聚,推動了上海的發展,重塑了長三角大灣區的格局,成為上海建設世界級城市群中一支強勁的力量。
地域相連,經濟相融,人緣相親。事實上,浙江與上海的聯系是天然的。
從現實來看,上海作為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其使命不只體現在自身發展的水平上,更重要的是服務中國大局,代表中國參與全球合作競爭。而囊括浙江8個城市的長三角正是上海需要“奮發求作為”的所在之一,即攜手長三角城市群合作共商、共享、建設世界級城市群,是改革開放40年之后的新一輪發展的必由之路。
從歷史來看,1843年,上海開埠后,外國資本由上海滲透到長江流域,浙江的資源輸入對上海的繁榮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海派文化形成之后,浙江迅速對海派文化產生了強烈的認同感。
這一期間,作為市場的推動者和載體,浙江企業開始逐步布局上海。但浙商的精明之處在于,依托上海,而不全部依靠上海,比如康恩貝公司。20世紀80年代,康恩貝把公司總部從浙江蘭溪遷入上海,生產總部依然留在勞動力相對低廉的蘭溪。這一商業模式被許多企業效仿,比如寧波的杉杉、臺州的吉利和飛躍集團等,都把營銷、研發等機構放到了上海。
企業是最好的經濟紐帶
隨著長三角一體化浪潮奔涌,浙商在“跳出浙江發展浙江”中不僅為區域發展作出了貢獻,亦反哺和延伸了浙江的內在動力。
首先是在滬浙商直接投資浙江。
1992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吳曉波在《激蕩三十年》中寫道,1992年的春天給中國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于后來的很多記憶中,這一年整個兒都是春天。
就在這樣一個春天里,大批政府機構、科研院所的知識分子主動下海創業,這批后來被稱為“92派”的人中有如陳東升、馮侖、潘石屹等人,還有來自浙江東陽一個農民家庭的郭廣昌。
1992年,復旦大學團委干部郭廣昌放棄出國的念頭下海,而郭廣昌的“海”就是上海。郭廣昌僅憑從親戚朋友處借來的3.8萬元啟動資金,帶領復星創業團隊一路狂奔,26年后締造了資產超過4000億元的投資帝國。順理成章地當上上海市浙江商會第九屆理事會會長后,郭廣昌做的較多的事是帶領在滬浙商反哺浙江。
2014年,復星集團與富春控股在杭州,共同打造了首個浙商回歸投資城市綜合體項目。2015年,成立了浙商成長基金,成為浙江省內首個浙江商會牽頭、會員聯合參與的資源整合和融資開發平臺。
資金反哺的潮流隨之在上海浙商中涌動。儲建根任董事長的上海楚喬衛浴電器有限公司投資308萬美元,在嘉興桐鄉成立了一家電氣有限公司。張國標任董事長的上海富春建業集團有限公司先后投資京杭大運河余杭段物流基地、嘉興乍浦港三期建設等項目。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基礎設施是浙江的短板。從地理上上看,浙江首先要和長三角實現互聯互通。由復星集團牽頭的民營聯合體于2017年9月11日與浙江省政府簽約了杭紹臺鐵路。它是國家首批社會資本投資鐵路示范項目之一,預計2021年底建成。建成后的杭紹臺鐵路將結束嵊州、新昌和天臺不通鐵路的歷史。屆時從杭州出發,最快30分鐘到嵊州和新昌,40多分鐘到天臺,1個多小時直抵臺州市區。
其次是依托上海,帶動浙江發展。就像康恩貝那樣。
他在臺州開眼鏡廠,所接的外貿單主要是上海的公司給的代工單子。
《南風窗》記者采訪了一位浙江商人,他在臺州開眼鏡廠,所接的外貿單主要是上海的公司給的代工單子。像這樣,以上海為市場和信息中心,在上海接單,回浙江生產,從而形成了以浙江為生產基地的區域合作的良性產業鏈,在浙江是一個普遍現象。比如,儲建根2004年回鄉成立了浙江楚喬電氣有限公司,在浙江桐鄉投資建起了國際化生產流水線。他把在家鄉生產的楚楚浴霸,通過上海銷往全國各地,建立起了穩固的銷售網絡,并逐步開始走向國際化道路。
走出去的浙商回到家鄉投資,或者是依托外地帶動家鄉發展,不只是財富積累的延伸,也是浙商歷史中由市場力量、民間意志和本土文化共同孕育的基因。
“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沒有豐盛的礦產,沒有廣袤的黑土地,人均耕地占有量在全國位居最末。浙江人的原始資本積累最早是從海上做生意。
唐宋以后,浙江寧波成為中國早開放的貿易口岸之一。遍及海內外的貿易往來,為浙江人種植了闖蕩天下的基因,注定了浙江人是天生的市場動物。只要有生意可做,浙江人一概涉足。浙江人認為,處處都是市場,處處都有機會。一顆螺絲釘、一粒紐扣對于浙江人來說,都是財富。
有了這個基因,當外部條件最佳時,不再滿足于低成本優勢,低附加值產業的浙江人,會在內在沖動、政府推動、內外合力的作用下選擇“做大做高”。這種企業的自主發展和擴張,成為了區域整合最可持續發展的市場化推手。
杭州互聯網要“落地”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在商業的浪潮里漸漸習得了獨有的優勢。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民營經濟比較發達的體制機制優勢,二是天獨厚的深水岸線和港口優勢,三是數字經濟相對領先的新經濟優勢,四是灘涂資源豐富形成的可利用空間潛力優勢。
隨著長三角一體化的推進,浙江的優勢能否持續展現,是個值得探討的話題。
首先是民營企業面臨產業變革的壓力和挑戰。
從歷史上看,浙江民營企業發展走在全國前列,在省內經濟結構中占有較高比重。現階段,浙江中小型民營企業大多集中在日用消費品行業,比如杭州的女裝,寧波的男裝,寧波慈溪的小家電,臺州、余姚的塑料,諸暨大唐的襪子,紹興、蕭山的紡織等等。

這些企業多為家族企業,它們缺機制、缺管理、缺人才、缺技術、可替代性強。一般看來,這些企業可能被邊緣化,被替代,但是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史晉川卻保持樂觀。他告訴《南風窗》記者,目前的浙江民營企業更多是接單、制作和售賣,沒有涉足研發、設計和品牌營銷等環節。嚴格來說,它們更像車間,不需要面對市場風險,從長期來看,他們的發展可能會圍繞大企業、大品牌自動分工,成為研發、設計和品牌營銷等某個環節。這對于中小民營企業是一個更有益的方向。而且他們將會享有更加完善的法律保障體系,受上游企業的干擾如欠款等問題將大幅減少。
其次是外溢效應遭遇質疑,對有明顯互聯網化和金融化為趨勢的杭州等城市尤其如此。
2018年中國企業500強名單中,在杭州的企業占24家。杭州作為二線城市,其大企業總部數量甚至高于一線城市廣州。但現實的情況是,杭州對周邊區域的產業外溢完全不如廣州。相比而言,廣州的大企業則更加傳統,汽車、日化、醫藥等,但他們的外溢效應更強,對周邊的產業帶動效應也愈發明顯。
杭州作為二線城市,其大企業總部數量甚至高于一線城市廣州。但現實的情況是,杭州對周邊區域的產業外溢完全不如廣州。
但史晉川仍然十分樂觀。杭州的外溢雖然還不明顯,但隨著中國互聯網工業的真正形成,以擁有“阿里云”的阿里為代表的杭州大企業,外溢效應會更加突出。
互聯網啟蒙時代稀里糊涂掙大錢的日子已經結束了,互聯網發展的下半場正在到來。互聯網行業的外溢效應或許有質的飛躍。
通過“互聯網+”這樣的數字產業,特別是包括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等企業的集聚,將進一步促進傳統制造業和數字產業互相滲透、融合,推進傳統制造業向產業鏈中高端升級,關聯開放經濟的產業鏈。
互聯網“落地”,并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這正是長三角所急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