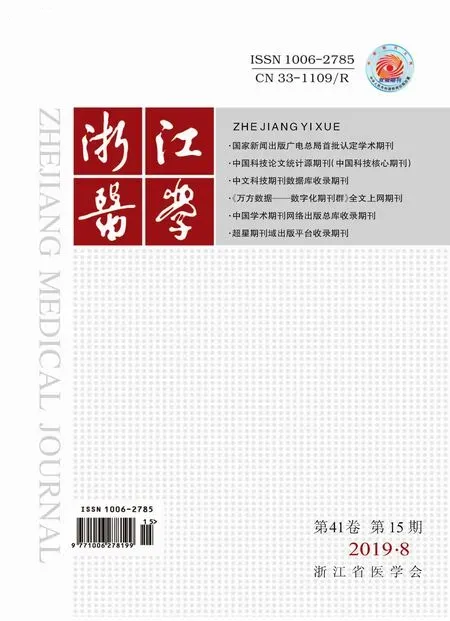橋本甲狀腺炎合并甲狀腺乳頭狀癌的診療進展
鄔一軍 朱敏潔 田赫迪
橋本甲狀腺炎(hashimoto thyroiditis,HT)是最常見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之一,亦被稱為慢性淋巴細胞性甲狀腺炎。1912年日本醫生Hakaru Hashimoto發現HT并進行了描述,其好發于30~50歲女性,是引起原發性甲狀腺功能減退癥的最常見原因[1]。甲狀腺癌是最常見的內分泌系統腫瘤,根據腫瘤起源或分化差異,又以甲狀腺乳頭狀癌(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PTC)最為多見,占90%以上,但其病程發展相對緩慢[2]。早在1955年,Dailey等[3]首次報道了HT與PTC之間的關系,此后的半個多世紀眾多學者對HT與PTC之間的相關性進行了系統的深入研究。本文結合筆者多年的臨床經驗,并參考近10年文獻資料,就HT合并PTC的流行病學特征、發病機制、診斷、治療和預后作一述評,以供臨床參考。
1 流行病學特征
目前,HT的年發病率為0.3‰~1.5‰[4],這主要是依據手術后病理學檢查結果的統計,而實際的HT發病率應遠遠高于這個數字。根據美國營養及健康普查數據,如果以甲狀腺過氧化物酶抗體及球蛋白抗體等生化指標作為診斷標準,HT的患病率可達46‰,其中女性的患病率為男性的8倍[5]。1987年Ott等[6]指出HT合并PTC的發病率為0.5%~23%。此后關于兩者合并發生的報道數量持續增加,但不同報道間發病率差異較大,目前的研究更著眼于HT與PTC的發生是否具有相關性。2017年有學者對多個國家的5 312例HT患者進行分析,其中9.03%伴有PTC,與正常人群的PTC發生率(7.05%,2 236/31 708)相比有統計學差異,并且女性HT患者較男性更易并發PTC(3.9∶1);此外,該研究還發現在11 155例PTC患者中18.9%伴有HT,與正常人群的HT發生率(8.23%,894/10 862)相比有統計學差異,并且女性PTC患者較男性更易伴發HT(4.8∶1)[7]。隨后的大量研究同樣發現兩者發病有一定的相關性。對于HT患者,伴發PTC的比例高于其他類型甲狀腺惡性腫瘤和良性甲狀腺疾病,有循證醫學研究提示HT合并PTC、其他類型甲狀腺惡性腫瘤以及良性結節的發病率分別為40.5%、7.9%、21%,其結果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TC患者術后回顧發現合并HT的發生率亦相對較高[8-9]。
2 發病機制
自Virchow[10]于1956年提出慢性炎癥是癌癥起源以來,該理論在諸多疾病中已得到證實。到目前為止,HT與PTC之間分子水平的關聯機制仍未明確。可能的基因分子學假說包括:(1)p-Akt(磷酸化的蛋白激酶B)在甲狀腺癌組織和甲狀腺包膜侵襲區域表達增加,PI3K/Akt途徑在HT和甲狀腺癌這兩種密切相關的疾病中起重要作用[11];(2)RET/PTC基因重排同時存在于PTC與HT的濾泡細胞中,它可能是炎癥或腫瘤進展的早期改變[12];(3)已被證明絲/蘇氨酸特異性激酶基因V600E(BRAFV600E)發生基因突變與PTC的發生、發展及預后密切相關[13]。在對204例患者的研究中發現,HT合并PTC將導致BRAFV600E基因突變率減低,并對甲狀腺癌的預后產生影響[14]。從免疫學角度來看,PTC的免疫機制包括依賴或不依賴免疫反應的兩種復雜過程,而HT作為一種甲狀腺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與免疫過程有著緊密的聯系,其中包括腫瘤的免疫監視作用。PTC的特點為生長緩慢及淋巴轉移,這可能與甲狀腺癌中的淋巴細胞浸潤相關,這種淋巴細胞浸潤或許會誘發HT的產生。PTC中存在B細胞浸潤時常獲得良好的預后,B細胞浸潤在甲狀腺癌細胞間,以甲狀腺球蛋白(TG)和甲狀腺過氧化物酶(TPO)為主要的靶抗原,產生TGAb和TPOAb。在甲狀腺炎的小鼠實驗中發現,TG和TPO似乎介導了CD8+T細胞的細胞毒性反應[15]。同時,在HT患者的甲狀腺細胞中有淋巴細胞的浸潤,會導致免疫豁免或者免疫監視減弱,因此甲狀腺細胞出現異常增殖時常不能獲得抑制,易出現甲狀腺癌[16]。總之,現有的研究并不能完美地解釋PTC與HT的分子相關性,HT患者由于甲狀腺自身長期的特異性免疫反應可能發展成為PTC,而PTC患者中存在的抗腫瘤免疫性使HT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得以發生和發展。
3 診斷
3.1 檢驗和影像診斷 診斷主要是依據甲狀腺相關的檢驗指標以及超聲的特異性影像學表現。TGAb和TPOAb是診斷HT的特異性指標,其檢驗的靈敏度分別為90%和74%[17-18]。PTC患者血清甲狀腺功能等一般在正常范圍內,少數會有促甲狀腺激素(TSH)水平的變化,但不特異。HT特征性超聲的表現為受累腺體呈彌漫性改變,具有廣泛低回聲,內部存在網格狀強回聲。PTC特征性超聲的表現為微小鈣化、低回聲、邊緣不規則、縱橫比>1、血供豐富等[19]。合并HT會影響PTC的正確診斷,原因是:(1)HT表現的彌漫性改變以及甲狀腺腺體網格狀強回聲,有時很難與甲狀腺多發結節鑒別;(2)HT甲狀腺腺體的回聲不均,增加了甲狀腺結節良惡性的鑒別難度,易造成誤診;(3)HT合并PTC常伴有多灶癌的發生,不仔細鑒別容易引起漏診。
3.2 細胞和組織病理學診斷 細針穿刺細胞學(FNAB)由于操作簡便和高靈敏度在診斷甲狀腺病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FNAB涂片,HT與PTC均可以由特征性的細胞改變得以確診。HT診斷主要是依據嗜酸性細胞,即淋巴細胞/漿細胞浸潤甲狀腺濾泡[20]。PTC診斷主要依據乳頭狀結構、核內包涵體、毛玻璃樣核、核溝、多核巨細胞、砂粒體等。Kumarasinghe等[21]指出在HT病變的基礎上出現上皮細胞增多,細胞核擁擠,細胞嚴重異型性及細胞間結合力破壞等現象時更應該傾向于合并腫瘤的診斷。對HT合并PTC患者進行FNAB檢查時,需要考慮到兩種疾病合并對穿刺準確性帶來的影響:(1)HT常伴有甲狀腺質地改變及多發結節,難以準確穿刺到病變部位,容易漏掉甲狀腺隱匿癌和微小癌;(2)HT合并PTC常有多發結節及多灶癌的特性,需考慮到FNAB假陰性的可能,必要時需結合超聲影像,多次、多針穿刺,以免漏診。組織病理學是診斷HT合并PTC的金標準,這需要粗針穿刺來獲得。HT的病理表現為存在彌漫性淋巴細胞浸潤,出現生發中心,細胞胞質嗜酸性變伴核增大(Hurthle細胞),正常濾泡細胞破壞等。HT合并PTC的組織病理學表現為細胞核不規則的輪廓擴大或拉長,核質比例增大,出現核溝和假的包涵體,染色質減少或染色質邊緣化,其組織移行帶間常出現以下病理表現:彌漫的淋巴細胞浸潤→上皮細胞增生→不典型增生→甲狀腺癌巢[22]。
4 治療
絕大部分HT患者可以隨診觀察。若病情逐漸加重,可嘗試抑制自身免疫的方法,如補充硒元素等。若HT導致甲狀腺功能減退則需行甲狀腺素補充治療。HT合并PTC診斷明確時需手術治療,治療原則主要依據甲狀腺癌的治療指南,術中行快速冷凍病理學檢查確診。臨床應依據腫瘤大小、數量、性質、位置及有無淋巴結轉移情況來制定手術方式:(1)單側腫瘤,腫瘤大小≤1cm,可行單側腺葉+峽部切除術;(2)單側腫瘤,若>1cm或合并對側良性結節,可行全甲狀腺切除術;(3)雙側腫瘤須行全甲狀腺切除術;(4)常規加行喉前淋巴結和患側Ⅵ區淋巴結清掃術;(5)若發現側頸淋巴結轉移,則需行全甲狀腺切除+中央區+患側頸淋巴結清掃術。鑒于HT合并PTC本身的特殊性,如甲狀腺彌漫性腫大產生壓迫癥狀、多發結節、多灶癌、隱匿性癌等特點,以及術后殘余結節仍易形成新的癌灶而導致再次手術等,術者在術前需和患者充分溝通,告知HT對PTC所致影響,并根據術中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手術方式。
由于HT患者甲狀腺體積較大,組織脆硬,術中容易引起出血和組織殘留,因此操作過程中需要仔細輕柔,注意鉗夾手法并及時止血,同時注意保護喉返/喉上神經以及甲狀旁腺。對于一側腺葉切除的患者,由于HT病情程度的變化會引起殘留甲狀腺功能的不穩定,故需要長期復查甲狀腺功能來調整甲狀腺激素的補充劑量。
5 預后
研究表明,PTC在合并HT的情況下,腫瘤會更易呈多灶性生長,單個腫瘤的體積往往較小,因而不易造成包膜侵犯、淋巴結轉移和遠處轉移,上文提及的HT是PTC的一個保護因素在此得以印證[23]。Moon等[24]薈萃分析了71項已發表的研究成果,結果顯示PTC伴發HT與腫瘤的局部侵犯、淋巴結轉移和遠處轉移以及復發成負相關。而Ye等[8]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甲狀腺癌預測因子,統計2 052例甲狀腺癌患者的T3、T4、TSH、TG和TPO,發現HT使患甲狀腺癌風險增加,但和腫瘤包膜侵犯、淋巴結轉移、血管轉移等無顯著相關性。一項針對PTC患者的前瞻性研究中,在腫瘤完整切除的基礎上對其進行24~120個月的隨訪,結果顯示HT和PTC的復發無關[25]。因此,HT對于PTC預后的影響尚有爭議。
6 小結
參考目前的研究報道,HT與PTC的相關性雖逐漸明朗,但結論仍未明確,兩者在形成機制上關系如何亦未有定論。許多文獻從臨床上獲得的結果也存在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種種跡象表明,HT對PTC發展、轉歸的影響亦有多種可能。因此,需要進一步臨床研究與基礎實驗以明確HT與PTC兩者間的相關性及作用機制,更好地指導HT合并PTC的診斷和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