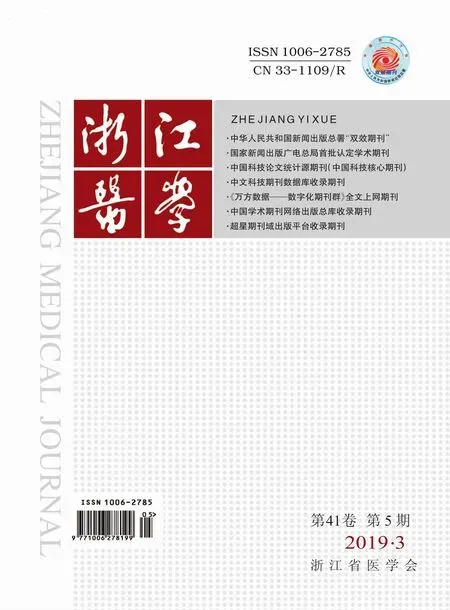超聲檢查在克羅恩病診斷與評估中的價值
陶錢紅 呂文 方建華
克羅恩病是一種累及胃腸道不同部位的慢性炎癥性疾病,也可同時累及腸外組織,其發病受環境、遺傳、自身免疫、腸道菌群等多種因素影響。克羅恩病的臨床表現缺乏一致性,其中累及消化系統表現為腹痛、腹瀉;累及其他系統則有前葡萄膜炎、口腔復發性潰瘍等非特征性表現;全身癥狀則有發熱、貧血、體重下降等。克羅恩病最大的特點是具有終生復發的傾向,它的臨床表現與疾病活動度通常不匹配,根據臨床表現來調整治療方案可能會嚴重影響患者病情的控制并增加醫療成本,因而方便、廉價、有效的評估檢查手段顯得尤為重要。目前臨床用于診斷與評估克羅恩病活動度、并發癥的方法主要有結腸鏡、腸道CT、MRI和C反應蛋白(CRP)、ESR及鈣衛蛋白水平等。結腸鏡只能觀察消化道的黏膜層,而克羅恩病為透壁性炎癥,其更深層次的腸壁及動脈血流狀況在內鏡下無法直觀評價,且結腸鏡作為一種侵入性檢查,通常不易為患者接受。病理活檢是臨床診斷克羅恩病的金標準,但當炎癥處于活動期伴發出血時,活檢并不被建議。作為克羅恩病結腸鏡下標志性特征的卵石癥在腸道CT下陽性率較低[1],且CT具有放射性、價格高昂等缺點。糞鈣衛蛋白也可較好反應腸黏膜的炎癥狀態,還可預測藥物治療的療效,便捷、特異性高,臨床應用價值逐漸增大。而超聲檢查近年來以其非侵入性、快速可用性和低成本等優點也開始用于克羅恩病的輔助診斷。本文就常規超聲、能量多普勒超聲、超聲造影、超聲彈性成像、超聲內鏡等各種超聲檢查在克羅恩病診斷與評估中的價值綜述如下。
1 常規超聲檢查在克羅恩病診斷與評估中的價值
腸道超聲檢查已成為疑似炎癥性腸病患者早期診斷的首選影像學檢查手段[2]。徐曉蓉等[3]研究發現,活動期克羅恩病患者常規超聲下表現主要有以下幾點。(1)病變為節段性分布(以末端回腸及其鄰近結腸多見),這是由于病變腸段之間的正常黏膜無炎癥浸潤。(2)增加的腸壁厚度是檢測腸內炎性活動的最顯著參數,常見的界值為小腸壁厚2mm,大腸壁厚3~4mm。一旦截止值從3mm增加到4mm,靈敏度從88%降低到75%,而特異度從93%增加到97%[4]。當前,臨床多選擇腸壁厚度>4mm為判斷界值,但其靈敏度較低,因此未來可以進行更多的臨床試驗以選擇更精確的數值。同時腸壁增厚也存在于其他炎癥性或腫瘤性腸病中,因此應用時應結合臨床表現及其它影像學資料。而病變腸管長度對于克羅恩病活動期的判斷沒有意義[5]。(3)腸壁分層的消失,也是炎癥活動的指標,這是由于腸壁脂肪浸潤、水腫或纖維化[6]。正常腸壁在超聲下呈不對稱的三明兩暗圖像即黏膜層、黏膜下層、漿膜層高回聲,活動期時以黏膜下層回聲增高、增厚最為顯著;黏膜肌層、肌層則呈低回聲,活動期時以固有肌層為主,因而分別專注于黏膜下層及固有肌層,即可更簡單、更直觀地判斷病變活動度[7]。(4)腸管可纖維化,使得蠕動減慢,甚至狹窄繼發擴張[8]。(5)腸道炎癥通常不局限于腸壁,比如腸系膜外部的脂肪變化可能比腸壁本身的改變提供更多腸段炎癥狀態的信息。(6)病變腸段周圍可見多個腫大淋巴結,考慮為炎性反應增生,但這在緩解期也可見。(7)在超聲檢查中,克羅恩病的并發癥如腹腔膿腫表現為低回聲病變,伴有后部回聲增強和鄰近高回聲的肥大腸系膜;瘺管表現為細小低回聲的導管或腸袢之間的小區域或腸袢與其他結構(皮膚、膀胱等)之間的小區域,其中可能包含由空氣或腸內容物引起的內部回聲斑點[9]。若在超聲下看到氣體樣強回聲,尤其是貫通腸壁全層者則考慮腸穿孔[10]。且即使當抗TNF治療導致腸壁表面開始閉合時,直腸超聲仍可識別出未愈合的瘺,因此它是評估治療效果和避免早期停止治療導致復發的有效選擇[11]。克羅恩病患者緩解期時,腸壁增厚通常不明顯,故超聲下不易診斷;但通過治療前后超聲聲像圖的對照,可較好地評估療效[3]。
李少春等[12]發現,腹部超聲對克羅恩病診斷、定位、并發癥判斷的準確率均要顯著高于X線,分別為86.0%、100.0%、82.5%。Panés等[13]則指出腹部超聲檢測這些病變的靈敏度為 85%(95%CI:83%~87%),特異度為 98%(95%CI:95%~98%),但個體經驗、病情嚴重程度及受累腸段的定位對結果也影響很大。Wilkens等[14]將超聲與結腸鏡評估克羅恩病的有效性進行比較,發現超聲在結腸鏡無法完善的情況下,可對活動性克羅恩病患者的病變范圍與嚴重程度作出正確評估,可作為結腸鏡的重要補充。Castiglione等[15]研究指出,MRI比超聲能更好評估克羅恩病,因此超聲可在MRI前作為克羅恩病的初始檢查。綜上,超聲檢查不僅可診斷克羅恩病,監測治療的效果,控制內鏡檢查的最佳時間,還能提供內鏡無法到達區域的信息[16]。
2 能量多普勒超聲在克羅恩病診斷與評估中的價值
能量多普勒超聲不受血液流速、血管位置的影響,能較好地觀察微小血流、末梢血流、低速血流,從而評估腸壁血管化程度[17]。克羅恩病除了腸壁增厚外,同時還存在新生血管的增多[7],病變段腸壁在能量多普勒下可分為Limberg 0型(正常腸壁)、LimbergⅠ型(腸壁增厚)、LimbergⅡ型(在LimbergⅠ型基礎上出現短血管)、LimbergⅢ型(在LimbergⅠ型基礎上出現長血管)、LimbergⅣ型(LimbergⅢ型基礎上出現的長血管能與腸系膜相連)。克羅恩病的炎癥水平與血流速度、腸壁血管化等級、Limberg分級均呈正相關。目前認為LimbergⅠ、Ⅱ型為克羅恩病緩解期,LimbergⅢ、Ⅳ型為活動期[7]。胡浩清等[18]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測量了腸壁內動脈阻力指數,發現克羅恩病患者均明顯低于對照組,但無法據此區分活動期與緩解期。Ribaldone等[19]研究發現,術后1年的克羅恩病患者接受腸鏡與超聲復查,54.5%的患者可同時顯示腸壁厚度>5mm和正功率多普勒,提示在隨訪過程中,可先行能量多普勒超聲檢查,陽性的患者再進一步接受結腸鏡檢查以評估復發情況,并調整治療方案。劉暢等[7]將疾病活動指數與能量多普勒超聲進行比較,發現后者判斷克羅恩病活動度的準確度更高;但是,若不能選擇合適的能量閾值,會降低準確度,進而遺漏克羅恩病的病情變化。因此當前,將能量多普勒超聲應用于克羅恩病的診斷與評估,還需要更多的臨床研究結果加以佐證[11]。
3 超聲造影在克羅恩病診斷與評估中的價值
通過檢測腸壁的血管化程度來評估克羅恩病活動度,超聲造影不失為一種好方法。它可以量化與炎癥性指標如CRP或疾病活動指數直接相關的血管化程度。歐洲醫學和生物學超聲學會聯合會明確了超聲造影在炎癥性腸病患者中的具體應用指征,包括以下內容:(1)估計炎癥性腸病的疾病活動度;(2)區分克羅恩病中的纖維化和炎癥狹窄;(3)確認疑似膿腫;(4)確認瘺的途徑[20]。但此共識存在異議,Wilkens等[21]研究發現,超聲造影或增強MRI均不能區分克羅恩病中增厚的腸壁為炎性還是纖維化。明確狹窄的性質影響著疾病的治療方案制訂,因此還需深入探究超聲造影在此中的作用。還有研究發現,Limberg分型越高,血管分布范圍越大,超聲造影的峰值時間、流入時間越長,達峰強度越高[7,22],說明在評估克羅恩病活動度時,可綜合考慮以上因素。但Serra等[23]提出超聲造影參數提供的是定性而不是定量的血管化評估,這使得它的作用局限于彩色多普勒檢查結果可疑或陰性時。Ripollés等[24]避開腸系膜組織及管腔選取增厚腸壁中強化最明顯區域作為感興趣區,以內鏡下確定的嚴重程度作為參考標準,定量分析感興趣區的增強對比劑攝取情況(腸壁感興趣區灰度值上升百分率),評估受累腸壁的血管化,得出這些定性的超聲造影參數預測中度或重度炎癥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分別為96%和76%。胡英等[25]把腸壁感興趣區灰度值上升>55%作為判斷克羅恩病活動度的臨界點時,靈敏度、準確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93.2%、90.3%、83.3%,而以腸壁厚度、腸壁血流分級作為判斷標準時,準確度則分別為80.6%和69.4%,3者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最近,有研究又以內鏡和臨床指標作為參考準則,分析了在檢測克羅恩病活動度方面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分別為93%、87%,且活動期小腸絕對碘密度及相對碘密度均顯著高于正常小腸(均P<0.05)。這提示臨床可進一步研究碘量化指標在評估克羅恩病活動度和監測療效中的價值。超聲造影可區分血管與其它組織,可用于區分膿腫和蜂窩織炎。在膿腫的診斷中,超聲超影與MRI的結果沒有明顯差異,而在瘺管和淋巴結病變診斷中,MRI的靈敏度更高[27]。綜上,超聲造影可用于判斷克羅恩病活動度并預測疾病復發風險,但其評估并發癥的作用還有待深入探討。
4 超聲彈性成像在克羅恩病診斷與評估中的價值
超聲彈性成像包括剪切波彈性成像與應變彈性成像等,是一種用于評估纖維化的非侵入性技術。它通過測量準靜態機械力(手動壓縮、心血管脈動、呼吸運動)引起的組織應變來量化判斷組織的硬度、病灶的特性和深度范圍,因此認為其能可靠地反映克羅恩病患者的腸道纖維化程度。Dillman等[28-29]近年用剪切波彈性成像技術先后在克羅恩病大鼠模型和人體中區分了腸道急性炎癥和腸壁纖維化,并認為腸壁剪切波速度隨著腸壁纖維化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但由于組織內炎癥存在,兩者并非線性關系。多達30%的克羅恩病患者在確診后10年內出現纖維性狹窄,而這對治療有明確的影響,因為病變以纖維化為主時,不太可能對抗炎治療(包括生物制劑)有反應,此時最好是采用手術干預或內鏡下擴張。了解克羅恩病病變炎癥和纖維化病變的相對比例,有助于優化治療決策和疾病管理[30]。但是Serra等[23]指出,超聲彈性成像結合應變率并不能區分克羅恩病腸道狹窄為炎癥性還是纖維性,因為腸道狹窄通常炎性與纖維化并存,且缺乏準確的參考組織,腸壁下方結構復雜,即使僵硬也存在剩余蠕動。因此,臨床需要大樣本研究以探討是否可以根據腸超聲彈性成像可靠地檢測腸纖維化,并確定標準化量化腸纖維化的最佳方法[31]。
5 超聲內鏡在克羅恩病診斷與評估中的價值
超聲內鏡集合了內鏡與超聲的特點,目前已被廣泛應用于炎癥性腸病的診斷,它可以在結腸鏡發現病灶時,直接利用超聲觀察[32]。且它能垂直觀察受累腸壁的各層結構,從而評估病變情況。因此相比于常規超聲,超聲內鏡對克羅恩病并發癥(如肛周瘺管和膿腫)及腸壁外腫大的淋巴結具有更高的陽性檢出率[33]。邱恩琪等[34]研究結果顯示,超聲內鏡診斷克羅恩病的靈敏度、特異度和準確度分別為87.5%、87.8%和87.6%。且對于克羅恩病直腸及肛周并發癥的診斷,大腸超聲內鏡較于瘺管造影術、CT和MRI檢查等已被證明具有更好的效果,可為手術治療提供精確的解剖信息[35-36]。此外,超聲內鏡可用于鑒別克羅恩病和潰瘍性結腸炎[32]。但是由于克羅恩病在上消化道如食管、胃和十二指腸等處較少見,因此需大樣本研究進行更確切的觀察。雖然超聲內鏡在評估克羅恩病活動度方面具有優勢,但其要求操作者不僅要具有熟練的內鏡技術,還要有一定的超聲知識,且仍需結合病理結果及臨床表現共同考慮[33]。
6 小結
綜合考慮診斷克羅恩病及評估克羅恩病活動度、并發癥的靈敏度和特異度,以及患者的接受程度、費用、便捷性、風險、適用范圍等,超聲檢查相比于其他檢查具有明顯的優勢。在常規超聲檢查中,活動期克羅恩病患者主要表現為全層腸壁增厚或以內側腸壁增厚為主,輕者僅表現為黏膜下層增厚,并呈稍高回聲。能量多普勒超聲可顯示活動期克羅恩病患者血管化程度加重;超聲彈性成像可觀察克羅恩病患者腸道纖維化嚴重程度;超聲內鏡可觀察到克羅恩病患者腸外并發癥。臨床若綜合使用以上各種超聲檢查技術,能明顯提高診斷與評估克羅恩病的準確性,并預測疾病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