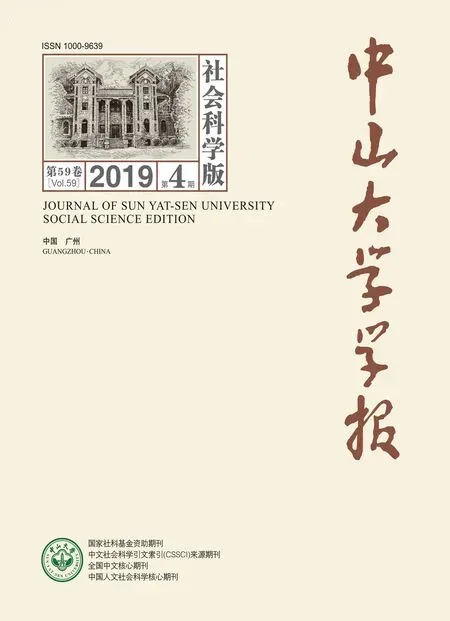文化自信的對話性建構*
金 惠 敏
中國和平崛起,進而參與全球治理,以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解決世界乃至人類普遍性問題,遠不再是從前那種國際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豪言壯語,而是切切實實地正在發生著的偉大歷史事件。與經濟、科技、軍事和政治上大國地位日益凸顯的過程相呼應,從1980—1990年代在民間開始醞釀,到中央層面上2011年胡錦濤首開關注①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1年7月1日),《人民日報》2011年7月2日,第2版。,2016年習近平兩次隆重闡述②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報》2016 年5月19日,第2版;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6年7月1日),《人民日報》2016年7月2日,第2版。,接著2017年在十九大開幕會上莊嚴昭告③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17、19、23、41,41頁。,文化自信逐漸演變為現今政治宣傳、學術研究和日常生活最活躍的話題之一。四大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它榮居其一,而且與其他自信相比,被渥眄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攀升至從未有過的歷史高度④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17、19、23、41,41頁。。
文化自信“信”什么?當然是信“自”了,是對自身的信心與驕傲。但“自”“自身”又是什么呢?對此,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有最新、最權威的表述。他指出,文化自信就是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自信,這種文化首先由兩大成分構成:一是“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然則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文化絕不停留于一種觀念或話語的形態,相反,它“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⑤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17、19、23、41,41頁。。由于其實踐性品格,由于其從而被宣示的“不忘本來、吸收外來”“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以及“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文明交流”“文明互鑒”“文明共存”而非“文明隔閡”“文明沖突”“文明優越”等基本原則,這樣的文化當然也是“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了包括外來文明成果在內的一切人類文明成果的,是本來文化的當代化,是外來文化的在地化,是作為話語的人類一切優秀文化的具身化和現實化[注]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第23、25、59、41頁。。對此,以習近平為首席作者的《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講得異常清晰,不存在歧義和歧解的空間:“創造創新是文化的生命所在,是文化的本質特征。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文化的發展,都離不開繼承傳統和借鑒外來,更離不開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凡是源遠流長、歷久彌新的文化,既滲透著歷史基因又浸潤著時代精神,既延續著本土文化的血脈又吸納著外來文明的精華。”[注]劉奇葆:《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本書編寫組:《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36頁。這即是說,如果就其來源而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也一定是“我中有他”“我中有異”的,當然此時的我中之他、我中之異已非先前之他、之異,它們因脫離其原先的語境而不再是其自身。它們獲得了新的歸屬,即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一個有機部分。
按理說,有十九大報告之權威表述以及近年來數以千計萬計的闡釋類文章,對于什么是“文化自信”這樣基礎性的問題不應該再有什么討論的余地了。但事實是,我們發現,文化自信并非不言而喻,而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甚或言之即非。這其中,對文化自信的民族主義和復古主義的偏執理解尤為劌目怵心[注]參見金惠敏:《人類文化共同體與中國文化復興論》,《人文雜志》2019年第2期。,似乎早已氤氳成一種公共闡釋,乃至社會情緒。例如,每逢中外某種摩擦或沖突之發生,文化自信便經常火爆為網絡口水大戰,甚至有時還被傾瀉為一場場街頭鬧劇或悲劇,以至于官方總是不得不出面提醒“理性愛國”云云。
文化自信事關國家命運、民族強盛,事關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換言之,文化自信既是中國的問題,也是世界的問題,甚或是全人類的問題。文化自信是顯示一個國家軟實力的核心標志,或簡言之,文化自信即文化軟實力。如所周知,“提高文化軟實力,不僅關系到一個國家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而且關系到一個國家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④劉奇葆:《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本書編寫組:《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36頁。。一個被扭曲了的文化自信如文化民族主義,不是文化軟實力,而是文化破壞力,必將誤國誤民,并殃及世界。職是之故,如何正確把握、熔鑄和傳揚我們的文化自信便是一項亟待研究的政治課題和學術課題了。
正確理解文化自信,關鍵在于正確理解一個“自”字,即正確理解什么是文化自我和文化特殊性。基于這一認識,本文將針對文化民族主義和文化原教旨主義的文化特殊論,從能動自我、結構自我兩個新創概念,從前蘇聯文論家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論,重新界定自我和特殊性,將其作為一種對話性的生成和建構,提出自我即對話、特殊性即對話的理論命題。文化自信由此而得以成為一個開放的而非封閉的、動態的而非靜止的、生活的而非教條的、當代的而非復古的概念,即是說一個對話性的或曰間性的概念。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我們需要這樣的文化自信!
一、能動自我、結構自我與文化“自”信
談論文化自信,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當是其首要的所指。毫無疑問,重振文化自信就是恢復對于自身文化傳統的自信,凝聚自我文化身份。盡管在結構主義者看來,自我是各種話語和體制的想象性建構,但這僅僅是就其構件而言的;一旦這些構件得以形成一個有機體,發揮其功能,那么它便不再是構件而成結構了。結構主義一個致命的弱點是在自我中只看見構件,而不見結—構,不見構件之結合而成一新的功能體,更不見此結構實乃一生命。作為結構(structure)的自我也是生命的自我,是能動(agency)的自我[注]在當代社會學中,結構指社會對個體的影響,而能動則是個體行動和改變社會的自由。套用馬克思的話,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這叫“能動”;但說他們并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而必須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創造,則指的是“結構”(See Anthony Giddens & Philip W. Sutton, Essenti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2014, p.23-26)。筆者的“能動”概念要寬泛一些,不僅指個體的行動(表面上),更指個體的生命及其能量(深層里),因為有生命,而后才有行動,行動的本質是生命的沖動和運動。此外,筆者還特別強調結構的能動性,即結構而成生命,與能動的結構性(起源上或構成上)和結構化(對外在資源的整合),于是結構與能動的二元對立被徹底打破。不過在具體使用中,筆者有時也保留了能動的積極性與結構的消極性,二者仍是各有其意義側重點的術語。。凡結構必有生命隱含于其間,反過來說,無生命則不成結構。試想,假使不存在能動的言說者,那究竟是誰在推動德里達所謂的能指的“延異”?能指無能,能指自身無能于“延異”,能指的“延異”根本上是言說者為了實現其最終意指的“延異”。
與結構主義將主體風干于虛無縹緲的符號世界不同,吉登斯夫子自道:“就社會理論而言,最重要的進展并非與一個語言轉向多么相關,而是更系乎這樣一種被修正過來的觀點,即主張言說(或意指)與行動相交接,這一修正提供了一種嶄新的實踐(praxis)概念。”[注]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An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1986 [1984], p.22,25.其“結構化”(structuration)理論若就字面上看似乎不過是符號自身的游戲性展開,仍然閉鎖在結構主義的深宅大院,但實際上由于他將結構置于鮮活的實踐之中,讓言說與行動相交接,結構因其不只是對行動者的限制,而且也是行動者借以行事的規則和資源,那么,了無生命跡象的結構便進入了生命的過程:“結構并不‘外在’于個體:作為記憶的雪泥鴻爪,作為在社會實踐中的具體顯現,它在某種意義上毋寧說是‘內在’于,而非如涂爾干所假定的,是外在于個體的活動。結構絕不等同于限制,它永遠是限制與使動(enabling)兼而有之。”③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An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1986 [1984], p.22,25.吉登斯雖非完全否認結構,例如在涂爾干那里(“社會事實”[注]涂爾干以“社會事實”(socialfacts)指稱符號系統、意識形態、經濟制度、道德義務、宗教信仰及其實踐,它們對于個體的構成和行動具有“外在性”(exteriority)和“制約性”(constraint)。此外,涂爾干還提出“將社會事實視作物”(consider social facts as things),其意在突出社會“事實”具有堅硬如自然之“物”即輕易不為直覺所透視、不為個人意志所塑造的特性(See Anthony Giddens,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of Marx, Durkheim and Max We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86-91)。在否定的意義上,涂爾干的“社會事實”也是吉登斯結構化理論的來源之一。)對于行動者的制約作用,但他更愿意做的顯然是,賦予結構以生命,讓結構具有“使動”因而具有生命的功能。不過,在此需要明確一下,結構之“使動”并非意味著結構本身自動地給予行動者以行動的能力,而是行動者將死的結構(規則和資源)使用為活的生命,使其在為生命活動的服務中轉化為生命的一個組成部分。對此,吉登斯未作嚴格而清晰的界分,其解說即“結構與能動相互包含。結構是使動,而非只是限制,它使創造性行動得以可能”[注]Anthony Giddens & Philip W. Sutton, Essenti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p.25.,歧義叢生,讀者極易陷進結構本身在行動這樣的錯誤觀念之中。準確地說,作為規則和資源的結構只是有助于行動者達到其目的,其本身無能行動,“使動”的是行動者。但無論如何,在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中,結構與能動不再是兩個對立的范疇,不再是結構取消能動,或者能動無視于結構,它們在實踐中合二為一:接合,并融合。吉登斯之引結構入能動或者說化結構為能動的這種理論努力,在結構主義深入人心的1980年代里,實屬難能而可貴!
對于我們的命題,結構即生命,即能動,吉登斯道出了它的第一重意義,即結構融入能動而獲得能動,換言之,是能動賦予結構以生命或生命的力量;但更根本的則是其另一重的含義,即結構化(讓我們繼續使用吉登斯這一未盡其用的術語吧)在起源上即產生能動。在這里,我們不必談論生命在其原初出現時便是各種元素的陰陽化育,每一種文化——其身份,其特殊性——的形成較之自然生命的誕生都更顯其在來源上、構造上的復合性。沒有哪種文化不是結構而成的。結構化,更準確地說,趨向于結構,乃生命之形成過程,結聚、構造而成生命。我們不是生命的先在論者,即堅持先有生命而后再有生命對結構的使用這樣庸常思維中的論點,而是認為自然的生命是自然的結構化,文化的生命是文化的結構化。此乃其一。但是,其二,一旦結構而成生命,那么生命便以其能動而對自然進行積極的回應和改造。在人的生命這個層次上,文化以人作用于自然的方式,但更以在人作用于自然的過程中與其他人建立互動關系即主體間性的方式被創造出來。是人的生命創造了人的文化,這一創造物為文化生命;而既然作為生命體,它便一定要繼續外突、外顯、搶占和入侵,這仍是一個結構化過程,即是說,它仍需不斷地結構進其身外的自然和社會語境以及與其相遇的其他文化,如同滾雪球一般把一切能夠吸附的東西都碾壓進來。這樣的文化就更顯其結構化之本質特征了!可以認為,文化從來就是結構性的,無論其在始源上抑或在表現形態上。
然而,揭示和坐實文化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必然導向對其作為生命的否定。叔本華以剝洋蔥為喻,說尋找人生的意義如同剝洋蔥,剝到最后一無所有。羅蘭·巴特也使用過這一比喻,認為根本不存在作品或作品的內核,而只有一層層疊加的文本或文本間性,文本之內無一物。延展這一比喻,也許結構主義者會說,尋求文化的生命,或者,界定文化的特殊性,就像剝洋蔥一樣,但見一層層的結構,而不見生命本身。其錯誤顯而易見,即如前所謂,結構主義者不了解結構與構件的不同:結構是有機的,而構件則是無機的。例如在個體的結構中,若是刪除其文化、其肢體等構件,那么個體及其生命亦將不復存在。這也就是說,生命是整個的洋蔥,而非某一層面的洋蔥。同理,文化是結構的,但也是結構整體的或結構有機體的。
既然結構即生命,結構即能動,那么結構自我與能動自我的關系,在二者作為生命、自主和獨立個體的意義上也就沒有必要劃江而治了,它們本就是一家。自我可以還原為結構,而結構亦可組構為自我。結構自我同時即是能動自我,反之不謬。據此命題,我們可以從容不迫地斷言,中華文化既是結構性的,但也是生命性的。無論其構成多么混雜,其來源如何多樣,如歷史學家所證明的,中華文化都仍然具有其區別于其他文化的特殊身份,都是一個有機能、有意志的生命存在。就像將主體風干為語言符號,以結構來解構中華文化特殊性的嘗試,也注定是勞而無功的。作為生命,每一種文化都有其基因般的存在。不要不相信文化的生命性存在,即便在吉登斯之結構化的意義上。
中華文化產生于中華民族的生活實踐和社會實踐,能夠滿足中華民族的文化需求,包括日常倫理需求和形上之精神需求以至信仰需求,生生不息而成所謂之“傳統”,薪火相傳,綿延不絕。傳統是活著的歷史,而遺產則是有待復活的歷史。至于人們讓哪些遺產復活,或者,讓哪些遺產繼續冷藏,則取決于其不停躁動著的生命欲望及其所外化的社會實踐。我們熱愛自己的文化傳統,并非表明我們多么地戀舊、念舊,而是我們所置身其中的文化體即我們的生命與其形式建構了比較牢固的粘合。因而必須指出,人不是文化的形式主義者,其所秉承的總是文化現實主義。現實流變,文化亦相應地跟著變化。就其決定性作用而言,文化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生命和實踐。這本來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物質決定精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推及文化內部而言,即視文化由生命與其外化(而為所謂的“文化”)兩部分構成,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命題仍然有效。人們常常是錯把文化的話語維度當成了其生命維度。其實,文化的話語以及話語實踐維度之所以重要,只是因為它附著于生命,是生命的表征;然而滑稽的是,它有時竟儼然代表著生命,以生命本尊自居!因此,我們不能抽象地談論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傳統,而是要立足于當代文化之現實需要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文化復古主義者忘記了其腳下的大地,其實質是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
強調中華文化的自我性、自我能動性,或者,作為能動自我的中華文化,絕不意味著一個自我封閉的單子世界,相反,它是一個自我敞開的“大同”世界,因為生命在于能動,在于運動,而運動則必須是離開自身而向外伸張,伸張到身外的世界,異在的世界。生命有賴于異在和他者!趁便指出,古人所謂的“大同世界”并非同一性的世界,而是美好的“相與”世界,是我“與”你而非我“馭”你的世界,進一步,也是我“與/予”你的世界,相互贈與/予,彼此得益;用英語說,是GreatWith-ness的世界,是“GreatWith-Win”的世界。
結構主義的自我觀也并非全無道理。自我首先是生命的自我,身體的自我,物理的自我,人生功名利祿無不托于此身,故老子有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老子》第13章)誠哉斯言也!身體是自我之根柢,它們一體不二,是以習謂“身體自我”亦為不謬。但另一方面,自我也是,或許應該更是,象征秩序的自我,認識論的自我,話語的自我,社會的自我,等等。前者處于一種無意識狀態,是盲目和盲動的存在;后者則是對自我的認識,即是說,自我認識到了他的自我存在。當自我成為自我意識的對象時,自我遂開始成型。自我是一種意識現象,自我是自我意識。然而處于意識中的自我不是孤立的自我,渾噩的質料,而是關系中的自我,進入象征秩序的自我。我是誰?我自身是無法定位我自身的,自我的出顯必須借助于他物、他人,在他者所構成的關系網中確定自身的位置。拉康說,這個他者在人之初是鏡像,嬰兒在鏡子里發現其自我;及其長也,鏡像被替換為語言,是語言符號構造了其之為自我。
德國語言分析哲學家圖根德哈特反對經典近代傳統將自我意識與客體意識對立起來的做法,他從第一人稱“我”的出現及其意謂角度揭示了呈現在意識中的自我與世界(其他客體)之間一存俱存、一亡俱亡的相互依賴關系:“通過述謂語言,對其他客體的意識和將自己作為其中的一個客體的意識統一起來,兩者都處于對一個客觀世界的意識關聯之中,我和其他人在這個世界中都有各自的位置。”[注][德]恩斯特·圖根德哈特著,鄭辟瑞譯:《自我中心性與神秘主義:一項人類學研究》,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第22頁。引文根據該書德文版(Ernst Tugendhat,Egozentrizit?t und Mystik: Eine anthropologische Studie,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 Auflage 2004, S. 28-29)有所改動,下同。這就是說,自我同時意識到其自身和不屬于其自身的其他客體,而且更為關鍵的是,圖根德哈特進一步指出:“如果一個命題言說者沒有對一切事物即對一個客觀世界的意識,他就不可能有自我意識。同樣,如果他不能夠指稱自己的話,他就不可能有對客觀世界的意識。”[注][德]恩斯特·圖根德哈特著,鄭辟瑞譯:《自我中心性與神秘主義:一項人類學研究》,第22,22頁(Ebd., S. 29)。自我與世界相生相克、相反相成。淺近言之,以“我”所標志的自我是區別性的,而所謂區別也就是同時假定了兩個事物的存在,在此即自我和世界的存在。“我”在世界之中,“我”從世界中走出即與世界相揖別而后出顯為自我。在命題語言中,“我根本不是用‘我’來確認我自己”[注][德]恩斯特·圖根德哈特著,鄭辟瑞譯:《自我中心性與神秘主義:一項人類學研究》,第21頁(Ebd., S. 28)。“確認我自己”(mich … identifiziere)可以理解為“建構自我的身份”。,我無法做到這一點,“我”必須經由對“我”的述謂即作為主語“我”的謂詞部分將“我”表述出來。那謂詞部分表述的固然是“我”之性狀,但此表述所借用的種種元素則不屬于“我”,即“我”是被“我”之外的事物(作為能指)所確認和建構的。
這就回到了拉康和海德格爾多次說過的“不是我在說語言,而是語言在說我”的那一著名論斷。自我的確立及其意義需要通過外于它的符號體系來完成。在此意義上,一旦說到“自我”,也就先已說到了他者;同理,一旦說到“主體”,也就先已說到了“交互主體”。依據圖根德哈特的表述,一旦有人說“我”,他也就是說到了與其相同的多個說“我”者:
沒有人會單單為了自己而說“我”,理解這個詞,意味著理解了,每個人說出“我”時,他指涉他自己……而一旦我會對自己說“我”,那么,對我來說,諸多其他的說“我”者就是實際存在的了。這樣,不僅一個獨立存在的客觀宇宙為我而構造起來,我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這個宇宙中的一部分也由彼此獨立的感知著的說“我”者構造起來,每一個言說者都具有自己的感受、愿望、意見等等。④[德]恩斯特·圖根德哈特著,鄭辟瑞譯:《自我中心性與神秘主義:一項人類學研究》,第22,22頁(Ebd., S. 29)。
由此而言,自我的確立也同時帶有了倫理的意義。薩特是錯的,他人不是地獄。蘭波是對的,蘭波說,我就是一個他人(Je est autre)[注]Arthur Rimbaud, Oeuvres complètes, éd. Antoine Adam, Paris: Gallimard, 1972, p.250.。他人是自我的成就者!自我需要依賴他人而成就自身。自我從來就不是單純的自我,打開看,它就是社會的構造物。在其現實性上,即當其實現和展開之時,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但自我也不會在這種總和中喪失自己,泯然眾人,而且如圖根德哈特所警示,“如果他不能夠指稱自己的話,他就不可能有對客觀世界的意識”。這種說法并不導向唯心主義,它指示的是,恰恰是因為有了主觀之“我”,整個世界才可能被劃分為自我的世界與自我之外的世界,后者無論是自然抑或社會都具有不輕易服從于我的主觀意志的外在性。自我是重要的,自我帶出了世界。當然,它同時也被世界所帶出。二者相攜而出!
在圖根德哈特所演示的語言哲學和拉康等人的后結構主義視野中,如果從復古主義和教條主義角度來要求和期待文化自信,那么其中的自我就像自言自語地說“我”是誰、“我”怎樣一樣顯得不可思議。因為,如圖根德哈特所發現,“沒有人會單單為了自己而說‘我’”,即便是瘋人的自說自話,然一經使用語言,其表達便不再屬于自我而進入世界了,盡管瘋言瘋語中的世界是被扭曲了的世界。不存在私人語言,如維特根斯坦所堅持,這個我們好理解,任何語言都是公共的,語言的世界是公共的世界;不過遺憾的是,許多人并不十分了解,即使語言被私人化地使用,使私人言說具有特定的內容和風格。但這樣的言說也仍然是公共的,其公共性在于言說總是言說給他人,言說根本上是交往性的,言說者聽眾的多寡無法撼動語言的公共性。個人日記也不是私人言說。或許在某些情況下,一份日記除卻其作者本人之外沒有任何其他讀者,但記日記的過程則是一個與理性的對話過程,是整理、清理、梳理個人化的活動和感受、感想。通過付諸言說這樣的行為,私密的空間先已為理性所探視、檢閱和規制,即原則上已成為公共的空間,而后只要作者本人同意,其他人是可以閱讀和分享的,不存在任何根本性的障礙。海德格爾講得好:“依其意義而論,每一言說都是向他人且與他人之言說。至于在此是否實際地存在著面向某一具體之他人的一種特定的致辭,對于言說的本質結構是無關緊要的。”[注]Martin Heidegger,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Gesamtausgabe, Band 20,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9, S.362, S.362, S.361.由此而論,“作為此在即共在的存在方式,言說在本質上就是共享(Mitteilung)”②Martin Heidegger,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Gesamtausgabe, Band 20,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9, S.362, S.362, S.361.,換言之,“言說即造成公共”③Martin Heidegger,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Gesamtausgabe, Band 20,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9, S.362, S.362, S.361.,無待乎言說什么以及以什么方式言說!同樣道理,一種文化,無論其如何宣稱、強調自己的特殊性,只要其特殊性一經言說,也無論是自己言說還是由他人言說,就已經進入話語、翻譯、交往和他者了,因而也就一定是公共的、共享的和世界性的。
文化復古主義和教條主義總是在念叨,中華文化是特殊的、獨一無二的、不可轉譯的,具有不可與外人道哉的微妙。例如,有中國學人就放言,漢學者,西學也,即其以西方的話語和方法得出此話語和方法所預定的結論,與真實的中國及其文化毫不相干。面對來自中國同行的輕視,作為外人的法國漢學家朱利安表現出有節制的抱怨,似乎深得“怨而不怒”的中國古訓:“對于并未成長在其文化氛圍中的外國人能否進入其中,他們表現得有所保留。”[注][法]朱利安著,高楓楓譯:《美,這奇特的理念》,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44頁。在此朱利安說的是,能否深入中國傳統“美學”淵源。再者,這些國學原教旨主義者還堅持,在一個對話主義時代,若是沒有自身的特殊性,不凝聚自我的身份,中國文明也將失去與世界文明進行對話的資本與前提。
這些聽起來都很在理,文化確乎是特殊的,是在一定的地域中生活的人們所建構起來的生活方式以及支撐這一生活方式的價值、精神、信仰和制度。但是,讓我們再次從能動自我及其結構化屬性的角度來駁難吧,如所周知,文化特殊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身份并非一開始就是特殊的,任何一種文化從其起源處便是混雜、融合的結果,西方文化如此,中華文化亦非例外;而且文化也是流動的,在其發展過程中,它總是不斷地為我所用地汲取外來文化營養。文化不挑食,它是雜食者,故能成其葳蕤。據《國語》之記言,中國古人早就明白雜合之于生命成長的重要性:“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注]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470頁。雜合是萬物生長的規律,是人丁興旺的規律[注]認識到“同則不繼”這一規律,“于是乎先王聘后于異姓”(徐元誥:《國語集解》,第472頁)。,進而也是諸如調口、衛體、聰耳、役心、成人、立純德、訓百體(百官之體)[注]徐元誥:《國語集解》,第470—471,472頁。的規律,而這一切(它已經是全部的人類生活)不也說的是文化嗎?!即是說,雜合同樣是文化生長的規律。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夫如是,和之至也。”②徐元誥:《國語集解》,第470—471,472頁。
秦相李斯更是直擊雜合之于文化發展的意義。在其《諫逐客書》中,他以音樂為例:“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禹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禹,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倘使只是固守一種本地音樂,如秦樂,“真”則“真”矣,純則純矣,然如此便不能“快意”“適觀”即滿足視聽等感官的“當前”需求了!在傳統和需求之間,需求總是被優先考慮。在此文中,李斯之“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云云[注]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56頁。,也同樣是暗示說,一切風俗即文化形式都必須讓道于民富國強這個堅硬的指標,以此為鵠的,則沒有什么文化是不可移易的,即便是“真秦”之文化。顯然,李斯看到了文化以雜合的方式向前發展,如泰山之不讓土壤,河海之不擇細流,而且他也透徹地體悟到文化的存廢興替悉以人之需要為轉移,并不株守某一傳統而不放。如果說《諫逐客書》之“客”乃文化之他者或一切異質的因素,那么李斯所呼吁的便是一種容異、用異、融異的文化理念。如《國語》所示,這也是一種文化之所以能夠生生不息、歷久彌新的根本原因。
我們承認文化的特殊性,而且還堅持文化特殊性是文化對話的前提或必要條件——例如說,越是特殊的,便越是普遍的。在這兩點上,我們的立場與文化復古主義沒有什么不同。我們與復古主義者的分歧在于:復古主義者逡巡于特殊性,將特殊性絕對化、先驗化、單子化、神秘化、神圣化、禁忌化,不敢越雷池半步,他們不知道“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這一屈騷之問,于是其特殊性成了獨斷論的、僵尸般的特殊性。而我們,如前所示,則以特殊性為起點,將特殊性移置在能動自我和結構自我這一雙重變奏的理論框架之內,從而使特殊性變身為流變不居、開放性、互文性和對話性的概念了。前文有所提及,能動自我不偏嗜任何一種指意形式,它唯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來做出指意的抉擇。任何符指、話語均在其身外,并作為其可能的營養物。甚至,能動自我之特殊性一旦成型,它便成為外在,成為傳統,成為話語了,故而在永不消歇的能動自我面前,沒有什么比自我之當前的、應身的需求更有發言權和決定權了。能動自我在不斷地尋找能夠滿足自體需求之新的表意符號,并形成新的表意系統,即形成新的文化或者新的身份、新的特殊性。但能動自我就其作為能動自我而言,其對新的表意符號的尋求和對接,進而形成新的文化,此一過程具有無意識的特點,是之謂“文化無意識”。然而它仍可稱為一種對話,即于存在論意義上的對話,作為特殊性的文化在不言不語中汲取他者而豐富和強健自身。
能動自我一旦能夠自我反思、自我界定,那它便即刻成為結構自我、意識自我、話語自我、述謂自我、互文自我等等稱謂的那種自我了。與能動自我不同,結構自我是自由自覺地與身外的世界進行對話,通過此對話建構自我的身份和特殊性。無論對于能動自我抑或結構自我,在本質上,自我即他者,自我即對話。其區別僅在于:在前者,自我是無意識生成的;在后者,自我則是有意識地建構起來的。在我們看來,結構主義對自我之建構性的揭示并不必然意味著自我的組合和拼貼,因而是被動的、惰性的。與多數結構主義理論家不同,我們把結構理解為“機”構(institution),即功能性構成,這種功能性也是結構主義所矢口否認的自主性。
從能動自我和結構自我出發,我們將自我和自我的特殊性視作對話,即是說,自我既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對話性,也具有認識論意義上的對話性。離開了他者和異質,自我亦不復存在。自我與他者相異相成!依據以對話性為其本質屬性的能動自我和結構自我,文化“自”信既然以自我的文化或者其文化的自我性和特殊性為根本,那么毫無疑問,它也必然將是對話性的,生成于對話,顯露于對話,璀璨于對話!
以能動自我和結構自我界定對話,并以被如此界定的對話理解文化自信,就其基本原則而言,這一理論并非晚近社會學、人類學、結構主義以及文化研究的獨門秘籍,其實前蘇聯文論家和哲學家米哈伊爾·巴赫金早在1920年代寫作的《論行為哲學》《審美活動中的作者與主人公》《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問題》等著作中就已提出了成體系的對話主義學說,且其一生都在深化之、拓展之,終成20世紀西方對話理論的集大成者。完全可以期待,檢視、撿拾巴赫金的對話主義遺產,將強化和更新我們對于文化自信之對話性的認識。然而,令人不無遺憾的是,在已然是碩果累累的巴赫金研究界,這份珍貴的資源并未得到令人滿意的開掘和使用。那么我們就勉力為之吧!我們不擬研究巴赫金全部的對話理論,而是僅僅聚焦在自我、差異、特殊性這些與文化“自”信密切相關的要素上。我們將追隨巴赫金將其悉數植入對話,并以如此被充實的對話校正那種對文化自信的教條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的理解偏差。
二、巴赫金:外位性作為對話
特殊性或者說文化的特殊性在巴赫金那里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其一是作為特殊性之根的自我的唯一性。特殊性雖然是在比較中顯出,是觀念性的,但決定這一顯出有別于其他物之顯出的基質則是其本身的特殊存在。如果說前者是文化這棵大樹的枝葉或花朵,那么在一定的歷史語境中形成的文化本身,即是說仿佛作為有機體的文化,其唯一性,則是它不在我們視野之內的根須。其二是由這種唯一性所給定的自我對于其認識對象的外位性,而反過來說,被認識的對象也同樣具有唯一性,因而也具有其對于自我的外位性。
巴赫金在其《論行為哲學》中的原話是這樣說的:“我存在著”,“我的的確確存在著(整個地)”,“我以唯一而不可重復的方式參與存在,我在唯一的存在中占據著唯一的、不可重復的、不可替代的、他人無法進入……的位置。現在我身處的這一唯一之點,是任何他人在唯一存在中的唯一時間和唯一空間里所沒有置身過的。圍繞這個唯一之點,以唯一時間和唯一而不可重復的方式展開著整個唯一的存在。我所能做的一切,任何他人永遠都不可能做。實有存在的唯一性質是絕對無法排除的。”總之,“任何人都處在唯一而不可重復的位置上,任何的存在都是唯一性的”[注](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論行為哲學》,《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一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0—41,17頁。。
關于自我的性質,巴赫金語意清晰而連貫:我存在,我唯一,我積極,我外位,且我之外的任何人均此性質。然則,依據巴赫金的理論,這種密不透風、堅如磐石、獨往獨來、標新立異的自我并不妨礙其與他我即另一個自我之間的相互理解、認識和交流;相反,自我的唯一性及其外位性倒是實現、達成在原本彼此有其特殊存在的個體之間對話性“表接”(articulation)的必要條件。所謂“表接”,就是對話語與生命的表述性鏈接。
在其《論行為哲學》中,巴赫金是在考察“審美移情”現象時帶出個體的唯一性及其外位性的,不過需要指出,這在邏輯上絕對是前者以后者為前提,即巴赫金是從審美個體的唯一性和外位性來看待和要求于“移情”的。巴赫金知道,“審美觀照的一個重要(但不是唯一)方面,就是對觀賞的個體對象進行移情,即從對象的內部,置身其間進行觀察”②(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論行為哲學》,《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一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0—41,17頁。。不錯,所謂“移情”當然就是移入、進入對象內部的情感和認識游歷了,這一直以來便是移情的基本語義。但是且慢,巴赫金從中區分出兩種情況,或者說,存在著兩種性質的移情:一是積極的移情,一是消極的移情。積極的移情是觀賞主體在其中永遠活躍地存在著的行為,而消極的移情則是在觀賞過程中主體的放棄自我而與對象合二為一。關于積極的移情,巴赫金有生動的描述:“我積極地移情于個體(即作為個體的對象——引注),因而也就一刻都不完全忘掉我自己和我在個體身外所處的唯一位置。不是對象突然控制了消極的我,而是我積極地移情于他。移情是我的行為。”[注](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論行為哲學》,《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一卷,第18,18,18,18—19,17—18頁。與此相反,消極的移情,他也稱之為“單純地移情”②(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論行為哲學》,《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一卷,第18,18,18,18—19,17—18頁。,其特點是“與他者重合、失掉自己在唯一存在中的唯一位置”③(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論行為哲學》,《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一卷,第18,18,18,18—19,17—18頁。。但他又認為“單純的移情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假如我真的淹沒在他人之中(兩個參與者變成了一個——是存在的貧乏化),即不再是唯一的,那么我不存在這一點就永遠不會成為我的意識的一部分,不存在不可能成為意識存在中的一個因素,對我來說根本沒有這個意識存在,換言之,存在此刻不能通過我得以實現。消極的移情,沉迷、淹沒自我——這些與擺脫自己或自我擺脫的負責行為毫無共同之處;在自我擺脫中,我是以最大的主動性充分地實現自己在存在中的唯一地位”④(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論行為哲學》,《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一卷,第18,18,18,18—19,17—18頁。。這里有兩點需要解釋:第一,當我意識(移情)到作為對象的某物時,我之不存在也蘊涵在這一意識(移情)之中,因為我雖然不會意識(移情)到“不存在”,如胡塞爾所發現,意識總是關于某物的意識,但這“不存在”由于依附于“存在”即某物,于是便也顯示出其存在來,就像在中國山水畫中,空白(留白)是靠有物而存在的。在移情中,不存在是我的一種狀況,因而意識到我之不存在也就是意識到了我的存在。在我意識到我不存在而意識中只有對象時,并不是我意識到了絕對的不存在,而是意識到了一種特殊的存在,即以一種不存在的方式而出顯的存在。相反,如果我與對象完全化為一體,那么我和我的意識將即消失,對象亦隨之煙消云散。要之,移情盡管看起來是“我不存在”,但實際上則是我自始至終意識到我之“不存在”。與此相關,第二,在移情中的放棄自我、擁入對象是表面上消極而實則積極的作為。移情的積極性在于:我是主動地投奔對象的(a);我始終意識到我的自我放棄即“我不存在”的(b);在我意向于對象時,對象也以我或我的意識而生成,即對象被攬入我的意識,成為我的意識的填充物(c)。順便指出,如果所有的移情都是主體之積極的移情,那么準確言之,便不再有兩種移情現象,而只是存在兩種不同的移情觀了。進一步,那大約也便不再有王國維之借鑒叔本華而得出的“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的區分了[注]王國維之言“有我之境,以我觀物”與“無我之境,以物觀物”(彭玉平:《人間詞話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324頁)本身即已透露,縱使客觀性較強的“以物觀物”也是有一“觀”之主體的。。是的,沒有絕對的無我之境,若此,那是誰在意識?誰在想象?誰在體驗呢?!
人們通常把移情理解為“入乎其內”,巴赫金提醒,移情還是“出乎其外”,而無論入乎其內或者出乎其外,他堅持,始終都是我之入、我之出,是主體之我的積極作為,而且正是由于這一點,存在才不再是僵死之物,而是人與物的相互作用,存在于是成為所謂的“事件”。也是在此意義上,巴赫金稱移情中若真是出現主客體的合二為一則是“存在的貧乏化”。這涉及移情的對話性和主體間性結構,本文隨后再論。
我們習慣于將“入乎其內”和“出乎其外”作為移情前后相繼的兩個階段,而巴赫金認為,這只是一種理論抽象,并非實際的移情過程。他稱前者為“移情”,后者為“客觀化”:“誠然,不應以為先有純粹的移情因素,之后依序出現客觀化、成形化的因素;這兩個因素實際上是不可分的,純粹的移情只是審美活動的統一行為中一個抽象的因素,不應把它理解為是一個時段;移情與客觀化兩個因素是相互滲透的。”⑥(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論行為哲學》,《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一卷,第18,18,18,18—19,17—18頁。面對千差萬別的移情現象,區分移情和客觀化似乎沒有多少意義,它可能是同時發生的,也可能是交替出現的,可能是以移情為主、客觀化為輔,或者相反,等等。然而對于巴赫金的理論建構來說,這種區分卻是至關緊要的:它使巴赫金得以將客觀化作為較移情更加重要的審美元素,然后借此以引出其外位性理論:“在移情之后接踵而來的,總是客觀化,即觀賞者把通過移情所理解的個體置于自己身外,使個體與自己分開,復歸于自我。只有觀賞者復歸于自我的這個意識,才能從自己所處位置出發,對通過移情捕捉到的個體賦以審美的形態,使之成為統一的、完整的、具有特質的個體。而所有這些審美因素:統一、完整、自足、獨特——都是外在于所觀察個體(指被觀察的審美對象——引注)自身的;在他的自身內部,對他和他的生活來說,這些因素并不存在……現實生活的審美反射,從原則上說并不是生活的自我反射,不是生活過程、生活的真實生命力的自我反射。審美反射的前提,是要有另一個外在的移情主體。”[注](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論行為哲學》,《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一卷,第17,18頁。客觀化即觀賞者的外位性,其重要性在于:它創造了審美對象,即對象呈現出具有審美性質的形象;審美對象不屬于此對象本身,對象本身沒有審美性可言,是一個外在于審美對象的“移情主體”賦予其審美的效果,即看起來是一個審美的對象。這種美學觀有唯心主義的嫌疑,但巴赫金這里不關心美在本質上是主觀的抑或客觀的傳統論爭,而是強調審美效果的發生有賴于一個外在的觀賞者或者觀賞者的一個外位性。
如果有人一定要將巴赫金劃歸主觀派或客觀派的營壘,那么我們毋寧視其為第三派——主—客觀派,他超越了這種舊式的美學,而將移情作為使主客體相互作用并使雙方都有所增益的活動:“通過移情可以實現某種東西,這既是移情對象所沒有的,也是我在移情行為之前所沒有的;這種東西豐富著存在即事件,存在已不再是原樣了。”②(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論行為哲學》,《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一卷,第17,18頁。移情豐富了存在,使存在發生新的變化,成為充滿意義的事件。但萬勿忘記,這一切都是觀賞者的外位性所帶來的!如果說外位性在主客體之間創造了審美的效果,那么這也就是意味著它不僅沒有阻隔,反倒是確保了主客體之間的往來交通,進而說這也意味著外位性還具有促成主客體之間、自我與他者之間構織對話或主體間性的功能。移情是必然通向主體間性的,就像胡塞爾的“意向”之必然通向主體間性那樣。就外物之充盈于、內化于主體或意識而論,移情與意向無異。
有學者稱,巴赫金的文化外位性觀點源自其關于審美活動的外位性觀點即審美移情說,是審美移情說的延伸和運用,二者之間乃源與流的關系[注]參見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詩學》,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72—173頁。。我們不擬在事實上做此求證,因為如前指出,審美移情說的邏輯前提是自我的唯一性,且其同樣為文化外位觀的邏輯前提,這即意味著,文化外位觀未必要繞道審美移情說才能取得其自身的合法性。在此我們只想堅持:自我的唯一性同時統領著以外位性為其樞機的審美移情說與文化外位觀,而后兩者之間卻并無統屬關系,它們位處同一層級,于是就文化外位觀而言,它亦可直承自我的唯一性。但是,必須承認,熟悉審美移情及其為巴赫金所突出的外位性特征,確乎能夠為進入文化外位性的討論提供便利。在技術層面上說,它提供了一個轉入文化分析的工具箱,其中有積極移情、消極移情、客觀化、存在即事件,等等。
為豐富和砥礪這些工具,現再次引入王國維的觀點。前文未及時說明,“入乎其內”和“出乎其外”是王國維詞話的關鍵詞,流布甚廣:
詩人對自然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注]彭玉平:《人間詞話疏證》,第304,313頁。
這里說的不是接受,而是創作方面;不是面對藝術創作,而是社會人生。顯然,在王國維,出和入的對象是沒有限定的,因而我們可以把文化合理地包括進來,此其一也。其二,對象之或出或入在價值上并無高下之分,僅是所帶來的效果不同而已:入則可寫,體物狀物,纖毫畢現,栩栩如生,是所謂“入乎其內,故有生氣”者也。而“出乎其外”,其優點是可以“觀之”。所謂“觀”,乃居于對象之外而觀之,故“觀”便假定了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距離。前引巴赫金謂移情之“客觀化”,即是讓對象保持為對象,即客體,而這同時也是讓觀者保持在一個主體的位置。觀的本質是外位性的。
關于入乎其內和出乎其外,特別是觀之外位性,王國維還說過:“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風月。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鳥共憂樂。”⑤彭玉平:《人間詞話疏證》,第304,313頁。輕視外物是出于外物、居于外位,從而統觀外物,故可能卓有高致;而重視外物則是入于外物,與外物一體,隨物賦形,神與物游,是故俗趣盎然。前者跡近“有我之境”,后者則為“無我之境”。但無論輕視或重視,都始終不能是無“視”,其所指向的也始終都是“外”物。
這種被置于審美關系中的人物之論,簡明言之,審美移情說,如前申明,雖然不是我們轉向巴赫金文化外位觀的邏輯前提,即是說,有無這個審美移情說,我們都可以從自我的唯一性順順當當地過渡到文化外位觀;然而有了它,對于我們更好地完成這一過渡,是不無助益的,因為自我的唯一性已經在審美移情說這里演練過一番,而對于文化外位觀,不過是重復演練一遍而已。現在我們有充分的準備來談論巴赫金的文化外位觀了。
下引是巴赫金談論其文化外位觀最集中、最完整的一次。作為引文,它是長了一些,但作為對一個重大論題的闡述,它則又是言簡意賅的,值得一氣讀完。若是采取邊引邊論的方法,自是中規中矩矣,然則于巴氏之語意,殆支支吾吾、支離破碎耳!我們且先試讀之,論析隨后:
存在著一種極為持久但卻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錯誤的觀念:為了更好地理解別人的文化,似乎應該融于其中,忘卻自己的文化而用這別人文化的眼睛來看世界。這種觀念,如我所說是片面的。誠然,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到別人文化之中,可以用別人文化的眼睛觀照世界——這些都是理解這一文化的過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如果理解僅限于這一個因素的話,那么理解也只不過是簡單的重復,不會含有任何新意,不會起到豐富的作用。創造性的理解不排斥自身,不排斥自己在時間中所占的位置,不摒棄自己的文化,也不忘記任何東西。理解者針對他想創造性地加以理解的東西而保持外位性,時間上、空間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對理解來說是件了不起的事。要知道,一個人甚至對自己的外表也不能真正地看清楚,不能整體地加以思考,任何鏡子和照片都幫不了忙;只有他人才能看清和理解他那真正的外表,因為他人具有空間上的外位性,因為他們是他人。
在文化領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強大的推動力。別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較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但也不是全部,因為還會有另外的他人文化到來,他們會見得更多,理解得更多)。一種涵義在與另一種涵義、他人涵義相遇交鋒之后,就會顯現出自己的深層底蘊,因為不同涵義之間仿佛開始了對話。這種對話消除了這些涵義、這些文化的封閉性與片面性。我們給別人文化提出它自己提不出的新問題,我們在別人文化中尋求對我們這些問題的答案;于是別人文化給我們以回答,在我們面前展現出自己的新層面,新的深層意義。倘若不提出自己的問題,便不可能創造性地理解任何他人和任何他人的東西(這當然應是嚴肅而認真的問題)。即使兩種文化出現了這種對話的交鋒,它們也不會相互融合,不會彼此混淆;每一文化仍然保持著自己的統一性和開放的完整性。然而它們卻相互得到了豐富和充實。[注](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答〈新世界〉編輯部問》,《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四卷,第410—411頁。
這多像從自我的唯一性出發對于審美移情論的闡說啊!巴赫金堅決反對純粹移情式的即入乎其內的對于他者文化的理解。他提出的理由是:融入他者文化,觀其所觀,言其所言,行其所行,入乎其內,與他者渾然一體,即完全地成為他者,雖為理解行為之必需,但這在獲得一種視角(他者視角)的同時丟失了另一種視角(自我視角),也就是僅剩單一的視角,而使用任何單一視角的理解不過是對此視角之所見、之所習見的跟隨和復制。
巴赫金的理想是“創造性的理解”,而要實現此創造性理解,則必得有另一視角的存在,在此就是自我視角。保持而不放棄自我視角,就是在入乎其內的理解中同時能夠出乎其外,保持一個外位性的位置。這一位置為自我所有,因而出乎其外也就是返回自我或自我的位置。外位性即自我的外位性,即自我面對其對象時所由以立其身的外位性。顯然,對于巴赫金來說,理解的外位性意味著多重視角或多重視界。
這是外位性在理解活動中的第一項價值。其第二項價值是,外位性能夠使主體對客體“整體地加以思考”,即對客體做整體的觀照,將客體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這也就是王國維所謂的“出乎其外,故能觀之”。觀,乃統觀,統而觀之。更精準地說,凡觀皆為統觀。那么,這種統觀的性質是什么呢?或者說,統觀能夠使我們看到什么呢?巴赫金的回答是:“只有他人才能看清和理解他(對象——引注)那真正的外表,因為他人具有空間上的外位性,因為他們是他人。”顯然,統觀之所觀即內容乃對象之“真正的外表”。此觀為外觀,在外位之觀以及由此所得到的外觀、外表。這尤其貼合于西洋油畫的觀賞情況:近看是涂料,是死的物質,遠觀是圖像,是活的藝術形象。也許讀者早已看出,在巴赫金,這作為外表的外觀并非與內蘊、本質相對立,它不是皮相、淺表。它是客體事物本身所呈現出來的表象,出自客體,未與客體斷裂,雖經由主體的反映和建構,但在根本上仍歸屬于客體。一句話,所謂的“真正的外表”就是對象本身的整體形象。沒有外位之眼,便沒有客體的整體形象。
然而,必須指出,這種外位性的整體形象、“整體地加以思考”或出乎其外的“觀之”只是指向對象一方的。蘇軾告誡,“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題西林壁》),我們一直奉之為至理名言,但實際上即便跳出廬山的局限,人們亦未必就能獲得廬山的“真面目”,那只是一種從外觀得到的廬山形象。因此,指向客體的所謂“整體地加以思考”僅僅是指向該客體一方之整體(多么悖論的措辭啊),而非包括主客體以及超越此兩者的全能視角之下的整體。這樣的統觀、整體思考不過仍是一己之視角和一隅之所見。改借杜詩說,何以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在認識上沒有絕頂!認識永遠是被限定的認識。巴赫金對此早有認識:“審美移情(不是指失掉自我的單純的移情,而是引出客觀化的移情)不可能提供關于唯一存在(在豐富的事件性方面)的情形,而只能提供對外在于主體的存在的審美觀察(也包括觀察主體本人,但卻是外在于自己主動性的主體,是消極性的主體)。對事件參加者的審美移情,還并不就是對事件的把握。”[注]② (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論行為哲學》,《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一卷,第20頁。這就是說,審美移情即使有積極主體之主導而非消極主體之完全化入客體,即使能夠始終堅持外位性的客觀化、統觀化,那至多也不過是觸及了客體一方極其有限的內容。審美移情達不成一個“豐富的事件”,它無法做到對“事件”的整體把握。由此而言,外位性的根本價值仍在于其對自我本位及其視角乃至多重視角的保證和堅持,在于其反對純粹移情論或“無我之境”的文化交流觀。被限定的視角涵蓋了對多視角和全視界的吁求,進一步說,也是包涵了對交互透視、主體間性和對話主義的期盼。在對話主義者巴赫金看來,單獨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把握我們共在于其間的作為事件的世界:“即使我看透了我面前的這個人,我也了解自己,可我還應該掌握我們兩人相互關系的實質,把我們聯系在一起的統一而又唯一事件的實質;在這個唯一事件中,我們兩個當事者,即我和我的審美觀察的客體,都應當在存在的統一體中得到評定。”②所謂的“統一體”便是由對話而建立起來的共在場。用巴赫金本人的定義說:“統一體不是指天然生成的一個唯一的單體,而是指互不溶合的兩個或數個單體之間的對話性協調。”[注](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書的修訂》,《巴赫金全集》(六卷本)第五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81頁。在此,外位性自身已經無足輕重,其輕重將取決于能否導向進一步的對話。
因此,言及文化間之理解,重要的不是“別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較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也不是“一種涵義在與另一種涵義、他人涵義相遇交鋒之后,就會顯現出自己的深層底蘊”——的確是有此情況: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重要的是,“不同涵義之間仿佛開始了對話”。同樣道理,重要的不是“我們給別人文化提出它自己提不出的新問題,我們在別人文化中尋求對我們這些問題的答案;于是別人文化給我們以回答,在我們面前展現出自己的新層面,新的深層意義”,也不是“倘若不提出自己的問題,便不可能創造性地理解任何他人和任何他人的東西”,而是“我們”和我們“自己的問題”與他人和他人的問題構成了一種對話性關系。
顯然,巴赫金之所以堅持外位性的奧秘在于對話,在于創造事件性的對話。不是為了安然于自我不受外物、外界干擾的存在狀態,不是為了堅守自身文化的特殊性,當然更不是為了自得于其“文化的封閉性與片面性”,恰恰相反,堅持外位性最終是為了創造一種文化間的對話,在此對話中實現他所推崇的“創造性的理解”和彼此間均會發生的改變和增值。對話需要自我,需要自我的外位性,不過,說到底,對話需要的實則是其所必然意謂的多重視角。無多重視角,便無對話之可能。
復歸本文之初心,巴赫金的自我的唯一性和外位性,或可謂“外位自我”,說的就是文化的自身存在,其地方性,其歷史性,其差異性,其特殊性,而尤為可貴的是,巴赫金沒有將這些硬化,石化,固化,無意識化,而是軟化,氣化,語言化,動態化,將個體之不可移易的身體性存在轉變為一種視角。其方式就是將其牽引到對話的場域,一旦開始對話,他們就不再是自身存在,而成了一種關系性存在,既是其自身,又非其自身,是對話個體,是赫爾曼斯所稱揚的“對話自我”[注]See Hubert J. M. Hermans,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A Dialogical Self”,https://doi.org/10.1080/10720530390117902, published online,10 Nov 2010, and originallyin Journal of Constructivist Psychology, vol. 16, 2003-issue 2, pp.89-130.。對話并不消滅個體,但也不保全個體,于是“即使兩種文化出現了這種對話的交鋒,它們也不會相互融合,不會彼此混淆;每一文化仍然保持著自己的統一性和開放的完整性。然而它們卻相互得到了豐富和充實”。因為個體仍然堅執地存在著,故而總是能夠“保持著自己的統一性”和“完整性”,但由于進入了對話,故而它又是開放的,處于無限的開放之中。在這個意義上,巴赫金指出:“特定的文化的統一體,乃是開放的統一體。”[注](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答〈新世界〉編輯部問》,《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四卷,第409頁。這種開放既是歷時性開放,也是共時性開放。
如果單從其對永不消逝的和堅硬的個體的堅持和張揚方面觀之,抑或,單從其對個體之間話語性連結的渴望和要求方面而言,即是說,單從以上任何一方面考量,巴赫金在西方思想史上都不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獨此一家,但能夠將兩者結合起來,要求個體進入話語性的對話,而在此對話中同時還應葆有個體的存在,這樣的智者在20世紀的西方并不多見。
三、巴赫金的對話不是主體間性或文本間性,而是個體間性或言語間性
這里需要對巴赫金對話主義理論的一種結構主義如在托多羅夫那里的解讀略做澄清或修正。在托多羅夫看來,巴赫金對話主義的另一種說法是互文性:“為了表示每一述說(énoncé)與其他述說的這種關系,他使用的術語是對話主義。”[注]Tzvetan Todorov,Mikha?l Bakhtine: Le Principe Dialogique, Paris: Seuil, 1981, p.95.需要辨別:“énoncé”指述說的結果或內容,“énonciation”指述說行為。而“在最基本的層面上,兩種述說之間的一切(tout)關系都是互文性的”[注]Tzvetan Todorov,Mikha?l Bakhtine: Le Principe Dialogique, Paris: Seuil, 1981, p.95, p.95-96.。托多羅夫引巴赫金原話為證:“被并置的兩種語言作品,兩種述說,進入了一種特殊的語義關系,我們稱其為對話關系。這種對話關系是在語言交際深處所有述說之間的(語義)關系。”⑤Tzvetan Todorov,Mikha?l Bakhtine: Le Principe Dialogique, Paris: Seuil, 1981, p.95, p.95-96.顯而易見,在巴赫金,互文關系即對話關系,或者,互文性即對話性,反之亦然。而這進一步也似乎是,對話僅僅漂浮在文本、述說的表層,而非發生在其存在具有唯一性的自我或個體之間,簡言之,似乎對話僅僅是話語性的。
對于這種可能的誤導,結構主義的傳譯也許負有主要責任,但巴赫金本人恐亦難辭其咎。在其對話理論中,話語不時地躥躍到最突出的位置,例如成為一種對人進行本質界定的視角:“人的存在本身(外部的和內部的存在)就是最深刻的交際”,“存在就意味著交際”[注](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書的修訂》,《巴赫金全集》(六卷本)第五卷,第378頁。,“人的行為是潛在的文本”[注](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文本問題》,《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四卷,第301,313頁。,“人的身體行動應該當作行為來理解”——“而要理解行為,離開行為可能有的(我們再現的)符號表現(如動因、目的、促發因素、自覺程度等等),是不可能的”[注](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文本問題》,《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四卷,第301,313頁。,“生活就其本質說是對話的”,“生活意味著參與對話:提問、聆聽、應答、贊同等等”[注](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書的修訂》,《巴赫金全集》(六卷本)第五卷,第387,387,387頁。。巴赫金這種從“文本”或“文本間性”來界定對話,從而界定人的存在的理論,無論怎么辯解都難逃其遮蔽人之物質性存在的嫌疑。這也許是巴赫金必須為其對話理論所付出的代價。
再例如,當其對人文科學(或曰精神科學)與自然科學(或曰精密科學)進行區分時,巴赫金同樣表現出濃重的文本中心主義而非物質主義的音色:
人文科學是研究人及其特性的科學,而不是研究無聲之物和自然現象的科學。人帶著他做人的特性,總是在表現自己(在說話),亦即創造文本(哪怕是潛在的文本)。如果在文本之外,不依賴文本而研究人,那么這已不是人文科學(如人體解剖學和生理學等等)。[注](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文本問題》,《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四卷,第301,300,299,297,312頁。
說人文科學研究人文,自然科學研究自然,這表面上看不會有什么問題,但若是將人文僅僅等同于人所借以表達自己的語言、人所創造的文本,進而說,研究人文而不考慮其物質屬性,那么這樣的研究不啻與尸骸對話:無言說者的話語一如沒有生命的尸骸。然而,世界上壓根兒就沒有這樣的話語。一切話語都是人的話語,一切文本都是人的文本;而人不僅是話語的、文本的存在,也是現實的、生命的存在;總之,是欲求—言說的存在。人文科學固然以話語、文本為其對象,但它不是將其作為空洞的能指,而是作為活生生的人的符號表現。所有符號都是指示性的!有所指,有所透漏,或者有所藏匿,總之不是自我指涉的。德里達的“延異”是意指的延異,不是無所指的延異。我們不反對巴赫金斬釘截鐵的斷言,“文本不是物”③(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文本問題》,《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四卷,第301,300,299,297,312頁。;不反對他將人文科學定性為文本研究;同樣,我們也不反對他關于精神科學所說的:“精神(無論自己的精神還是他人的精神)不能作為物(物是自然科學的直接對象)出現,無論對自己和他人來說都只能表現為符號,體現于文本中。”④(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文本問題》,《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四卷,第301,300,299,297,312頁。但是必須堅持,人文科學不是純書齋式的學問,不是能指的游戲,而是探究文本對現實世界的種種意指。
巴赫金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多次表示過“作為話語的文本即表述”⑤(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文本問題》,《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四卷,第301,300,299,297,312頁。(而表述總是意味著有所表述)、文本“是意識的表現,是反映某種事物的意識之表現”⑥(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文本問題》,《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四卷,第301,300,299,297,312頁。(而根據胡塞爾,意識總是意向性的,即有對某物的意識)之類的意思。但毋庸為尊者避諱,其對話理論未能將話語和作為生命的話語對談者之從屬關系清晰地展示出來,并使之勾連為一個嚴密的體系。不過這并不關緊;關緊的是,對于我們試圖予以澄清、重構、發展的對話理論,巴赫金都已或東或西、或明或暗地觸及和指示過了,借著他的指點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邁向我們自己的結論。例如,如下的說法就足以使我們不再認為巴赫金的對話僅僅發生在文本或話語的層次:“語言與表述的對立,就如同社會與個人的對立。所以,表述完全是個人的。”[注](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二卷,第399頁。“一般來講,要擺脫外位因素的實體存在恐怕是個無法實現的任務。”[注](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巴赫金的講座》,《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七卷,第338頁。“人作為一個完整的聲音進入對話。他不僅以自己的思想,而且以自己的命運、自己的全部個性參與對話。”[注](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書的修訂》,《巴赫金全集》(六卷本)第五卷,第387,387,387頁。“人是整個地以其全部生活參與到這一對話之中,包括眼睛、嘴巴、雙手、心靈、精神、整個軀體、行為。”[注](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書的修訂》,《巴赫金全集》(六卷本)第五卷,第387,387,387頁。對巴赫金而言,顯而易見,個體的不可言說的方面也是包含于對話之中的。是個體在言說,而非語言在言說。個體的表述(parole,通譯“言語”)內蘊著言語(langage,通譯“言語活動”)與語言(langue)之間的張力。語言之所以不言說,是因為語言不具備言說的意志和動力。索緒爾講得清楚,“語言不是說話者個人的活動……語言從來不允許有意圖”[注]引文見(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二卷,第398頁。索緒爾的法文原文是:“La langue n’est pas une fonction du sujet parlant, ...elle ne suppose jamais de préméditation”, “La parole est au contraire un acte individuel de volonté et d’intelligence.”(Ferdinand deSaus sure,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ublié par Charles Bally et Albert Sechehaye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Albert Riedlinger, quatriéme édition, Paris: Payot., 1949 [1916], p.30) 注意:《巴赫金全集》中文版將“parole”翻譯為“表述”而非“言語”,將“fonction”翻譯為“活動”而非“功能”,原則上并不錯,但與通用譯法不同,需要讀者鑒別。,“表述是一種意志和思維的個人行為”[注](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二卷,第398頁。。這些話,巴赫金都抄引其法語原文;此中之深意,他該是多么地心領神會啊!純粹語言學可以不研究具體的言說,但對話哲學則必須將個體考慮進來,且許以一個始源的位置。
在談到作者與其作品中的人物的關系時,巴赫金區別了前者的兩種主動性:
作者具有積極的主動性,但這個主動性帶有特殊的對話性質。針對死物、不會說話的材料,是一種主動性,這種材料可以隨心所欲地塑制和編織。而針對活生生的、有充分權利的他人意識,則是另一種主動性。這是提問、激發、應答、贊同、反對等等的主動性,即對話的主動性。[注](蘇)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曉河等譯:《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書的修訂》,《巴赫金全集》(六卷本)第五卷,第375頁。
在此,與巴赫金的著意點不同,我們并不擔憂作者是否以己之意而強加于其筆下的人物,即以主客體關系的方式錯待作為主體間性的對象;我們關心的是在巴赫金所倡導的作者與人物之間對話性關系的范型中已悄然透露出:其一,作為個體的作者具有對話的積極主動性,他是一場對話的發動者。我們知道,唯其作為個體,作者才有所謂的“主動性”。話語從不主動。其二,人物作為作者對話的對象不是未經形式化的質料,而是活生生的另一存在,是他人或他人意識。于是,這也就決定了,對話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活動,而非主體與客體之間的活動,且主體又首先是作為個體而存在的。對話以個體存在為基礎,而后尋找一種主體間性。在巴赫金,對話原則上就是主體間性。但如果說主體是話語的建構,如結構主義所堅持的那樣,我們毋寧說創制一個更貼合巴赫金意謂的術語:個體間性。個體之間彼此尋找溝通,而他們能夠溝通的則一定是話語。當然如果把主體理解為個體在言說中的符號延伸,那么說對話即主體間性亦無不可。但麻煩在于,現在的主體概念已經被結構主義風化為一具沒有血肉的木乃伊。嚴格說來,巴赫金的對話是個體間性,而非僅僅作為“文本間性”的主體間性;其個體間性的對話已經涵括了結構主義的主體間性。在此我們不由得感嘆,那些聲稱是索緒爾子孫的法國結構主義者,其實對于索緒爾的遺產不過是各取所需罷了,他們丟棄了他的言語學,而單單拿走了其語言學[注]索緒爾將語言學分作“語言的語言學和言語的語言學”(Ferdinand deSaus sure,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37)兩個部類。。這當然不是學科對象意義上的,而是哲學上的,他們這樣做造成了嚴重的哲學后果,即他們的哲學只能是荒無人煙的哲學,他們在能指的盛宴中饑斃。而巴赫金(此處是沃洛希諾夫)雖然難說對索緒爾多么滿意,但無論如何,結果是他兼取其語言學和言語學,并進而做了哲學上的混融,其對話既有話語、又有個體,是個體間的對話。
這里有必要指出兩點:其一,堅持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哲學的沃洛希諾夫不完全等同于信奉個體間性對話的巴赫金;其二,沃洛希諾夫并未完整把握索緒爾的思想,而巴赫金卻不動聲色地抓住了索緒爾語言學的樞機:在“言語活動”中語言和言語的互動關系。“言語活動”是索緒爾語言學的直接對象或第一對象,而后他才從中抽象出“語言”和“言語”兩個部分,并始終堅持其相互依存、渾然一體的實存狀態。對于語言學來說,語言或言語,無論索緒爾委何者占據一個更核心的位置,但對他有一點則是確定無疑的,即言語是對語言的個體性使用。因而言語活動或言語既是個體性的,也是社會性的[注]索緒爾警示:“言語活動有個體性的一面,也有社會性的一面;我們無法離開這一方面而去設想另一面。”(Ferdinand deSaus sure,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24)合而言之,“言說主體利用語言符碼以表達其個人的思想”(Ibid.,p.31)。。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索緒爾的“言語活動”即是巴赫金的“對話”。如上證明,巴赫金的對話雖然有時有偏向話語一維的嫌疑,但從其整個學術生涯觀之,基本上是結合著個體性的。其對話是個體間性,在個體之間尋求話語的溝通。
結 語
本文在引進能動自我、結構自我、外位自我等概念,界定文化自信之“自”即“自性”“自我”“特殊性”的過程中,實際上已經完成了對文化自信的理論認知和圖繪。以下所謂的結語不過是對前文已經達到的結論做更簡明的表述罷了:
第一,能動自我告訴我們,一種文化的發展和變化總是以其當前的、現實的需要和狀況為出發點,它原則上并不特別揀選自己的歷史和遺產,也不特別排斥外來的文化和文明,一切都以其是否有用、有益為取舍。在此意義上,能動自我是不折不扣的現實主義者或功利主義者。
第二,從結構自我可以得知,文化自性、文化特殊性、文化身份在緣起上便是復合的、構成的、雜融的(a),在認識論上都先已/同時假定了一個文化他者(客體)的存在(b),即是說,文化自我與文化他者(客體)被自我意識一道建構出來,它們相攜而生,舍此則無彼。
第三,能動和結構并非兩個相對立的概念。文化因結構而成其自身,因結構而獲得其能動,并以結構化的方式不斷地發展和壯大自身,而所謂結構化乃是一個將身外文化(包括異質文化)引入自身系統并予以粉碎和整合的過程。文化因而在本質上即是對話性的。文化即文化間性。
第四,外位自我實乃對話自我,它要求文化自信必須成為一種間性自信,一種對話自信,即一種文化對話主義,其中既有自我的存在,也有他者的進入,二者共同創造了一個事件性的空間,文化從而得以更新和發展。依據巴赫金外位性理論,文化自我或文化特殊性是要通向對話的,甚至也可以說,是為對話而存在的。此乃打開流行格言“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正確方式。
不言而喻,在能動自我、結構自我、外位自我或者對話自我面前,文化民族主義和復古主義據以抵抗從當代文化需要出發對傳統文化之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主要堡壘(即文化特殊論)將灰飛煙滅。如果說從前的文化自信是后殖民的文化自信,是抵抗性的和二元對立性的文化自信,具有情感的合理性和歷史的真實性,那么新時代的文化自信則應理性地、包容性地成為間性文化自信,其中的對話原則同時將文化特殊性作為本體論的存在和認識論的存在。一句話,文化自信是自我開放的對話性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