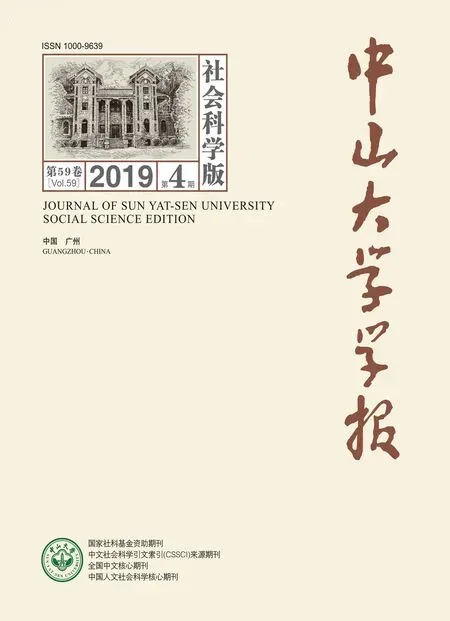清代“吹腔”源流及其與周邊聲腔的關系*
陳 志 勇
吹腔是清代中葉興起的一種戲曲聲腔,傳播甚廣,即如余從《戲曲聲腔劇種研究》所言,吹腔“‘陰魂不散’,到處都有它的影子”①余從:《戲曲聲腔劇種研究》,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0年,第140頁。。乾隆四十五年、四十六年(1780、1781)兩淮鹽政使伊齡阿、湖廣總督舒常、湖北巡撫鄭大進、江西巡撫郝碩、廣東巡撫李湖等地方要員向朝廷奏報查辦戲曲的奏折中,皆提到吹腔或石牌腔(吹腔的別名)與楚腔、秦腔、弋陽腔一樣,在“江廣、四川、云貴、兩廣、閩浙等省,皆所盛行”②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內廷演劇始末考》,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58—64頁。。吹腔不僅被一些地方劇種吸收為重要唱腔,而且與昆腔、弋陽腔、四平腔、梆子腔、徽調二簧、江西宜黃腔皆有著或近或遠的關系。吹腔是清代戲曲聲腔史上一支影響廣泛的唱腔,但學界對其關注并不充分,有些問題仍處于模糊狀態。本文擬從吹腔的名實關系辨正入手,系統考察吹腔的形成史,梳理吹腔的藝術形態及其與梆子戲、徽調的特殊關系,以深化對此聲腔的認識。
一、“吹腔”源流考
吹腔從字面上理解,誠如李家瑞所言,就是“以管吹為主要樂器的腔調”③李家瑞:《北平俗曲略》,北京:中國曲藝出版社,1988年,第66頁。。在我國古代的戲曲音樂史上,較為常見的吹管有笛、笙、簫、嗩吶。理論上,凡是以這些樂器伴奏的聲腔皆可稱之為吹腔。但事實并非完全如此,例如在清代前中期山東等地較為流行的姑娘腔,就是嗩吶伴奏,《古本戲曲叢刊》六集所收《十出奇》第十二出“擒寇”就有姑娘腔,標明為吹嗩吶伴唱,但現實生活中人們不會以吹腔稱之。再如,以笛子伴奏的昆腔,它的愛好者也不會將之視為吹腔。正因如此,一些昆曲笛師“遇昆班夾演的吹腔戲,皆拒絕為之伴奏”[注]王永敬主編:《昆劇志》下卷,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974頁。,這或許有維護昆腔正統地位的考慮,但也表明吹腔與昆腔之間有明顯的區別。對于二者之間的不同,戲曲史家周貽白論之甚詳:“吹腔為固定的一種調子,其每句間歇處有過門;昆山腔則隨牌調轉移,各有唱法。起唱時笛子隨腔,腔停則笛止,不用過門。”[注]周貽白:《中國劇場史(外二種)》,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6年,第376,320頁。可見,吹腔作為一種特定的聲腔,有其獨特的聲腔屬性和音樂特性。
清乾隆間嚴長明的《秦云擷英小譜》指出了吹腔的原產地:“弦索流于北部,安徽人歌之為樅陽腔(今名石牌腔,俗名吹腔)。”[注]傅謹主編:《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清代卷·專書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11頁。嚴長明準確點出吹腔發源于安徽的樅陽和石牌一帶。樅陽、石牌同屬安慶府,相距僅百里,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難以清晰區分吹腔最早是產生于樅陽還是石牌。不過,作為懷寧的下轄大鎮,石牌較之樅陽更具區位優勢,因為乾隆二十五年(1760),安徽布政使司由江寧移駐安慶,安慶始為省會,自此安徽省、安慶府、懷寧縣同城而治。石牌藝人進入安慶城極為便利,城中也多石牌戲班,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浙江海寧人周廣業《客皖紀行》記載,當年十二月初十日安慶城中“乏水”,“連日優人佐觴,地無昆腔,石簰所出,皆信口咿啞,彼處名石簰班”[注]沈文倬:《周廣業〈客皖紀行〉〈客皖錄〉》,《文獻》1981年第2期。。
盡管刻意去區分樅陽腔和石牌腔并無意義(事實上也難做到),然而是否可以簡單地將吹腔與樅陽腔或石牌腔劃等號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弄清楚誕生于安慶的吹腔是如何產生的。
我們可以吹腔為起點,運用“逆向追溯法”,先找到與吹腔在藝術上具有直接“親緣”關系且又早于吹腔的腔調。歐陽予倩在上世紀20年代認為,吹腔(藝人稱“嚨咚調”)出于弋陽腔,而從吹腔又產生了平板二黃[注]歐陽予倩:《談二黃戲》,《小說月報》17卷號外,1927年6月。。周貽白也持類似看法:“所謂吹腔,它與二黃平板實為同一體系,而二黃平板舊有四平調之稱。”⑥周貽白:《中國劇場史(外二種)》,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6年,第376,320頁。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戲曲行業中,四平調是二黃平板的舊稱,它是由吹腔發展而來的一種聲腔,與明代流行的四平腔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此外,學界還認為,在弋陽腔與吹腔之間有個過渡聲腔,就是晚明時期流行的四平腔。也就是說,四平腔是吹腔的直接源頭[注]如吳新雷主編《中國昆劇大辭典》指出:“吹腔,昆劇中吸收的地方聲腔,從徽班中傳來。早在明末清初的時候,由弋陽腔演變而成的徽州四平腔因受昆腔的影響,在安徽樅陽、石牌一帶形成了一種新腔,初名‘樅陽腔’或‘石牌腔’,仍用曲牌體,后來逐漸變為板式體,用七字句、十字句,稱為‘吹腔’。”(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0頁)。如此,弋陽腔—四平腔—吹腔—二黃平板(四平調)的演化之跡甚明,以下對此軌跡略作考述。
四平腔在晚明年間已見于文獻,刊刻于萬歷間的《群音類選》在解釋“諸腔”時曰:“如弋陽、青陽、太平、四平等腔是也。”[注]胡文煥編:《群音類選》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南京圖書館藏明刊本,第1453頁。稍晚,顧起元《客座贅語》指出四平腔的源頭是弋陽腔:“又有四平,乃稍變弋陽而令人可通者。”[注]顧起元著,譚棣華、陳稼禾點校:《客座贅語》卷9,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03頁。對于如何“稍變弋陽”而得四平,陸小秋、王錦琦論之甚明:“(安徽藝人)學習了昆曲的伴奏形式,取消了靠鑼鼓和人聲幫腔,改用曲笛(或嗩吶)伴奏,有了一定的宮調約束,使得唱腔的進行與銜接都比較平穩……這種‘其調少平’比之于原來高腔自具一格的新腔,就是四平腔。”[注]陸小秋、王錦琦:《論徽劇聲腔的三個發展階段及二簧腔的形成》,《戲曲聲腔研究》,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7年,第11頁。可見,四平腔是以弋陽腔為主體,融合昆腔的一些藝術形式改造而成的。
徽劇史研究專家陸小秋和王錦琦還通過曲譜的比較發現,在四平腔與吹腔之間還有一個過渡的聲腔——昆弋腔[注]路應昆《“昆弋腔”辨疑》提出,昆弋腔是否存在有待證實,《綴白裘》中以昆弋腔替換梆子腔是規避朝廷亂彈禁令的巧妙做法,不可作為昆弋腔存在的直接證據(《戲曲研究》第94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5年,第71—81頁)。。也就是說,昆弋腔是四平腔融合昆腔的變體[注]陸小秋、王錦琦:《“梆子”、“梆子腔”和吹腔》,《戲曲藝術》1983年第4期。。入清后,四平腔吸收昆腔的腳步并未停止,它繼續在曲調中融進昆曲的因素,使得唱法更加細膩婉轉。為四平腔變體的昆弋腔雖然仍保持曲牌聯套體,但聯套的方式更加靈活,甚至大量采用民歌、俗曲穿插其間,故而有學者大膽推測繼承昆弋腔藝術基因的吹腔“可能先由民間曲調發展而來”[注]李連生:《四平腔與吹腔關系蠡測》,王評章、葉明生主編:《中國四平腔研究論文集》上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第281頁。。徽州一帶的藝人稱昆弋腔為“昆平腔”,江西貴溪一帶的坐堂班藝人則稱之“四昆腔”[注]陸小秋、王錦琦:《論徽劇聲腔的三個發展階段及二簧腔的形成》,《戲曲聲腔研究》,第16,28頁。,這些稱謂皆折射出昆弋腔為四平、昆腔交融的產物。
清代中前期劇壇的一個重大變化是西北的梆子腔南下東進,安慶作為當時安徽的首府也是梆子戲伶人進駐的重要城市。梆子腔在安慶及其周邊地區流動演出時大量采用當地方言,“并受昆弋腔中滾調的影響(形成“回龍疊板”),衍變為‘撥子’”⑤陸小秋、王錦琦:《論徽劇聲腔的三個發展階段及二簧腔的形成》,《戲曲聲腔研究》,第16,28頁。。在安徽方言中,“撥”“梆”音近,皖南的徽戲藝人認為“撥子就是梆子”[注]劉靜沅:《徽戲的成長和現況》,《華東戲曲劇種介紹》第三集,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5年,第62頁。。撥子音調高亢激越,演唱時以梆擊節,與梆子腔相同;甚至徽劇“老撥子”原板的唱腔和秦腔的花音原板仍極為相近,故而,撥子也被人稱之為徽梆子、安慶梆子或亂彈。
梆子腔對昆弋腔的影響更多體現在板腔體的演唱方式上。本來,弋陽腔經過四平腔、昆弋腔的演進,尤其受到滾調的大量運用,有些曲牌已經開始被淘汰,將此稱之為“曲牌遺失期”亦不為過。例如乾隆年間宮廷大戲《勸善金科》八本第十二出中的吹腔本無曲牌,編創者卻別出心裁,直接從唱辭中提煉牌名,曲牌【晚風柳】源自唱句“垂柳被那晚風吹”,【搖錢樹】出于“恨生生失去一棵搖錢樹”,其他類如【羅衣濕】【金水歌】【紅顏歡】【褪花鞋】【羊腸路】【開籠鶴】【繁華令】【念阿彌】,莫不如法炮制。昆弋腔意欲突破曲牌體的勢頭,后因梆子腔的到來而獲得徹底釋放,因此出現了一些板式變化體的上下句唱段,吹腔由此誕生。在乾隆年間的《綴白裘》等歷史文本中亦可看到,早期的吹腔是曲牌體與板腔體并存的特殊形態。
吹腔作為南方的腔調,曲調柔美婉轉,撥子則繼承梆子戲高亢激越的特點,二者各有所長,藝人將它們在同一劇目中配合演出,形成“吹撥”同劇演出的良好效果。例如乾隆間《綴白裘》中所選《斬貂》就是前唱吹腔,后唱撥子。吹腔與撥子兩種聲腔相互配合,取長補短,和諧共存于安慶戲班中,而被稱為“石牌腔”或“樅陽腔”。
清中葉,“石牌腔”以安慶為中心興盛起來后,迅速向外擴展傳播。今天不少地方劇種還能見到吹腔的影子,只是名稱五花八門,如婺劇稱“蘆花調”,紹劇稱“陽路”,萊蕪梆子稱“亂彈”,湘劇、南劇、滇劇稱“安慶調”,貴州梆子稱“安琴”,祁劇、桂劇、廣東漢劇稱“安春調”,閩劇稱“滴水”。從曲調和演唱風格來看,它們還基本保持吹腔的本來面目。
二、南北兩種吹腔
清中前期,發源于安慶的石牌吹腔在南方廣泛流傳的同時,北方也有一種吹腔——西秦腔(又稱甘肅腔)到處流動演出。康熙五十一年(1712)始任綿竹縣令的陸箕永有竹枝詞云:“山村社戲賽神幢,鐵撥檀槽柘作梆。一派秦聲渾不斷,有時低去說吹腔。”[注]潘超、丘良任、孫忠銓等編:《中華竹枝詞全編》第六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719頁。西秦腔以唱吹腔為主,同時也吸收了此時山陜梆子腔的板腔體演唱形式,故入川的西秦腔只是“有時低去說吹腔”。后來大約在乾隆四十年(1775)前后,這種四川吹腔被魏長生帶入北京,廢除笛子改為胡琴伴奏,形成“琴腔”新調。
據流沙研究,西秦腔的源頭就是由陜西入甘肅的隴東調,它的基本唱腔由兩句體【吹腔】(含【批子】)和四句體【二犯】組成[注]流沙:《清代梆子亂彈皮黃考》,臺北:“國家”出版社,2014年,第67—71,28,37—45頁。。隴東調由弋陽腔演變而來,“干唱的弋陽腔加上管樂(嗩吶)伴奏后,再從某一個音樂曲牌中抽出兩句腔,以組成上下兩句為一個樂段的曲調,這就形成原始性的吹腔……嗩吶再換用笛子伴奏的四句腔,因無適當名稱,就被陜西人稱為‘吹腔’了”[注]流沙:《清代梆子亂彈皮黃考》,臺北:“國家”出版社,2014年,第67—71,28,37—45頁。。西秦戲早期的腔調“隴東調”在今天隴東南皮影戲中還有遺存,多稱“老東調”[注]趙建新:《隴東南影子戲初編》,臺北: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1995年,第101頁。。康熙年間浙江人查嗣瑮《土戲》的詩句“玉簫銅管漫無聲,猶勝吹鞭大小橫。不用九枚添綽板,邢甌擊罷越甌清”[注]查嗣瑮:《查浦詩鈔》,《四庫未收書輯刊》第八輯第2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76頁。,即記述陜西鳳翔府一帶演唱吹腔的情況,當地的土戲僅有簫、嗩吶與打擊樂器伴奏,這種吹腔或就是隴東調。
由于西秦腔系中同時包含有長短句的吹腔和齊言四句體的梆子腔,二者在藝術上漸趨融合,故在李調元看來,“吹腔與秦腔相等,亦無節奏,但不用梆而和以笛為異耳”[注]李調元:《劇話》卷上,《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八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47頁。。從西北走出的吹腔,被人們系以產地,稱為“秦吹腔”。
乾隆六十年(1795)刊行的《霓裳續譜》“西調”俗曲集中即有“秦腔”和“秦吹腔”兩個類別。如第十九種曲【秦吹腔花柳歌】,傅惜華認為“‘秦吹腔’,疑為‘西秦吹腔’之簡名,乃秦腔劇中之一種調名”[注]傅惜華:《明清兩代北方之俗曲總集》,《曲藝論叢》,上海: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3年,第25頁。,此論頗有見地。錢南揚《梁祝戲劇輯存》收錄吹腔《訪友》,標為“嚨咚調”,即是秦吹腔,其曲詞多為七字句,也有三三七、三五七句式[注]錢南揚:《梁祝戲劇輯存》,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22—28頁。。秦吹腔在今天的廣東海陸豐地區的西秦戲中還有遺存,西秦腔常用的吹腔在“唱腔結構的特征、每頓的過門、旋律走向、調式調性,以至藝術風格”都與之十分相近[注]黃鏡明、李時成:《廣東西秦戲淵源質疑》,《梆子聲腔劇種學術討論會文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15頁。。
對于安慶吹腔和秦吹腔,熟悉的行家一聽旋律就能分別,因為它們一南一北,不僅風格有差異,而且雅俗難易有別。潘鏡芙、陳墨香《梨園外史》第二十一回講到,梅蘭芳的祖父梅巧玲拿來吹腔劇本《盤絲洞》,這一本戲上因有“一江風”“梁州序”的牌名,被人認為是昆腔,熟知昆腔與吹腔的延四爺對此給出了解釋。他的話對于我們認識這兩種不同的吹腔有所幫助:
延四爺道:“這另是一路吹腔,同那尋常吹腔不是一樣。那一路的吹腔,本于北曲,是有‘一凡’的。這一路的吹腔,本于南曲,是沒有‘一凡’的。那一路是亂彈的先聲,這一路是昆曲的變相,難易雅俗差的多了。”[注]潘鏡芙、陳墨香:《梨園外史》,北京:寶文堂書店,1989年,第252頁。
這段話道出兩個重要信息:一是明確告訴我們吹腔有南北之分,二者有較為明晰的分疏;二是南北吹腔的腔調、源頭和審美風格有差別。需要指出的是,引文中北曲吹腔中的“一凡”就是【三五七】,它是相對“二凡”而言。這種北方的吹腔隨著梆子戲的腳步,在南方流傳甚廣,今天仍有遺存,如浙江紹劇中的【三五七】就是吹腔【隴東調】發展而來,只是紹劇稱為【嚨咚調】。浙江金華徽班的【龍宮調】,浙江杭嘉武班的【嚨咚調】,江西宜黃腔的二凡平板等,皆是北方吹腔流落南方戲曲中的孑遺[注]流沙:《清代梆子亂彈皮黃考》,臺北:“國家”出版社,2014年,第67—71,28,37—45頁。。
南北兩種吹腔在乾隆年間的一些劇本中有直接的體現。現藏國家圖書館的抄本《十出奇》是一部以梆子腔為主體的花部戲,而《慶安瀾》則是一部吹腔戲。這兩部戲的作者都是山陰人周大榜。據鄭志良考證,周大榜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卒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注]鄭志良:《山陰曲家周大榜與花部戲曲》,《明清戲曲文學與文獻探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16—437頁。,他創作的兩部劇反映的是乾隆年間江浙地區梆子腔、吹腔的藝術面貌。《慶安瀾》以吹腔為主體,雜以梆子腔、民歌鮮花調、梆子腔吹調和【慶安瀾入破】曲牌。在劇本中,每支吹腔都標明“配笛唱”和“配嗩吶唱”,并存在一支吹腔由笛和嗩吶交叉伴奏的情況。特別要指出的是,在《慶安瀾》和《十出奇》中除了流行于南方的吹腔外,還出現了北方而來的吹腔,周大榜為凸顯它與南方吹腔的區別,特意標為【梆子腔吹調】。在《慶安瀾》中,【梆子腔吹調】出現在四出戲中,共有14支曲子,它們既能單獨組曲演唱(如第二折《變桃》、第十二折《眺海》、第十五折《幻斗》),也能與南方的吹腔搭配組曲(如第19折《收珠》)。這種情況在《十出奇》中也存在,用南吹腔的有兩出戲(第十七出《吞聘》、第十八出《降神》),共5支曲;北吹調則有五出戲(第二出《囑妾》、第五出《武娶》、第七出《文求》、第九出《議糧》、第十二出《祝誕》),共15支曲。北吹調也分笛和嗩吶伴奏,在句式上與南吹腔并無明顯差別,皆以齊言上下句為主,并夾雜著三三五,三三七,三五七等雜言唱句。若細論唱句體式的差別,則是南吹腔的雜言要多,其保留昆弋腔曲牌體的痕跡似乎更重,而北吹調則基本是齊言的五言或七言對句,雜言唱句較少。
乾隆年間花部劇本的存在,對于認識南北吹腔的藝術差異和二者的融合,提供了最直接的文獻支持;同時也能較好地看待吹腔源頭的兩種分歧:一是以陸小秋、王錦琦為代表提出的“吹腔源自四平腔”的說法;一是以流沙為代表,認為“吹腔源自西秦腔”的觀點。頗有意味的是,這兩種看法有一個相同點,就是皆認為吹腔更早的源頭是弋陽腔,同時也受到昆腔的影響。最確鑿的證據是,在一些現存的吹腔戲中還存在昆頭子的情況,即在唱吹腔之前先唱一支昆曲,如《十出奇》第九出《議糧》在唱【吹調】前,先以嗩吶配樂演唱【山坡羊】。
南北吹腔在梆子戲的影響下,開始向板腔體過渡,處于曲牌聯套與板腔變化體之間的特殊形態。對于揚州等地流傳的吹腔,徐珂《清稗類鈔》將之稱為“弋陽梆子秧腔戲”,文曰:
昆曲盛時,此調僅演雜劇,論者比之逸詩變雅,猶新劇中之趣劇也。其調平板易學,首尾一律,無南北合套之別,無轉折曼衍之繁,一笛橫吹,習一二日,便可上口。雖其調亦有多種,如《打櫻桃》之類,是其正宗。此外則如《探親相罵》,如《寡婦上墳》,亦皆其調之變,大抵以笛和者皆是……昆曲微后,伶人以此調易學易制,且多屬男女風情之劇,故廣制而盛傳之,為昆曲與徽調之過渡,故今劇中昆曲已絕,而此調則所在多有也。[注]徐珂:《清稗類鈔》“戲劇類”,第十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015—5016頁。
徐珂將吹腔判斷為“昆曲與徽調之過渡”,較為準確地道出吹腔介于昆弋腔與徽調之間的狀態。他主要是從兩個層面作此結論:從音樂體制上而言,吹腔處于齊言句中夾雜長短句的特殊形式,革去了昆曲“轉折曼衍之繁”;在劇目題材上,吹腔多男女風情的旦角戲,而后來的“徽調”則以生角戲為主。
民間時興的吹腔受到內廷戲曲機構的關注并將之引入清宮,因而在內廷戲本中頻繁浮現吹腔的身影,如《忠義璇圖》五本第二出蔣忠妻賽花唱【吹腔】:“雪花飄蕩空中下,來來往往是客商。兒夫英明傳天下,打盡了天下才郎。”完全是七字齊言句式。五本第十三出眾人合唱吹腔,五本第二十出李逵獨唱吹腔。另一本宮廷大戲《勸善金科》則采用了更多的吹腔唱段,四本第十四出妓女賽芙蓉不甘墮落風塵,情愿遁入空門為尼,鴇母、龜頭前來堵截,三人輪唱十支吹腔。八本第十二出,女鬼書吏審案時與眾女鬼輪唱七支吹腔。就句式而言,以上戲出中的吹腔起句多為三五七格式,其余唱句不計襯字完全是七字齊言句。嘉慶之后,吹腔更加頻繁地出現于內廷戲本中,如齊如山舊藏《雙合印總本》第二、三、六、七出中大量使用吹腔[注]齊如山舊藏《雙合印總本》,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藏本。;另從內廷戲曲檔案來看,標注“吹腔”的戲目越來越多,吹腔已經成為宮廷戲曲聲腔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員。
三、吹腔與二簧腔
在吹腔興起階段,最早記載二簧腔的史料是成書于乾隆四十年的李調元《劇話》,他認為起于江右的胡琴腔“又名二簧腔”[注]李調元:《劇話》,《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八冊,第47頁。。這則材料顯示,二簧腔已在此前形成并流行于江西等地。四川人李調元對花部戲曲較為熟悉,曾與川籍名伶魏長生關系甚篤,他的記載應比較符合二簧腔的實際情況。時間往后推移二十年,則有李斗《揚州畫舫錄》卷5提及當時南方有二簧腔流行:“雅部即昆腔,花部為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班。”[注]錢泳《履園叢話》卷12亦有類似的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23頁)。同卷還提及伶人樊大睅昆、弋、梆、羅和二簧“無腔不備”,人謂“戲妖”[注]李斗著,汪北平、涂雨公點校:《揚州畫舫錄》卷5,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31,130頁。。值得注意的是,李斗《揚州畫舫錄》特意指出“安慶有以二簧調來者”④李斗著,汪北平、涂雨公點校:《揚州畫舫錄》卷5,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31,130頁。;那么,從安慶來的“二簧調”究竟是什么聲腔呢?它與同期產自安慶的吹腔又是什么關系?我認為,乾隆年間興起的二簧腔就是石牌腔,而石牌腔即如上文所指出的,是吹腔和撥子兩種聲腔的合稱。
據《凌次仲先生年譜》卷1記載,乾隆四十五年揚州詞曲局設立后,李斗就被征召參與對劇本的查飭工作[注]張其錦編:《凌次仲先生年譜》卷1,見陳祖武選:《乾嘉名儒年譜》第10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第140頁。。按常理而言,身處揚州詞曲局的李斗應該對江南地區戲曲聲腔的流行情況是比較清楚的,《揚州畫舫錄》提及的安慶二簧調,應該是對當時安慶最流行的戲曲聲腔的一種準確判斷。如上文所言,當時安慶一帶興起的聲腔就是石牌腔。令人疑惑的是,李斗為什么不像兩淮鹽政使伊齡阿、湖廣總督舒常、湖北巡撫鄭大進、江西巡撫郝碩、廣東巡撫李湖等地方要員向朝廷奏報查辦戲曲的奏折中,直接稱之為石牌腔或吹腔,卻另題新名“二簧腔”呢?筆者以為這與徽班御前承應有關。組織徽班的揚州鹽商為來自安慶的石牌腔取個新奇又文雅的名字,又能規避朝廷的“亂彈”禁令。眾所周知,梆子戲在北京因為搬演“粉戲”而受到朝廷的查禁,至乾隆五十年(1785)議準:
(京師)城外戲班,除昆、弋兩腔仍聽其演唱外,其秦腔戲班,交步軍統領五城出示禁止。現在本班戲子概令改歸昆、弋兩腔,如不愿者聽其另謀生理。倘有怙惡不遵者,交該衙門查拿懲治,遞解回籍。[注]《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779,宣統元年(1909)上海商務印書館。
李斗的《揚州畫舫錄》成書于乾隆六十年(1795),主要記述的就是此前二十余年間揚州的城市史。如上文所論,石牌腔所包含的高撥子就是吸收梆子戲藝術養分的產物,徽班藝人或組織徽班的鹽商有意淡化高撥子而突出吹腔,而稱二簧。徽州鹽商在揚州壟斷了鹽業的經營,為向乾隆皇帝邀寵,他們在乾隆下江南及其慶壽期間,組織徽州戲班進獻御前。乾隆五十五年(1790),弘歷八旬萬壽慶典,四大徽班進京賀壽演戲,其中三慶班的高朗亭就被花譜《日下看花記》稱為“二簧之耆宿”[注]小鐵笛道人:《日下看花記》,張次溪編:《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年,第103頁。。從此,二簧調頻繁進入北京文人品評伶人的花譜視野,如《聽春新詠》將北京劇壇分為三部,雅部為昆腔,徽部唱二簧,西部演梆子,這說明徽班演唱二簧腔為京城人所熟知[注]留春閣小史:《聽春新詠》“例言”,張次溪編:《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第155頁。。即便到了道光中葉,楚伶進京唱紅了漢調西皮,導致“吹律不競”,但仍有徽班的二簧腔為個別人所特嗜:“若二簧、梆子靡靡之音……臺下好聲鴉亂。”[注]蕊珠舊史:《長安看花記》,張次溪編:《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第310—311頁。
“簧”的本義是指管樂發聲的薄片,古時就有簧片之謂。笛子與嗩吶都屬于簧片樂器。王芷章認為,之所以吹腔被稱為“二簧腔”是因為吹腔為笛子伴奏,“且多用雙笛,由于笛膜相當于笙中之簧,故稱為二簧”[注]王芷章:《中國京劇編年史》附錄,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年,第1236頁。。此論道出了二簧腔之“簧”來源于笛子的特殊構造,可備一說。筆者《“二黃腔”名實考辨》也從語源學的角度考證了二簧腔的命名與笛子之簧片有關[注]陳志勇:《“二黃腔”名實考辨——兼論“皮黃合流”的相關問題》,《中山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何昌林則另有新說,他認為“二簧”是指“在兩句一轉的唱腔中,可以使用兩次‘大過門’,即兩次‘簧’(‘大過門’即‘簧’)”,“簧”在高腔中就是幫腔,“由于出現了兩次,故稱‘二簧’”[注]何昌林:《從三簧說到二簧》,《戲曲研究》第十二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4年,第246頁。。不過,何先生的這種說法應者寥寥。
近讀乾隆年間山陰人周大榜梆子戲、吹腔劇本《十出奇》和《慶安瀾》發現,劇中的吹腔唱段皆明確標注是由笛伴唱還是由嗩吶伴唱,故筆者認為“二簧”之得名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二“簧”指兩種管吹樂器——笛子與嗩吶。它們正是安慶吹腔的兩種主要伴奏樂器。由兩種簧管樂器指稱由它們伴奏的聲腔,這種命名的方式是戲曲聲腔史上常見的。例如,伶人將笛、嗩吶改為胡琴伴奏,李調元《劇話》記載:“胡琴腔起于江右,今世盛傳其音,專以胡琴為節奏,淫冶妖邪,如怨如訴,蓋聲之最淫者。又名二簧腔。”[注]李調元:《劇話》,《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八冊,第47頁。二簧腔又稱為“胡琴腔”,亦是同樣的命名原理。
由此可見,二簧腔的得名主要是與吹腔相關,很大程度折射出吹腔在清中葉不同尋常的影響力和傳播力。
弄清楚了二簧腔即吹腔和高撥子,也就明白它與后世皮黃腔中的二黃調的差別與差距。差別,意味著二簧腔不可混同于二黃腔,它們是兩種不同的聲腔;差距,則意味著二簧腔在藝術上遠沒有二黃腔成熟和精致,如二簧腔還處于長短句式與齊言句式混雜的狀態,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板腔體。又據《十出奇》《慶安瀾》中吹腔形態顯示,當時的二簧腔僅有正板和急板,板式遠沒有后世二黃腔那么豐富和完善。正板是吹腔中最主要的板式,稍走低調的人稱“二簧平板”;急板節奏緊促,與舒緩的平板形成互補。另外,后世以“老二黃”來稱謂嗩吶二簧,二簧平板則被稱為“小二黃”,這些叫法透露出二簧與二黃之間的藝術聯系。簡言之,清中葉以笛和嗩吶伴奏的二簧腔是后世二黃腔的“童年期”的形態,當它吸收西皮腔的藝術養分予以自身改造,就脫胎換骨演化為一種新腔——二黃腔。清中葉《燕蘭小譜》《金臺殘淚記》等戲曲文獻對此演進過程有所記載。《金臺殘淚記》指出“甘肅腔曰西皮調”[注]張際亮:《金臺殘淚記》卷3,張次溪編:《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第250頁。,而吳長元《燕蘭小譜》認為:“蜀伶新出琴腔,即甘肅調,名西秦腔。其器不用笙笛,以胡琴為主,月琴副之。工尺咿唔如話。”[注]吳長元:《燕蘭小譜》卷5,張次溪編:《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第46頁。張際亮《金臺殘淚記》又指出:“此腔當時乾隆末始蜀伶、后徽伶盡習之。”[注]張際亮:《金臺殘淚記》卷3,張次溪編:《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第250頁。西秦腔本是以笛伴奏,后改為胡琴,并向板腔體的梆子腔靠攏,從而衍生了新的西皮調。徽伶以西皮調更為新奇可聽,廣受觀眾歡迎,故轉向西皮調學習并改造徽調吹腔,從而生成二黃腔。
四、吹腔與宜黃腔
宜黃腔是清代撫州宜黃縣產生的一種聲腔。據流沙等學者考證,最早記載宜黃腔的文獻是康熙間浙江余姚人徐沁《香草吟》第一出“綱目”的眉批[注]流沙:《清代梆子亂彈皮黃考》,第308頁。,文曰:“作者惟恐入俗伶喉吻,遂墮惡劫,故以‘請奏吳歈’四字先之,殊不知是編惜墨如金。曲皆音多字少,若急板滾唱,頃刻立盡。與宜黃諸腔,大不相合。吾知免夫。”[注]徐沁:《香草吟》第一出“綱目”的眉批,國家圖書館藏康熙間曲波本。這里提及的“宜黃諸腔”不明所指,故其是否包含“宜黃腔”也難坐實。較早出現“宜黃腔”之名的文獻是昭梿的《嘯亭雜錄》,是書卷8謂“近日有秦腔、宜黃腔、亂彈諸曲名。其詞淫褻猥鄙,皆街談巷議之語”[注]昭梿:《嘯亭雜錄》卷8,何英芳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36頁。。昭梿將已進京的宜黃腔與秦腔、亂彈腔并列而稱,說明此腔已有相當的影響力,但其言語間又流露出對地方戲強烈的鄙薄之意。
宜黃腔在清中葉就已進入北京,且能與當時流行的秦腔、亂彈腔同時受到昭梿的關注,說明其聲腔主體特征是明確的。宜黃腔的唱腔有【平板吹腔】【批子】和【嗩吶二凡】,伴奏樂器以笛子和大嗩吶為主。【批子】即吹腔頓腳板[注]陸小秋、王錦琦:《“梆子”、“梆子腔”和“吹腔”》,《戲曲藝術》1983年第4期。。在乾隆間的《綴白裘》折子戲“趕子”“擋馬”皆能見到。可見,宜黃腔早期的聲腔【平板吹腔】【批子】由笛子伴奏,【嗩吶二凡】則是以嗩吶伴奏,故它們皆屬于吹腔系統。
乾隆年間宜黃腔藝人改換了主要伴奏樂器,他們以胡琴代替笛子和嗩吶,“并將【平板吹腔】和嗩吶【二凡】統一起來,從而構成以【二凡】為主體的胡琴腔”[注]流沙:《清代梆子亂彈皮黃考》,第309,310,304頁。。胡琴腔由倒板(原嗩吶二凡倒板第一句)、十八板(原嗩吶二凡倒板第四句)、正板(原嗩吶二凡正板)、流水板(原嗩吶二凡流水板)、散板(原嗩吶二凡流水板)、平板(原出平板吹腔)組成[注]流沙:《宜黃諸腔源流探》,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3年,第39,68,38頁。。稍作說明的是,與宜黃腔聲腔結構不同,安慶二簧腔以笛子伴奏的吹腔為主,以嗩吶二簧為輔,而宜黃腔將西秦腔的小筒胡琴提升為主奏樂器,使之較安慶二簧腔在藝術上更為接近后世皮黃聲腔系統中的二黃腔,甚至不妨認為“宜黃腔是一種原始的二黃”⑤流沙:《清代梆子亂彈皮黃考》,第309,310,304頁。。
正由于宜黃腔以【二凡】為主體聲腔,故而流沙等學者更主張它源自北吹腔,即宜黃腔的源頭是來自大西北的西秦腔。這一觀點有據可證,程硯秋舊藏《缽中蓮》傳奇中就有【西秦腔二犯】的聲腔名稱。“二凡腔,是因其源于【西秦腔二犯】而得名”⑥流沙:《清代梆子亂彈皮黃考》,第309,310,304頁。,具體而言,以三五七為主體的隴東調吹腔是西秦腔早期聲腔,在其基礎上變出一種半句吹腔的“批子”。“二犯”就是通過批子演變而來。流水板的二犯與一板一眼的秦吹腔并奏,形成曲牌與板腔的混合體[注]流沙:《宜黃諸腔源流探》,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3年,第39,68,38頁。。二犯流水板、倒板、一板一眼的正板共同構成宜黃腔早期的嗩吶二凡。一板一眼的秦吹腔后來演化為平板吹腔,批子也保留下來,成為宜黃腔中重要的聲腔成分。
但要指出的是,宜黃腔雖脫胎于西秦腔,但在西秦腔的基礎上又有所改進,例如在調式上,宜黃腔的嗩吶二凡將西秦腔的宮調式改為商調式,僅平板吹腔保留了西秦腔的宮調式。在調性上,宜黃腔的二凡調改西秦戲的正宮調為凡字調,音調要低。在板式上,宜黃腔在西秦腔流水板的基礎上,還發展出倒板、正板、流水板等多種,形成了較為豐富的板式體系[注]流沙:《宜黃諸腔源流探》,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3年,第39,68,38頁。。由此可見,戲曲聲腔的發展永遠都是遵循繼承與創新的規律,新腔脫胎于老調,又能吸收其他藝術元素而創立新的聲腔。所以,即如宜黃腔與西秦腔的關系:既保持了母體血脈,又流淌著自己的藝術新血液。它們在藝術上的“同”與“不同”,啟發我們應以辯證和發展的眼光去審視吹腔與宜黃腔之間的藝術聯系。
結 語
吹腔是清代戲曲聲腔史上獨具特色的腔調,它與西秦腔、二簧腔、宜黃腔、二黃腔的關系錯綜復雜,這給它的源流蒙上神秘的面紗,也給我們了解它的前世今生帶來了不小的困惑。
從上文的論述可以看到,吹腔的興起,實際上是清代戲曲聲腔演進的一個特殊歷史階段。在時間起止上,前可追溯至康熙年間梆子戲裹挾秦吹腔南傳東進,后可延宕至嘉慶道光年間吹腔在皮黃腔系中遺留與衍化。這個過程基本上與清代亂彈流行時間和時長相埒。
繼就清代劇壇稱謂吹腔為“亂彈”來看,吹腔作為亂彈戲的一種,也如亂彈一樣,有一個繼承傳統與融合新質,重組舊腔與再創新調的過程。而清中葉的二簧腔和宜黃腔正體現出曲牌體與板腔體混合演唱的特殊狀態,處于由曲牌體結構向板腔體結構過渡階段。事實上,二簧腔和宜黃腔都是吹腔階段的產物,它們都是由吹腔向二黃腔邁進的中間狀態,亦不妨將它們皆視為后世皮黃腔系中二黃腔的早期形式。所不同的只是宜黃腔較之二簧腔改換胡琴伴奏要早,故在清中葉,宜黃腔在聲腔進化上,更接近后世的二黃腔。這也就是為什么歐陽予倩對二黃腔是來源于安徽、江西還是湖北作一番考證后,得出是幾省藝人“集體合作”結論的原因所在[注]歐陽予倩:《談二黃戲》,《小說月報》第17卷號外,1927年6月。。
考察吹腔與二簧腔、宜黃腔的關系,還可以發現一個特別的現象:在清中葉,無論是二簧腔還是宜黃腔,它們的腔調系統組成都呈現南北聲腔互補的共性特征。安慶二簧腔是由南方聲腔色彩鮮明的吹腔與受秦腔影響較大的高撥子組合成的復合腔系,宜黃腔則是南方聲腔吹腔與西秦腔變化而來的二凡調組合而成。南北聲腔在安徽、江西等地的融合,從而誕生了新的聲腔。這種腔調生成的新路徑熔鑄了南方與北方戲曲聲腔的長處,賦予聲腔更豐富的表現力和涵容度。后來,產生于湖北的西皮與來自徽、贛的二黃,再次實現北腔與南調的融合。可以說,南北聲腔的不斷融合、改造與提高,成就了皮黃聲腔的藝術高度。
吹腔源流及其演變軌跡的復雜性,不僅是因為它存在南北兩個藝術品種,而且還在于它以極為靈活與開放的姿態,不斷與周邊的聲腔發生融合而衍化出新的品種。故而,本文在研究思路上,試圖通過“減頭緒”以實現“立主腦”的研究目標,即以二黃腔的來源問題為導向,通過考鏡吹腔的源流來探尋與之有關系的安慶二簧腔、江西宜黃腔對后世二黃腔生成的獨特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