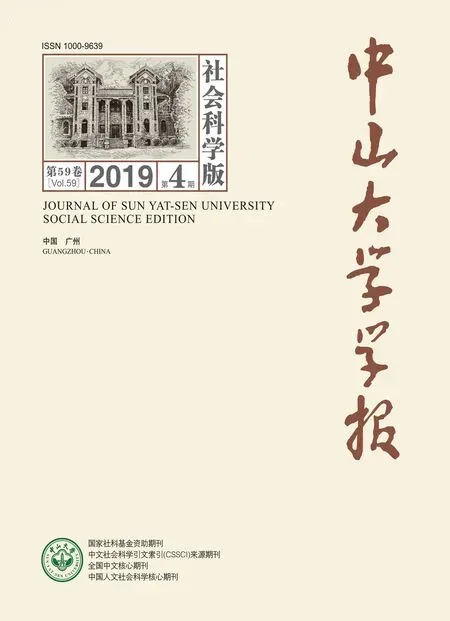沉寂與復興: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利益理論*
陳天祥, 黃寶強
一、引 言
在公共行政的理論傳統中,對于何種行政才稱得上是良好行政以及如何確保和實現良好行政,一直存在著雙峰對峙的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保持客觀中立和堅持效率至上是良好行政的典范,它不關心政治事務和價值問題,只負責以最為理性和有效的方式執行法律和政策,古典公共行政理論和實證主義取向的行政學者是這種觀點的主要持有者。另一種觀點則堅持認為良好行政必須承擔起相應的政治責任,對一些倫理要求和規范性價值有所回應和有所擔當,持這一觀點的學者主要是規范取向的研究者。這兩種觀點構成了一個“沖突的連續體”①Alasdair Maclntyre. After Virtue,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7, p. 222.,在公共行政領域時而此方占據主流位置,時而彼方成為重要的修正性力量,兩種觀點之間的對立鮮明地體現在公共行政在促進和實現公共利益中扮演何種角色的爭論上。與關于良好行政的爭論一樣,就什么是公共利益、如何實現公共利益以及公共行政在其中扮演著何種角色等問題,也存在著截然不同的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公共利益存在于給定的法律和政策當中,有效地執行這些法律和政策就意味著公共利益的實現。因此,公共行政的責任就是通過提高組織和管理技術、改進和優化決策程序以及理性化行政行為來最大化政策執行效率,古典公共行政理論和實證取向的行政研究者是這一觀點的主要支持者。另一種觀點則堅持認為,公共利益并非只是體現在給定法律和政策中的具體內容,而是在具體的行政過程中得以建構和實現的某種東西。在這種觀點看來,公共行政必須將公共利益視為一種行動準則或價值導向,以此來規范和指導行政行為,持這一觀點的學者主要是規范取向的公共行政學者。
實際上,在第一種觀點下,公共利益因其在實踐中無益于提高行政效率、在研究上又無益于行政過程的經驗性描述而得不到重視,甚至“遭受著極大的中傷或者經常被遺忘”[注]Norton Long. Conceptual Notes on The Public Interest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1990, Vol. 22(2), pp.170-181.。因此,當古典公共行政理論和實證主義行政科學居于支配地位時,公共利益在公共行政領域一直處于被遮蔽的狀態,從未被充分地思考和討論過。真正使公共利益成為關注焦點并引發持續爭論的是夏博特的開創性工作。然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對夏博特工作進行的回應大都發生在政治學領域,公共行政領域并未給予應有關注,以致于像麥克斯懷特(O. C. McSwite)所說的那樣:“公共利益在學術和實踐領域完全消失了。”[注]O. C. McSwite. Postmodernism,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In Gary L. Wamsley , et al. eds. Refounding Democratic Public Administration: Modern Paradoxes, Postmodern Challenge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6, p. 202.
進入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爆發了強烈的反國家、反權威和貶斥官僚的熱潮,政府陷入了嚴重的合法性危機,治理能力受到強烈的質疑和挑戰。首先,在現實層面,美國在戰后采取的國家干預主義最終導致了嚴重的經濟滯脹和公民生活質量的持續下降,與之伴隨的則是種族沖突、貧富分化等社會問題的日益加劇,導致公眾對政府的強烈失望與不滿。其次,在學術層面,建立在工具理性和效率準則基礎上的古典公共行政理論和實證主義行政科學對以上問題難以作出有效的回應,其理論的有效性受到強烈的質疑。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公共行政領域迎來了一場規模空前的“重建運動”[注]關于這場重建運動的詳細論述,參見Richard Stillman II. The Refounding Movement in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From “Rabid” Anti-Statism to “Mere” Anti-Statism in the 1990s, Administrative Theory & Praxis, 1995, Vol. 17(1), pp. 29-45.,其中,一些規范取向的重建者認為傳統公共行政理論所假定的以效率為核心的工具性角色已經難以應付日益復雜的社會治理問題了。鑒于此,他們試圖通過恢復公共利益的合法地位、發掘公共利益的規范性內涵以及重新界定公共行政在促進和實現公共利益中的作用,為更為積極的行政角色、更為廣泛的行政責任和更加民主開放的行政過程提供支持,以此來應對政府面臨的合法性危機。在沉寂多年后,公共利益終于等來公共行政領域對它的“平反”,并作為表達對積極有為的公共行政角色訴求的核心概念而得到重新闡釋、建構和發展。本文主要考察公共利益在公共行政領域被遮蔽、復興和被重構的過程,并認為,公共利益理論的復興和重構為一種更具政治屬性、更加開放的民主行政范式提供了強有力的概念和理論支撐,但這種基于規范性視角重構的公共利益理論仍然存在著一種內在張力,這種張力雖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卻仍然需要被認真對待和分析。
二、古典公共行政理論與實證主義行政科學對公共利益的遮蔽
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古典公共行政理論和實證主義行政科學相繼占據著公共行政話語的主流地位,它們對行政組織的工具理性和效率準則的追求大大簡化了公共行政在治理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承擔的責任。在這種背景下,公共利益得不到重視,甚至被視為行政效率的干擾因素而遭受批評,并且由于缺乏概念上的清晰性和可操作性而被實證主義取向的行政科學視為空洞無用的分析工具而邊緣化甚至被遺棄。
(一)被忽略的公共利益:古典公共行政理論的觀點
在美國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先后興起的公務員改革運動、進步主義運動和科學管理運動中產生并發展起來的古典公共行政理論,僅將行政視為法律和政策的執行性活動,認為最大化地提高執行法律和政策的效率是公共行政的主要目的,公共行政學則應當是一門研究和發現提高行政效率的原則和方法的科學性事業。在這種工具性觀點和效率準則的導向下,古典公共行政理論表達了以下三個方面的行政觀念:堅持政治和行政二分;認為行政是一種無異于商業管理的管理性活動;認為行政活動可以運用科學的方法和原則加以組織和開展[注][美]羅森布魯姆、奧利里著,張夢中等譯:《公共管理與法律》,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6頁。。從這三種觀點來看,公共利益既不在公共行政所關心的恰當范圍之內,也不是管理性活動的主要目的,更不是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的科學方法和原則,因此便順理成章被忽略掉了。
首先,就政治和行政二分而言,古典公共行政理論堅持認為行政是一種有別于政治的事務性活動,正如威爾遜(Woodrow Wilson)試圖表明的,“行政不在政治的適當范圍之內”[注]Woodrow Wilson.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887, Vol. 2(2), pp.197-222.,它不應關涉政治問題,而要以中立性的立場執行政治決定,即執行既定的法律或政策。公共利益主要通過政治性活動來確定和表達并體現在給定的法律或政策中,不應由行政人員來確定。在具體的行政過程中,行政人員不應因個人判斷或偏好而違背法律或政策的初衷,而是要忠實地執行既定法律和政策,既定法律和政策落實的程度越大,實現公共利益的程度就越大。
其次,古典公共行政理論視行政為一種無異于商業管理的管理性活動,威爾遜甚至直接提出“行政的領域就是商業的領域”③Woodrow Wilson.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887, Vol. 2(2), pp.197-222.的觀點,成為當時改革者所信奉的普遍教條,主導了大量的政府改革事項。正如沃爾多(Dwight Waldo)所述,對商業的意識形態、組織形式和管理技術的接受和采納,“因為歷史環境而變得不可避免,也因為對‘效率’的急迫需求而變得令人滿意”[注][美]德懷特·沃爾多著,顏昌武譯:《行政國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第51頁注釋②。,當時美國正處于商業繁榮的時代,人們普遍認為,只要政府按照商業模式組織和運轉,就能取得商業領域所取得的那種效率和成就。在商業模式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諸如經濟、效率和生產力等術語廣泛彌漫于當時的行政思想和改革運動中,而像公共利益、社會公平和個人權利等價值性概念則在理論和實踐中被忽略了。
最后,古典公共行政理論將科學方法和原則應用于行政事務的訴求意味著對建立一門行政科學的迫切需要。威爾遜提出了建立行政科學的最早倡議,主張“行政科學”的主要任務是“把行政方法從經驗性實踐的混亂和浪費中拯救出來,并使它們深深植根于穩定的原則之上”⑤Woodrow Wilson.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887, Vol. 2(2), pp.197-222.,而使用這些方法和原則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正如古利克(Luther Gulick)所說:“在行政科學中,效率就是基本的‘善’,……是行政價值尺度上的第一公理。”[注]Luther Gulick. Science Value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Luther Gulick and L.Urwick eds. Papers on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201.當然,古利克同時也指出,對效率的強調會使行政與政治價值尺度的某些要素——公共利益自然也包含在這些要素當中——明顯相沖突,因此,古利克妥協道,“我們最終不得不根據政治和社會秩序的價值尺度來緩和純粹的效率概念”[注]Luther Gulick. Science Value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Luther Gulick and L.Urwick eds. Papers on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201.。但古利克的妥協在古典行政理論中并沒有體現出來,尤其是在科學管理運動的影響下,對組織和管理的“穩定原則”的追求以及對效率的強調得到進一步強化,包括公共利益在內的一些價值要素被進一步從行政研究中剔除了。
(二)被遺棄的公共利益:實證主義行政科學的觀點
與古典公共行政理論一樣,以西蒙(Herbert Simon)為代表的實證主義行政研究者也致力于提高行政效率并將公共行政發展成一門事實上的行政科學。但是,實證主義取向的行政科學在以下三個方面不同于古典公共行政理論的訴求:聚焦于對公共行政的組織學考察、將行政活動視為具體的決策行為并致力于建構行政決策的理性模型、對實證主義尤其是邏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強調。雖然西蒙等實證取向的行政學者批評了古典公共行政理論的政治行政二分觀點及其管理原則的“諺語”性質,但與古典行政理論相比,他們在對公共行政的角色設定、公共行政人員的行為要求和對行政知識的界定上所表現出的工具性、理性化和科學性傾向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實證主義行政科學對公共利益的厭惡也絲毫不弱于古典公共行政理論。
首先,西蒙特別強調公共行政的組織特征與功能,作為組織的公共行政,其主要功能是通過運用一定的決策程序和管理技術,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完成既定目標。因此,西蒙認為,和“是否誠實”一樣,“是否有效率”也是衡量組織行為好壞與否的主要標準[注]Clerance Ridley and Herbert Simon. The Criterion of Efficiency,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38, Vol. 199, pp. 20-25.。西蒙的效率準則是指“用最小化的努力取得最大化的政策目標”或“在給定可用資源的條件下,選擇能產生最大收益的備選方案”[注]參見Herbert Simon, Donald Smithburg and Victor Thomps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p.12;[美]赫伯特·西蒙著,詹正茂譯:《管理行為》(原書第4版),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年,第237頁。。這種效率準則是針對完成給定的政策目標而言的,“它并不關心給定政策要達到什么樣的目的,更不會關心給定政策中所體現的價值問題”[注][美]西蒙:《管理行為》(原書第4版),第10,27—43,333頁。。在西蒙看來,行政組織及人員不應遵從諸如公正、平等和自由等規范性價值,而只需關心如何達成既定的組織目標。在這樣一種觀點下,公共利益顯然不是行政組織所考慮的問題,它只是隱含在給定的具體政策當中,而這些政策是否包含關于公共利益的考量,那是政治系統中的立法者或政治家所考慮的問題,由此,公共利益在行政的組織行為中被清除掉了。
其次,西蒙將行政行為視為由行政人員在其自身的有限理性范圍內進行的滿意決策行為。誠如馬沙爾和喬杜里(Gary Marshall and Enamul Choudhury)所指出的,西蒙的這種有限理性和滿意決策可能會導致行政人員不加批判地借助于工具技術來提高其信息搜集和處理能力,而行政決策過程中的公共參與和通過公共參與來澄清公共利益都變得沒有必要了[注]Gary Marshall and Enamul Choudhury.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Re-Presenting a Lost Concep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97, Vol. 41(1), pp.119-131.。在這種決策的理性模型中,行政人員需要的是一些清晰明確且合乎邏輯的決策程序或行為準則,而不是諸如“命令統一”、“控制幅度”等充滿矛盾的行政諺語,西蒙認為這些行政諺語只不過是一些藝術術語,對于決策行為和研究活動沒有多大的用處⑤[美]西蒙:《管理行為》(原書第4版),第10,27—43,333頁。。很明顯,公共利益就像這些行政諺語一樣,并不是一個能夠為行政行為提供明確的操作化準則的術語,它甚至比行政諺語更糟糕,反映的只是個人的觀點和偏好。總之,在西蒙的決策模型中并沒有公共利益的恰當位置,它既不會吸引行政人員的注意力,更不能對其決策行為提供有用的指導。
最后,以西蒙為代表的實證主義者致力于將公共行政建設成為以追求科學性知識為目的的行政科學,而只有以事實為基礎、經過嚴格的邏輯推理和經驗驗證的知識才稱得上是科學知識。因此,實證主義者首先要求對事實與價值作出區分,而行政科學“和任何科學一樣,只關心事實性的論述。……但凡出現道德論述,我們總是能將其分解為事實和倫理兩個部分,而只有前者才與科學有關”⑥[美]西蒙:《管理行為》(原書第4版),第10,27—43,333頁。。其次,行政科學需要一套能夠對經驗事實進行精確描述的概念工具,并且“為了能夠科學地應用這些概念,它們必須具有可操作性”[注]Herbert Simon. The Proverbs of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46, Vol. 6(1), pp. 53-67.。正如索洛夫(Frank Sorauf)所說,行政科學應開發“用于討論政治政策的道德性和明智性的知識工具,而不是模糊的道德化與合理化”[注]Frank Sorauf. The Conceptual Muddle, In Carl Friedrich ed. The Public Interest, New York: Aetherton, 1962, pp. 183-190.。公共利益作為一個具有價值承載的術語,既不能清晰地描述經驗事實,又不能被操作化,也不能幫助我們建構事實性命題并對其進行經驗驗證。就此而言,公共利益對發展公共行政的科學性知識毫無用處,因此被視為無用的分析工具而遭到了遺棄。
(三)被批判的公共利益:夏博特的分析性審查
實際上,在傳統時期,仍然有一些政治學家和公共行政的“傳統主義者”[注]關于公共行政的“傳統主義者”,參見Orion White and Cynthia Mcswain. The Phoenix Project: Raising a New Ima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Ashes of the Past,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1990, Vol. 22(1), pp. 3-38.并沒有放棄對公共利益的重視和考察[注]參見Pendleton Herr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New York: McGraw-Hill, 1936; Merle Fainsod.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Nature of the Regulatory Process, In Carl Friedrich, et al. eds, Public Poli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pp. 297-323; Paul Appleby. Morality and Administration in Democratic Government,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2; Emmette Redford. The Protection of the Public Intere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4, Vol. 48(4), pp. 1103-1113.,但古典的和實證取向的行政研究者并沒有認真對待這些學者的工作,真正對這些學者的工作進行分析性審查的,是夏博特(Glendon Schubert)的開創性工作。夏博特從行政決策制定的角度出發,根據學者們對公共利益與行政行為之間關系的不同假定將既有觀點分為三個不同的類型,它們分別是行政理性主義者、行政柏拉圖主義者和行政現實主義者,然后對這三個類型的觀點進行了分析、比較與批判。
首先是行政理性主義者。在夏博特看來,行政理性主義者是一群實證主義者,其主要代表就是古利克和西蒙。夏博特指出,行政理性主義者將公共利益視為由政黨和立法者根據公共意志轉化而來的、體現在具體政策目標中的某種東西,行政人員的任務不是界定公共利益的具體內涵,而是用專業的技術知識和方法有效地完成既定政策。在夏博特看來,行政理性主義者所建立的模型“是一個香腸機,從一端倒入公共意志,從另一端就會生產出一段段整齊的、包裹在各自腸衣中的公共利益”[注]Glendon Schubert. “The Public Interest” I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Theorem, Theosophy, or Theo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7, Vol. 51(2), pp. 346-368.。夏博特就此批評道,西蒙在這一模型中所假定的“行政人”角色實際上變成了“機器人”,他們在決策中的自由裁量權“被最小化甚至直接取消了,責任存在于不受意識支配的行為當中,科學則是天外救星”[注]Glendon Schubert. “The Public Interest” I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Theorem, Theosophy, or Theo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7, Vol. 51(2), pp. 346-368.。總之,行政理性主義者在決策過程中并不關心公共利益,他們把它視為一個內在于給定政策中的東西,隨著政策的完成,公共利益會自動實現。對此,夏博特不無諷刺地評論道:“據說,即便莎士比亞式故事情節的展現也需要有傻子的介入,而理性主義者所假定的行政理想則是自動實現的。”[注]Glendon Schubert. “The Public Interest” I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Theorem, Theosophy, or Theo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7, Vol. 51(2), pp. 346-368.
其次是行政柏拉圖主義者或行政理想主義者。行政柏拉圖主義者認為公共利益存在于行政人員的良心當中,其本質是“由公共官員通過超越感官的心理行為”[注]Glendon Schubert. “The Public Interest” I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Theorem, Theosophy, or Theo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7, Vol. 51(2), pp. 346-368.構造出來的。在行政柏拉圖主義者那里,公共利益實際上變成了“精英們所認為的對公眾有利的東西”[注]Glendon Schubert. The Public Interest: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the Political Concept,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60, p. 201, 201.,行政人員認為公共利益是什么,公共利益就是什么。因此,和行政理性主義者相反,行政柏拉圖主義者反對行政人員過于消極中立的技術性角色,主張將其置于政策制定過程的核心位置,賦予他們在表達和實現公共利益中最大化的自主性和自由裁量權。在如何界定和實現公共利益方面,夏博特將行政柏拉圖主義者分成了兩派。第一派是整合主義者(integration theorists)或行政工程師(administrative engineers),主張通過整合政治與行政的途徑來實現公共利益,在其中,行政人員被擬人化為良好管理者的形象,扮演著政治性和行政性的雙重角色,他們被教導不僅“要聰明”(clever)、“要明智”(wise)并且“要良善”(good)[注]Glendon Schubert. “The Public Interest” I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Theorem, Theosophy, or Theo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7, Vol. 51(2), pp. 346-368.。第二個派別是基爾特理想主義者(guild idealism),認為公共利益的實現需要一個“在政治上自主并保持價值中立的文官隊伍”[注]Glendon Schubert. “The Public Interest” I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Theorem, Theosophy, or Theo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7, Vol. 51(2), pp. 346-368.,即行政人員承擔的應是一種有別于政治責任的技術責任或專業責任,在專業上或技術上負責就是對公共利益負責。盡管兩種派別的觀點有所不同,但他們都強調公共利益的實現需要一個積極主動、有能力并且具有高度自主性的行政官員隊伍,因此,夏博特認為,不論是哪一個派別,他們的公共利益觀點及其對行政人員角色的假定根本上都與治理的民主理論相對立[注]Glendon Schubert. The Public Interest: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the Political Concept,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60, p. 201, 201.。
最后是行政現實主義者。行政現實主義者將公共利益視為政治過程中各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行政人員只不過是其中的力量之一,以一個行動者的身份承擔著不同的角色。夏博特根據現實主義者對這些角色的不同假定,將他們分為三個類型,分別是本特利主義者(bentlians)、心理現實主義者(psychological realists)、過程理論家(process theorists)。本特利主義者認為公共利益是利益集團相互競爭的結果,行政人員在其中發揮著催化劑的作用,他們不僅要在各種沖突性力量之間進行協調并最終達成某種均衡,而且有時還要直接在各種沖突性利益之間進行選擇,于是,他們變成了“諸神(各利益團體)爭奪的棋子”[注]Glendon Schubert. “The Public Interest” I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Theorem, Theosophy, or Theo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7, Vol. 51(2), pp. 346-368.。心理現實主義者認為公共利益是由具有自我意識的行政人員確定并提供的,政治過程中各種力量之間的競爭發生在行政人員的內心世界,他們要在內在于他們頭腦中的一系列價值之間進行權衡和選擇。在這一過程中,行政人員不僅受自身的價值觀或信仰的影響,而且還受到其他外部環境壓力的影響,但不論如何,行政人員的自我意識或主觀性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②Glendon Schubert. “The Public Interest” I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Theorem, Theosophy, or Theo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7, Vol. 51(2), pp. 346-368.。過程理論家同樣將公共利益視為各種競爭性力量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但這一相互作用的過程就發生在行政機構,“機構自身就是戰場”,行政人員扮演的是“命運戰士”(soldier of fortune)的角色,即確保所有的參賽者都有公平進入這一“戰場”的機會,而戰爭的結果自然會表明公共利益是什么③Glendon Schubert. “The Public Interest” I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Theorem, Theosophy, or Theo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7, Vol. 51(2), pp. 346-368.。也就說,對于過程理論家而言,行政人員既不在各種沖突性利益之間進行協調和選擇,也不按照自身的價值體系界定公共利益,他們僅僅是互動或競爭過程的維持者,而公共利益就是這一過程本身的最終產物。
實際上,夏博特是帶著對理論有效性的訴求來分析和審查既有公共利益觀點的,希望從這些觀點中尋找到一些能夠就公共利益與行政行為之間的關系作出某種具體假定,并且這些假定能夠用經驗證據進行驗證的理論。但是,夏博特的分析結果表明,現有對公共利益的研究并沒有形成一種內在一致且有效的理論。最終,夏博特不無遺憾地總結道,在現有的公共利益文獻中,“并不存在一個名副其實的公共利益理論,……它可能只不過是一個給某些時候的特定妥協任意貼上的一個標簽。無論如何,公共利益既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當前可用于分析政治行為的理論與方法”[注]Glendon Schubert. The Public Interest: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the Political Concept, 1960, p. 223.。夏博特對公共利益理論有效性的訴求與西蒙等實證主義者的要求本質上是一致的,正如薩里斯伯雷(Robert Salisbury)所評論的,也許夏博特對傳統公共利益理論(尤其是行政柏拉圖主主義者)有效性的評價標準并不恰當,因為他們的分析多少都帶有規范性的目的,都試圖尋找和確定行政人員在促進和實現公共利益過程中的實質性規范或準則,雖然這些規范和準則并不能提高他們所提議的決策過程的清晰性,但是尋求對這些決策過程的實證檢驗似乎就有些離題了[注]Robert Salisbury. The Public Interest: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a Political Concept by Glendon Schuber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1, Vol. 55(2), pp. 387-388.。夏博特對行政現實主義者尤其是過程理論家的態度最能體現薩里斯伯雷的評論,他雖然對三個類型都進行了批判,但明顯體現出對行政現實主義者中的過程理論家的偏愛[注]馬駿、葉娟麗著:《西方公共行政學理論前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125頁。。夏博特偏愛過程理論家的原因是因為能夠對過程理論家所假定的公共利益與行政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經驗驗證,也就是說可驗證性成為了某種行政行為或角色被接受的原因,這未免顯得有些本末倒置了。而且,過程理論家對行政機構及其人員行為和角色的假定并不比行政理性主義者的“機器人”更積極,最多也不過是正當過程的維持者而已。
總之,夏博特的分析性審查雖然向我們展示出傳統公共利益理念的三個基本類型,讓我們能夠看清在這三個類型中公共利益為行政人員所提供的不同身份角色。但他對公共利益理論的有效性要求和古典公共行政理論以及西蒙的實證主義行政科學一樣,都嚴重限制了我們關于公共利益的政治屬性和倫理維度的思考,消除了公共利益作為一種政治象征和價值載體對政治過程和行政行為所具有的規范性引導作用。同時,對公共利益理論之經驗有效性的要求大大簡化了公共行政及其人員在真實的治理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責任,限制了自主性和主動性的發揮。公共利益在古典公共行政理論、實證主義行政科學和夏博特批判的先后打擊下,在公共行政領域陷入了長期的沉寂,但隨著經濟社會環境變化所導致的政府信任危機以及由此產生的公共行政“重建運動”,公共利益重新被一些規范取向的重建者所發掘和重構,并成為他們表達對公共行政核心訴求的一個重要概念而得到熱烈討論。
三、公共利益理論的復興:基于規范性視角的思考與重構
實際上,實證主義行政科學和夏博特的公共利益理念很快引起了部分學者的回應,在他們看來,與其將公共利益視為一個等待被實現的具體目標,倒不如將其視為一個象征性或價值性的術語,去發掘它對具體的政治過程和官員行為所具有的功能性作用[注]參見Frank Sorauf. The Public Interest Reconsidered,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957, Vol. 19(4), pp. 616-639; Howard Smith. 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1960; Anthony Downs. The Public Interest: Its Meaning In A Democracy, Social Research, Vol. 29(1), 1962; Stephen Bailey, The Public Interest: Some Operational Dilemmas, In Carl Friedrich ed. The Public Interest, New York: Aetherton, 1962, pp. 98-106; Richard Flathman. The Public Interes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Normative Discourse of Politics, New York: Wiley, 1966.。但是,公共行政領域的回應卻顯得有些遲滯,其實這并不難理解,早期的回應者大都將公共利益放在民主的政治過程當中加以考察,強調公共利益的政治功能,即其對民主制度下的政治運行所具有的調節功能和催化效應。但對公共行政而言,正如斯皮策(Michael Spicer)所說,自從成為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研究領域開始,就始終存在著一種反政治(anti-politics)的傾向[注]Michael Spicer. In Defense of Politic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Value Pluralist Perspective.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0, p. 2.。公共行政一直被要求從政治中分離出來,作為以專業知識見長的工具,負責客觀中立地執行既定的法律或政策,行政人員即便沒有被視為理性主義者所假定的“機器人”,也并沒有被賦予相應的政治功能和道德責任。公共行政中的這種反政治傾向嚴重阻礙了學者們對公共利益政治和倫理維度的思考,因此,要想改變公共利益在公共行政領域的困境,不僅需要重新發掘公共利益的規范性內涵,更要走出工具理性和效率準則的狹隘視域,將政治重新帶入到行政中來,承認和恢復公共行政在治理過程中所扮演的合法角色,賦予行政人員以重要的政治使命和道德責任。美國20世紀60年代末期的經濟社會背景和學術困境正好為這一“政治的回歸”提供了契機,在本文引言所述的重建運動中,黑堡學派是思考和發掘公共利益的規范性內涵并試圖建構積極的行政角色的最為突出和最具代表性的努力。因此,我們的論述將主要以黑堡學派對公共利益的規范性思考與重構為主。
正如前文所述,黑堡學派對公共利益的考察是建立在重新界定公共行政角色基礎上的,它將公共行政視為國家統治的核心[注]楊炳霖:《“黑堡宣言” 于今日中國之意義———對建設公共行政規范理論的啟示》,《公共行政評論》2012年第6期,第130頁。,特別強調公共行政的政治屬性和倫理責任,重申了其在政治系統和治理體系中的合法角色,并將其目的指向了公共利益。黑堡學派認為對于追求公共利益而言,公共行政要比政治政黨、利益集團和大眾媒體等社會中的其他要素提供了更多的制度化的努力[注]Gary Wamseley, Charles Goodsell, John Rohr, Camila Stivers, O. C. White and James Wolf. Pubic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Process: Shifting the Political Dialogue, In Gary Wamseley, et al. eds. Refound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90, p. 41, 36.。可以說,黑堡學派所設定的公共行政角色既沒有行政柏拉圖主義者那么任意和精英化,也沒有行政理性主義者那么消極和中立化,它所承擔的是一種制度化的功能與角色。
(一)作為治理的公共行政與作為治理目的的公共利益
與古典公共行政理論、實證主義行政科學和夏博特不同,黑堡學派拒絕將公共行政僅僅視為執行政策或維持正當過程的中立性工具,而是將其視為現代政府的核心,是“治理和政治都無法擺脫的一部分”⑤Gary Wamseley, Charles Goodsell, John Rohr, Camila Stivers, O. C. White and James Wolf. Pubic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Process: Shifting the Political Dialogue, In Gary Wamseley, et al. eds. Refound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90, p. 41, 36.。因此,公共行政不能只聚焦于治理的工具或手段本身,還必須關注治理的一種超越性目的或價值承諾,簡言之,就是要關注公共利益[注]Gary Wamseley, et al., “Pubic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Process: Shifting the Political Dialogue,” In Gary Wamseley, et al. eds, p.49.。在追求公共利益的過程中,黑堡學派認為行政人員所扮演的絕不是西蒙所說的“行政人”或夏博特所偏好的“命運戰士”,而更像是亨利(Pendleton Herring)所說的“政治家的行政相對人”[注]轉引自Glendon Schubert. “The Public Interest” I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Theorem, Theosophy, or Theo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7, Vol. 51(2), pp. 346-368.。作為政治家的行政相對人,他們不僅承擔著有效執行政策的責任,還必須在憲政秩序中發揮平衡輪(balance wheel)的作用,以憲法價值和公共利益為準則,在三個權力分支以及眾多利益群體之間進行協調和抉擇,以避免政治運行陷入僵局。因此行政人員除了專業上的優勢之外,還必須具備某些政治才能和道德品質,與此相應地,應該賦予他們更大的自主性和更多自由裁量權,以便在具體的行政過程中更好地促進和實現公共利益。
此外,黑堡學派還以積極公民權(active citizenship)為核心在行政人員和公民之間建立起了一種全新的合作與伙伴關系[注]參見Camila Stivers. Active Citizenship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Gary Wamseley, et al. eds, pp. 246-273; Camila Stivers. Refusing to Get It Right: Citizenship, Difference, and the Refounding Project, In Gary Wamseley and James Wolf, eds. Refounding Democratic Public Administration: Modern Paradoxes, Postmodern Challenge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6, pp. 260-278.。行政人員不再只是價值無涉的政策執行者、“地動儀式”的公民需求回應者或理性中立的“倫理仲裁者”,而是要同時扮演“分析師”、“教育者”和“促進者”的角色[注]關于“地動儀式”的公民需求回應者,參見Gary Wamseley, et al. Pubic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Process: Shifting the Political Dialogue, In Gary Wamseley, et al. eds, 1990, p.48; 關于理性中立的“倫理仲裁者”,參見O. C. McSwite. Postmodernism, Public Administration,and the Public Interest, In Gary Wamseley and James Wolf, eds, 1996, p. 206, 218; 關于“分析師”、“教育者”和“促進者”的論述,參見Gary Wamseley, et al. Pubic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Process: Shifting the Political Dialogue, In Gary Wamseley, et al. eds, 1990, p. 48; Thomas Barth. Administering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Facilitative Role for Public Administrators, In Gary Wamseley, et al. eds, p. 174.。作為分析師,行政人員要利用自身的專業知識和工作經驗,通過批判性地利用其它學科知識分析和思考治理實踐中的重要問題;作為教育者,行政人員要幫助公民熟悉和理解治理所面臨的復雜問題及其挑戰,教會他們學會權衡和取舍;作為促進者,行政人員必須擴展治理過程中直接且真實的公民參與,重塑公民參與治理的過程,通過改善和提高公民之間以及公民與政府之間對話和互動的性質與質量,再造公民與政治之間的關系。在這種關系下,公民不再僅僅是服務的接受者或顧客,而是治理的參與者和自我需求的實現者,公共利益的內涵也不再由立法者、政治家或行政人員單獨確定,而是在行政人員的組織和促進下,在公民參與和對話的過程中所達成的某種東西。因此,在黑堡學派那里,公共利益既是公共行政的主要目的,也是指導行政行為的規范性基礎,同時還是行政人員與公民新型伙伴關系的紐帶。顯然,對公共利益的具體性、清晰性和經驗有效性的要求并不能滿足這種積極行政角色和民主化行政過程的要求,黑堡學派需要從規范性視角重構我們對公共利益的理解。
和公共行政的傳統主義者以及夏博特批判的早期回應者一樣,黑堡學派反對社會科學家長久以來將公共利益視為沒有意義的概念或“傲慢專制的工具”的觀點,強調公共利益對于行政人員的行為所具有的日常的、常識性的和實踐性的意義[注]Gary Wamseley, et al. Pubic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Process: Shifting the Political Dialogue, In Gary Wamseley, et al. eds, 1990, p. 40.。黑堡學派認為界定公共利益具體內容的嘗試不僅是困難的,甚至具有某種危害性,因為公共利益獲得合法性的關鍵不在于其客觀性或確定性,而在于與其具有利害關系的所有相關者是否都有機會共同參與對它的定義,而對確定性內容的追求顯然是由政策制定者或專家確定的,公民的任何參與性活動必然會受到限制。因此黑堡學派主張對公共利益的考察應轉向一種理想和過程(an ideal and process)的視角[注]② Gary Wamseley, et al. Pubic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Process: Shifting the Political Dialogue, In Gary Wamseley, et al. eds, 1990, p. 40, 40.。在這種理想和過程的視角下,公共利益被指向了一系列思維習慣的集合,這些集合包括:
嘗試處理一個問題的多個層面,而不是只考慮選定的幾個層面;尋求在審慎考慮中包含長遠視野,平衡過于關注短期結果的自然傾向;考慮受眾個體和群體競爭性的要求與需求而不是偏持某一個立場;具備更多的知識等。②
在這種理想和過程視角的基礎上,黑堡學派的主要成員古德塞爾(Charles Goodsell)和麥克斯懷特分別發展出了作為政治象征的公共利益和作為對話過程的公共利益兩種不同的觀點。
(二)作為政治象征的公共利益
古德塞爾對公共利益的考察承接了亨利的思想,即將公共行政視為一個合法的、具有平衡作用的、憲法化的治理制度,并將公共利益視為這一制度實踐的規范性基礎[注]Charles Goodsell,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In Gary Wamseley, et al. eds, p. 96, 103-111.。但與亨利不同的是,古德塞爾并不認為公共利益的概念是通過識別某些特定團體的利益而被給予實質性內容的,也不認為公共利益只能通過促進某些特殊利益才能實現,他將公共利益視為一種政治象征或制度力量,并且認為行政人員是公共利益的主要制度體現者和支持者。
根據庫珀和埃爾德(Roger Cobb and Charles Elder)對政治象征的界定與劃分[注]Roger Cobb and Charles Elder. The Political Uses of Symbolism,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1973, Vol. 1(3), pp. 306-338.,古德塞爾認為公共利益這一概念應屬于“體制”(polity)層面的政治象征,即和法定程序一樣,公共利益指定了一種公認的治理規則,并延續或灌輸著一種特定的價值。在此基礎上,古德塞爾總結了作為政治象征的公共利益在六個方面的構成性規則或價值,并且指明了行政及其人員在維護和實現這六個規則或價值上的優勢⑤Charles Goodsell,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In Gary Wamseley, et al. eds, p. 96, 103-111.:
其一,在合法性—道德性方面,對公共利益的追求要求公共官員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并且其行為要恪守正直和誠信等基本道德戒律。公共行政可以通過自身的職業化、對責任的要求、獲得和行使立法性授權以及告發政黨對權力的濫用等方式來促進政府中的合法性和道德性事業。其二,在政治回應性方面,公共利益要求政府的行為和施政目標要與公民或相關群體的期望相一致。由于公共行政人員自身的來源及構成,他們個人的政治觀點和價值偏好可能要比國會議員、法官和民選政治家更接近公眾,他們的政治回應性可能更為真實、具體且更具代表性。其三,就政治共識而言,公共利益的模糊性為不同的個體或群體擱置差異并達成共識提供了可能,而作為國家或政府行為的一部分,并且由于其行為所具有的公共性和普遍性,公共行政在表達和凝聚政治共識上具有更大的優勢,它能夠激發公民的一種共同體認知,進而促使他們去思考集體性或公共性的利益,而不是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其四,就關注邏輯而言,既然公共利益涉及到一系列社會目標的實現,那么,那些制定和落實這些社會目標的人有責任就社會目標的正當性、為實現目標而制定的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以及這些政策自身的合理性和連貫性作出解釋。公共行政可以通過運用政策分析的方法,或像法院用抗辯程序制度化原告和被告之間的爭論那樣制度化競爭性利益之間關于社會目標的爭論、提煉和達成,借此追求社會目標和公共政策的邏輯性。其五,就對效果的關注而言,關注公共利益意味著必須考慮政策效果的廣泛性和長遠性,而不只是著眼于對少數人的影響或短期的利益。與政府的其他機構相比,公共行政具有無與倫比的專業性、知識、信息和經驗,這使得它比任何其他機構都能更好考察公共政策效果的廣泛性和長遠性。最后,在議程意識方面,追求公共利益意味著要不斷尋找和發掘那些未被表達出來的利益以及那些不涉及個人利益但對整個社會而言十分重要的問題和需求。由于行政人員的管轄權依賴于政府功能的持續性,他們要比政治家更傾向于不斷地尋找社會中存在的問題并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尋找資源以解決這些問題,其結果就是一種尋找并回應那些未被代表的需求和未被解決的問題的制度得以產生。
古德塞爾所提出的公共利益的六個構成性規則或價值凸顯了行政人員一種強烈的政治屬性和功能,有力回擊了古典公共行政理論和實證取向的行政學者所提出的公共行政及其人員作為中立性工具或只為自己代言的政治行動者的假定。同時,古德塞爾還指出了公共利益的價值可以將我們的注意力轉向政府政策的公共對話過程,引導我們更好地將這些價值嵌入到行政過程中去。但在古德塞爾那里,公共行政及其人員始終居于這一行政過程的核心位置,多少有些麥克斯懷特所說的“理性仲裁者”的性質,在其中,我們既看不到實質性的公共對話,更找不到投身于對話與互動中的公民,古德塞爾的公共利益模型仍然沒有給公民留下多少參與的空間。同樣作為黑堡學派成員的麥克斯懷特則試圖從后現代主義視角為公共利益建構一種對話—過程理論,在這一視角中,我們才真正看到質性的公民參與和對話的可能性。
(三)作為對話過程的公共利益
麥克斯懷特同樣將公共利益視為公共行政領域中的主要象征,認為“其巨大的吸引力和修辭力量為行政事業提供了基礎,發揮著衡量恰當行動的試金石的作用”[注]O. C. McSwite. Postmodernism,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In Gary Wamseley and James Wolf, eds, 1996, p. 199, 217, 217, 219, 200.。但麥克斯懷特是從后現代主義的認知視角來思考公共利益的,他反對現代性視角下對一種適用于所有情境的、整體性的真理與善的信奉與追求。正如麥克斯懷特所說,一旦我們將我們的制度標向真理與善,任何團體和派別都會認為自身版本的真理與善就是整體的真理與善,或試圖將其自身表述為至少是這一整體真理與善的最佳近似②O. C. McSwite. Postmodernism,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In Gary Wamseley and James Wolf, eds, 1996, p. 199, 217, 217, 219, 200.。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對話都變成了將自己理解的真理與善上升為最高的或整體性的真理與善的意識形態爭論。根據這種理解,行政人員自然也具有這種致力于實現自身版本的真理與善的傾向。但另一方面,為了應對這種意識形態的沖突,行政人員又必須擔任理性的“倫理仲裁者”的身份,“這個仲裁者處于制度的核心位置,他能夠審查意識形態爭論,并通過客觀且深思熟慮地判斷對其加以處理”③O. C. McSwite. Postmodernism,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In Gary Wamseley and James Wolf, eds, 1996, p. 199, 217, 217, 219, 200.。而作為仲裁者的行政人員仲裁意識形態爭論的指導原則是什么呢?麥克斯懷特認為只能是公共利益。于是,公共利益往往就變成了行政人員自身所認為的真理或善,甚至變成了維持他們自身地位的道德說辭,而公共利益的真正來源及受眾——公民,變得沉默且缺席了。因此,基于現代性視角所闡發的公共利益理念,即便是古德塞爾式的公共利益模型,也不能被視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基礎。于是,麥克斯懷特將視角轉向了后現代主義,認為后現代主義情境為恢復一個有活力的公共利益理念以及清晰界定公共行政在治理結構和治理過程中的角色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
后現代主義拒絕承認存在著整體性的真理與善,認為所有團體和派別所持有的都只不過是多樣化、局部性和暫時的真理與善。因此,沒有任何一個團體或派別能夠將自身版本的真理與善標榜為最高的或整體性的真理與善,他們各自所持的真理與善必須通過以真正溝通為基礎的一系列對話過程并且以試探性的模式被凝聚到一起④O. C. McSwite. Postmodernism,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In Gary Wamseley and James Wolf, eds, 1996, p. 199, 217, 217, 219, 200.。在這一過程中,對話不再是競爭性的意識形態爭論,而是所有公民都參與其中、以合作為基礎的試探性和重復性活動。對話的結果也不再是由理性的仲裁者依據他所理解的真理與善所做出的最終裁定,而是一種包容性或復合性的意義表達與呈現。依據這樣一種后現代主義視角,麥克斯懷特尋求建立一種非常具體的治理路徑,在其中,公共行政被置于更為廣闊的治理情境和更具權威授權的制度背景當中,并且服務于那些通過對話過程而圍繞在它周圍的公民⑤O. C. McSwite. Postmodernism,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In Gary Wamseley and James Wolf, eds, 1996, p. 199, 217, 217, 219, 200.。在這種治理情境和制度背景中,行政人員所扮演的不是公共利益的持有者或界定者,更不是眾多競爭性利益之間的理性仲裁者,而是公共利益于其中得以呈現并最終實現的對話過程的組織者、維持者和促進者。公共利益也不再是超驗性的規則或價值,而是能夠促進公民參與和互動、產生共識和意義的對話過程本身。由此,行政人員遵循的不再是一種他自身所理解的公共利益,而是一種經驗性原則,這一原則以促進和維持參與、互動與對話為目的,行政人員將被導向對話過程的每一個具體時刻,去思考參與者將要說些什么和做些什么,進而對對話過程進行引導和調整。麥克斯懷特的這一設想使得公民的實質性參與和對話成為可能,與此同時,公共行政在治理過程中的合法性基礎不再是追求超驗性的真理與善的倫理仲裁者身份,而是追求有效的、可持續的對話過程的組織者和促進者角色,“英雄將不復存在,但治理過程將獲得它從未有過的事實上的合法性”[注]O. C. McSwite. Postmodernism,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In Gary Wamseley and James Wolf, eds, p. 222, 200.。
麥克斯懷特之所以發展公共利益的對話過程理念,其目的是要借助后現代主義的認知視角把過程導向的社群主義路徑引入到治理中來,以削弱現代性視角所推崇的理性化、中立性的治理路徑。現代性視角下的這種治理路徑以超驗性規則和價值為指導,推崇治理的技術主義,試圖尋求社會問題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在這種路徑下,“一旦社會問題上升到失控的地步,政治壓力將會選擇執行一種技術性的、確定的、有效的、機械的和強制性的解決方案”②O. C. McSwite. Postmodernism,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In Gary Wamseley and James Wolf, eds, p. 222, 200.。很明顯,這是一種封閉性的治理路徑,治理的主體由政治家、專業行政人員和技術專家構成,公民被排除在具體的治理過程之外。而社群主義的治理路徑則是一種開放性的治理路徑,包括公民在內的所有相關者都被納入到具體的治理過程中來,他們的關系不是服從關系和競爭關系,也不是簡單的聚集起來各說各話,而是在平等對話的基礎上相互合作,加深理解,就治理問題達成共識,公民在其中獲得了一種真實的存在感和意義感。在這種開放性的治理路徑中,公共利益不再是外在于治理過程的、先驗的東西,而是治理本身所呈現出來并最終達成的東西。
(四)黑堡學派之后關于公共利益的規范性思考
黑堡學派對公共利益的思考與重構打破了長期以來公共利益在公共行政領域被邊緣化的局面,對古典公共行政理論和實證主義行政科學的理念發揮了重要的修正性作用。更為重要的是,黑堡學派對公共利益的規范性思考與重構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和扭轉了關于公共行政的性質與角色的假定,正如焦斯(Philip Jos)所指出的,對公共利益的考察已經動搖了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公共行政學所試圖為行政責任所提供的可行依據[注]Philip Jos.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y Revisited: Moral Consensus and Moral Autonomy,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1990, Vol. 22(2), pp. 228-248.。繼黑堡學派之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公共利益的視角出發思考公共行政的責任和角色,他們同黑堡學派一樣從規范性的視角建構公共利益的內涵和價值,進而為更加積極的行政角色和更為廣泛的行政責任提供新的規范性基礎和行動準則。在這些學者中,一部分人沿著古德塞爾的進路,秉持公共利益作為政治象征的觀點,不斷豐富和發展其政治屬性和價值內涵,在此基礎上,他們主張賦予公共行政及其人員更多的自由裁量權,以在促進和實現這些屬性和價值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注]參見Norton Long. Conceptual Notes on The Public Interest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1990, Vol. 22(2), pp.170-181; Carol Lewis, In Pursuit of the Public Interes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6, Vol. 66(5), pp.694-701; Janet Denhardt and Robert Denhardt. The New Public Service: Serving, not Steering(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M.E. Sharpe, 2007, pp. 65-82.。另外一些學者則同麥克斯懷特一樣,從后現代主義的視角考察公共利益,他們特別強調公共利益的構成性和復合性特征。構成性特征是指尋找和發現公共利益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它在不斷的對話、互動和表達中體現出來,而不是通過一次性的活動賦予其確定不變的內容;復合性特征是指對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是選擇性或排斥性的,而是包容性或整合性的,它是所有已經表達出來和未表達出來的利益的最終合成物。這種思路需要一個持續的、包括所有相關者在內的對話和互動過程,因此公共行政及其人員就肩負起了麥克斯懷特所強調的對話過程的組織者和促進者的角色[注]Gary Marshall and Enamul Choudhury.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Re-Presenting a Lost Concep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97, Vol. 41(1), pp. 119-131.。
總之,以黑堡學派為代表的公共利益的規范性觀點,無論是就公共利益的內涵而言,還是就公共行政在促進和實現公共利益中扮演的角色而言,都與古典公共行政理論和實證主義行政科學迥然不同。尤其是它們借此所闡發的公共行政在治理過程中的積極角色和廣泛責任,更是與古典公共行政理論和實證主義行政科學的觀點截然對立。雖然從傳統主義者到新公共行政的一些理論家均致力于扭轉和修正古典公共行政理論和實證主義行政科學的工具理性和效率準則傾向,但他們都沒有認真對待公共利益。傳統主義者最多只是強調了公共利益的功能性作用,沒有深入發掘和建構它的規范性內涵。以弗雷德里克森(H. George Frederickson)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則更偏好于將社會公平而不是公共利益作為公共行政理論與實踐的價值基礎和倫理要求,將其列為公共行政的三大支柱(效率、經濟與公平)之一[注]參見H. George Fredericks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Social Equit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90, Vol. 50(2), pp. 228-237; H. George Frederickson. Social Equit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Origins, Development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and London: M.E. Sharpe, 2010.。只有黑堡學派明確提出將公共利益視為公共行政的一個規范性基礎或行動準則,致力于發掘和建構它的規范性內涵,并借此表達他們對一種新型公共行政范式的核心訴求,這一范式呼喚著在治理過程中一個身份更加多樣化、更具開放性、更為積極主動且更具政治和倫理責任的公共行政的出現。
四、公共利益規范性理論的內在張力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對公共利益的認知、思考和處理方式,以及就公共行政在促進和實現公共利益過程中的角色所形成的兩種對立性觀點鮮明地體現了存在于公共行政領域中的一種持續的內在張力,這種張力主要表現為民主與權威、價值與效率這兩組概念之間的沖突。顯然,對不同價值的側重是造成他們對公共利益的認知和對公共行政角色的假定存在明顯差別的主要原因。古典公共行政理論和實證主義行政科學青睞一種在價值上保持中立、在功能上較為消極的工具性公共行政,這導致他們對理性化行政行為、操作化政策目標以及經驗性行政過程的追求,于是公共行政被建構為一種以技術主義為基礎、拒絕公民參與的理性行政范式。在這種行政范式下,公共利益因其概念上的非經驗性和非操作化而無益于指導實踐中的行政行為,也無益于增加有關行政實踐的科學性知識,甚至還會因其虛假的客觀性而合法化行政機構及其人員的個人偏好而有損于既定政策的初衷,因此被視為無用甚至有害的概念而遭到邊緣化。
規范理論家們則更偏好在政治上有所回應、在價值上有所擔當并且致力于促進和實現公民參與的公共行政,他們所建構的是一種更具政治屬性、更強調開放性和參與性的民主行政范式。因此,一方面他們希望賦予行政人員更多的自主性和自由裁量權,使其能夠在治理過程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但自主性的發揮和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并非不受限制,而是必須遵循一定的價值規范和倫理規則。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公共利益重新進入他們的視野并被視為指導行政行為的規范性基礎或行動準則,從而得到新的理解和重構。另一方面,他們又致力于將公民帶入到治理過程中來,要求行政人員組織和促進持續有效的公民參與,通過真正的對話與合作來表達和實現公共利益。可以說,黑堡學派對公共行政與公共利益的規范性思考較為有效地回應了這兩個方面的要求,古德塞爾所提出的公共利益的六個構成性規則和價值迎合了第一個方面的需要,麥克斯懷特基于后現代主義視角所闡發的公共利益理念則回應了第二個方面的訴求。
但是,恰恰是以上兩個方面的規范性訴求,鮮明地體現出了權威與民主之間的內在張力。一方面,對行政人員積極角色的強調即便沒有那么強烈的行政哲學王色彩,但也明顯具有柏拉圖式“監護人階級(guardian class)”的身份特征,黑堡學派甚至要求公共行政人員扮演一種“賢明的少數(judicious few)”的角色[注]對公共行政“監護人階層”角色的闡述,參見Charles Fox and Clarke Cochren. Discretionary Public Administration: Toward A Platonic Guardian Class, In Henry Kass and Bayard Catron, Eds. Images and Identitie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0, pp. 87-112; 對公共行政“賢明的少數”角色的闡述,參見Gary Wamseley, et al. Pubic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Process: Shifting the Political Dialogue, In Gary Wamseley, et al. eds, 1990, p. 48.。作為“監護人”或“賢明的少數”,行政人員不僅在專業知識和治理經驗方面優于被監護的普通公民,而且在對公共利益的感知和理解上也要高于普通公民,因此在實際的治理過程中行政人員扮演著更具權威性的角色,掌控和主導著一切,而公民則顯得十分被動和順從。于是,公共利益變成了公共行政治理權威的合法性基石,公共利益對行政人員的規范和指導仍然沒有走出夏博特所批評的“要聰明、要明智、要良善”等道德勸誡。在這種情況下,實質性的公民參與仍然難以實現,行政人員仍習慣于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治理經驗和對公共利益的自我理解來合成公民的訴求并對其進行回應。另一方面,麥克斯懷特基于后現代主義視角所闡發的公共利益理念和社群主義的治理路徑體現出對實質性民主的強烈要求。這種社群主義的治理路徑確實能夠將公民帶入到治理過程中來,產生真實的參與、對話與合作,但它是建立在拒絕公共行政的治理權威基礎上的。在對話過程中,行政人員既不是公民的“監護人”,也不是“倫理仲裁者”或“賢明的少數”,他們只是民主化治理過程的組織者、促進者和維持者,與公民一道通過試驗性和重復性的對話過程來促進理解、達成共識。兩者之間的內在緊張絲毫不弱于它們與古典公共行政理論和實證主義行政科學之間的分歧。
實際上,黑堡學派關于公共行政與公共利益的觀點在民主與權威之間的內在緊張體現出的是麥克斯懷特所說的“新規范主義”和“話語運動”之間的張力[注]O. C. McSwite. The New Normativism and the Discourse Movement: A Meditation, Administrative Theory & Praxis, 1998, Vol. 20(3), pp. 377-381.。新規范主義力圖為行政權威的行使尋找合法性基礎,因此堅持要在機構(institution)的具體實踐中來表達和實現公共利益,雖然它也強調參與和對話,但這種參與和對話要么是按機構本身而設定,要么被植根于機構背景當中。話語運動質疑和反對權威,致力于創造一個開放的治理空間,在其中,人們能夠就公共利益進行正確的和真實的對話并達成共識。麥克斯懷特認為,新規范主義和話語運動彼此不能合并,但他仍然希望新規范主義在開放性和民主化方面更進一步,加入到話語運動的行列,因為“畢竟,它們面臨著共同的敵人,即一個沒有價值和話語的技術主義的未來”③O. C. McSwite. The New Normativism and the Discourse Movement: A Meditation, Administrative Theory & Praxis, 1998, Vol. 20(3), pp. 377-381.。
遺憾的是,繼黑堡學派之后關于公共利益的規范性思考并沒有像麥克斯懷特所期望的那樣就兩者之間的張力給出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案,他們或者偏向于民主化或社群主義式的治理路徑,發展公共利益的對話—過程觀點,或者偏向于自由裁量主義或柏拉圖式行政監護人那樣的權威治理路徑,強調公共利益的政治功能和倫理導向。或許我們本就不應該致力于消除這一內在的緊張狀態,正如摩根(Douglas Morgan)所說的那樣,恰恰是公共行政中一直存在的批判性張力,才能使一個兼顧政府能力、人民主權和少數人權利的“治理的憲政體系”得以維持和運轉。它既允許公共行政人員參與到公共利益的界定和塑造中來,同時又能夠適時運用民主的要素對其加以限制和引導,從而確保既不讓政府權威過分強大,同時也不會讓其過于軟弱和無能[注]Douglas Morgan. The Public Interest, In Terry Cooper, ed. Handbook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Expanded), New York: Marcel Dekker, 2001, pp. 151-178.。只有這樣,我們才不至于偏向任何一個極端,從而既能擺脫因政府的無能而陷入混亂與失序,又能免于過度的政府權威對自由和民主等規范價值造成損害。公共利益恰恰就是這一內在張力的一個焦點,同時也是這一內在張力在動態的過程中能夠取得平衡并得以維持的一個支點。
(感謝暨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顏昌武副教授對本文修改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