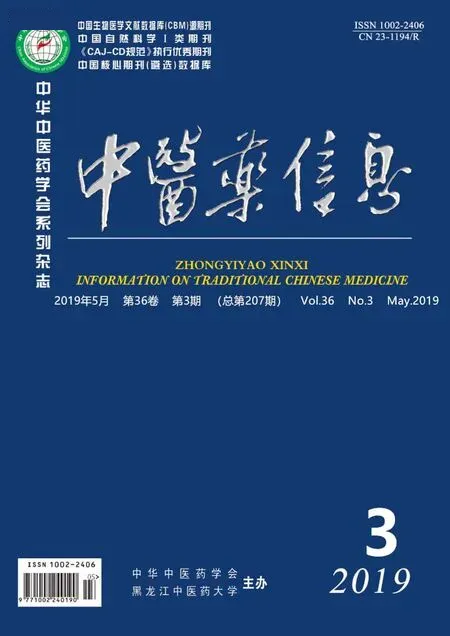原發性肝癌生物標志物與中醫微觀辨證學創新和發展
馮文杏,周小舟,張衛,韓志毅,孫新鋒,馬文峰
(廣州中醫藥大學第四臨床醫學院,廣東 深圳 518033)
原發性肝癌是危及人們生命健康的一大問題,常見的是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發病率占90%[1],其次是肝內膽管細胞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HCC是世界第六大常見惡性腫瘤和第四位癌癥相關死亡原因[2]。我國每年因HCC死亡的人數約38.3萬人,占全球HCC死亡人數的51%[3]。病毒性肝炎、脂肪性肝炎、過度飲酒、黃曲霉素等均與肝癌的發生相關,所以腫瘤發展過程中存在各種病原因素、腫瘤異質性等,宏觀和微觀存在一定差異。HCC起病隱匿,很多患者診斷時已是晚期,僅1/3的新確診患者適合于治愈性治療,故預后較差。
隨著技術的進步和對HCC生物學的理解增加,不斷有新的標志物被發現。提高對血清和組織標志物的認識可以對這一致死性疾病的早期診斷和早期的診療策略產生積極的影響。由于其非侵入性、目的性及能反復評估的潛力,血清標志物可以成為更有潛力監測和早期診斷HCC的工具,到目前為止,許多生物標志物已被推薦用于HCC診斷。中醫藥對HCC的治療具有較好的療效,但目前現代醫學和中醫藥都尚未發現有效的藥物作用靶標。運用宏觀辨證思維雖可洞察病機,但由于不同病原因素對HCC的致病影響不同,可導致臨床癥狀表現不同、治療效果不盡相同,顯示異質性,即存在微觀差異。
1 HCC診斷、預后和預測的組織標志物
內皮細胞標志CD34和抗平滑肌抗體(SMA)陽性,提示廣泛的新血管化過程和肝竇毛細血管化。三種特異性免疫標志物過度表達(Glypican-3,GPC3;HSP70;Glutamine synthetase-GS)已被認為是小的和早期HCC選擇性標志物[4]。P21激活酶5(PAK5)可能成為HCC有利的診斷/預后標志[5]。內皮細胞特異性標志如CD31、CD34或von Willebrand因子有顯著的預后潛能;血管生長因子(VEGF)和其他調節因子高表達與總體生存率(OS)、自由生存復發和切除后早期復發相關;上皮細胞間質化(EMT),可獲得不受限制的運動性和遠處轉移的潛力[6];60%HCC p53基因失去活性[7];選擇性抑制VEGF途經已集中于HCC分子治療領域的靶向研究,尤其是索拉菲尼,一種持續的Raf/Map酶抑制劑。
2 HCC血清標志物及基因組學時代
因低敏感性和低的特異性,對甲胎蛋白(AFP)作為監測性的檢測指標已漸漸引起爭議。日本的研究結果提示,在AFP水平低和US無可疑發現時,甲胎蛋白異質體-3(AFP-L3)升高是HCC形成的早期預測因子;AFP-L3%陽性的患者能更早形成血管侵犯和肝內轉移,AFP-L3%被考慮作為HCC侵襲性標志[8];異常凝血酶原(Des-r-Carboxy Prothrombin,DCP)參與腫瘤血管形成,增加血管生成因子如VEGF-R、VEGF和MMP-2基因表達,Meta分析提示DCP在HCC中有中等的準確性[9];研究顯示,在VEGF中單個核苷酸多態性(SNPs)是HCC切除患者生存預測因子[10];p53基因突變在HCC早期無變化,主要在HCC晚期血管形成時才有變化,這就限制了其在診斷中的作用。TGF-b1 mRNA血清水平在HCC患者中升高,并且與肝癌形成和腫瘤血管形成相關;miRNA在HCC細胞中不同的表達提示其在預測HCC預后的潛在價值。本課題組建立了X基因陽性與陰性的HepG2細胞,用 ELISAs法對深圳和美國韓國移民HBV未感染者、HBV和HCV相關的慢性肝病及HCC患者進行癌相關抗體研究。發現,抗URG11和URG19多見于HBV相關HCC患者中,而抗URG7,DRG2多見于HBV相關沒有發生HCC患者中;另外,在發生HCC之前有4個或更多抗體被檢測出[11-13]。
應用高通量測序技術尋找肝癌新的標記物的研究層出不窮。DNA異常甲基化在肝癌細胞中被發現,Zhang等[14]利用焦磷酸測序技術發現在肝癌腫瘤細胞中平均甲基化水平要比癌旁細胞更低;Wu等[15]認為白細胞中整體DNA甲基化水平可以作為肝癌風險診斷標記物;另外在肝癌患者游離的DNA中也發現了高度甲基化CpG島[16]。在轉錄物組水平上通過深度測序發現一種新的帶有編碼區域的基因DUNQU1,在HCV呈陽性中特異性表達,而且FGFR2的可變剪接與病毒感染、腫瘤大小和復發等相關[17];研究發現HBV相關HCC患者甲基化前五的DNA是DAB2IP、BMP4、ZFP41、SPDY1和CDKN2A,去甲基化的前五個DNA是CCL20、ATK3、SCGB1D1、WFDC6和PAX4[18]。
MicroRNA(miRNA)可調節細胞增殖、分化、凋亡等。已經發現mRNA異常增殖表達與肝癌的發生發展有關,最有可能成為HCC早期診斷的標志物[19-20];Hou等[21]通過對肝癌miRNA組的分析發現,miR-199a/b-3p在肝癌中顯著下調;Law等[22]對肝癌miRNA轉錄物組進行研究揭示了miR-1323在肝癌中的高表達;在關于HBV相關HCC患者的隊列研究中發現,女性的miR-26a和miR-26b表達高于男性,miR-26a和miR-26b低表達與短期生存相關。另外一些研究認為長鏈非編碼RNAs(long noncoding RNAs,lncRNAs)對HCC診斷和預后是一種新的標志物;具有調節蛋白、RNA活性、轉錄、蛋白轉運和細胞代謝的作用,眾多研究證明了lncRNAs在HCC的形成、發展和預后作用[23-25]。
3 肝癌微觀辨證學研究及HCC氣血辨證創新和發展
微觀辨證學崛起于20世紀80年代,是一門介乎基礎與臨床學科之間主體學科[26],秉持“司外揣內”的中醫思想,認為疾病的證候是在一定病因刺激下發生發展而成,其中的病因刺激一方面可以理解為傳統的風、寒、暑、濕、燥、火等邪氣或病理產物,亦可以更深入細化到神經、免疫、代謝等環節,微觀辨證即從這個角度觸發,意在探尋宏觀證候下的微觀規律,打破了傳統辨證的思維局限。肝癌的發生是一個復雜過程,是多環節、多因素的,運用多學科交叉,能為肝癌辨證分型提供生物學依據[27]。費鳳英等[28]發現TM三項聯檢聯,即AFP、AFP-L3和 α-L-巖藻糖苷酶(AFU),可提高AFP陰性肝癌診斷率,或對肝癌辨證診斷有價值;張紅等[29]發現肝癌不同證型中AFP、CEA存在差異;黃爭榮等[30]應用SEIDI-T0F-MS篩選出2個可鑒別肝郁氣滯型與肝膽濕熱型肝癌患者的差異蛋白質;李夢萍等[31]研究發現,不同證型肝癌患者肝組織某些miRNA水平有差異,其中miR-122-3P明顯高于正常組,氣虛血瘀組最明顯。這些研究對肝癌的辨證診斷從傳統的象、證等深入到血清標志物、蛋白質水平甚至基因表達層次,是中醫宏觀與微觀聯系的探索,亦是嘗試對難以把握的宏觀辨證一個客觀量化。
氣血辨證是中醫辨證的方法之一,在臟腑經絡學說的基礎上,從氣血的角度分析疾病證候。“善言氣者,必彰于物”“氣”與“物”是相互維系的,微小物質的變化或可反映氣血的變化,揭示規律,在這一想法啟示下,導師周小舟教授首創了HCC氣血微觀辨證學。自90年代以來,導師運用中醫、中西醫結合研究對HCC氣血微觀辨證診斷和治療進行了一系列探索,初步發現不同證型之間存在血清腫瘤標志物等微觀差異。研究比較69例氣虛血瘀證和74例氣滯血瘀證HCC患者病原因素、臨床表現和病理類型發現:年齡小于50歲患者占比、疼痛癥狀、病理分型為彌漫型和巨塊型肝癌及AFP 20~200 ng/mL陽性率,后者明顯高于前者;吸煙、HBsAg陽性占比,伴有肝硬化、病理類型為單個小結節型、TNM分期IV 期及AFP>400 ng/mL陽性率,前者明顯高于后者。研究結果提示:年齡、吸煙、HBsAg陽性、肝硬化、病理類型等因素可能是形成不同證型的微觀基礎[32];采用抗癌方聯合TACE治療64例氣虛血瘀型原發性肝癌患者臨床顯示,患者的血清AFP水平改善、1年生存率、中醫臨床證候改善等均高于對照組[33]。此外,導師也探索了金屬離子、免疫細胞等與肝癌證型之間的關系[34-36]。中醫經典的辨證論治以宏觀的象為把握點,這一系列對微觀的研究將推進對不同疾病證候發生發展的規律的了解,是對宏觀“氣血辨證”的補充。
4 結語
腫瘤異質性在HCC中是廣泛存在的,有復雜的基因突變背景。對血清和組織標志物的探索和研究最終將導致這一致死性疾病的早期診斷和較好的早期治病策略。經典的病理學和特征指標僅僅部分能夠檢測個體腫瘤的臨床行為(特征),新的分子檢測和方法將不得不加入到以形態學為基礎的診斷過程中。在科學發展的契機下,多學科交叉有利于與對這一疾病的早期診斷、預防和預后預測,這種綜合模式與中醫辨證論治思想在某些方面有相同之處,或可為中醫對疾病整體觀與微觀辨證之間的關系架起研究的橋梁,從而發展建立客觀可行的中醫辨證模式,亦是中醫傳承和創新發展的重要手段。為中醫診斷體系的建立、特別是為未來HCC中醫藥定靶治療帶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