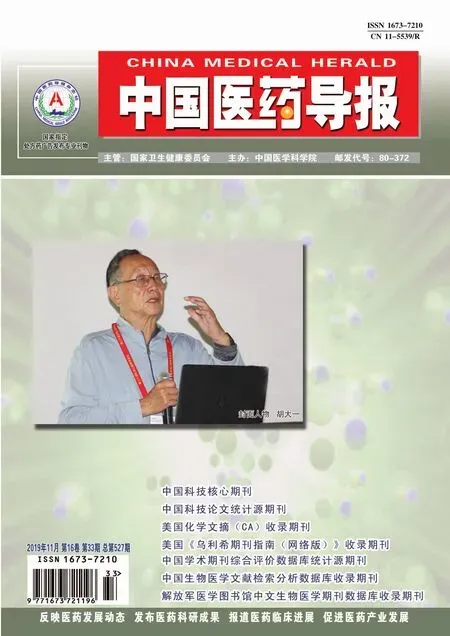王居易經絡診察治療經筋病的臨證經驗
孟笑男 于海闊 孫 潔 李春穎
1.北京中醫(yī)藥大學附屬護國寺中醫(yī)醫(yī)院針灸科,北京 100035;2.首都醫(yī)科大學宣武醫(yī)院康復科,北京 100053;3.北京小湯山醫(yī)院中西醫(yī)結合康復科,北京 102211
經筋作為經絡系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十二經脈循行分布的筋肉相連,分為十二部經筋,具有維系周身、聯絡百骸、司運關節(jié)之功。在《說文解字》,將“筋”解釋為“肉之力也”,應屬于肌肉、肌腱、筋膜、韌帶等軟組織范疇[1]。而經筋病主要是在經筋分布之處出現的筋肉攣急、疼痛、弛緩不用、強直等癥[2]。目前在臨床中治療經筋病的原則尚無系統(tǒng)體系而言,主要治療原則受到“以痛為俞”的影響,其源自《靈樞·經筋》,即“治在燔針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俞”,孫思邈命名為阿是穴,或者稱之為“痛點”,醫(yī)者直接在痛處針刺或手法,亦可取得一定臨床療效[3-8]。而王居易教授認為,“以痛為俞”只是針灸臨床一種具體的操作方法,本身并無錯誤,然而治療經筋病還需系統(tǒng)地以經絡診察為基礎,以經絡辨證為主體[9]。
1 察辨經絡,“原合”配穴
經絡診察是王居易教授從《內經》中提煉升華所創(chuàng)立的一套屬于中國古代傳統(tǒng)醫(yī)學的物理診斷方法[9]。《靈樞·刺節(jié)真邪論》中提到“用針者,必先察其經絡之實虛”。關于具體的操作方式它提出幾種方法,《靈樞·經水》“審、切、循、捫、按,視其寒溫盛衰而調之,是謂因適而為之真也”。因此經絡診察可總結成五種方法,分別為審、切、循、按、捫:醫(yī)者需要首先審視經脈循行部位(審),用其手觸摸經絡(切),循推經絡循行之縫隙(循),按壓(按)和彈撥分肉之間,通過其指下的感覺(捫),察看經絡有無異常變化[10]。經絡內聯臟腑,外絡肢節(jié),因此疾患都可在與之相對應的經絡上出現異常表現,通過人體的體表來認識經絡,來探查疾病。外在經絡狀態(tài)是內在氣血注于外的重要體現,通過經絡的變動從而知曉內在臟腑異常,此為察外而知內也。實際上這五種方法在中醫(yī)望聞問切中均涉及一部分,而最大的區(qū)別在于經絡診察主要是從經絡的角度來進行。
王居易教授認為十二經筋與其對應經脈并行,并靠經絡氣血濡養(yǎng),雖不直接入絡臟腑,但其若發(fā)生異常變化,亦會影響對應經絡狀態(tài),在經筋及對應經絡出現異常改變;除了跌打外傷所致的經筋病外,大部分與其相對應的經絡以及經絡聯系的臟腑都有密切關系。因此在臨床治療時,要通過經筋病具體部位,首先辨別其對應經絡,然后沿其所屬經絡循行進行經絡診察,有可能會發(fā)現經絡狀態(tài)的異常變化,多以局部細小結節(jié),結絡及脆絡,或者某一段循行部位壓痛為著[11]。經筋病多以筋肉攣急疼痛、或弛緩不用、或強直等癥為著,為病后必對其經絡氣血運行產生阻滯作用,因此王居易教授在臨床中,除了局部取穴之外,更加注重對所屬經絡對應的合穴及原穴選取作為經絡辨證思路取穴。
五俞穴中之合穴,所主“逆氣而泄”,王居易教授理解,“氣”范指本經的氣機,“逆”則為發(fā)生變動而所生逆亂,“泄”既意為瀉實,又可理解為調整逆亂之氣機;經筋病有礙本經氣血之正常循行,所致逆亂可取合穴來調整;王居易教授認為陰經和陽經原穴在治療時作用不同:陰經原穴偏于補益本經氣血之功,而陽經原穴偏于行氣活血之效[12];而對于經筋病如若新病,取對應陽經原穴,加強行氣血,祛淤滯之功;對于久病氣血耗傷,則可選用對應陰經原穴補益氣血之不足;《素問·五藏生成篇》:“諸筋者,皆屬于節(jié)。”節(jié)為關節(jié)活動之處,人體的正常運動有賴經筋、關節(jié)的完整性及正常的功能作用,合穴與原穴所分布位置,大多位于肘膝及腕踝關節(jié)附近,這與經筋的分布節(jié)點存在重合:全身筋肉眾多,按十二經脈循行分布可劃分為手、足三陰三陽,共十二部經筋;每部經筋皆始于四肢末端,上行頭面胸腹部,在循行過程中,遇骨節(jié)部位則數筋結于此而成“聚”,而合、原之部,恰為經筋集聚之所,因為選用此穴,在治療中也起到了提綱挈領之意[13]。因此,王居易教授在選取本經穴位時,多會原穴與合穴同取,起到標本兼治,氣血同求之意。
2 “五節(jié)”理論,層次治療
古代中醫(yī)經典中認為人體分為以下五種組織:皮、肉、脈、筋、骨。《靈樞·經脈第十》:“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骨為干,脈為營,筋為剛,肉為墻,皮膚堅而毛發(fā)長。谷入于胃,脈道以通,血氣乃行。”王居易教授將其稱之為“五節(jié)”。“五節(jié)”存在大小、粗細、寬窄之分。古人說的不同部位有不同形狀即為“節(jié)”,皮有皮節(jié),脈有脈節(jié),肉有肉節(jié)、筋有筋節(jié)、骨有骨節(jié)。
“諸筋者,皆屬于節(jié)”(《素問·五臟生成論》)。然而對于經筋病,首先要正確理解“筋”的概念。王居易教授認為,從現代解剖學的角度來看,筋的實質應為筋膜、韌帶[14],亦或神經、肌肉[15],或是兼而有之[16],這是現代醫(yī)學對“筋”的廣義認識。這其實與祖國傳統(tǒng)醫(yī)學對于“筋”的理論范疇不謀而合。而“五節(jié)”中提到的“筋”只是狹義范疇,是一個具體的概念,而從廣義來講“筋”應該分屬于“五節(jié)”所對應的任何一節(jié)或者幾節(jié),即凡是依附關節(jié)系統(tǒng)、維持關節(jié)穩(wěn)定、協(xié)助運動者皆可以稱之以“筋”,這個筋可以是包被著筋膜的肌肉,可以是肌腱,當然也可以是韌帶、關節(jié)囊、椎間盤[17]。《靈樞·經筋》中關于十二經筋進行了詳細描述:“足太陽之筋,起于足小指,上結于踝,斜上結于膝……”,這說明經筋作為一個聯絡肢節(jié)、維系周身的連續(xù)性系統(tǒng),具有系統(tǒng)分布性和完整分布性的特點。又如《針灸甲乙經》記載“陽溪者……在腕中上側兩筋間陷者中”“天柱……大筋外廉陷者中”,陽溪穴之兩筋則為拇短伸肌腱與拇長伸肌腱;天柱穴之所臨“大筋”則相當于豎脊肌、肩胛提肌、斜方肌等肌肉組成[17]。因此“五節(jié)”中皮、脈、肉、筋、骨的概念,王居易教授認為此乃筋經病病位的具體描述,而非特指某一個組織結構,由皮至骨,其層次逐漸加深。《素問·痹論》有云“痹在于骨則重,在于脈則血凝而不流,在于筋則屈不伸,在于肉則不仁,在于皮則寒”;《靈樞·九針十二原》中就精辟地概括為“皮肉筋脈,各有所處,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
因此,王居易教授在治療經筋病時,注重使用“五節(jié)”來定位經筋病的病位。而病位的確定則是需要靠經絡診察來確定經絡異常出現的位置,如果壓痛,結節(jié)、結絡等異常出現皮脈肉筋骨不同深度層次,則針刺時則要刺至相應的層次,切不可過之或不及[18-20],正如《靈樞·終始》描述到:“在骨守骨,在筋守筋”。
3 注重針刺、手法結合
王居易教授在臨床上治療筋經病的手法思路,主要受到《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之影響,在臨床應用中將其精煉為“割皮解肌”“揲法”“結筋法”“解肌法”和“訣脈法”,且王居易教授提倡若條件允許可在針刺后,即刻進行局部手法治療,針對患處氣血形成最直接有效的調整恢復,逐步形成了筋經病治療中針刺和手法并用的特色。
“割皮法”在古文中,指割開解剖局部肌肉,而在臨床中,王居易教授并不是真正將局部皮肉切開,而是用手法模擬割開的效果,達到所需的臨床療效。其具體操作為拇指末端和食指前段提捏少量皮膚并迅速向上提拉,到一定程度兩手指松開皮膚,局部皮膚受到手法刺激會形成痧,具有良好的疏通氣血之功。“揲法”主要用于肌肉較為豐厚之處。主要是利用醫(yī)者的拇指及其與四指將皮下個結構包括經筋,肌肉等分離,改善局部經絡狀態(tài),加快氣血運行的一種手法。具體操作:拇指末端和同其余四指從局部肌肉組織深層,提捏并使用一定力度向上提拉,到一定程度五指松開,局部皮膚受到手法刺激會感覺局部強烈酸痛感,甚者可成痧。“結筋法”是在揲法的基礎上,將發(fā)生粘連或移位的經筋解開。具體操作主要是在肌肉的起止點或關節(jié)附近,重按粘連部位或者有結塊、結節(jié)、結絡等部位,同時在深層組織部位來回捏提,使粘連散開。“解肌法”主要的作用部位不是在肌腱附著點,而是在肌肉的肌腹處,用一定的力度將粘連的肌纖維分離。具體操作方法:用拇指指腹作用于肌腹,并將一定的力度在其上反復循撥,使粘連的肌肉得以分離。“訣脈法”就是在患者經絡循行之處出現異常瘀阻之處,進行局部放血,從而“宛陳則除之”。具體操作:在經絡診察中,利用“審”,發(fā)現異常之處,利用放血針點刺放血,達到活血化瘀之功。
以上五法王居易教授在臨證治療筋經病時會選擇其一或幾種手法同時操作進行,使得臨床療效錦上添花。
4 驗案舉隅
病案1:患者,女,法國籍,31 歲,主訴為“右小臂下疼痛2 年余加重6 個月”,于2013 年1 月在王居易經絡研究中心門診就診。患者因長期伏案工作,逐漸出現右側小臂外側疼痛,無放射痛,無頸項不適感,曾于北京大學第一醫(yī)院行頸椎核磁未及特殊異常,考慮“局部軟組織損傷”,目前無特殊用藥,刻下癥見:右小臂下疼痛,勞累后明顯,納眠尚可,二便尚調,舌質暗,苔白,脈細。西醫(yī)診斷:局部軟組織損傷,中醫(yī)屬筋經病。察經:右側手少陰心經神門至少海段廣泛壓痛,其中神門下可及脆絡,少海處可及明顯壓痛及結節(jié);余察經未及明顯經絡異常變化。考慮患者手少陰心經異常,取本經神門,少海穴。神門穴采用0.25 mm×25 mm毫針直刺,垂直皮膚進針約15 mm;少海穴位均采用0.25 mm×40 mm 毫針直刺,垂直皮膚進針約25 mm;所有穴位行提插手法,平補平瀉得氣后留針30 min,同時少海采用艾條懸起灸15 min,起針后患者訴疼痛基本消失,后囑患者勞逸結合同時加重艾灸少海,隨訪3 個月未再復發(fā)。
按語:此筋經病患者屬青中年,經絡診察未及其他經絡異常,故病變經絡可鎖定在局部。患者訴右小臂下疼痛,在經絡循行可累計手少陰心經及手太陽小腸經,而在察經中,手太陽小腸經并未出現明顯異常,而手少陰心經異常明顯,因此病在手少陰心經。同時患者諸多痛點,并無悉數全取,而取本經原穴及合穴,神門雖多用做補益心經氣血,調整睡眠,而在此案中,經筋病日久氣血不足,亦可造成局部疼痛不適,因此原穴補益本經氣血,活血化瘀通絡;少海為心經合穴,可調整本經逆亂之氣機,原合同用,調補兼施,再加之合穴艾灸,加強調整氣機之功,收效甚佳。同時在針刺諸穴時注重針刺層次,“皮脈肉筋骨”之中,此病位位于筋肉之間,因此根據俞穴結構不同[12],針刺深度亦不盡相同,總之務必針刺達到病位所處層次。
病案2:患者,男,65 歲,主訴為“左肩關節(jié)疼痛伴活動受限3 年余加重1 個月”,于2018 年12 月在北京中醫(yī)藥大學附屬護國寺中醫(yī)醫(yī)院針灸門診就診。患者3 年前因居住濕地后出現左側肩關節(jié)疼痛,并逐漸出現活動受限,曾于北京大學第三醫(yī)院行肩關節(jié)核磁“肩關節(jié)退行性改變”,曾間斷局部理療及外用藥物治療(具體不詳),癥狀時有反復,1 個月前因勞累后上述癥狀加重,刻下癥見:左肩關節(jié)疼痛伴活動受限,向前抬舉受限,勞累后明顯,納稍差,夜眠尚可,小便尚調,大便稍干,兩日一行。舌暗紅,苔少,脈沉細。西醫(yī)診斷:肩關節(jié)周圍炎,中醫(yī)屬筋經病。察經:左側手太陰肺經經渠脆絡,太淵處空虛感,尺澤處可及明顯壓痛及結節(jié);雙側足太陰脾經三陰交處可及壓痛及結節(jié),陰陵泉處可及結節(jié),余察經未及明顯經絡異常變化。考慮患者手太陰肺經異常,取左側太淵,尺澤穴。太淵穴采用0.25 mm×25 mm 毫針直刺,垂直皮膚進針約15 mm;尺澤穴位均采用0.25 mm×40 mm 毫針直刺,垂直皮膚進針約25 mm;所有穴位行提插手法,平補平瀉得氣后留針30 min,同時太淵采用艾條懸起灸15 min。隔日1 次,第3 次復診時,患者自述局部疼痛較前緩解不明顯,考慮患者應為手足太陰經同病,在上述穴位基礎上加左側太白及陰陵泉,太白針刺同太淵,陰陵泉針刺同尺澤,同時在患者太淵至經渠段行“揲法”至出痧,同時患者左肩關節(jié)向前抬舉受限,在左側中府和云門處行“揲法”及“解肌法”各15~20 次直至患者局部肌肉放松。連續(xù)治療2 個半月后患者自覺左側肩部疼痛基本消失,同時活動受限較前明顯改善。隨訪2 個月未再復發(fā)。
按語:此筋經病患者屬中老年,經絡診察可及手足太陰經異常,故病變經絡在太陰經。期初獨取手太陰經原穴及合穴,太淵雖多用做補益肺氣,而在此案中,經筋病日久氣血虧虛,局部疼痛不適,因此原穴補益本經氣血;尺澤為肺經合穴,調整本經氣機。然而收效不佳,此時關注患者久居濕地,而手足太陰經異常,提示濕邪甚重。一為由表而入外感濕邪;二為脾失健運,內生濕邪。而太陰經主“濕”[18],可散外界之濕,亦可健利內濕。故后取尺澤、陰陵泉二穴,一則為手足太陰經經氣聚合之所,能調整太陰經之氣;二則兩穴五行屬水,可疏導水液積滯以化濕。后病程日久,氣血瘀滯局部所致軟組織粘連,于病變經絡行直接行“揲法”與“解肌法”使粘連得解,肌肉復松,諸癥皆減。
5 小結
經筋病與臟腑病病因病機不盡相同,因此在針灸治療經筋病時診療思路也不盡相同。然而王居易教授50 余年的臨床實踐中,不拘泥于“以痛為俞”的理論束縛,反復強調無論針灸治療何種疾病,都必需體現針灸理論的核心與特色,即應在經絡診察基礎上進行經絡辨證,從而更加準確地選經取穴提高臨床療效[21-22]。在治療經筋病時首先明確“筋”的廣義范疇,注重整體與局部結合,即重視經筋病所累經絡,整體辨經,同時根據經絡特定穴的不同特性及區(qū)域分布特點,選取相應的“原合”特定穴組;同時局部將“五節(jié)”理論作為評價病變層次深淺的重要指導,借鑒“天、人、地”之“三才”理論,進一步細化層次治療,有的放矢;最后強調在臨床中針刺與手法的結合,根植經典,創(chuàng)新古法,在臨床中逐步積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手法治療經筋病,極大地提高了臨床療效,也為臨床中治療經筋病提供了系統(tǒng)的診療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