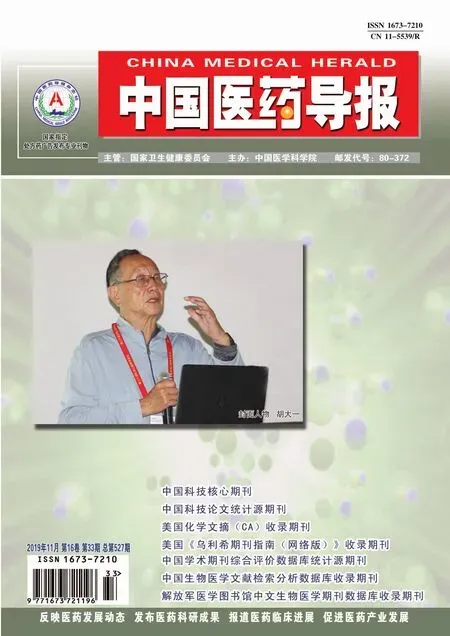補脾調氣法在非小細胞肺癌治療中的應用
劉殿龍 陳 雨 崔述生 侯 煒
1.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腫瘤科,北京 100053;2.北京東方醫院腫瘤科,北京 100078;3.北京市鼓樓中醫醫院名醫館,北京 100009
肺癌目前已成為世界上發病率最高的惡性腫瘤,非小細胞肺癌(NSCLC)占肺癌的75%~85%,確診時常已晚期,預后較差[1]。臨床實踐中的化學治療作為臨床一線治療,其經典有效,但也存在較為嚴重的副作用。靶向治療、免疫治療及腫瘤干細胞治療作為近幾年新興的治療手段,雖然在療效及不良反應方面較化學治療均有一定優勢,但因藥物價格昂貴、耐藥發生率較高而令醫患雙方苦惱。因此,如何更好地與現代醫學治療聯合應用以達到對腫瘤的治療增效減毒、延長患者生存期及提高患者生存質量成為中醫藥腫瘤防治科研工作的重中之重[2]。
補脾調氣法是中醫理論指導下的重要治法,提倡補益顧護脾胃、調理舒暢氣機為治療根本,其應用適合于NSCLC 治療的全過程。在NSCLC 治療中的應用范疇及義涵廣泛,包括在患者放化療期間幫助“減毒增效”、提高患者生活質量;在高齡、體質較差患者不能耐受放化療及手術治療時改善患者癥狀、延長總生存期;幫助根治術后患者康復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機體免疫力及抵抗力,即術后近期中醫康復治療;延緩乃至防止復發、轉移等,即術后遠期中醫預防治療。
1 NSCLC 脾虛氣機不調的病機演變、典型癥狀及相應治法
1.1 脾虛不足,腫瘤始生
現今多數觀點認為正虛再疊加癌毒、血瘀、痰飲是NSCLC 發生發展的的主要病因病機。正虛與邪實究竟哪一方是腫瘤產生的始動因素和主要因素目前尚無定論,而脾虛不足與氣機升降失司是腫瘤產生的重要病機基礎則是被廣泛認可的。早在晉代《諸病源候論》中就明確提到:“凡脾胃不足,虛弱失調之人,多有積聚之病。”[3]而《證治匯補》更是進一步認為腫瘤產生的始動因素就是脾虛不足:“積之始生,因起居不時,憂恚過度,飲食失節,脾胃虧損,邪正相搏,結于腹中。”[4]另外現代研究也從腫瘤微環境角度[5]證實了以上觀點。這些論述足以說明脾虛不足與腫瘤發生的重要關系以及補脾調氣法在臨床中應用的重要性。
1.2 脾失健運,濕蘊于內
《金匱翼·脹滿統論》曰:“濕氣歸脾,壅塞不行其脈濡,其體重”[6],說的就是脾虛濕蘊,土不治水。NSCLC患者常因化療導致損傷胃腸或患者久病多虛,屢投補氣養血、填精益陽濕膩之品,導致中焦脾胃運化失職,濕濁內生,濕邪為病,遏阻氣機。其癥見胃納呆滯,胸悶痞滿,面色蒼白或淡黃,倦怠乏力,或有身熱,口黏不渴,舌白苔膩,脈弦細而濡。臨床常用三仁湯加味,方中砂仁、白寇仁、薏苡仁三仁相伍,宣上暢中利下,通暢三焦以使濕行氣暢,間接達到健旺脾氣、和調三焦之氣的效果,諸癥自除。NSCLC 患者常有胸水兼癥,當屬《金匱要略》[7]中的懸飲、支飲范疇,其本為肺脾氣虛,癌毒可趁虛侵襲。應予傷寒防己黃芪湯加味。黃芪與白術可謂補脾調氣法中第一對藥,可起到三方面效果:一是補益脾肺之氣以復正常津液代謝;二則兩者均有利水消腫的作用;三可益氣固表。二者乃玉屏風散的重要組成部分,可增強衛外功能,扶正以祛邪[8]。
1.3 脾運失司,津停化濕,濕聚生痰
《醫林繩墨》載:“積者,痰之積也。”[9]中焦運化失司,津停化濕,濕聚而生痰,是NSCLC 發生的重要病理基礎之一。肺癌的痰飲治療是重要的主攻方向,痰飲既是肺癌的病理產物,又是病情加重的因素,運用補脾調氣法化痰在肺癌治療中不但可以減輕癥狀、延緩病勢,還能一定程度上避免南星、皂莢之類的辛溫化痰藥導致的耗氣傷陰的副作用。痰證常見頭暈目眩、胸悶嘔惡、痞脹不舒、小便不利。肺癌患者則更有咳嗽痰多、嘔吐涎沫,甚則痰鳴氣喘之癥。臨床上常治以二陳平胃散加味。若熱象明顯、痰黃質黏、苔黃膩者,多選用黃連溫膽湯。另注意配伍和胃之甘草、砂仁、神曲等,以免苦涼傷及脾胃。《松崖醫經》:“善治痰者順氣為先”[10],這深切符合治法“調氣”的基本精神。腫瘤大家樸炳奎教授在臨床中就習用陳皮、半夏、貝母、桔梗等藥,分別發揮其行氣、降氣、順氣、宣氣共奏調氣之效[11],再佐用清熱化痰排膿之金蕎麥,治療NSCLC所致的氣順痰消頗有佳效。
1.4 脾運失常,氣行不暢,進而血行不暢,而成瘀滯
《醫林改錯》云:“氣既虛,必不能達于血管,血管無氣,必停留而瘀。”[12]脾為氣生之源,氣為血之帥,氣暢則血行無阻,氣虛氣滯則血行無力有礙;肺失宣肅,氣機不暢,氣滯血瘀,阻塞脈絡,瘀與濕、痰互結,久之而為腫塊。NSCLC 發生后會造成對周圍組織器官的壓迫和血管、神經的侵犯,阻滯氣血的運行,臨床上表現為局部的疼痛、皮色青紫、出血、舌有瘀斑、脈沉澀等瘀證之象。補陽還五湯是中醫方劑中重要的理血劑,強調行血以補脾補氣為先,重用黃芪四兩,具有很好的補氣活血通絡之功效,在臨床上尤適用于氣虛氣滯血瘀證型的NSCLC 患者[13]。需要注意的是此時補而不滯尤為重要,除了原方中川芎、地龍可起到一定作用外,可酌加青皮、綠萼梅、大腹皮等助氣由內達外的順氣之品,頗有佳效。
1.5 脾病可進一步影響其余臟器
《雜病源流犀燭·脾病源流》:“脾統四臟,脾有病,必波及之,四臟有病,亦必待養於脾,故脾氣充,四臟皆賴煦育,脾氣絕,四臟不能自生……凡治四臟者,安可不養脾哉。”[14]脾胃為后天之本,其重要功能之一是將水谷精微化生為氣血,即采后天以補先天。脾虛失調日久,窮必及先天之本腎,如NSCLC 晚期患者或老年患者其脾本虛,后天不足難充養先天,以致脾腎兩虛,正氣愈虛,調補不易。又有脾虛土弱則肝木易乘而犯脾,木氣因土弱而過亢,易進一步影響情志失調,使肝臟木氣過旺進一步克脾,惡性循環。如臨床中NSCLC 患者常有太息、胸悶、兩脅不舒等情況,又或者生活中脾氣急躁,常欲發泄。可應用逍遙散合痛瀉要方治療。也有患者“脾土虛弱,無以生金”而致肺脾兩虛,癥見氣短懶言、咳嗽氣喘、胸悶痞滿、大便不調、食欲不振等。可采用參苓白術散合麥門冬湯治療。臨床治療應做到既病防變,未病先治。補脾調氣法以實脾補土為基礎,強調治療其余臟腑必先理脾。
2 補脾調氣法在NSCLC 發生發展各階段的應用
2.1 幫助NSCLC 患者治療“減毒增效”
《景岳全書》指出治積之要,在于攻補的適當,若腫瘤病程較長,元氣日虛,此時過用攻法,則癌邪強而正氣弱,過猶不及,導致“胃氣切近,先受其傷,愈攻愈虛”[15]。諸藥入口,必藉胃氣,首先脾胃是受納藥物的首要臟器,若脾胃虛弱則連藥物的容納都會令患者倍感痛苦,諸如很多NSCLC 患者臨床中口服靶向藥物治療后產生惡心嘔吐、食欲下降的情況,現代醫學認為這屬于藥物的副作用,目前主流的止嘔藥物如5-羥色胺3(5-HT3)受體拮抗藥對嘔吐治療有一定效果,但對于痞滿食欲減低等沒有較好的應對手段。中醫學認為此屬于脾胃受納功能失常,正適合辨證應用補脾調氣法,臨床上酌情應用白術、太子參、砂仁、木香、粳米、焦山楂、焦神曲等厚腸實脾、養胃助運之藥。治療后可以減弱藥物副反應,使主要成分吸收更佳,從而實現“減毒增效”。
脾還有散布腐熟后的水谷精微的作用,《素問·經脈別論》:“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16]類比之,口服藥的成分輸布過程中脾氣也起到了重要的轉導作用,因此調理脾胃之藥的應用亦可改善對口服藥物的吸收乃至布散。補脾調氣法是從脾胃納藥、散藥及養護脾胃三方面起到“減毒增效”的作用。
2.2 改善NSCLC 患者生存質量
臨床中NSCLC 患者有精神不振、肌肉酸痛、四肢廢用、不耐疲勞、食欲減低等情況,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中醫學認為其屬于虛勞、懈怠、解墯、五勞七傷、四肢勞倦等范疇。NSCLC 患者的疲勞其與脾臟生理功能失常及腫瘤邪氣侵傷的密切關系不言自明,《素問·示從容論》就有:“四肢解墯,此脾精之不行也。”[16]《東垣十書·四肢不收》:“脾胃虛則怠惰嗜臥,四肢不收。”[17]脾與肌肉筋骨活動關系密切,與疲勞的產生及消除均有重要關系,脾和氣調則機體氣血充旺,清氣得升,四肢輕健有力,活動自如,精神振奮,反之則機體氣血乏源則不耐疲勞,精神萎靡、活力低下。
補脾調氣法中常用的黃芪、黨參、白術、山藥等以補脾益氣為主,陳皮、枳殼則運脾行氣,使脾和氣充,健運無礙,能輸布水谷精微至全身肌肉四肢,使之濡養;脾健氣調,氣機升降如常,精神不振、肌肉酸痛等癥自消。脾臟化生中氣,上則為宗氣,下可養元氣,使一身之氣充足。脾之健運可充養先天之腎氣,可使肝的疏泄功能正常。脾氣正常,間接提升了肝、腎之氣,一段時間后可全面改善人體的陽氣。從而改善患者生活自理能力,更好的參與到社會生活和工作之中。體現中醫治療以人為本,在保證患者生活質量的前提下追求延長生存期。有研究表明補脾調氣法改善患者的疲勞狀況、增強患者體力的效果可能是由于降低了自由基對組織細胞的損傷實現的[18]。臨床中其療效毋庸置疑,具體機制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2.3 預防NSCLC 治療后的復發轉移
孫秉嚴認為“人患癌與否,關鍵看癌毒與抗癌之力孰強孰弱”[19]。NSCLC 成因往往因為正氣不足,無力抵抗癌毒,正邪相搏,痰瘀互結。加之脾虛氣機不調,導致痰濕內蘊或血脈瘀阻,為癌毒走竄、侵犯遠端而致肺癌的復發、轉移埋下禍根。《金匱要略》云:“四季脾旺不受邪”[7],《醫門法律》又云:“胃氣強,則五臟俱盛;胃氣弱,則五臟俱衰”[20]都明確指出了脾胃對人體的重要作用,一是脾旺則抗邪有力,二是脾胃強盛則能使五臟俱盛。脾旺則不受邪,這“邪”中當然也包括癌毒,雖然癌毒邪氣強盛,不能完全避免其侵襲,但一定的預防和抵擋作用是可以起到的[21]。另外脾健氣調之后,可使五臟俱安,后天之氣充盛,氣血旺達,營氣濡養與衛氣抗邪之力就足,很多肺組織部分切除后的患者肺功能在經過治療后就可以得到改善[22],平常也不易發生呼吸道感染。這與前文提到的“故脾氣充,四臟皆賴煦育”相呼應,也符合中醫學“培土生金”的思想[23]。
3 討論
現今的NSCLC 治療手段主要有手術、化療、放療、靶向治療、免疫治療等,患者在尋求中醫治療時往往已經接受過或正在接受上述治療手段,也有少數高齡或體質差患者對上述手段均無法耐受而尋求中醫姑息治療延長生存期。因為上述治療手段在殺傷癌細胞的同時不可避免的會對機體造成一定影響,所以患者接受治療后或多或少會表現出精神萎靡、肢軟乏力、納差便溏等脾虛氣機不調的情況,這種情況尤適合應用補脾調氣以改善癥狀、提高生活質量和延長生存期;另一方面,藥理研究表明黃芪、人參等常用補脾益氣的君藥含有抗腫瘤活性成分[24-28],可通過免疫調節達到抗癌目的,這也佐證了前文“脾旺抗邪”的觀點。此外,許多醫師在臨床中習用清熱解毒法與以毒攻毒法治療肺癌,常用如蝮蛇、全蝎、木鱉子、澤漆[29]等,這在控制腫瘤生長的同時也難免會傷及脾胃,常佐用一些甘溫之品以防苦寒太過,如吳茱萸、生姜、甘草等,此時再適當應用補脾調氣法,更可使毒減效増。補脾調氣法雖常用以四君為代表的補脾調氣之藥,但根據前文病機之論述,脾病日久已經影響他臟的情況十分常見,故臨床用藥又不應拘泥于調補脾氣,其余如疏肝理脾法、抑木扶土法當然也應根據辨證論治靈活應用,只應注意當前的主要矛盾,確立大法。綜合來說就是在腫瘤相對穩定或無進展期,應攻補并用,綜合運用補脾調氣與祛濕、化痰、活血方法,以達到控制復發轉移、延緩病勢作用;而當腫瘤生長迅速,應加強攻邪力度,采用解毒、散結為主的中藥,同時兼以扶正,最大限度抑制腫瘤進展,同時注意祛邪而存正氣,顧護脾胃。中醫的精髓在于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補脾調氣法是論述臨床上的治療側重和提示醫師顧護脾胃、調理氣機之重要,既不是讓臨床工作者因噎廢食、束縛手腳,更不是一味盲補大補,使補不中旳、氣機壅滯反成病患,違背法中“調氣”二字的要旨。
綜上所述,在NSCLC 發生發展的各階段、在經過現代醫學治療后或不能耐受治療時,補脾調氣法都有一定的應用價值,適用性較為廣泛,義涵也較寬泛,臨床上應靈活應用。中醫治法目的不外為調整臟腑氣血陰陽,使人體達到“陰平陽秘”的理想狀態,攻補就如同陰陽兩面,總要抓住辨證的關鍵選取適當的治療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