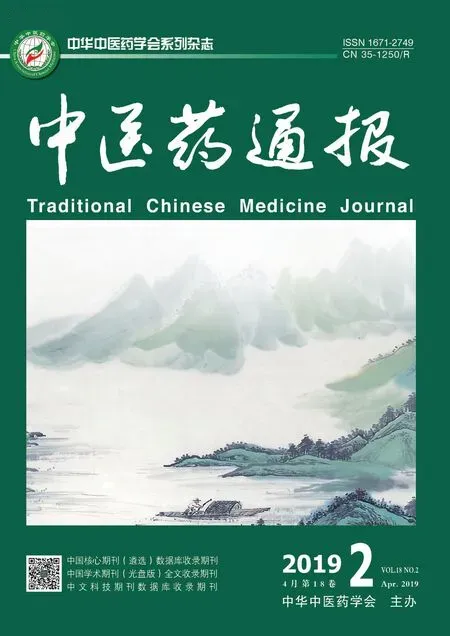以麻黃湯、《千金》還魂湯為例論中醫理法方藥的順思維
● 莫迪麟
麻黃湯(麻黃三兩、桂枝二兩、杏仁七十枚、甘草一兩)是出自張仲景《傷寒論》的名方,主治太陽傷寒表實證。外感病之中,寒邪傷人以發熱為主要臨床特點,以三陰三陽為發生發展變化過程,即為傷寒病。傷寒病之中,若太陽經先受寒邪所犯,而正邪交爭有力,即以麻黃湯作汗解,以宗《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其有邪者,漬形以為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之治法。若太陽經受邪,正氣無力抗邪,衛強營弱,則先以桂枝湯調和營衛,后以熱粥解肌發汗,宗陳修園《長沙方歌括》之“解肌還借粥之功”的治法。
麻黃湯貴為名方,院校《方劑學》教材無不以麻黃湯列為全書首方,院校《中藥學》教材無不以麻黃列為全書首藥。院校發展數十年,莘莘學子無不牢記麻黃湯“辛溫發汗,宣肺平喘”之功用,亦無不牢記麻黃具有“發汗解表,宣肺平喘”之功用。后世名醫,將麻黃湯擴展應用到臨床各科,如外科、耳鼻咽喉科等,使麻黃湯的運用范圍達到極致。若突然提出麻黃湯原方原量,可以治昏厥如死狀之危急重證,學子必然會十分迷惑,是如何治,機理為何等,為何同樣的藥與量,可以治療太陽傷寒表實證的外感病,亦可以治療卒死無知覺的危急重證?這先要從《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五備急方·卒死第一》分析。
《備急千金要方》為唐代孫思邈所撰,成書于永徽三年(即公元652年),后經北宋校正醫書局林億等校刊30卷,當中記載及補遺張仲景《傷寒論》及《金匱要略》藥方及原方描述,據孫思邈記述,當時醫家即使手藏張仲景之竹簡亦不公開,故云“江南諸師秘仲景要方不傳”。《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五備急方·卒死第一·還魂湯》記載:“治卒感忤鬼擊,飛尸諸奄,忽氣絕無復覺,或已死絞,口噤不開,去齒下湯,湯入口不下者,分患人發左右捉踏肩引之,藥下復增,取盡一升,須臾立蘇方。”方用“麻黃(三兩),桂心(二兩),甘草(一兩),杏仁(七十枚),上四味,咀,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三服。”如果從藥物組成與藥量來說,本方雖命名為還魂湯,但與《傷寒論》中的麻黃湯完全一樣。但本方立方本旨是否源于張仲景,還要仔細分析。《備急千金要方》最后一句云“仲景方桂不用”,可見孫思邈確實有參考張仲景之書,考《備急千金要方》是搜集唐初以前的醫藥著作,其中包括了南朝陳延之《小品方》及東晉葛洪《肘后備急方》。現存本《肘后備急方》卷一,名為《救卒中惡死方第一》,當中就有“又張仲景諸要方,麻黃四兩,杏仁七十枚,甘草一兩。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令咽之。通治諸感忤”之記載,《肘后備急方》之記載,比《備急千金要方》之記載少了一味桂枝(文獻亦有稱桂心),而《肘后備急方》冠以“張仲景諸要方”,顯然東晉葛洪之本方本旨,亦指向張仲景之書。考張仲景之書,其《金匱要略·雜療方第二十三》第十二條曰:“救卒死,客杵死,還魂湯主之方”,方用“還魂湯”,組成用“麻黃三兩(去節一方四兩),杏仁(去皮尖)七十個,甘草一兩(炙),上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分令咽之,通治諸感忤。”其中“通治諸感忤”一句,以及藥物組成及藥量,《肘后備急方》與《金匱要略·雜療方第二十三》完全相同。可見《肘后備急方》之救急方方源屬《金匱要略·雜療方第二十三》無異。而《備急千金要方》所載之還魂湯,與仲景方不同,原因有二。其一是孫思邈參考《金匱要略·雜療方第二十三》及《肘后備急方》后,認為加桂后更適合于救卒中之急,但欲后世之醫者能知本方方源屬張仲景,故在結尾加上“仲景方桂不用”;其二是《金匱要略·雜療方第二十三》雜亂不堪,版本眾多,通行本之《金匱要略·雜療方第二十三》本無桂心,但孫思邈參考其他古文或罕見本,補遺桂心,補遺后由于與通行本不同,故在后補充“仲景方桂不用”。
無論是古代,還是中醫高等院校發展的數十年中,均甚少人研讀《金匱要略》之《雜療方第二十三》《禽獸魚蟲禁忌并治第二十四》《果實菜谷禁忌并治第二十五》三篇。由于這三篇被認為內容散亂難讀,價值未定,故通常不列為必讀之篇章。但據以上考證,當中救急之術經醫書傳世至今,還未受到重視,實屬可惜。筆者考清代乾隆年間編纂之《四庫全書》,本書收錄了從先秦到清乾隆前期的眾多古籍,當中包括完整收錄的很多重要醫經,全書總共約8億字。當中提及還魂湯之處,不計算《備急千金要方》,只有6處,包括陳無擇《三因極一病證方證》、危亦林《世醫得效方》、王肯堂《證治準繩》、朱橚《普濟方》、徐大樁《蘭臺軌范》、吳謙《醫宗金鑒》。而以上醫書對還魂湯藥物組成與藥量,均跟從《備急千金要方》。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對還魂湯的記載,更是寥寥可數。雖曰如此,亦有學者留意到還魂湯之用法,亦即麻黃湯之救急用法。1982年《江西中醫藥》第3期刊發《謝勝臣老中醫治驗二則》[1],在“寒實厥證案”醫案中,謝老認為該病人“風寒之邪閉阻經絡,陽氣不得仲越,心氣內閉”而昏厥如死狀,經通關散、開關散治之無效,轉用千金還魂湯,兩劑而醒,文中作者陳宇春后按語引《醫宗金鑒》之方解釋千金還魂湯之機理。
無論是《金匱要略》還魂湯,還是《備急千金要方》還魂湯,其方源與立方本旨都是從麻黃湯來,透過麻黃與杏仁的配伍發動全身之陽氣,其差別者,在于麻黃湯發動陽氣以發汗解表,宗《素問·陰陽別論篇》“陽加于陰謂之汗”之要旨,而還魂湯是以發動全身之陽氣,以通郁閉之氣機,加桂枝或肉桂與否,在其陽氣之充足與否。本方之要旨,重在麻黃之“發其陽”。而所謂還魂湯所治之卒中狀如尸厥,正是氣機郁閉之甚,筆者認為仲景雖無載其卒中之機理,但據《史記·扁鵲倉公列傳》當中太史公司馬遷對虢太子卒中之假死描述,可以參考,其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別下于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還魂湯,就是借麻黃之力,會通上下表里之陰陽,應當不止限于《醫宗金鑒》的解釋,即“治邪在太陰,卒中暴厥口噤氣絶”[2]之說。當然,若仔細分析麻黃湯與《備急千金要方》還魂湯,還有細微的地方要注意,例如《備急千金要方》還魂湯之麻黃不用去上沫,服后亦不用“覆取微似汗”,亦不需“余如桂枝法將息”,讀者還望再思考。
如果在地上舍到一張處方寫上四味藥:麻黃、桂枝、杏仁、甘草,學子定必會想起麻黃湯主治太陽傷寒表實證;如果是三味藥:麻黃、杏仁、甘草,學子極其量只會想起三拗湯[3]。即使扁鵲再世,告之學子:“此乃禁方”,學子亦不信以為然此方可救急扶危。造成此等原因,乃學子學習方劑沿用著“理法方藥”的逆思維,即從方劑的組成反推機理,以及從“方論”去學習方劑。要知道,一位傳統中醫處方,必然透過四診合參,辨病與證而后得其疾病之機理,確立對人之治法,嘗試透過藥物來體現治法,這就是中醫的特色。然而,由于古醫經無論記載文字以及傳抄都十分困難,以致記載病情寥寥數語便罷了,后學之士難以掌握,必然會以自己對藥物的理解,反推方劑的應用機理。另一方面,由于古醫經語精少而難讀,于是“方論”便普及起來,“方論”就是醫家利用自己的理解批注方劑,由金成無己《注解傷寒論》開始的第一部方論,到后世如汪昂《醫方集解》、吳儀洛《成方切用》、羅美《古今名醫方論》、王子接《絳雪園古方選注》等等,都是著名的方論。換個角度來說,現今院校的《方劑學》,似乎也可以列入“方論”發展史。“方論”雖然能令學子容易入手,但“方論”很多時未必按“理法方藥”順思維去反映方劑確立的本旨,更多的是利用君臣佐使的配伍、藥物的特性分析全方之應用,使原有的“理法方藥”順思維失去。因此要進一步提升中醫的臨床能力,學習方劑時必需從“方論”與“經典”兩方面入手。筆者牙齦腫痛未再作,已無自汗、惡風,舌淡紅,苔薄,脈平。查:牙齦無紅腫。守上方稍有出入2周,每二日1劑,2個月后隨訪牙齦腫痛未再作。
4 小結
傳統觀點中,凡見“紅、腫、熱、痛”均認為與“上火”有關,所以無論患者本人還是臨床大部分首選的是清熱降火法,但時而不能見效,甚至反受其害而不自知。筆者認為,牙齦炎是由多種原因引起的,雖與“火”有關,但不全然是“火”,概括之多因飲食不節、病后體虛、年邁體弱等原因導致臟腑功能失調。故臨證之時,善治病者,當從病之根本施治,雖皆為牙宣,但細審病機,其病因病機多有不同,總以胃、腎為其關鍵。正如元·朱震亨所說:“牙衄者……有兩經之別,一主陽明腸胃,一主少陰腎經。”因此,臨床應謹守病機,方證統一,方能取得桴鼓之效。不過,在治療該病的同時,患者應注意口腔衛生的維護,多吃新鮮蔬菜、水果,少食辛辣炙煿之品,忌煙酒,才能夠取得更佳的臨床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