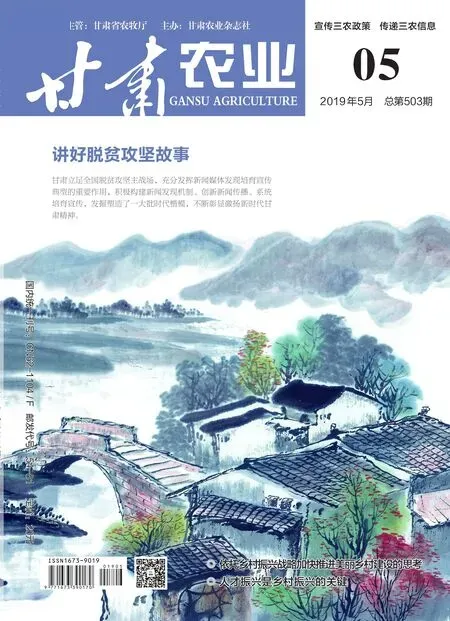加強和創新鄉村基層社會治理
季存華
中共菏澤市牡丹區委黨校,山東 菏澤 274000
鄉村基層社會治理其實質就是對鄉村自然資源及報括鄉村習俗、政治、經濟制度、公共社會財富和服務的分配和處置。其目標是達到社會公平正義、經濟運轉高效、社會和諧、生態良性發展的目標。
鄉村治理是社會治理最關鍵、最基層,也是最難的基層治理。基層治理的好壞,效果如何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關系到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實現。如何在新時代推進鄉村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實施全面振興鄉村戰略有著重要意義。
一、建國后鄉村基層社會治理歷史演變
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后,我國由奪取全國政權過渡到鞏固政權,發展經濟加強社會管理的上來。其中對鄉村基層社會治理在探索中不斷發展和前進。
第一階段(1958-90年代中期)實行村級“政社合一”。我國在1958年開始推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即公社將生產與社會管理統一掌握到政府組織手中。無論耕地荒地、農具農機、種子肥料,還是瓜果、蔬菜、糧食等一切歸于集體所有。既社會成員共同占有。對鄉村社會成員統一集中勞動和管理。.
1964年之后,這種村級“政社合一”的管理權限逐步下放到生產隊。從此以后一直長時間延續和執行這管理體制,只是具體形式在各地有所差別。
1980年代中國農村率先拉開改革的序幕,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責任制,土地產權和使用權分離,土地等生產資料及財物進行重新配置,但在各地又有所不同,農戶對土地等財產的權、責、利的權限劃分比較模糊。
村級“政社合一”的體制具有以下特點:一是覆蓋廣,基本上包括絕大部分甚至全體社會成員;二是三級相連(政府、村委、村民)連接;三是村委包攬責任,即俗稱“誰家的孩子誰管”,幾乎所有的社會管理事務都有所在的行政村村委負責處理;四是對資源再分配處置權存在自上而下的等級,等級越高對資源分配處置權就越大。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這種鄉村基層治理體系的效用,是鄉村社會治理得到維系的原因。這一管理體制化解和抵消了組織外的社會沖突和干擾,鄉村社會秩序得以維持并正常運轉,正是得益于這種體制得存在。
第二個階段(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90年代中葉以后,我國鄉村發生了兩個社會現象的變化。一是農村人口的流動出現,離家進城的人數越來越多。據不完全統計,2000-2010年10年間,全國自然村由363萬個減至271萬個,有90多萬個自然村銷聲匿跡。有的地方甚至出現荒蕪村、無人村。二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鄉村社會治理能力下降、經濟意識增強、社會治理環境發生變化。現在的鄉村基層治理不再是對封閉的固定人群的治理,而是對不斷變化的、流動的、差異的社會治理。村民對個人事務的處理不再單一的依靠村委解決,對法院、婦聯、仲裁機構等社會組織有更多的選擇性。同時社會資源的配置大多進入市場,由市場分配調節。因此鄉村社會成員對基層政府的依賴性降低,社會治理職能退化。
二、困擾基層社會治理的難題
近年來,鄉村基層社會治理效果不好,甚至有的地方問題頻發,表現為:基層社會政治情緒化,群體事件不斷,基層黨組織功能弱化,對社會輿情把控不準,黑惡勢力有所蔓延抬頭。
(一)基層治理主體虛置,人民群眾缺位
社會治理誰是主體誰是客體、誰是基層社會治理的主要力量?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作為國家和社會主人,人民不能也不應缺席于國家和社會的治理;廣大村民應該在社會治理中唱主角,是基層社會治理的主體。現實生活中,在社會基層治理中政府往往被治理主體的位置上,承擔了過多工作。把民眾當作治理的客體和“物”化的對象。替民做主,造成人民群眾在基層社會治理中“不在場”,甚至成為“看客”的尷尬場面。在治理過程中導致個別基層政府過度關心政績和形象工程。有的甚至損害了群眾利益。正因如此,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一再指出和強調,發展要以人民為中心,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
(二)基層治理的價值取向出現一定偏差
鄉村基層社會治理上要達到的目標也就是鄉村振興的總要求:產業興旺 、生態宜居 、鄉風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在基層治理實踐中,部分基層政府認為社會治理就是“治理社會”,“治理社會”就是力求社會穩定。維護穩定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價值取向。有的基層政府按照“屬地管理、分級負責”和“誰主管、誰負責”原則,嚴防死守。有些基層制定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的“三不”操作原則,導致許多問題與矛盾被強制性地壓縮在村鎮而沒有得到實質性解決。當一些問題和矛盾長時間得不到妥善解決,民眾得情緒得不到釋放。多數群體性事件都是因長期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與矛盾積累到臨界點而爆發的。這種治理理念是典型得傳統管理理念和價值取向。不僅不能化解基層社會矛盾,反而會破壞基層社會治理秩序,出現南轅北轍得治理效果。
(三)部分基層黨組織社會治理作用“弱化”
“一個執政黨如果不能把黨建設好,把國家治理好發展好,盡管有悠久的歷史、豐富的經驗、廣泛的影響,也為人民做過不少好事,照樣會毀于一旦。”從總體上看,我國大部分基層黨組織在基層社會治理方面都發揮出了應有的作用,但也有一些地方的基層黨組織在基層社會治理方面的作用有所“弱化”,具體表現為:某些基層黨組織在社會治理中被靠邊站,不再被認為是社會治理得主心骨,失去核心地位和領導權。某些基層黨組織政治功能弱化,組織力不強,對人民群眾沒有吸引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某些黨員干部自身素質低,法制觀念淡薄,在群眾需要黨組織解決問題得時候優柔寡斷,不具有共產黨員的擔當精神和服務于人民的意識,導致基層黨組織在人民群眾心中的威信和核心地位下降。不斷樹立基層黨組織應有的政治權威,發揮領導核心的作用。
(四)社會基層黑惡勢力有所抬頭
在鄉村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中農村黑惡勢力滋長蔓延有所抬頭。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發展,農村社會的治理環境發生了變化加;國家在農村基層治理制度的缺失,管理松散和缺位;真正的農村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離家進城,留守人員大多為老人、婦女和兒童,“從而導致基層群眾自治組織治能力長期得不到有效培養”“黨在基層力量的退化或退場必然有其他力量補場或進場”。一些所謂的鄉村“能人”趁虛而入,滲透和介入基層社會治理。而留守在農村的老少婦兒顯然處于弱勢群體的處境,為鄉村黑惡勢力的蔓延抬頭提供了發展環境。同時一些農村基層干部素質不高、黨性不強、濫用職權、貪污腐敗,成為農村黑惡勢力滋長蔓延的保護傘。
(五)不能很好的把握社會輿情
眾所周知,我國已邁向全面網絡化的大數據時代。農村網絡的普及成為群眾表達看法、排泄不滿情緒,反映社會問題的主渠道。雖然社會網絡輿情表面上是反映和傳播一些社會熱點問題,但往往一些關于政治、經濟、民生、治安和腐敗問題都有可能成為輿情的導火索并能夠迅速成為網絡輿論的熱點。如果對社會輿情不能夠及時疏導處理和把控,就有可能演變成群體突發事件,產生一些方面效應甚至引起社會混亂。
三、加強和創新鄉村基層社會治理新舉措
社會治理主要指基層社會治理。進入新時代,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這意味著基層治理實踐由地方性實踐探索上升為國家層面得認同。
(一)以創造美好生活為治理目標
現代鄉村基層社會治理,是在黨的領導下,遵循中國鄉村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按照“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留的住“鄉愁”的理念,振興鄉村,把鄉村建設成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農村。這就意味著現代鄉村的治理應該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從群眾身邊的困難問題著眼,從與老百姓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項目做起,以群眾得實惠、增進民生幸福為出發點,把創新基層社會治理與滿足居民群眾需求緊密結合起來,把解決問題的過程變成尊重民意、化解民憂、維護民利的過程。旨在不斷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二)以黨建引領為治理前提
堅持和完善黨對鄉村基層治理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鄉村工作的具體貫徹。始終把基層黨組織在社會治理中處于核心地位,擁有領導權,加強黨引領做為鄉村善治的一條紅線。不斷強化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功能,進一步提升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加強黨員干部的學習培訓,增強服務群眾、清正廉潔、敢于擔當,充分發揮先鋒模范帶頭作用的意識和政治自覺。使基層黨組織在社會治理中成為群眾的領頭羊和主心骨,對群眾形成感召力和凝聚力,充分發揮其領導和核心作用。
(三)加強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自治法治德治都是社會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自治增活力、法制強保障、德治揚正氣,自治以其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而凝聚共識,實施共治;法治以其規則剛性、程序透明、準則有效而定分止爭、懲惡揚善;德治以其核心價值、公序良俗、社會賢達而弘揚正氣、引領風尚”[1]。自治是法治與德治的基礎,法治是自治與德治的邊界和保障,德治是較高追求,德治以自治與法治為基石,并對自治與法治形成有力補充。
自治、法治、德治都是鄉村社會治理基本關鍵路徑。“三治融合”不是三條路徑的平行也不是簡單相加。關鍵在一個“融”字。“融”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產生的效果不是“和數結果”而應具有“乘數效應”,是倍數的增加。
“三治”有優先次序,但更要同時發力、交織前進,才能發揮“三治”結合的“乘數效應”。這要求在“三治”建設中要統籌兼顧,通盤設計。同時,社會力量成長是“三治”結合的“點睛之筆”,要充分吸納社會力量有序參與,使整個基層社會治理迸發活力。如此,才能實現自治、法治與德治的結合,甚至走向它的高級階段“三治融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
(四)堅持人民群眾參與為關鍵
加強基層治理主體多元化建設同時,堅持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唯物史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突出人民群眾在社會治理中的主體地位。激發人民群眾的無窮的創造精神和活力。讓人民群眾在社會治理中充分發揮其智慧和力量。才能使鄉村基層社會治理走向良治和善治。沒有群眾的參與,自治形同虛設;沒有群眾的遵從,法治舉步維艱;沒有群眾的自覺,德治難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