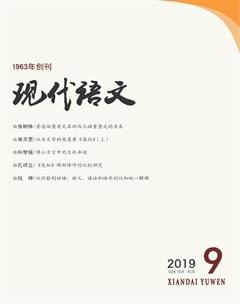20世紀(jì)30—40年代中國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的儒學(xué)傳統(tǒng)與語言表達(dá)
趙雨


摘? 要:儒家文化作為長期根植于中華民族心理的支柱性存在,不僅深刻影響 著詩歌、繪畫、書法等傳統(tǒng)藝術(shù)門類,與電影在中國的發(fā)展也密不可分。在厘清“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概念基礎(chǔ)上,從積極入世精神、“仁”之思想與“天 人合一”觀念三個(gè)方面,來論述儒家文化傳統(tǒng)對早期中國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美學(xué)與語言表達(dá)的影響,探尋中國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的發(fā)展脈絡(luò),并以此對當(dāng)下國產(chǎn)電影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 作現(xiàn)狀形成觀照。
關(guān)鍵詞:中國早期電影;現(xiàn)實(shí)主義;儒家文化
在中國,作為一種舶來的藝術(shù)門類,電影無論在創(chuàng)作手法還是電影理論方面,都受到西方很大的影響。因此,提及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思潮,我們必然會(huì)想到20世紀(jì)80年代國內(nèi)諸如張暖忻、鄭洞天等影人對法國新浪潮之父安德烈·巴贊“電影是現(xiàn)實(shí)的漸近線”理論的推崇與實(shí)踐,也會(huì)想到第六代導(dǎo)演對意大利新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的創(chuàng)作手法亦步亦趨的集體效仿。然而,我們似乎忽略了中國自第一部電影《定軍山》誕生之日起便走上了與西方完全不同的電影之路這一既定事實(shí),也淡漠了中國電影其實(shí)自20世紀(jì)30年代便已形成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歷史傳統(tǒng)。筆者認(rèn)為,這與數(shù)千年傳承下來的以儒家文化居主導(dǎo)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體系是分不開的。
一、“現(xiàn)實(shí)主義”與中國電影
中國電影的發(fā)展之路是不同于西方國家的,這一點(diǎn)從世界電影與中國電影開端的不同便可窺探一二。1895年,法國的盧米埃爾兄弟拍攝了《工廠大門》,成為世界上第一部電影,也奠定了歐洲電影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美學(xué)基礎(chǔ)——記錄本性,它與之后相繼出現(xiàn)的法國詩意現(xiàn)實(shí)主義、意大利新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有著一脈相承的關(guān)系。與之不同的是,中國最早期的電影卻與戲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而與“記錄”“現(xiàn)實(shí)”等字眼毫無瓜葛。然而影戲傳統(tǒng)包裹下的中國電影其實(shí)絲毫沒有減少對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注與表現(xiàn),這就涉及到“現(xiàn)實(shí)主義”一詞定義的涵蓋面問題。
“現(xiàn)實(shí)主義”作為一種文藝思潮,發(fā)軔于19世紀(jì)的歐洲文學(xué),多以揭露城市文明的黑暗面、資本主義社會(huì)對人民的壓迫為主題,并致力于對客觀現(xiàn)實(shí)的真實(shí)描摹。正如高爾基所言:“對于人和人的生活環(huán)境作真實(shí)的,不加粉飾的描寫的,謂之現(xiàn)實(shí)主義。”[1](P163)由此可以看出,現(xiàn)實(shí)主義文藝思潮于歐洲發(fā)軔之初,就強(qiáng)調(diào)其“客觀性”的特征。馬克思主義理論肯定了現(xiàn)實(shí)主義對客觀性的強(qiáng)調(diào),恩格斯曾指出:“作者的見解越隱蔽,對藝術(shù)作品來說就越好”[2](P462)。仔細(xì)品味這句話的含義,不難看出,恩格斯并沒有否定藝術(shù)家主體的傾向性,而是“認(rèn)為作品的傾向性應(yīng)該從場面和情節(jié)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反對作品赤裸裸地鼓吹作者的社會(huì)觀點(diǎn)和政治觀點(diǎn)”[3](P7)。與此同時(shí),馬克思主義理論還主張作品應(yīng)“真實(shí)地再現(xiàn)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這也成為現(xiàn)實(shí)主義的一個(gè)重要特點(diǎn)。王一川教授在《當(dāng)前中國現(xiàn)實(shí)主義范式及其三重景觀——以新世紀(jì)以來電影為例》一文中,曾闡述了現(xiàn)實(shí)主義的三個(gè)基本特征:“現(xiàn)實(shí)主義一般具有如下三個(gè)基本特征:一是客觀性,即在藝術(shù)觀念層面,按照客觀生活的本來面目去加以描寫,再現(xiàn)客觀事物及人與人之間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以達(dá)到藝術(shù)反映的內(nèi)在真實(shí)性的要求;二是典型性,即在藝術(shù)形象層面,注重創(chuàng)造典型形象;三是批判性,即從與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系來說,大膽暴露社會(huì)問題,體現(xiàn)強(qiáng)烈的批判性。”[4]這一歸納是筆者所極力認(rèn)同的。
通常認(rèn)為,中國電影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表達(dá)早在二十世紀(jì)一、二十年代就已初露端倪。《難夫難妻》(1913)控訴了封建買辦婚姻制度對年輕人的毒害,《黑籍冤魂》抨擊了當(dāng)時(shí)鴉片流毒的罪惡,這些內(nèi)容都是取材于當(dāng)下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可以看出,這一時(shí)期的電影更多偏向于啟蒙主義或改良主義,將批判的矛頭對準(zhǔn)封建制度,同時(shí)教化意味過于濃厚,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在中國初具規(guī)模,應(yīng)在20世紀(jì)30年代。比如:《城市之夜》《都會(huì)的早晨》對社會(huì)時(shí)弊的針砭;《大路》《八千里路云和月》提倡抵御外侮,等。法國電影史學(xué)家喬治·薩杜爾曾經(jīng)說過這樣一段話:“誰要是看過袁牧之的《馬路天使》,如果不知道該片是在1937年出自一個(gè)對法國電影一無所知的年輕導(dǎo)演之手,他一定會(huì)以為這部影片直接受讓·雷諾阿或是意大利新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影響。”[5](P547)由此可見,中國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美學(xué)是有著自己獨(dú)特的發(fā)展歷程與藝術(shù)成就的,而其初具規(guī)模便始于20世紀(jì)30年代。
我們知道,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進(jìn)程中,儒家思想由春秋時(shí)期孔子所開創(chuàng),為孟子、荀子所繼承,至漢代董仲舒“罷黜百家,獨(dú)尊儒術(shù)”,再到宋明程朱理學(xué)、陸王心學(xué)對儒學(xué)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一直到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等人接納西學(xué)融合而建構(gòu)現(xiàn)代新儒學(xué)。這條道路雖歷經(jīng)坎坷,但其脈絡(luò)卻始終未斷。盡管現(xiàn)在儒家已不再像過去那樣被奉為正統(tǒng)思想,但它早已成為隱形的文化傳統(tǒng)根植于中華民族心理深層。正如牟鐘鑒先生所言:“儒學(xué)根植于民族心理深層結(jié)構(gòu),僅從政治和學(xué)術(shù)的顯要層面上取消它,遠(yuǎn)不足以摧毀它,它有相當(dāng)一部分已深入骨髓、融入血液,在民族感情的催化下,便會(huì)隨機(jī)萌生復(fù)發(fā)。”[6]與此相應(yīng),儒家美學(xué)觀念也深刻影響著中華民族文藝的發(fā)展與風(fēng)格的形成。下面,筆者就分別從儒家入世精神與批判性主題、“仁”之思想與人物形象塑造、“天人合一”觀念與藝術(shù)創(chuàng)作手法的等方面,來論述儒家文化傳統(tǒng)對早期中國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美學(xué)與語言表達(dá)的影響。
二、“先天下之憂而憂”:
入世精神與社會(huì)批判性主題
在儒、釋、道三家中,儒家無疑是最具有入世精神的。所謂“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禮記·大學(xué)》),修身齊家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治國平天下,這就是傳統(tǒng)士大夫的最高人生理想與終極目的。因此,他們都具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zé)”的家國情懷,具有“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的憂患意識(shí),還具有“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dòng)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積極進(jìn)取精神。正是在入世精神的指引下,杜甫寫下了“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shí)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的愛國名篇;辛棄疾流露出“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可憐白發(fā)生”的悲嘆,林則徐發(fā)出了“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吶喊。就連隱逸遁世的陶淵明也未能全然忘懷天下,正如朱熹所言:“隱者多是帶性負(fù)氣之人為之,陶(指陶潛)欲有為而不能者也。”[7](P3327)這些都是儒家文化傳統(tǒng)對古代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影響,投射到中國電影中也不例外。
如果說儒家的入世精神在20世紀(jì)一、二十年代電影初創(chuàng)時(shí)期體現(xiàn)出來的是濃厚的教化意味與社會(huì)改良的主題的話,那么,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直接打破了影人們對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美好幻想。他們紛紛投入左翼電影運(yùn)動(dòng)之中,用影像直接干預(yù)現(xiàn)實(shí),因?yàn)樗麄兂浞忠庾R(shí)到“電影負(fù)著時(shí)代前驅(qū)的責(zé)任”[8]。縱觀這一時(shí)期的電影創(chuàng)作,我們可以從《大路》《風(fēng)云兒女》《十字街頭》中感受到編導(dǎo)呼吁人們團(tuán)結(jié)一心抵御外侮的慷慨激昂,也可以從《壓歲錢》《城市之夜》《馬路天使》《都會(huì)的早晨》中感受到對尖銳階級(jí)矛盾和巨大貧富差異的忿恨與批判,更能從《漁光曲》《萬家燈火》《一江春水向東流》中感受到整個(gè)時(shí)代的悲哀。這些難道不都是儒家“自任以天下之重”的積極入世精神在當(dāng)時(shí)影人身上的真實(shí)寫照嗎?
圖1? 費(fèi)穆《城市之夜》海報(bào)(1933)
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以費(fèi)穆、孫瑜等人為代表的影人都是將西學(xué)智識(shí)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融會(huì)貫通的集大成者。以費(fèi)穆為例,長久以來他都被認(rèn)為是中國文人電影的開創(chuàng)者,其作品如《孔夫子》《小城之春》并不具備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的表征。然而費(fèi)穆在1940年那個(gè)特殊的年代選擇拍攝這部看似陳舊的歷史題材電影——《孔夫子》,不僅表達(dá)了他對儒家文化的理解與推崇,其借古喻今之意也是顯而易見的。費(fèi)穆是這樣理解孔子的:“生于憂患,長于憂患,一生凄凄惶惶,而憂患無已。孔子常自認(rèn)為是一個(gè)失敗者,但從不肯放棄他的工作。他是入世的,絕不像當(dāng)時(shí)一般所謂‘避世的賢者,只是獨(dú)善其身。”影片中陽貨被拘時(shí)問:“陽貨何罪?”一個(gè)畫外音嚴(yán)厲地斥責(zé)道:“賣國之罪!”將批判的矛頭直指汪偽當(dāng)局,足以見得導(dǎo)演批判現(xiàn)實(shí)、警醒世人的良苦用心。再如《小城之春》,一片頹敗景象之下,表現(xiàn)的不正是當(dāng)時(shí)知識(shí)分子入世不能而郁郁不得志之心嗎?
綜上所述,20世紀(jì)30~40年代的電影具有高度一致的社會(huì)批判性主題,而這種電影主題與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緊密結(jié)合的現(xiàn)象,正是儒家積極入世精神與憂患意識(shí)的集中體現(xiàn)。
三、“泛愛眾”:
“仁”之民本思想與人物形象塑造
《論語·學(xué)而》:“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jǐn)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xué)文。”筆者認(rèn)為,這句話集中體現(xiàn)了孔子“仁道”內(nèi)在的思想蘊(yùn)涵與精髓。由此,“泛愛眾”成為儒家的一個(gè)主導(dǎo)思想而代代相傳。《孟子·盡心下》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荀子·王制》也提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這些思想家不約而同地都將關(guān)注的目光投向了老百姓身上,在某種程度上說,這與意大利新現(xiàn)實(shí)主義“還我普通人”的口號(hào)是不謀而合的。在距今一千多年以前的唐朝,偉大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詩人杜甫就已經(jīng)發(fā)出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fēng)雨不動(dòng)安如山”的呼吁,足以見出儒家“泛愛眾”的思想對中國文學(xué)藝術(shù)產(chǎn)生了多么深刻的影響。
以此來觀照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電影,我們可以清晰地發(fā)現(xiàn),編導(dǎo)在人物選擇視點(diǎn)上的相似性,即影片中正面人物多為備受壓迫的社會(huì)底層民眾,平民視角、現(xiàn)實(shí)關(guān)懷更加凸顯了這一時(shí)期電影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特征。可以說,數(shù)千年傳承下來的這種儒家仁道思想、仁者情懷與當(dāng)時(shí)流行的馬克思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文藝觀念有著一定的契合,影人們也是著力刻畫“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共同構(gòu)成了這一時(shí)期電影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景觀。為了更直觀地展現(xiàn)這一景觀,筆者特意選取了幾部代表性熒屏中的人物形象,具體如表1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的仁愛思想與墨家所謂的“兼愛”、基督教所提倡的“博愛”有著本質(zhì)性的不同,它是一種由“孝悌”觀念出發(fā),進(jìn)而達(dá)到與人“忠”“信”,再上升到普遍的人類之愛。也就是說,“泛愛眾”是一種從自己、家庭推至社會(huì)層面的仁愛。因此,我們也可以從這一時(shí)期的電影中歸納出另一種普遍現(xiàn)象,就是許多影片在批判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殘酷性的同時(shí),更習(xí)慣于以家庭為單位,從一個(gè)家庭的遭遇鳥瞰整個(gè)社會(huì)和時(shí)代的變遷。如:作為四十年代的冷峻現(xiàn)實(shí)主義之作,《萬家燈火》用一種樸素的寫實(shí)風(fēng)格,在不動(dòng)聲色中展現(xiàn)了主人公胡智清一家由本來和睦到矛盾重重再到互相理解的過程,影片致力于通過真實(shí)的生活場景疊加和人物關(guān)系變化,形象地反映了當(dāng)時(shí)物價(jià)飛漲、市民失業(yè)等戰(zhàn)后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現(xiàn)狀。正如有學(xué)者指出的:“在這場家庭沖突中,并不是媳婦‘不對,也不是兒子‘不對,更不是婆婆‘不對,而是‘這年頭兒的不對!”[9](P79)再如《一江春水向東流》,通過素芬一家的悲歡離合展現(xiàn)了從戰(zhàn)前、戰(zhàn)中到戰(zhàn)后的歷史變遷,同時(shí)也通過張忠良這一人物對待母親、素芬態(tài)度的變化,刻畫了一個(gè)進(jìn)步青年在時(shí)代洪流中墮落的典型形象,可謂發(fā)人深省。在這一時(shí)期,像這樣類似的借家庭視角表現(xiàn)社會(huì)變遷的電影不勝枚數(shù),這與儒家由親至疏、推己及人的仁愛觀不無關(guān)系。
四、“有我之境”:
“天人合一”觀念與藝術(shù)創(chuàng)作手法
《莊子·達(dá)生》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自古以來,中國各個(gè)哲學(xué)流派都曾試圖探討“天”與“人”的關(guān)系。在道家看來,天屬于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儒家內(nèi)部雖然觀點(diǎn)不盡相同,但總體上來看,都更多地賦予天以人的情感色彩。董仲舒可謂是儒家自覺且系統(tǒng)探討天人關(guān)系的第一人,他在《春秋繁露·深察名號(hào)》中明確提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的觀念,認(rèn)為天與人具有相同的結(jié)構(gòu),人是天的派生,人事與自然規(guī)律相似,故而天人可以相互感應(yīng)。數(shù)千年傳承下來,“天人合一”“天人同構(gòu)”就成為儒家美學(xué)的基本原理,也成為中國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長盛不衰的美學(xué)觀念。如繪畫:“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妝,冬山如睡。四山之意,山不能言,人能言之。”(惲格《南田畫跋》);再如詞曲:“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fēng)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馬致遠(yuǎn)《天凈沙·秋思》),如此等等。
與西方繪畫有所不同,中國山水畫有其獨(dú)特的表現(xiàn)技巧,它不太重視光線明暗、陰影色彩的變化,而更重視整體環(huán)境帶給人的主觀感受,也就是說,它更注重“意境”的表現(xiàn)與追求。中國早期的電影創(chuàng)作也繼承了這一傳統(tǒng),通過對客觀物象的渲染傳達(dá)出編導(dǎo)(影片)的主觀情緒。蔡楚生在《漁光曲》中運(yùn)用了大量的空鏡頭,為我們展現(xiàn)出如水墨畫般的江南水鄉(xiāng)。片中婆婆死去時(shí),鏡頭語言轉(zhuǎn)向一棵枯樹和一群嘰嘰喳喳的烏鴉,這正是馬致遠(yuǎn)曲中意境的影像化呈現(xiàn)。在片尾小猴死去時(shí),鏡頭語言轉(zhuǎn)向了波光粼粼的水面與遠(yuǎn)處的青山,散發(fā)著無以言說的哀婉愁緒。再如《一江春水向東流》中反復(fù)出現(xiàn)的月亮這一意象,既穿針引線推動(dòng)敘事,也見證著素芬對張忠良的思念與對這個(gè)家庭的堅(jiān)守,更見證著張忠良是怎樣一步步自甘墮落隨波逐流的。片尾素芬跳入黃浦江,滾滾逝去的江水正是照應(yīng)了影片的題目——“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費(fèi)穆的電影《小城之春》等更不待言。可以看出,同為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中國與西方的藝術(shù)手法也有所不同,中國電影深受儒家“天人合一”觀念的影響,自覺沿襲中國書畫等古典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特色,將客觀的物象景觀賦予創(chuàng)作者的主觀情感,使影片的社會(huì)批判意圖與現(xiàn)實(shí)主義色彩“從場面和情節(jié)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
總起來看,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思潮曾一度是我國電影創(chuàng)作的主流,然而近年來卻鮮有突破。客觀地說,第六代導(dǎo)演曾在上一世紀(jì)90年代集體自覺實(shí)踐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美學(xué),長鏡頭、手持?jǐn)z影等藝術(shù)創(chuàng)作手法在電影中屢見不鮮,這在一定程度上延續(xù)和發(fā)展了中國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創(chuàng)作。在之后的很長一段時(shí)期,中國電影卻陷入了顧影自憐與青春疼痛的泥沼之中,借用李道新教授的觀點(diǎn),中國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創(chuàng)作與理論正經(jīng)歷著“隱形消解”的歷史時(shí)期[10]。放眼當(dāng)下,娛樂至上、青春荷爾蒙充斥電影市場,具有社會(huì)關(guān)懷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卻陷入了一個(gè)瓶頸階段。再反觀上一世紀(jì)三、四十年代那個(gè)特殊歷史時(shí)期,電影創(chuàng)作者自覺不自覺地繼承了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懷揣著使命感、責(zé)任感直指社會(huì)問題所在,這對當(dāng)下身陷桎梏的中國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是具有一定參考意義的,這也正是筆者撰寫這篇論文的意義所在。
參考文獻(xiàn):
[1][蘇]高爾基.談?wù)勎以鯓訉W(xué)習(xí)寫作[A].高爾基.論文學(xué)[C].孟昌,曹葆華,戈寶權(quán)譯.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78.
[2][德]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A].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周涌.被選擇與被遮蔽的現(xiàn)實(shí)——中國電影的現(xiàn)實(shí)主義之路[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xué)出版社,2010.
[4]王一川.當(dāng)前中國現(xiàn)實(shí)主義范式及其三重景觀——以新世紀(jì)以來電影為例[J].社會(huì)科學(xué),2012,(12).
[5][法]喬治·薩杜爾.世界電影史[M].徐昭,胡承偉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2.
[6]牟鐘鑒.新儒家的歷史貢獻(xiàn)與理論難題[A].鄭家棟,葉海煙主編.新儒家評(píng)論(第一輯)[C].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
[7][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M].王星賢點(diǎn)校.北京:中華書局,1986.
[8]鄭正秋.如何走上前進(jìn)之路[J].明星月報(bào),1933,(1).
[9]周星等.中國電影藝術(shù)發(fā)展史教程[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5.
[10]李道新.當(dāng)代中國電影:現(xiàn)實(shí)主義50年(上)[J].電影藝術(shù),19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