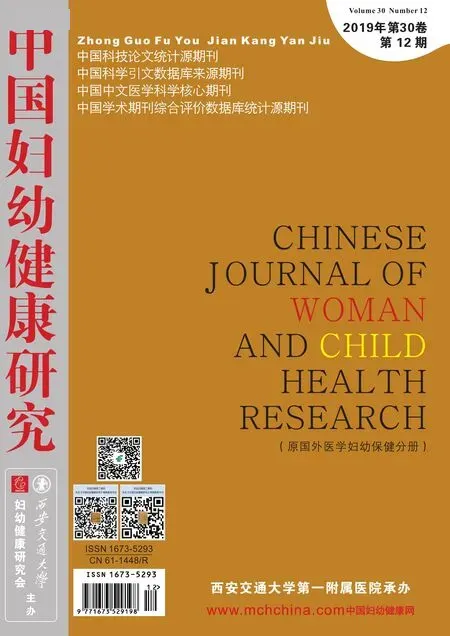嬰兒心理發展環境影響因素的研究進展
張羽頔,史慧靜
(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婦幼與兒少衛生教研室,上海 200032)
嬰兒心理發育是兒童早期綜合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生命初期是兒童生長和發育的“機會窗口期”。健康和疾病的發育起源(the 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health and disease,DOHaD)學說認為這一時期的環境因素會對兒童的生長發育和未來疾病發展情況產生極大影響,甚至對生命全程健康有決定性作用。
1嬰兒心理發育的基本概念和評價要素
1.1嬰兒心理發育的基本概念
人的心理發展(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從新生兒期即開始,嬰兒期心理發展包括感知覺(perception)、運動(motor)、語言、認知(cognitive)、情緒情感、個性及社會化發展等方面,其中以運動和認知的發育最為明顯。認知發育包括感知覺、注意力、記憶力、思維能力及想象力的發展,而認知功能發展的概念最早由讓·皮亞杰提出,其認為新生兒及小嬰兒時期認知功能已經開始發育,目前對于嬰兒認知功能的評估主要集中在記憶、感知、注意能力等方面。
嬰兒的運動發育包括粗大運動及精細運動兩方面,并各自沿著各自的方向發展,遵循其各自的發育順序規律。粗大運動主要指頭、軀干和上下肢的運動;而精細運動主要由小肌肉來完成,通常表現為手部動作的精巧協調能力和細巧技能,在精細運動發育過程中,逐漸由簡單到復雜發展。一般而言,運動發育的過程是連續的,粗大運動發育略早于精細運動。當然,不同嬰兒個體發育速度有快慢的差別,各發育階段也不是完全界限分明。
1.2嬰兒心理發育的基本評價方法
在現今的國內外研究中,常用貝利嬰兒發育量表(Bayley scales of infant development,BSID)、蓋塞爾發育量表(Gesell development scales,GDS)、年齡-發育進程問卷(age & stage questionnaires,ASQ)、丹佛發育篩查測驗(Denver development screening test,DDST)及《0~6歲兒童神經心理發育量表》(簡稱《兒心量表》)等進行嬰兒心理發育水平評價。
BSID量表內容包括智力發展指數(mental developmental index,MDI)和精(psychomotor development index,PDI)兩部分,修訂后為智力量表、運動量表和行為觀察量表三大部分,可測量嬰兒的運動、認知、社會化等方面的發育水平,多用于0~3歲的嬰幼兒[1]。中國兒童發展中心和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Children’s Developmental Center of China,CDCC)的專家根據此量表改編并進行中國標準化,形成了CDCC嬰幼兒智能發育檢查量表。
ASQ發育篩查是由父母(照看者)完成的兒童檢測系統,適用于1~66個月的嬰幼兒,其內容包括溝通、粗大動作、精細動作、解決問題及個人-社會5個能區的檢測,可對嬰兒認知、動作及社會化的發育情況進行評估和篩查。
DDST是目前在國內基層兒保體檢經常使用的兒童發育水平測量和篩查工具,適用于2周到6歲的嬰幼兒,內容包括個人-社交、精細動作-適應性、語言、大動作等4個能區的測量評估,涉及嬰兒認知、語言、運動、社會化等方面的發育情況。
《兒心量表》是由首都兒科研究所編制的適用于0~84月齡的嬰兒、幼兒及學齡前兒童的神經心理發育評價量表,包括大運動、精細動作、認知水平、語言和社交行為5個能區的評估。于2016年修訂發行的《兒童神經心理行為檢查量表2016版》(CNBS-R 2016)是我國唯一自主研發的認知發育診斷量表。
此外還有王慧珊等于2011—2013年聯合研發的兒童心理行為發育預警征(warning sign for children mental and behavioral development,WSCMBD)、Griffith精神神經心理發育評估量表(Griffiths mental development scales,GMDS)及Peabody運動發育量表(Peabody developmental motor scale,PDMS)等常用評價及篩查工具。
2影響嬰兒心理發育的宮內環境因素
除社會人口學因素外,對嬰兒心理發育產生影響的環境因素可分成宮內環境因素、產時因素及出生后環境因素三類,其中,宮內環境影響因素又可分為宮內環境污染物暴露、母親孕期身體健康狀況及母親孕期壓力性情感因素三方面。
2.1宮內環境污染物暴露
關于宮內環境污染物暴露對嬰兒發育影響的研究涉及了重金屬、可吸入顆粒物及有機污染物等影響因素。韓松(2013年)和許敏(2011年)等的多項研究顯示,宮內鉛暴露(包括宮內低水平鉛暴露)可對新生兒及1歲內嬰兒的認知發育產生不良影響,并且這種影響將持續至學齡前。但也有一項對尼泊爾6月齡嬰兒的研究顯示,宮內鉛、砷的暴露在6月齡時并未對嬰兒的心理發展產生影響[3]。
除了鉛暴露之外,陶瑞文(2017年)及Bhang等[4]在不同隊列研究中發現,宮內砷暴露對嬰兒的生長發育、行為和認知發育均有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但目前尚未有研究得出鎘暴露對嬰兒發育的影響。在有機污染物中,齊小娟等(2011年)、Tang等[5]及郭劍秋等(2017年)研究表明,苯、擬除蟲菊酯、五氯苯酚、有機磷和有機氯及多環芳烴(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PAHs)均對嬰兒的神經發育和行為發育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PCP、有機磷和有機氯對嬰兒心理發育的影響在不同性別之間存在差異。此外,曹志娟等(2016年)及王雙青等(2014年)在研究中發現,孕期PM2.5及二氧化氮等空氣污染物暴露,尤其是孕早期PM2.5的暴露對嬰兒認知-運動發育會造成不良效應。有研究顯示宮內尼古丁暴露也會對嬰兒的行為發育產生影響[6]。
2.2母親孕期身體健康狀況
母親生育年齡、孕期身體健康狀況及營養狀況等也會對嬰兒發育造成一定的影響。有研究發現,母親生育年齡與嬰兒的運動發育及認知發育水平有關[7],尤其是35歲以上高齡產婦的嬰兒心理發育水平明顯低于35歲以下的產婦。母親患有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壓及孕期超重/肥胖與新生兒期的認知及運動發育落后有關[8]。王為實等(2010年)學者認為,在高危妊娠孕婦中,采取合理孕期保健措施有利于在嬰兒3~4個月時獲得較高的心理發育水平。
對具有防洪公益服務和生產經營功能的綜合利用水庫工程按庫容法分攤的政策依據是水利部2007年出臺的 《水利工程供水價格核算規范》(以下簡稱《核算規范》)和《已成防洪工程經濟效益分析計算及評價規范》(以下簡稱 《效益分析計算》)(SL 206—1998)。
2.3母親孕期壓力性情感因素
有研究表明,母親孕期存在的壓力性情感因素對嬰兒出生后的心理發育水平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母親在孕期的應激程度和焦慮抑郁水平不利于子代嬰兒期的心理發育[9]。一方面,母親產前焦慮或抑郁情緒可導致皮質醇等壓力相關激素釋放入血,對胎兒發育和分娩結局造成一定的影響[10];另一方面,孕期心理應激量較大、負面生活事件較多、皮質醇水平較高等可能會對嬰兒認知發育及3~6個月時的情緒發展水平產生影響[4,11]。有研究者認為,母親孕期的壓力性情感因素對子代生命早期心理發展的影響也可通過腸-腦軸發揮作用[12]。
綜上,宮內重金屬污染物及有機污染物等環境污染物的暴露對嬰兒的心理發育水平會產生不良影響,同時,母親生育年齡及孕期生理、心理健康狀況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截至目前,國際上雖然有一些研究涉及了母親孕期的壓力和抑郁情況對嬰兒發育水平的影響,但是未綜合產后抑郁情況進行整體分析,并且多針對6~12月齡的嬰兒,對于3個月以下小嬰兒的研究較少見。
3影響嬰兒心理發育的產時因素
對嬰兒心理發育產生影響的產時因素主要包括出生時孕周、分娩方式、嬰兒出生體重等。
3.1出生孕周
在目前現有的研究中,早產不利于嬰兒生長發育這一觀點已經被廣泛接受,近年來有學者對此進行了細化的研究。早產兒與足月兒在3月齡時的認知發育水平有較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在11~12月齡嬰兒的認知-運動發育中依然存在。李彩霞等(2013年)和胡曉琴等(2012年)的研究顯示,早產對嬰兒發育水平的影響更大程度地體現在運動發育上,與足月兒相比,早產兒嬰兒期的粗大運動和精細運動發展水平均較為遲緩。在早產兒中,出生孕周越小,嬰兒發育遲緩越嚴重,極早產兒(出生孕周小于28周)在12月齡時的語言、認知等方面發育水平均低于足月兒[13],而晚期早產兒(出生孕周為34~36周)主要表現在粗大動作發育水平較低[14]。此外,早產兒在4、6及12月齡出現可疑發育延遲(suspected development delays,SDD)的患病率均高于足月兒[15]。
3.2分娩方式
盧平等(2014年)和金莉娜等(2016年)研究顯示,順產分娩的嬰兒比剖宮產嬰兒在智力、溝通、精細動作、大動作及個人-社會等能區的測試中獲得了更高的得分,可能與生產時經產道擠壓有關;并且自然分娩的嬰兒在3個月時的身長相對較長。但王為實等(2010年)認為,分娩方式對嬰兒3~4月齡時的心理-運動發育無顯著影響。
3.3嬰兒出生體重
在影響嬰兒心理發育的產時因素中,對于出生體重的研究不在少數,大部分學者認為,低出生體重嬰兒的認知發育和運動發育水平均低于平均水平;也有學者認為除了低出生體重外,巨大兒在12月齡的認知發育水平也低于出生體重正常嬰兒,并且超重嬰兒在運動、認知等方面的綜合評分低于正常同齡人[11,16]。
綜上,在影響嬰兒心理發育水平的產時因素中,產時孕周影響的研究已經較完備。近年來的研究除了關注低出生體重外也逐漸將注意力轉向出生體重的過低/過高兩方面;而在針對分娩方式的研究中,依然存在不同的意見,需要進一步的研究進行證實。
4影響嬰兒心理發育的出生后環境因素
相比宮內環境因素和產時因素,嬰兒出生后的環境因素更加復雜多樣,現有的研究大多關注喂養方式、身體活動、照顧者身份及母親產后焦慮抑郁情況等。
4.1喂養方式
有研究已經證實,接受純母乳喂養的嬰兒在認知和運動方面發育水平均高于非母乳喂養的嬰兒[7,17],并且在一定時間內堅持純母乳喂養時間越長的嬰兒認知發育水平相對更高[18];同時有研究顯示,堅持母乳喂養的嬰兒在6、9、12月齡時的認知與運動發育水平均高于同年齡段非母乳喂養的嬰兒[17]。
4.2嬰兒身體活動和睡眠
在對出生后影響嬰兒發育的因素中,室內外活動時間長短對嬰兒的心理發育水平,尤其是動作、運動發育影響較明顯。張丹等(2011)探究了季節變化與活動時間的關系,認為由于中國冬季氣溫較低不適宜戶外活動及穿著衣物較厚活動不便等原因,秋冬季節出生嬰兒活動時間相對較短,在動作發育水平上相對落后。
嬰兒身體活動情況受到主要照顧者相關行為的影響。夏彬(2016年)在研究中提到,做被動操及其他身體活動的嬰兒發育商較不活動的嬰兒高;懷抱時間長的嬰兒運動發育水平相對較低,使用行走裝置的嬰兒運動發育水平較自由活動的嬰兒低;穿著連襪衣褲的嬰兒活動減少,發育商低于平均水平。照顧者的行為也可以影響嬰兒的運動發育。曹志娟等(2016年)和鄧小丹(2017年)的研究中發現,照顧者對嬰兒進行早期引導式家庭教育有利于嬰兒認知-運動等多方面發育,其發育商高于未進行早期教育的嬰兒。
目前的研究中,對于嬰兒睡眠情況的調查多集中在睡眠時間和模式上,主要關注結局是體格發育,極少涉及到心理發育情況。在今后的研究中應對嬰兒的發育情況進行全面測量,綜合睡眠時間、睡眠模式及睡眠環境進行分析[19]。
4.3主要照顧者身份
嬰兒照顧者的身份也被一些研究所關注。大部分研究認為,以母親為主的照顧者身份對嬰兒運動-認知發展最有利[7,20];張麗等(2014年)認為,父母共同參與照顧的嬰兒在大運動發育水平上要優于其他身份的照顧者。此外,保持每天較長時間的母子交流也有利于嬰兒的認知發育。
4.4母親產后焦慮抑郁
與孕期壓力和焦慮抑郁水平對子代早期心理發展水平的影響類似,母親產后的焦慮抑郁情況對嬰兒的心理發育也存在一定的影響。有研究顯示,有產后抑郁傾向的母親,其子代在認知發育、運動發育存在疑似發育延遲的幾率更高,并且在運動發育水平上更加明顯[21]。此外,母親和父親產前產后壓力和抑郁狀態均會與嬰兒的認知和運動發育遲緩有關聯,并且這種影響有可能將持續到學齡期[22-23]。
綜上,在眾多對嬰兒出生后環境因素進行測量、分析的研究中,絕大部分研究認同母乳喂養尤其是純母乳喂養有利于嬰兒的心理-運動發育,但是將影響哺乳行為和嬰兒發育的早產、妊娠期疾病及產后抑郁等相關因素納入研究范圍的文獻較為罕見,需要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大部分學者關于活動時間較多及活動自由程度較高對運動發育有積極影響方面達成了共識。但是在研究嬰兒活動情況及照顧者身份時,可以將二者相結合,考慮兩個影響因素之間的相關性,對混雜因素進行控制。此外,對于嬰兒睡眠情況的調查多集中在睡眠時間和模式上,主要關注結局是體格發育而未涉及嬰兒的神經-心理發育。
5小結與展望
目前的研究已經對嬰兒心理發育有關的多方面因素進行了探討,例如宮內重金屬及有機物暴露、母親焦慮抑郁情況、分娩方式、喂養方式、照顧者行為等,但是依然有許多空缺亟待填補。對于分娩方式、母親產前產后抑郁情況及照顧者身份等因素的作用仍不能達成共識并形成定論,需要進行進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總體而言,現有的文獻大多是針對某一或某幾個因素對嬰兒的發育水平展開研究,缺乏全面地將從胎兒期受到的暴露與產時情況、出生后環境因素綜合在一起進行整體分析討論的研究調查。另外,目前研究中的結局絕大多數針對4個月及以上的嬰幼兒,對0~3月齡的小嬰兒心理發育水平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尚未提及,因此需要更多研究對嬰兒心理發育的影響因素進行縱向、全面及綜合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