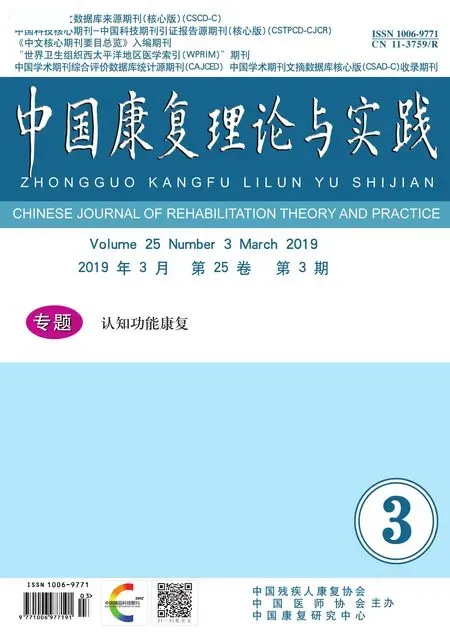腸道菌群與孤獨癥譜系障礙關系的研究進展
張春艷,朱路文,唐強
1.黑龍江中醫藥大學第二臨床醫學院,黑龍江哈爾濱市150040;2.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黑龍江哈爾濱市150001
孤獨癥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ASD)是一組以社交障礙、重復刻板行為和狹隘興趣為主要特征的神經發育障礙性疾病。ASD病因至今不明,目前認為遺傳和環境因素共同導致ASD的發生。近年來,ASD的發病率急劇上升。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報道,在0~8歲兒童中ASD患病率2012年為1/68,而2018年達1/59[1]。
ASD除上述核心癥狀外,還常共患胃腸道功能紊亂(如便秘、腹痛、腹瀉和嘔吐等)。與正常兒童相比,ASD共患胃腸道功能紊亂的可能性更高[2]。與ASD家族中發育正常的兄弟姐妹相比,ASD共患胃腸道癥狀發生率更高。有胃腸道癥狀的ASD患兒社交障礙和行為異常更明顯,影響患兒生活自理和融入社會的能力。胃腸道癥狀與社會交往障礙和異常行為的相關性可能與“微生物-腸-腦軸(microbiota-gut-brain axis,MGBA)”作用關系密切。胃腸道與中樞神經系統之間的雙向調節被稱為MGBA作用。該軸是綜合性的生理概念,綜合胃腸道和中樞神經間所有神經傳導、內分泌和免疫學信號的傳輸。
本文將依據MGBA作用,將腸道菌群對ASD的行為學和ASD分子表型進行綜述。
1 腸道菌群對ASD的行為學影響
1.1 腸道菌群對ASD模型的行為學影響
腸道菌群通過MGBA影響動物和人類的行為。目前動物實驗通過無菌動物(germ-free,GF)移植微生物、大劑量廣譜抗菌藥物干預無特定病原體(specific pathogen free,SPF)動物、向動物移植特定病原菌和喂食益生菌等證實腸道菌群與動物的行為學相關。
小鼠腸道菌群的結構和菌群數量改變可影響小鼠社交行為。Desbonnet等[3]通過三箱社交實驗觀察GF鼠的社交能力和社交偏好,結果與正常發育小鼠相比,GF鼠社交互動時間減少,表現出ASD樣行為表型,經過脆弱擬桿菌治療可以逆轉ASD行為表型[4]。
母體免疫活化(maternal immune activation,MⅠA)導致ASD小鼠腸道菌群改變,以梭狀芽胞桿菌和擬桿菌屬為顯著,給予脆弱類桿菌治療,可以降低腸道黏膜屏障的通透性,增加緊密連接蛋白質表達,減少炎性細胞因子如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ⅠL)-6的表達,改善腸道的炎性環境,使有毒物質不能進入腦內,減低腦內炎癥的發生,進而使ASD鼠社會交往、重復刻板、感知異常和焦慮癥狀得到改善[5]。
de Theije等[6]的研究顯示,母鼠產前暴露于丙戊酸鈉環境導致子代腸道菌群結構異常,以厚壁菌門和擬桿菌門數目增加顯著,說明腸道菌群結構改變影響子代小鼠中樞神經系統的發育,可產生類似ASD的行為。
BTBR T+tf/J(BTBR)鼠社交行為減少,刻板行為增多,腸道菌群改變,腸道黏膜通透性增加,免疫狀態改變。Coretti等[7]的研究表明,Parabacteroides和Sutterella菌屬增加,Dehalobacterium和Oscillospira菌屬減少,可能是BTBR鼠行為改變、腸道通透性增加和結腸炎性狀態相關的驅動因素。BTBR小鼠、Shank3B小鼠和ⅤPA小鼠中L.reuteri水平有明顯的降低,給予益生菌治療可以減輕上述小鼠的社會行為異常[8]。
1.2 腸道菌群代謝產物對ASD模型的行為學影響
腸道菌群代謝產生的脂肪酸、膽汁酸和維生素等產物轉移至循環系統,參與調控代謝、免疫調節和中樞神經發育等活動。腸道菌群的代謝物短鏈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SCFAs),包括乙酸、本體酸(proprionic acid,PPA)、丙酸、丁酸、異丁酸、戊酸和異戊酸等。
PPA主要由梭狀芽胞桿菌、擬桿菌門和脫硫孤菌屬分解產生,可以穿過血腦屏障(blood-brain barrier,BBB)導致類似ASD行為。研究表明,在大鼠側腦室內注射PPA,可導致大鼠社會行為改變,可能是通過多巴胺和血清素等神經遞質來影響大腦功能,引起行為改變[9]。
丁酸可合成神經遞質多巴胺、去甲腎上腺素和腎上腺素,影響中樞神經系統及其外周的行為活動。乙酸、丙酸和丁酸等可通過BBB進入中樞神經系統參與代謝,特別是對于早期大腦發育和細胞信號傳遞起重要作用[10]。過高的丙酸水平可產生類ASD樣行為改變。Nankova等[11]的研究表明,丙酸和丁酸通過調節PC12細胞中cAMP應答元件結合蛋白(cAMP respons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CREB)依賴的兒茶酚胺類神經遞質參與ASD。
總之,腸道菌群及代謝產物與各種ASD模型的行為問題有相關性,可能在ASD的基因和環境因素中充當一個重要的介質[12]。
1.3 腸道菌群對人類ASD的行為學影響
Wang等[13]認為,與正常發育的對照組相比,ASD患者腸道脫硫菌屬、擬桿桿菌和梭狀芽胞桿菌增加。Strati等[14]發現與正常人相比,ASD的厚壁菌門/擬桿菌門比例顯著增加,同時發現ASD念珠菌是正常人群的兩倍。假絲酵母可以釋放氨和毒素能誘發ASD樣行為[15]。鑒于ASD患兒有腸道菌群結構異常的情況,許多研究者通過改變腸道菌群來治療ASD胃腸道癥狀及相關的行為問題,因此將益生菌作為ASD綜合治療措施之一。
Grossi等[16]研究1例ASD并發嚴重認知障礙的10歲男孩,給予10種混合的益生菌治療,干預4周,然后隨訪4個月,結果表明,ASD患兒不但胃腸道癥狀減輕,還有ASD核心癥狀的顯著改善。Santocchi等[17]將100例ASD學齡前兒童患者分為胃腸組和非胃腸組,給予益生菌和安慰劑治療6個月,結果給予益生菌的ASD患兒不但在腸道癥狀、社會交往、感知認知、刻板行為和適應能力有改善,而且血清脂多糖、瘦素、腫瘤壞死因子α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和ⅠL-6等都有改變,這說明益生菌可改善胃腸道和社交等行為學障礙,也能治療分子表型的異常。
1.4 飲食對ASD的行為學影響
Malhi等[18]研究發現,飲食改變也可影響腸道菌群,進而改變社會交往和行為問題。與對照組相比,ASD患兒攝入的水果、蔬菜和蛋白質比較少,每日攝入鉀、銅、葉酸和鈣也少。ASD患兒采用口服Omega-3治療,干預12周,患兒表現出社交能力的明顯提高。無谷蛋白和/或酪蛋白的飲食能通過調整腸道菌群,改善ASD行為問題,增強生理功能,提高社交能力[19]。生酮飲食是指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飲食。給予ASD模型鼠生酮飲食能導致腸道菌群總數量的改變,提高社交能力,減少重復性行為。Newell等[20]發現,生酮飲食可減少糞便中腸道菌群的豐富度,使ASD尿液中某些細菌正常,提高社交能力。
2 腸道菌群對ASD分子表型的影響
至今ASD的病因病機不清楚,科學家們從許多方面提出假說。由于任何單一的假說都不能解釋ASD的復雜發病機制,因此需要涉及遺傳、生化、神經內分泌和免疫等多種因素來解釋。通過MGBA可將各自獨立的假說聯系起來,對ASD病因病機做出更好的解釋,也為治療ASD提供新的思路。
2.1 遺傳因素
腸道菌群和遺傳因素之間的關系,可能影響ASD的發生。例如某些宿主的等位基因位點對腸道菌群的影響,間接調整宿主健康狀態。研究者通過比對雙胞胎和小鼠品種等方法來衡量腸道菌群的遺傳性。盡管許多研究結論存在差異,但仍提供許多有價值的信息。在全基因組關聯研究中,研究者發現某些基因能夠顯著影響腸道菌群。例如由于5-羥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轉運體基因發生變異,使ASD患兒外周血清素增多,研究者在小鼠中誘導這種變異,小鼠不但表現出行為重復、刻板和動作遲緩等類似ASD的表現,同時出現腸道菌群失調和便秘等腸道功能異常的情況[21]。
Petra等[22]研究發現,在ASD患兒的腸道菌群中脫硫弧菌屬顯著增加,并且該菌屬是ASD中較為常見的菌屬。通過對ASD患兒兄弟姐妹的調查發現,其同胞間也可能共同攜帶該菌屬,脫硫弧菌屬是ASD家族中共同攜帶的菌屬,提示該菌在家族內的傳播可能與ASD的遺傳易感性有一定關聯。經過脆弱擬桿菌治療后,腸道菌群紊亂得以糾正,且ASD樣行為明顯好轉[5]。
2.2 單胺類神經遞質
5-TH能神經元系統紊亂是ASD的主要神經生化假說。血清5-HT是第一個被認為可識別ASD的生物標志物。5-HT不但在調節神經元分化、遷移、軸突生長以及髓鞘和突觸形成中發揮重要作用,也對腸道的運動、感覺以及分泌活動產生廣泛影響[23-24]。
腸道細菌在調節腸5-HT水平中發揮重要作用。80%~95%的5-HT受體存在于腸道中,因此,血中5-HT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腸道嗜鉻細胞(enterochromaffin cell,EC)分泌的5-HT。大約30%的ASD患兒血清中5-HT都有增加[25],說明ASD患兒體內的血清5-HT水平異常是受腸道菌群的影響。Finegold[26]研究發現,GF小鼠血清5-TH水平顯著低于SPF鼠,這可能是腸道菌群缺失導致的直接結果,也可能是代謝產物影響的繼發性結果。例如,由腸道細菌包括梭狀芽孢桿菌發酵產生的SCFA可增加EC細胞中Tphl mRNA的水平,進而在不改變5-HT再攝取轉運體(serotonin reuptake transporter,SERT)表達的情況下增加腸道5-HT水平[27]。
Sj?gren等[28]的研究表明,ASD模型小鼠的腸道菌群失調,特別是梭狀芽孢桿菌和擬桿菌類,通過脆弱擬桿菌調節腸道菌群,改變胃腸道通透性的缺陷,調整血清吲哚丙酮酸水平,顯著降低腸道中5-TH水平,最終糾正ASD相關的行為異常。
除了對腸道5-HT的影響,腸道菌群也能影響大腦中5-HT的水平,從而影響ASD的行為問題。白志余等[29]通過腹腔注射腸內代謝物造成腸道通透性增大的ASD動物模型。與對照組大鼠相比,實驗組大鼠的反應探索和逃避危險的行為有顯著差異,且海馬內、下丘腦內和紋狀體內5-HT含量都明顯降低,導致行為異常。ASD患兒體內5-HT明顯增多,提示胃腸道5-HT分泌失調。如果大量的腸道5-HT不能被及時利用,則會影響大腦發育,導致下丘腦室旁核中催產素的降低,并增加杏仁核中降血鈣素相關基因多肽水平,導致ASD患兒社交互動行為異常和便秘[23]。上述實驗說明,腸道菌群對腸道和腦內5-HT的水平都會有影響,從而導致ASD的異常行為。MGBA與5-HT的密切聯系,為ASD的研究提供新的可能及新的思路。
2.3 神經免疫相關分子
胃腸道是人體免疫細胞聚集最多的地方,健康的腸道菌群通過構建黏膜屏障,維持腸道微生態平衡和內環境的穩定,影響機體免疫系統,抵御外來病原微生物的入侵來保護自身[30]。Takeuchi等[31]通過GF小鼠和普通小鼠的免疫特性發現,GF小鼠存在免疫功能缺陷,經過正常菌群移植后可以使免疫功能恢復。
Lutgendorff等[32]研究發現,ASD患兒腸道菌群發生菌群結構和數量的變化,影響腸道黏膜免疫反應,動物ASD模型和人類ASD患者的腸道基底膜ⅠgG和補體C1q沉著,導致胃腸黏膜細胞的緊密連接蛋白減少[33],胃腸道黏膜通透性增加[34],破壞腸黏膜屏障功能。
腸道微生態系統失衡和腸道上皮細胞的屏障完整性遭受破壞時,導致許多細菌產物、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從腸道屏障轉移到腸系膜淋巴組織,并通過黏膜免疫細胞激活免疫系統[35]。被激活的免疫系統釋放的炎性細胞因子如ⅠL-1β、Ⅰl-6、干擾素-γ(interferon-gamma,ⅠFN-γ)和TNF-α等可激活迷走神經,進而調節中樞神經系統的活動和外在的行為表現。
此外,ⅠL-1β、Ⅰl-6、ⅠFN-γ和 TNF-α 等細胞因子增高,也可通過血液循環,穿過BBB,定植到大腦內皮細胞,誘發腦內的免疫反應,影響大腦發育并產生異常行為。
因此,ASD患兒胃腸道內存在的多種炎癥可能是腸道微生物紊亂引起免疫系統失衡的結果。
陳保林等[36]通過脂多糖誘導的ASD模型進一步證實,小鼠腸道滲透性增加,腸系膜淋巴結和派爾集合淋巴結(Peyer "s patch,PP)中樹突狀細胞、T細胞和B細胞比例明顯增高,腸上皮淋巴細胞增多,而固有層淋巴細胞減少,免疫細胞比例失調明顯,細胞因子ⅠL-6、ⅠFN-γ和TNF-α增高,ⅠL-10降低。這些提示,小鼠ASD樣行為,腸道屏障功能降低,免疫細胞比例異常,促炎性T細胞功能增強,抗炎性細胞功能被抑制,可能導致腸道黏膜免疫失調。這可能與ASD的胃腸道菌群失調和胃腸道炎性癥狀有關。
2.4 下丘腦-垂體-腎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HPA)軸相關分子
HPA軸對腸道菌群具有廣泛影響。目前認為ASD患兒常共患消化系統癥狀,可能與應激后皮質醇濃度有顯著相關性。壓力激活HPA,導致一系列神經內分泌因子的級聯反應,調節應激反應、消化和免疫功能。與正常發育的同齡人相比,ASD患兒存在皮質醇分泌增多的同時出現社交互動能力減弱,焦慮明顯,智力障礙,適應能力差,語言表達障礙,以及消化系統癥狀。而ASD患兒的HPA軸的激活是受炎性細胞因子如ⅠL-6和TNF-α調控才能激活[37]。
HAP軸在應激狀態下分泌皮質醇可對腸道免疫系統有重要作用,同時對腸黏膜通透性也有明顯影響,使腸道共生菌構成比發生改變[38]。應激狀態下,腸黏膜通透性增加,肥大細胞或緊密連接體斷裂,導致病原菌進入體內,菌群發生移位[39],導致腸道菌群結構和組成改變,腸道菌群平衡被打破[40]。Crumeyrolle-Arias等[41]和Rook等[42]研究發現,與SPF鼠相比,GF鼠外周循環促腎上腺皮質激素和皮質酮的濃度高。如果將SPF鼠腸道菌群移植給GF鼠后,HPA軸的應答部分可被逆轉。例如給予雙歧桿菌治療后,GF小鼠的HPA軸得到逆轉。
上述研究表明,HPA軸可影響腸道菌群的平衡狀態,益生菌可逆轉HPA軸對腸道菌群的調控。Ferguson等[43]認為,ASD不但伴隨HPA應激后皮質酮表達升高,還有腸道菌群失調的胃腸道癥狀;唾液乳桿菌和香腸乳桿菌作為益生菌,可以治療動物應激后腸道菌群紊亂,逆轉皮質酮分泌和神經發育異常,增加神經可塑性[44]。
3 展望
腸道菌群與ASD關系的證實為治療ASD多了一種可以選擇的新手段。
目前針對腸道菌群與ASD關系已有的研究還尚不構成體系。科學家們正在逐步探索腸道微菌群對中樞神經的影響。隨著不斷的研究,腸道菌群對ASD行為學、遺傳、神經生化和免疫等方面的作用逐漸被揭示。
腸道微生物組通過對腸-腦軸的調節將可能成為ASD研究的熱點之一。相信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必將為腸道菌群與ASD之間關系找到更多的循證醫學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