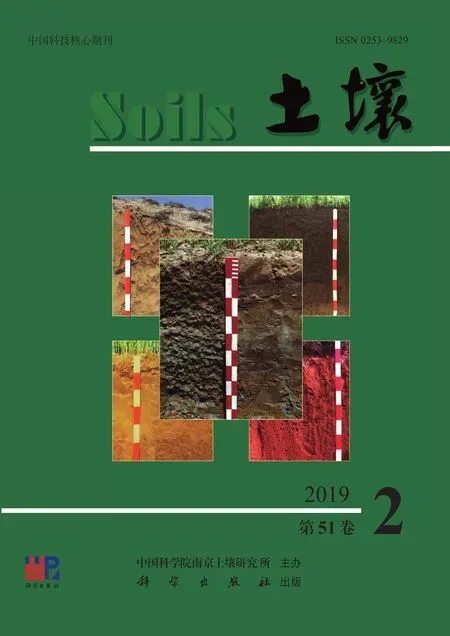關中塿土發(fā)生特性與分類研究進展①
齊雁冰,常慶瑞,黃 洋,劉夢云
?
關中塿土發(fā)生特性與分類研究進展①
齊雁冰,常慶瑞,黃 洋,劉夢云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資源環(huán)境學院,陜西楊凌 712100)
塿土是關中地區(qū)受人類活動影響深刻的重要農業(yè)土壤,而對其發(fā)生分類及系統(tǒng)分類的歸屬仍有較大爭議。本文綜述了塿土的形成過程和成土過程特點,塿土發(fā)生分類歸屬的變更,系統(tǒng)分類的主要診斷層、診斷特性和診斷現(xiàn)象,高級分類單元歸屬及空間分布,基層分類單元的主要診斷指標等方面的研究進展。在此基礎上,展望了塿土需要進一步開展的研究工作包括3個方面:①深入理解人為影響下塿土的成土過程,定量化分析覆蓋層的形成過程;②開展塿土覆蓋層厚度調查,界定堆墊表層的厚度標準;③進行土壤普查,建立塿土代表土系。
塿土;發(fā)生特性;系統(tǒng)分類;人為土;堆墊表層
塿土主要分布在陜西關中渭河兩側地勢平坦的高階地上,不但是我國最古老的耕種土壤之一,而且曾經(jīng)歷過長期與強烈的人為熟化過程,是典型的歷史自然體與勞動人民長期生產勞動的綜合體。通常認為該類土壤是在原褐土的基礎上,長期施用土糞而使表層不斷增厚致使原褐土剖面被埋藏,上層覆蓋層與原土壤層次在理化性質上截然不同,土壤發(fā)生過程改變,顯著區(qū)別于被埋藏的褐土[1]。塿土分布區(qū)素有800里秦川之稱,是我國人類活動開始較早、水熱資源優(yōu)越、土壤生產潛力大的地區(qū),同時南依秦嶺北接黃土高原,即是歷史上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發(fā)展農業(yè)的優(yōu)良基地。然而,由于典型的上下兩段式層次結構,長期以來針對塿土的發(fā)生學分類和系統(tǒng)分類常因概念模糊、界線不清的問題,一直爭議不斷[2],進而限制了塿土資源的科學利用,特別是隨著目前土壤系統(tǒng)分類基層分類工作的深入開展,為塿土建立科學的土壤系統(tǒng)分類體系已是必然趨勢。
自建國初期開始,國內外學者就對塿土的形成過程、分類歸屬進行過較多的調查與研究,從關中地區(qū)土壤類型的調查開始,對塿土這一長期受人為活動影響的農業(yè)土壤的覆蓋層形成過程及生產特性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描述[3-4],而塿土一名也是自1964年朱顯謨《塿土》[1]一書的出版而起,之后對塿土從發(fā)生分類到系統(tǒng)分類均進行過較多的闡述,這些調查與研究成果對于認識塿土的性質及其分類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和經(jīng)驗。然而,目前有關塿土的形成過程及其分類歸屬仍然存在較大的分歧,在發(fā)生分類階段塿土的歸屬就曾幾經(jīng)變更[2],到系統(tǒng)分類階段,塿土應歸為淋溶土綱(或雛形土綱)還是人為土綱仍然有較大的爭議。了解塿土的發(fā)生特性,建立完整的塿土系統(tǒng)分類體系,特別是土族和土系的基層分類是完善我國土壤分類體系及科學合理利用塿土的基礎性工作。基于此,本文綜述近年來塿土的發(fā)生特性、發(fā)生分類與系統(tǒng)分類研究進展,以期為推動塿土的系統(tǒng)分類研究提供依據(jù)。
1 塿土的發(fā)生特性
1.1 塿土的形成過程
關中平原位于秦嶺和渭北山系之間,系地塹式構造平原,是中華民族的發(fā)祥地和古代文明的搖籃。我國農民對于土壤的重視程度是其他民族無法比擬的,“精耕細作”、“種田如繡花”等深刻地描述了我國古代人民對于地表的利用與改造程度,強烈的人為活動對該區(qū)域自然資源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利用和改造非常深刻,對土壤的影響極為顯著,使該區(qū)域原自然土壤的形成過程遭到破壞,正常的土壤發(fā)育過程中斷,代之以人工熟化培肥過程產生,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土壤[1]。塿土的地球化學過程、特征與環(huán)境變化對塿土的系統(tǒng)分類、利用和改良均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際意義,并能反映特定的土壤形成過程及其相應的環(huán)境條件。
塿土剖面可以分為兩部分,一般認為下部為全新世早中期形成的自然土壤—— 褐土,它以晚更新世馬蘭黃土為形成母質,上部是風成黃土沉積和人類長期使用土糞堆墊并進行耕作熟化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堆墊層[1]。堆墊熟化層可分為現(xiàn)代耕作層、古熟化層、古耕層、古耕腐殖質層等多層結構。由于這種剖面組成的特殊性,使得塿土不同層次的性質反映了不同階段的成土環(huán)境。而有關堆墊層的形成目前比較統(tǒng)一的觀點是覆蓋層主要是人類長期施用土糞堆墊并進行耕作熟化的結果,但不排除黃土沉降及沙塵暴等自然影響[5]。龐獎勵等[6]的研究結果認為,堆墊層是2 000 a以來人類施加土糞、農業(yè)耕作活動和風塵堆積同時作用的綜合產物,其特征更多地受到人類活動強度和方式的控制。據(jù)潘繼花[7]的研究,塿土現(xiàn)代耕作層距今約3 100 a,埋藏耕作層距今約3 100 ~ 5 200 a,黏化層距今約3 100 ~ 8 600 a。而隨剖面層次由上到下,人為活動的影響逐漸減弱,到古耕層以下基本不受人為活動的影響[8]。杜鵑等[9]的研究表明,土糞施加是關中平原土壤耕作層堆墊增厚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在關中古代的土壤培肥過程中,休耕、草肥、蠶屎、人畜糞尿、舊墻土、綠肥種植是主要方式。漢至明代,農業(yè)生產中都實行以土拌糞的施肥方式,但表現(xiàn)出較強的種植方式與作物選擇的傾向性,在區(qū)田法以及蔬菜瓜果類經(jīng)濟作物的種植中才有施加土糞的記錄。清至民國時期,復種指數(shù)的顯著提高對地力要求更高,積制與施加土糞的過程明顯增強,這也是關中塿土上部覆蓋層快速堆墊的時期。在人為堆墊過程的同時總是伴隨著自然粉塵的堆積作用,但隨著農業(yè)發(fā)展水平及土地生產力需求的提高,土糞在土壤耕作層成土物質組成中的比例也會提高。關中平原水利灌溉的功效除補給水分以外,更為重要的作用在于灌溉攜帶的河流泥沙參與到土壤耕作層的形成與熟化過程中[10]。
堆墊層的厚度既是塿土肥力水平的表征,也是進行土壤系統(tǒng)分類時診斷層的重要依據(jù)。在堆墊層增厚的過程中,土糞中土的來源一般是村莊村民集中就近取土,這也是關中地區(qū)村莊附近現(xiàn)大量土壕的原因。劉鵬生[11]曾在楊凌附近(原西北農學院附近)約5 km2的范圍內對34個土壕進行了調查,計算出的土方量與堆墊層50 cm厚度所需土方量很接近。受到人為活動的影響,堆墊層厚度在空間上分布十分不均,無論在小尺度還是大尺度空間上差異非常明顯,最薄的僅25 cm左右,厚的可以達到100 cm以上。在大的空間尺度上人類活動越早、人口越密集的地區(qū)堆積越厚,如安戰(zhàn)士[3]在有關關中平原土壤調查的介紹中指出,古耕灰褐土(后稱為塿土)以武功、興平、咸陽、西安一帶堆墊層最厚,其次為鳳翔、扶風、寶雞一帶,而西安以東渭南南塬最薄;在小尺度空間上,劉鵬生[11]在楊凌的崔東溝、曹辛莊和杜寨等村莊的調查結果顯示,堆墊層厚度隨距離村莊距離的增大而降低,在村莊0 ~ 20 m的距離內,堆墊層厚度在55 ~ 94 cm,而距離村莊500 m后堆墊層厚度降低至35 cm。
1.2 塿土的成土過程
塿土分布在關中平原平坦的階地上,成土母質為黃土性沉積物。分布區(qū)屬暖溫帶半濕潤季風氣候,以落葉闊葉林植被為主。塿土的典型兩段式層次結構表明,塿土的成土過程是在自然成土過程與人為成土過程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據(jù)此,可以將塿土的成土過程劃分為自然成土過程、人為成土過程與自然-人為復合過程3個方面。剖面的下段為原褐土,成土過程以自然成土過程為主,幾乎不受人為活動的影響;上段為堆墊層,主要是人為成土過程;在堆墊層與褐土過渡段則為自然-人為復合過程。
原褐土段的自然成土過程主要包括黏化過程和鈣積過程[12]。黏化過程是褐土的主要成土過程,在濕熱與干濕交替的季風氣候條件下,土體內風化發(fā)育強烈,原生礦物分解成次生黏土礦物,黏土礦物因遇水失鈣分散而隨水分下滲,發(fā)生機械淋溶,在下部一定深度內淀積而形成明顯的黏化層。鈣積過程是在黃土母質中碳酸鈣隨水分向下淋溶與聚集基礎上形成鈣積層。在雨季土體內碳酸鹽和重碳酸鹽隨水分下行發(fā)生淋溶,到干旱季節(jié)可溶性碳酸鹽又隨毛管水上行而在黏化層下部淀積。
人類在褐土表層將自然植被轉變?yōu)樵耘嘀脖坏倪^程也就將褐土的自然成土過程為主轉變?yōu)楝F(xiàn)代人為耕作堆墊過程為主的過程,因此現(xiàn)代塿土的成土過程以熟化過程為主。這種熟化是以人為在原褐土表層長期施加土糞、翻耕、灌溉、栽培、收割的影響下,把土壤推向更適宜于生產要求并漸漸受人為控制和改造的旱耕熟化過程[2]。長期人為堆墊熟化的結果是在原土壤頂部覆蓋一定厚度的比較疏松多孔的土層,該覆蓋層常能觀察到炭渣、瓦片等侵入體。
在覆蓋層逐漸形成并漸進增厚的過程中,由于堆墊層的主要物質來源—— 土糞是農戶將黃土與作物秸稈、廄肥等相結合發(fā)酵的產物,黃土中含大量的碳酸鈣,在雨季可溶性碳酸鹽隨水向下淋溶,并在覆蓋層與褐土層過渡段形成碳酸鈣淀積層,此過程稱為復鈣過程[13]。此復鈣過程中的碳酸鈣來源則是人為作用的產物,而碳酸鈣的淋溶和淀積則是自然過程帶來的,因此此復鈣過程是自然與人為復合作用的結果。因此,在典型的塿土剖面上能夠觀測到位于覆蓋層與褐土層過渡層段的鈣積層和位于褐土黏化層之下的鈣積層。
2 塿土的發(fā)生分類
塿土的兩段式結構自有關中土壤調查以來就已被得到一致認可,但有關其名稱及分類卻幾經(jīng)變更。有關關中渭河流域土壤分布在我國一些古代著作中已有提及,《禹貢》和《管子地員篇》中均將此地土壤稱為“壚土”[1],則是因為先秦時期人類活動對土壤的影響還較小,土表覆蓋層較薄,剖面上僅形成“壚土層”。1949年以前國內外多位學者在關中地區(qū)進行土壤調查,均錯誤地認為覆蓋層是風和水的新近沉積物,稱此地主要土壤為栗鈣土和埋藏栗鈣土[14-16]。1958—1959年西北農學院對關中渭河流域的土壤開展了詳細調查[3-4],這次調查雖然糾正了前期對于覆蓋層成因的認識,但對于成土過程的認識不夠深入,而認為該地區(qū)土壤為耕灌灰褐土或古耕灰褐土。直到1964年朱顯謨先生借鑒群眾的叫法稱此地土壤為塿土,并出版《塿土》一書,對塿土覆蓋層的形成、塿土的成土過程、理化性質、改良利用進行了詳細描述,塿土的名稱才被正式確定下來并被眾多學者所了解。之后,施衛(wèi)省[13]對塿土的發(fā)生特性和區(qū)域分異開展了深入研究。
對于塿土的發(fā)生分類的分歧也一直圍繞塿土作為獨立的土類還是其母土——褐土土類的亞類。《塿土》一書將塿土作為一個土類,分為立茬土、油土、壚土和黃墡土4個亞類[1]。第一次全國土壤普查,塿土被作為一個獨立的土類,但1965年其又被作為一個亞類。第二次土壤普查初期,塿土被作為一個單獨土類,并將其分為壚塿土、立茬塿土、油塿土、黑瓣塿土4個亞類[2, 7],相應出版的《陜西農業(yè)土壤》將塿土土類劃分為油土、壚土、立茬土、黃塿土、淤塿土和斑斑塿土6個亞類[17],地區(qū)性土壤著作《西安土壤》①和《武功土壤》[18]也將塿土作為獨立土類。20世紀80年代中期,為了全面總結第二次全國土壤普查成果并對土壤分類制定統(tǒng)一標準,在昆明制定了“中國土壤分類系統(tǒng)”,此分類系統(tǒng)將塿土作為褐土的亞類確定下來,相應的《陜西土壤》[12]、《中國土壤普查技術》[19]和《中國土壤(第二版)》[20],以及此后的有關土壤地理學教材都把塿土劃為褐土的亞類。《陜西土壤》中將塿土亞類劃分為油土、紅塿土、灰塿土、立茬土、斑斑土和塿墡土6個土屬[12]。2001年,常慶瑞等[2]就塿土的發(fā)生分類歸屬的討論認為,覆蓋層厚度>50 cm可以將塿土作為一個獨立土類,如果<50 cm,則歸為褐土的亞類。自此之后,未再見有關塿土發(fā)生分類的相關報道。
3 塿土的系統(tǒng)分類
3.1 塿土在系統(tǒng)分類中的歸屬
人為活動對土壤的影響深刻,為了體現(xiàn)人類農業(yè)生產活動對土壤的影響,世界土壤資源參比基礎(WRB)土壤分類中根據(jù)中國土壤學家的意見,采用了灌淤層、堆墊層、草墊層、厚熟層和水耕層系列診斷層劃分出灌淤土、草墊土(歐洲堆墊土)、堆墊土、厚熟土和水耕人為土(水稻土)[21]。美國土壤系統(tǒng)分類中盡管未在土綱級別上單獨列出人為土土綱,但在診斷層上設立有人為表層、草墊表層,并設立人為擾動和人為轉運物質等特性,在相應的人為擾動正常新成土及厚層始成土中均有體現(xiàn)[22]。1999年,我國土壤系統(tǒng)分類明確設定人為土土綱,下設水耕人為土和旱耕人為土兩個亞綱,旱耕人為土中專門針對塿土,設立了土墊旱耕人為土土類。而實際上在此之間,有關塿土在系統(tǒng)分類中的歸屬幾經(jīng)變更,1985 年《中國土壤系統(tǒng)分類初擬》[23]將塿土列為半干潤硅鋁土亞綱的獨立土類,下設典型塿土、淋溶塿土、石灰性塿土和潮塿土4個亞類。1987 年《中國土壤系統(tǒng)分類(二稿)》[24]將其更改為典型塿土和潮塿土兩個亞類,而1991 年出版的《中國土壤系統(tǒng)分類(首次方案)》[25]將塿土劃歸人為土亞綱下的土類,也在新成土土綱中設置了人為新成土亞綱,到2002年的《中國土壤系統(tǒng)分類(第三版)》[26]中將符合檢索條件的塿土歸為土墊旱耕人為土,如果不符合檢索標準的,基本劃歸為淋溶土或雛形土。如閆湘等[27]采集的6個塿土剖面中有5個劃歸為土墊旱耕人為土,另1個塿土則因堆墊層厚度未達到50 cm而被劃歸為鈣積干潤淋溶土。
3.2 塿土的高級分類單元
土壤系統(tǒng)分類中高級單元主要反映土壤發(fā)生過程,即體現(xiàn)較長時間尺度和較大空間尺度上的成土因素的影響[26]。塿土診斷層及診斷特性也備受學者們的關注[28-30]。作為受人類活動影響深刻、具有典型堆墊層次的塿土,其系統(tǒng)分類首要的診斷層就是堆墊表層,在一些長期種植蔬菜的塿土表層可能形成肥熟表層,對于覆蓋層厚度不足50 cm的塿土其表層稱堆墊現(xiàn)象;對于表下層,除長期耕作形成的耕作墊積層(犁底層)外,其余診斷表下層基本與淋溶土或雛形土一致,如黏化層、鈣積層或雛形層。診斷特性相對簡單,塿土分布區(qū)土壤溫度基本屬于溫性土壤溫度狀況,半干潤土壤水分狀況,并具有石灰性,個別地下水位稍高地方還會有氧化還原特性,甚至在一些地方還會有鹽積現(xiàn)象。
目前對于塿土發(fā)生過程的認識已經(jīng)較為充分,診斷層及診斷特性已較完備。土綱主要包括人為土、淋溶土和雛形土。塿土的高級分類單元歸并的關鍵在于覆蓋層的厚度,按照《中國土壤系統(tǒng)分類(第三版)》[26]的檢索標準,只有覆蓋層超過50 cm的才被劃歸為堆墊表層,而在塿土分布區(qū),據(jù)前人的調查結果推斷能劃歸為土墊旱耕人為土的塿土主要分布在關中中部地區(qū),具體包括扶風-楊凌-興平-咸陽-西安一帶,此段內南北方向上平原較寬,地表平整度較高,土墊旱耕人為土連片分布;此帶向西能歸為土墊旱耕人為土的塿土在連續(xù)性上逐漸減少,在南北靠近秦嶺和臺塬區(qū)的地方堆墊層逐漸變薄,達不到堆墊表層的標準,而應歸屬干潤淋溶土;向東平原也逐步變窄,降水較平原中部和西部少,劃歸為土墊旱耕人為土的塿土的連片性也逐漸降低,覆蓋層厚度達不到堆墊表層標準的塿土通常劃歸為干潤雛形土。
3.3 塿土的基層分類單元
土壤基層分類體現(xiàn)小空間尺度及短期時間尺度上成土因素作用的變異性,我國土壤基層分類的整體架構已經(jīng)完備,而在實踐上對于土族和土系的調查正在逐步推進,特別是國家科技基礎性工作專項項目“我國土系調查與《中國土系志》編制”的實施,土壤的基層分類將會取得很大進步,而關中塿土區(qū)的土族和土系劃分目前僅見閆湘等[31]報道的9個土壤剖面,9個剖面劃歸9個土族和9個土系。同時這些基層分類的報道是在《中國土壤系統(tǒng)分類土族和土系劃分標準》[32]發(fā)表之前,其土族和土系歸并時在鑒別特征、命名等方面仍需進一步完善。
《中國土壤系統(tǒng)分類土族和土系劃分標準》[32]一文中提出的礦質土壤土族鑒別應包括4個特征:①顆粒大小級別與替代;②礦物學類型;③石灰性和酸堿反應類別;④土壤溫度等級。塿土分布區(qū)地表相對平整,土層深厚,一般都在200 cm以上,均達到劃分土系控制層段(0 ~ 150 cm)的標準;在土壤顆粒大小級別與替代上,塿土土壤母質一般為黃土,發(fā)育不是很強,土壤質地一般為壤土,土族顆粒大小級別可以區(qū)分出壤土和黏壤土兩類;因顆粒大小級別為“壤土或黏壤土”,“25 ~ 100 cm”土體的0. 02 ~ 2 mm部分原生礦物以石英(50% 左右)和長石(20% 左右)為主[33],介于40% ~ 90%,依據(jù)顆粒大小級別檢索的礦物學類型可以檢索到硅質混合型或混合型;塿土呈現(xiàn)弱堿性反應,pH通常在7.5 ~ 8.5,在發(fā)育較強的剖面上黏化層段無石灰反應,發(fā)育稍弱的通體有石灰反應,因此石灰性和酸堿反應類別可以檢索出石灰性或非酸性;塿土分布區(qū)屬暖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年平均氣溫12 ~ 14℃,平均土溫在15.6 ~ 16℃[34],對應的土壤溫度等級應為溫性。
4 展望
塿土是我國為數(shù)不多的受人類農業(yè)生產活動影響深刻的重要土壤類型,對其形成特征、成土過程、發(fā)生特性及發(fā)生分類和系統(tǒng)分類研究盡管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盡管目前人為因素對成土過程的影響已經(jīng)引起高度重視,土壤系統(tǒng)分類的推進也是土壤學科發(fā)展的趨勢[35],但是針對塿土仍然需要在以下幾方面進一步深入地開展研究。
1)深入理解人為影響下塿土的成土過程,定量化分析覆蓋層的形成過程。關中平原在長期農業(yè)活動如堆積、灌溉、施肥和耕作等影響下塿土所發(fā)生的變化及其在分類中的位置等研究工作必將在現(xiàn)有的基礎上繼續(xù)深入和發(fā)展[36]。深厚的覆蓋層是塿土之所以區(qū)別于其母土的根本,對于覆蓋層的形成目前一致的結論是人為土墊是主要成因,但這些有關成因的描述基本上不外乎兩點,一是從剖面上觀察發(fā)現(xiàn)有磚頭、瓦片、炭渣等人為活動的痕跡,另一方面則是從相關農業(yè)或地理書籍中有關農業(yè)生產的記載來推斷,缺乏對于覆蓋層形成原因的定量分析。現(xiàn)代碳同位素測年技術可以測定堆墊層中的侵入體如炭渣、瓦塊等的相對年齡,據(jù)此可以推斷塿土覆蓋層的形成時代及年平均堆墊厚度;土壤薄片微形態(tài)、光譜特征和現(xiàn)代儀器分析有助于增加土壤發(fā)生機理的新認識。
2)開展塿土覆蓋層厚度調查,界定堆墊表層的厚度標準。覆蓋層厚度是塿土系統(tǒng)分類歸屬的重要依據(jù),《中國土壤系統(tǒng)分類(第三版)》中堆墊表層的厚度標準是≥50 cm,而厚度在20 ~ 50 cm被認為是堆墊現(xiàn)象。在塿土系統(tǒng)分類檢索實踐中發(fā)現(xiàn)按照目前的標準,塿土剖面的覆蓋層厚度能夠達到堆墊表層的數(shù)量明顯較少,很多被認為非常典型的塿土剖面由于厚度達不到50 cm而難以被檢索為土墊旱耕人為土,以至于很多學者對于塿土有沒有必要被檢索為人為土,甚至有沒有必要專門針對塿土設定土墊旱耕人為土提出異議[37]。在《世界土壤資源參比基礎(WRB)》[38]及《美國土壤系統(tǒng)分類(ST)》中也均設有人為表層,前者對人為表層的定義為受人為活動(濕耕作)改變而形成擾動層和犁底層的土壤表層,并規(guī)定厚度≥15 cm,后者對人為表層的定義為在人為擾動或人為轉運物質影響下形成的表層,規(guī)定厚度≥25 cm,由此可見二者對人為表層的含義與《中國土壤系統(tǒng)分類(第三版)》一致,但厚度均低于我國的規(guī)定。吳克寧等[39]也對含人工制品的土壤的分類問題開展了研究。因此開展塿土覆蓋層厚度調查,重新界定堆墊層厚度標準顯得尤為重要,從而為《中國土壤系統(tǒng)分類(第三版)》的修訂提供依據(jù)。
3)進行土壤普查,建立塿土代表土系。目前基于發(fā)生分類的塿土空間分布、發(fā)生特性已經(jīng)開展過較多的調查和研究,而基于系統(tǒng)分類的塿土高級單元及基層單元空間分布狀況則報道甚少,且目前對其系統(tǒng)分類的歸屬仍有一定的爭議,因此非常有必要深入開展塿土分布區(qū)的土壤普查,在高級單元上掌握空間分布規(guī)律,基層單元上建立代表土系。
(謹以此文紀念塿土的提出者朱顯謨院士)
[1] 朱顯謨. 塿土[M]. 北京: 農業(yè)出版社, 1964: 1–169
[2] 常慶瑞, 閆湘, 雷梅, 等. 關于塿土分類地位的討論.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J]. 2001, 29(3): 48-52
[3] 安戰(zhàn)士. 陜西關中的土壤概況[J]. 西北農學院學報, 1959(3): 27–40
[4] 耿成杰, 李遠清, 劉廷立. 關中渭河流域兩岸的土壤及其改良利用[J]. 土壤通報, 1959(4): 20–27
[5] 龐獎勵, 黃春長. 黃土-古土壤序列的典型微結構與1萬年來的環(huán)境演化——以關中地區(qū)的全新世黃土剖面為例[J]. 吉林大學學報(地球科學版), 2002, 32(3): 268–273
[6] 龐獎勵, 黃春長, 查小春, 等. 關中地區(qū)塿土診斷層的形成過程及意義探討[J]. 中國農業(yè)科學, 2008, 41(4): 1064–1072
[7] 潘繼花. 土墊旱耕人為土發(fā)生特性的演變[D]. 南京: 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2008
[8] 潘繼花, 張甘霖. 典型土墊旱耕人為土主要常量元素的遷移富集特征、成因及其意義[J]. 土壤通報, 2013, 44(1): 14–20
[9] 杜鵑. 關中平原土壤耕作層形成過程研究[D]. 陜西西安: 陜西師范大學, 2014
[10] 龐獎勵, 張衛(wèi)青, 黃春長, 等. 關中地區(qū)不同耕作歷史土壤的微形態(tài)特征及對比研究[J]. 土壤通報, 2009, 40(3): 476–481
[11] 劉鵬生. 關中塿土的土體構造及其肥力[J]. 西北農學院學報, 1980(1): 17–29
[12] 陜西省土壤普查辦公室. 陜西土壤[M]. 北京: 科學出版社, 1992: 1–630
[13] 施衛(wèi)省. 塿土的發(fā)生特性和區(qū)域分異規(guī)律的研究[D]. 陜西楊陵: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1994
[14] 周昌蕓. 陜西渭河流域土壤調查報告[J]. 土壤專報, 1935(9): 24–28
[15] 梭頗. 中國之土壤[J]. 土壤季刊, 1936(1): 1–21
[16] 王文魁. 徑渭流域土壤及其利用[J]. 土壤季刊, 1945(3): 34–39
[17] 陜西省農業(yè)勘察設計院. 陜西農業(yè)土壤[M]. 西安: 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 1982: 1–290
[18] 陜西省農業(yè)區(qū)劃辦公室, 中國科學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武功土壤[M]. 西安: 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 1987: 1– 226
[19] 全國土壤普查辦公室. 中國土壤普查技術[M]. 北京: 農業(yè)出版社, 1992: 1–243
[20] 熊毅. 中國土壤(第二版)[M]. 北京: 科學出版社, 1987: 1–746
[21] 龔子同, 陳志誠, 張甘霖. 世界土壤資源參比基礎(WRB):建立和發(fā)展[J]. 土壤, 2003, 35(4): 271–278
[22] Soil Survey Staff. Keys to soil taxonomy. 12th ed.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Nat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Service.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4: 1–372
[23] 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分類課題組. 中國土壤系統(tǒng)分類初擬[J]. 土壤, 1985, 17(6): 290–318
[24] 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土壤分類課題組. 中國土壤系統(tǒng)分類(二稿). 土壤學進展(土壤系統(tǒng)分類研討會特刊)[J]. 1987: 69–104
[25] 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分類課題組和研究協(xié)作組. 中國土壤系統(tǒng)分類(首次方案)[M]. 北京: 科學出版社, 1991: 1–112
[26] 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土壤系統(tǒng)分類課題組, 中國土壤系統(tǒng)分類課題研究協(xié)作組. 中國土壤系統(tǒng)分類檢索(第三版)[M]. 合肥: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 2001: 1–275
[27] 閆湘, 常慶瑞,潘靖平. 陜西關中地區(qū)塿土在系統(tǒng)分類中的歸屬[J]. 土壤, 2004, 36(3): 318–322
[28] 史成華, 龔子同. 塿土的診斷層和診斷特性//《中國土壤系統(tǒng)分類研究叢書》編委會編. 中國土壤系統(tǒng)分類新論[C]. 北京:科學出版社, 1994: 158–162
[29] 田積瑩, 雍紹萍, 賈恒義. 塿土土體構型及其診斷特性的探討//《中國土壤系統(tǒng)分類研究叢書》編委會編. 中國土壤系統(tǒng)分類新論[C]. 北京: 科學出版社, 1994: 153–157
[30] 閆湘. 關中地區(qū)土壤發(fā)生特性與系統(tǒng)分類研究[D]. 陜西楊陵: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1999
[31] 閆湘, 常慶瑞, 王曉強, 等. 陜西關中土墊旱耕人為土樣區(qū)的基層分類研究[J]. 土壤學報, 2005, 42(4): 537–544
[32] 張甘霖, 王秋兵, 張鳳榮, 等. 中國土壤系統(tǒng)分類土族和土系劃分標準[J]. 土壤學報, 2013, 50(4): 826–834
[33] 潘德?lián)P. 黃土[M]. 北京: 地質出版社, 1958: 1–102
[34] 劉姣姣, 齊雁冰, 陳洋, 等. 陜西省土壤溫度和水分狀況估算[J]. 土壤通報, 2017, 48(2): 335–342
[35] 潘繼花, 張甘霖. 土墊旱耕人為土中磷的分布特征及其土壤發(fā)生學意義[J]. 第四紀研究, 2008, 28(1): 43–49
[36] 龔子同, 張甘霖. 人為土研究的新趨勢[J]. 土壤, 1998, 30(1): 54–56
[37] 張甘霖, 史學正, 龔子同. 中國土壤地理學發(fā)展的回顧與展望[J]. 土壤學報, 2008, 45(5): 792–801
[38]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World reference base for soil resources 2014[M]. Rome, 2015: 1–203
[39] 吳克寧, 高曉晨, 查理思, 等. 河南省典型含有人工制品土壤的系統(tǒng)分類研究[J]. 土壤學報, 2017, 54(5): 1091– 1101
①西安市土壤普查辦公室,西安市土壤肥料工作站. 西安土壤(內部資料). 1988
Review on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lassification of Lou Soil in Guanzhong Area
QI Yanbing, CHANG Qingrui, HUANG Yang, LIU Mengyun
(Colleg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
Lou soil, which i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is an important agricultural soil in the Guanzhong area of Shaanxi Province, but disputes still exist nowadays on its genetic process and classification in recent years. In this paper, we reviewed the soil formation process and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summarized the alteration of Lou soil in the genetic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 the past years, identified the diagnostic horizons, diagno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diagnostic evidences in Chinese Soil Taxonomy, predict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enior taxon (soil order, suborder, group and subgroup) in the area and established the diagnostic indicators for the basic taxon (soil family and series) in Chinese Soil Taxonomy for Lou soil. Finally, three future research focuses were proposed for the Lou soil: 1) Further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s of human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on Lou soil formation process to quantitively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cumulic epipedon; 2) Study the thickness of the cumulic epipedon to determine the scientific depth criteria of the cumulic epipedon in Chinese Soil Taxonomy; 3) Conduct soil survey to establish the representative soil series of Lou soil.
Lou soil; Soil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oil Taxonomy; Anthrosols; Cumulic epipedon
陜西省自然科學基礎研究計劃項目(2017JM4016)資助。
齊雁冰(1976—),男,河南淮陽人,博士,副教授,主要從事土地資源與空間信息技術方面的教學與研究工作。E-mail: ybqi@nwsuaf.edu.cn
10.13758/j.cnki.tr.2019.02.001
S15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