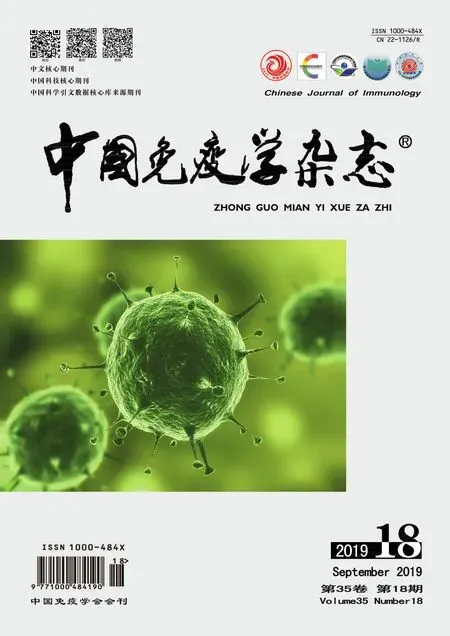IRF3在抗病毒固有免疫應答中的作用及調控機制①
季曉麗 張毓川 陳 瑋
(浙江大學醫學院免疫研究所,杭州310058)
固有免疫系統通過模式識別受體(Pattern-recognition receptors,PRR)識別病原體相關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或危險相關分子模式(Danger-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DAMP),這是機體抵御病原微生物入侵的第一道防線。PRR如Toll樣受體(Toll-like receptors,TLRs)、RIG-Ⅰ樣受體[Retinoic acid inducible gene-Ⅰ(RIG-Ⅰ)-like receptors,RLRs]、環鳥苷酸-腺苷酸合成酶[cyclic GMP-AMP (cGAMP) synthase,cGAS]等,識別相應的病毒RNA或DNA后啟動信號轉導,并誘導產生大量的Ⅰ型干擾素(Interferon,IFN),進而發揮強大的抗病毒效應[1]。作為機體固有免疫應答的關鍵轉錄因子,干擾素調節基因3(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s 3,IRF3)在抵抗和控制病毒感染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IRF3是IRF家族的一員,目前發現該家族有10個成員,分別是IRF1-IRF9和病毒IRF(v-IRF)。人源IRF3基因長約6.3 kb,編碼的蛋白質含有427個氨基酸,分子質量約55 kD。IRF3主要有3個結構域,為DNA結合結構域(DNA-binding domain,DBD)、轉錄活化結構域(Transcription activation domain,TAD)和羧基末端調節域(C-terminal regulatory domain,RD)。TAD包含核輸出序列(Nuclear export signal,NES)、核定位序列(Nuclear localization signal,NLS)、脯氨酸富含區和IRF相關結構域(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associated domain,IAD)。DBD是家族共同的保守結構域,位于蛋白的氨基端(N端),呈螺旋-轉角-螺旋的結構,具有與DNA結合的功能。除IRF1、IRF2外,其他IRFs都具有IAD,可與自身或其他家族成員形成同源或異源二聚體,也能與其他轉錄因子相互結合促進基因轉錄[2]。此外,IRF3 RD區的磷酸化位點與IRF3的活化息息相關[3]。
IRF3與IRF7具有高度同源性,都是調節Ⅰ型IFN合成的轉錄因子,但兩者在固有免疫應答中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其中,IRF3呈組成性表達,即在大部分組織中廣泛表達,且基本不受IFN表達的影響。與IRF3不同,IRF7僅表達于一小部分免疫細胞中,并且其表達依賴于IFN的表達。此外,IRF7的半衰期非常短。病毒感染后,在大部分細胞中,IRF3對早期誘導IFN的表達至關重要;IRF7對后期放大IFN的抗病毒效應發揮作用。IRF7能同時誘導IFNα和IFNβ的表達,而IRF3能夠誘導IFNβ基因,但不能誘導除IFNα4外的其他IFNα的表達[4]。
研究表明,IRF3能夠抵抗腦心肌炎病毒(Encephalomyocarditis virus,EMCV)、仙臺病毒(Senda virus,SeV)、水皰型口炎病毒(Vesicular stomatitis virus,VSV)等RNA病毒的感染,對單純皰疹病毒(Herpes simplex virus,HSV)Ⅰ型和Ⅱ型等DNA病毒感染也有抵抗作用。當IRF3基因缺失時,小鼠對上述幾種病毒的耐受性明顯低于正常小鼠。此外,IRF3缺失的胚胎成纖維細胞(Mouse embryonic fibroblasts,MEF)在病毒感染條件下誘導產生的Ⅰ型IFN數量顯著降低[5]。因此,IRF3是抗病毒免疫應答的核心轉錄因子,在機體抵抗病毒的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1 三條信號通路通過活化IRF3促進Ⅰ型IFN的產生
PRR如 TLRs、RLRs和cGAS等識別相應的病毒RNA或DNA后啟動信號轉導,招募相應的接頭蛋白β干擾素TIR結構域銜接蛋白(TIR domain containing adapter-inducing interferon β,TRIF)、線粒體抗病毒信號蛋白(Mitochondrial antiviral signaling protein,MAVS)和干擾素基因刺激分子(Stimulator of interferon genes,STING),活化下游的蛋白激酶TANK結合激酶1(TANK-binding kinase 1,TBK1),進一步促進IRF3磷酸化以及Ⅰ型IFN的產生[6,7]。然而,研究表明三條信號通路對IRF3的活化并非單一的逐級傳遞,而是TLR3/TLR4-TRIF、RIG-Ⅰ-MAVS、cGAS-STING與激酶TBK1、E3泛素連接酶TRAFs和轉錄因子IRF3/7等組成功能性復合體,彼此之間相互活化,形成復雜的信號網絡[8]。
總體來講,MAVS/STING/TRIF介導的IRF3的活化有這樣一個模型:①接頭蛋白和激酶的活化:RIG-Ⅰ、cGAS和TLR3/4活化后激活下游的接頭蛋白MAVS/STING/TRIF,繼而招募和激活TBK1/IKKε;②接頭蛋白的磷酸化:招募的激酶TBK1/IKKε反過來使接頭蛋白MAVS/STING/TRIF的保守序列發生磷酸化;③IRF3的募集:IRF3通過其保守的帶正電荷的表面與磷酸化的接頭蛋白MAVS/STING/TRIF結合;④IRF3的磷酸化:TBK1/IKKε因與接頭蛋白相互結合而與IRF3在結構上相互靠近,TBK1/IKKε可高效地誘導IRF3磷酸化;⑤IRF3自身結構改變:磷酸化后的IRF3即使擁有正電荷表面,也能從復合體中解離且發生二聚化,進入細胞核與NF-κB共同促進Ⅰ型IFN和細胞因子的表達[8]。
活化的IRF3形成同二聚體或與IRF7形成異二聚體,與NF-κB、轉錄共刺激分子CBP/p300等形成全復合體,進入細胞核啟動Ⅰ型IFN的轉錄。IRF3的DBD區識別并結合IFN啟動子區域的DNA序列GAAANNGAAANN,該序列被稱為IFN刺激應答元件(IFN-stimulated response element,IRSE),又被稱為IFN啟動子正向調控元件Ⅰ和Ⅲ(Positive regulatory domainⅠ-Ⅲ,PRDⅠ-Ⅲ)[9]。這些基因序列最初被發現與IFN的刺激基因相關,后又發現與自身IFN的啟動基因也同樣相關。因此,IRF3不僅能促進轉錄IFNβ和IFNα4,也能轉錄 IFIT1、CXCL9、CXCL10 和CCL5等IFN的刺激基因(IFN-stimulated genes,ISGs)。與其他轉錄信號通路一致,IFN基因的轉錄需要組蛋白的乙酰化修飾。組蛋白乙酰轉移酶CBP、p300、β-catenin、P300/CBP相關因子(P300/CBP-associated factor,PCAF)等作為IRF3的共刺激分子,能夠將核小體乙酰化。組蛋白乙酰化修飾改變核染色質的結構,同時RNA酶被招募到啟動子區域,從而有效地啟動基因轉錄。最新研究表明,轉錄因子發生二聚化后,如IRF3同二聚體或IRF3/7異二聚體,才能夠觸發p300解除自我抑制,導致p300的活化,發揮乙酰轉移酶的活性[10]。
IFNα和IFNβ是主要的Ⅰ型IFN,在抗病毒免疫中占據中心位置。IFNα和IFNβ通過異源二聚體IFNAR1和IFNAR2,激活Janus 激酶(JAK)1,誘導下游的信號轉導子和轉錄激活子(STAT)1及STAT2發生磷酸化,繼而誘導表達三百多種ISGs,如IRF7、Mx1、雙鏈RNA依賴性蛋白激酶(PKR)、ISG56、ISG15等。這些ISGs能夠抑制病毒生存、促使感染細胞死亡、活化固有免疫細胞并促進適應性免疫應答,從而最終控制病毒的感染[11]。
2 IRF3的活化與修飾
當細胞處于靜息狀態時,由于IRF3的NES起主導作用,IRF3主要定位于細胞質中,呈無活性的單體形式。位于胞質中的IRF3的IAD兩端自身抑制元件與IAD形成緊密的疏水結構區,掩蓋了位于IAD結構域內關鍵氨基酸殘基,致使IRF3處于自身抑制狀態[3]。
通過晶體結構分析發現,IRF3-C端(190~427)與SMAD家族的Mad同源域2(Mad homology 2,MH2)結構相似。做為被人們熟知的磷酸化結合結構域,MH2含有帶正電荷的表面,由幾組保守的氨基酸殘基組成,正是正電荷表面對SMAD與磷酸化的TGF-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受體相結合以及SMADs發生磷酸化、二聚化至關重要。與MH2相似,IRF3-C端也含有幾組保守的氨基酸殘基,分別為R211/R213、R255/R262/H263、R285/H288/H290、K360/R361,組成了帶正電荷的表面。研究證實,IRF3能夠與磷酸化的接頭蛋白MAVS/STING/TRIF結合與上述幾組氨基酸有關。將這幾組氨基酸突變后,將影響IRF3與接頭蛋白MAVS/STING/TRIF結合,繼而影響IRF3的磷酸化和二聚化。通過生化分析和細胞實驗發現,接頭蛋白MAVS/STING/TRIF的C端擁有共同的保守的pLxIS序列(p:親水氨基酸殘基,x:任何氨基酸,S:發生磷酸化的氨基酸位點),該序列能夠被激酶TBK1/IKKε磷酸化。只有磷酸化后的接頭蛋白MAVS/STING/TRIF才能招募IRF3,從而使IRF3被TBK1/IKKε磷酸化。IRF3-C端被上游激酶磷酸化后,通過電荷的排斥作用,IRF3的構象發生巨大變化,暴露出疏水活性中心以及關鍵的氨基酸殘基,導致IRF3活化。活化的IRF3即使擁有正電荷表面,也能使IRF3從復合體中解離且發生二聚化[8,12]。
2.1IRF3的磷酸化 IRF3-C端的磷酸化在IRF3的活化中起決定性的作用。TBK1/IKKε是IRF3上游的兩個同源蛋白激酶,病毒入侵后,在接頭蛋白MAVS/STING/TRIF的招募下,能夠直接磷酸化IRF3的C端。IRF3的活化主要受到C末端雙重磷酸化的調控,絲氨酸(Ser,S)385/386構成第一組磷酸化位點(GⅠ),Ser396/398/402/404和蘇氨酸(Thr,T)404這5個重要的磷酸化位點組成第二組(GⅡ),同時將GⅠ和GⅡ磷酸化才能夠使IRF3完全活化。研究表明,GⅠ對IRF3的二聚化非常重要,將絲氨酸385/386突變成丙氨酸后,IRF3將不能發生二聚化。GⅡ的磷酸化則是解除IRF3自身抑制以及與共刺激分子CBP結合的關鍵[13]。其中Ser396位點最為關鍵,點突變實驗驗證,僅Ser396的磷酸化即可誘導IFNβ表達。目前猜測,TBK1誘導IRF3 磷酸化的激活分為兩步,首先TBK1磷酸化IRF3的GⅡ位點,解除了IRF3自身抑制,使得共刺激分子CPB與IRF3結合;其次CPB促進TBK1磷酸化IRF3的GⅠ位點,使得IRF3發生二聚化。
IRF3的磷酸化也能負向調控自身的活化。第一個被發現對IRF3進行負調控的激酶是Mst1(Mammalian sterile 20-like kinase 1)。Mst1屬于Mst家族,是廣泛表達的絲、蘇氨酸激酶。Mst1與IRF3結合并介導了IRF3 Thr75和Thr253的磷酸化。Thr253的磷酸化會使IRF3發生空間位阻和靜電排斥,從而影響IRF3發生二聚化。而IRF3 Thr75靠近核定位序列,同時位于DBD區域,從而影響IRF3的定位以及與DNA結合的功能。此外,Mst1阻礙了TBK1的磷酸化,進一步阻止了IRF3的磷酸化。因此,Mst1阻礙了IRF3的活化磷酸化、同源二聚化,并影響其轉錄功能[14]。病毒感染后,IRF3-C端發生活化磷酸化,之后IRF3的Ser339發生磷酸化,促進Pin1(Peptidyl-prolylcis 1)對IRF3的泛素化以及降解,從而抑制了Ⅰ型IFN的產生。然而,IRF3 Ser339的激酶和其泛素化位點尚不明確。最新研究表明,腫瘤細胞產生的外泌體能夠負向調控固有免疫,其機制就是MEKK2能夠使IRF3 Ser173位蛋白磷酸化,繼而Lys77發生K33的泛素化,阻礙IRF3的二聚化以及入核過程[15]。
IRF3的活化依賴復雜的磷酸化蛋白組,因此,磷酸酶能對IRF3進行調控并不令人驚訝。研究發現,蛋白磷酸酶1(Protein phosphatase 1,PP1),最廣泛的磷酸酶之一,能夠直接與IRF3結合,并使Ser385和Ser396發生去磷酸化,從而減少Ⅰ型IFN的產生。在LPS、poly(I∶C)刺激或 VSV 感染下,過表達PP1能使IRF3的磷酸化水平降低,并且妨礙了IRF3的核轉位;反之,將PP1沉默后,IRF3的磷酸化水平增高。而此過程不影響TBK1、IKKε和IRF7的活化[16]。另外,絲蘇氨酸磷酸酶PP2A與接頭蛋白活化蛋白酶C1受體(Recptor of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C1,RACK1)也介導了IRF3 C末端的去磷酸化。過表達RACK1、PP2A或沉默兩者,都影響IRF3 Ser386/396/398的磷酸化。在靜息狀態下,PP2A-RACK1復合體在胞漿內與IRF3結合,維持IRF3的低磷酸化狀態。在LPS、poly(I∶C)刺激或SeV感染下,IRF3從復合體中解離。該研究表明,在高劑量SeV感染下,IRF3通過降解途徑終止活化;而在低劑量LPS、poly(I∶C)刺激或低劑量SeV感染下,IRF3活化的終止依賴去磷酸化而非降解[17]。CK2(Casein kinase Ⅱ)一方面通過激活PP2A介導IRF3的去磷酸化,另一方面又阻礙TBK1的活化,從而阻止IRF3的活化[18]。
PTEN(Gene of phosphate and tension homology deleted on chromsome ten)是一個抑制腫瘤的磷酸酶,是PI3K-AKT通路的負調控因子。研究發現,PTEN通過使IRF3 Ser97去磷酸化,促進了IRF3的入核,從而正向調控抗病毒免疫效應,而不依賴于PI3K-AKT通路。Ser97位于NES序列附近,對IRF3-C端的磷酸化和二聚化均無影響,只影響IRF3的入核。與此一致的是,核提取物顯示Ser97的磷酸化只能在胞漿被檢測到[19]。
2.2IRF3的泛素化 IRF3能夠發生多聚泛素化,其泛素化鏈既可能是48位賴氨酸(K48)連接的形式,也可能是63位賴氨酸(K63)連接的形式。一般認為,蛋白的K48連接的泛素鏈參與蛋白酶體途徑的降解,而K63連接的泛素鏈則與信號轉導、內吞等過程相關。目前發現IRF3的賴氨酸70位(K70)和K87能夠發生K48泛素化。雖然有報道IRF3也能發生K63泛素化,但是E3泛素連接酶和賴氨酸殘基位點尚不明確。
研究報道,Pin1、RBCK1(RBCC protein interacting with PKC1)、RTA相關泛素連接酶(RTA-associated ubiquitin ligase,RAUL)、三結構域蛋白21(Tripartite motif 21,TRIM21)、O類叉頭轉錄因子(Forkhead transcription factors of the O class,FOXO1)、卡西塔斯b系淋巴瘤蛋白c(c-Casitas b-lineage lymphoma,c-Cbl)等分子能介導IRF3在胞漿內發生K48泛素化和降解,從而抑制Ⅰ型IFN的產生,對抗病毒固有免疫應答呈負向調控。以上過程能夠被蛋白酶體抑制劑MG132抑制,證明IRF3可通過蛋白酶體降解[20-23]。Pin1的N端WW結構域能夠特異識別磷酸化的絲、蘇氨酸后面帶一個脯氨酸的結構。Pin1能識別IRF3磷酸化的Ser390-Pro340結構并與之結合,并介導其泛素化和降解。E3泛素連接酶RBCK1和RAUL介導了IRF3的K48位泛素化及降解。RAUL介導的IRF3 K48泛素化不依賴IRF3 Ser339的磷酸化,這表明RAUL主要調控IRF3的基礎水平。TRIM21介導了IRF3、IRF5和IRF7的K48泛素化及降解。FOXO1介導胞漿內IRF3 K48位泛素化及降解,并且不依賴E3泛素連接酶RBCK1和RAUL。c-Cbl的TKB結構域能與IRF3的IAD結構域相互作用,并介導IRF3的K48位泛素化和降解。
TRIM26與上述分子不同,其介導IRF3的K48位泛素化和降解發生在細胞核內。研究表明,TRIM26能夠促進IRF3和突變體IRF3-5D的降解,但不能促進IRF3-5A的降解,同時IRF3去除NES序列后也不能與TRIM26相互結合。病毒感染不僅促進IRF3的入核,也能促進TRIM26的入核,以上實驗都證明TRIM26介導的IRF3泛素化發生在核內[24]。
2.3IRF3的非經典的轉錄后修飾 近年來,免疫應答中非經典的轉錄后修飾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非經典的轉錄后修飾包括甲基化、乙酰化、SUMO化、ISG15類泛素化修飾和谷胱甘肽化等。IRF3能夠發生SUMO化、甲基化、ISG15修飾和谷胱甘肽化的修飾。
研究發現,人源和鼠源IRF3的K70位、K87位和鼠源IRF3 K152位能夠發生SUMO化,但誘導IRF3發生SUMO化的分子尚不明確[25]。SUMO修飾在不同的情況下可發揮完全相反的功能,一方面SUMO修飾可以拮抗底物發生K48位泛素化,阻礙其降解而起到正調控作用;另一方面SUMO化可以作為招募E3泛素連接酶的信號,來協助蛋白發生K48的泛素化和降解而起到負調控作用。其中,鼠源IRF3 K152位的SUMO化,負調控IRF3的轉錄功能[25];而IRF3的K70/K87 SUMO化能使IRF3蛋白保持穩定,不被降解,并且不影響IRF3的細胞內定位。SENP(Sentrin/SUMO-specific protease 2)做為去SUMO酶,能夠斷開SUMO與底物的連接。SENP2能夠使IRF3的K70/K87去SUMO化,從而促進IRF3的相同位點發生K48位泛素化并使之降解,從而對IFN的表達呈負調控的作用[26]。甲基轉移酶NSD3(Nuclear receptor-binding SET domain 3)使IRF3發生K366單甲基化,能夠維持IRF3的磷酸化狀態從而促進其轉錄活性,最終增強固有免疫的抗病毒效應。NSD3的PWWP1結構域與IRF3的C端相互結合,在核內促進IRF3的單甲基化,并抑制PP1與IRF3的結合,阻礙其對IRF3的去磷酸化作用[27]。Herc5(HECT domain and RLD 5)介導的IRF3的ISG化,破壞了Pin1與IRF3的相互作用,從而抑制IRF3的K48泛素化和降解,是抗病毒免疫效應的積極調控因子[28]。在未感染的細胞中,IRF3能夠發生谷胱甘肽化,但介導發生谷胱甘肽化的分子尚不明確。在病毒感染后,GRX-1能介導IRF3的去谷胱甘肽化,從而招募轉錄共刺激分子CBP-p300,但IRF3的磷酸化、二聚化、核轉位都與GRX-1能介導IRF3的去谷胱甘肽化無關[29]。
2.4調控IRF3的其他機制 IRF3的活化除了磷酸化、泛素化、甲基化等修飾的調控外,還與功能性復合物的形成、IRF3 的二聚化、入核以及與DNA 的結合等過程相關。任何環節受到阻礙都影響IRF3發揮轉錄因子的功能[30]。ERRα能與TBK1和IRF3相互作用,可阻礙TBK1-IRF3復合體的形成[31];Yes相關蛋白(Yes associated protein,YAP)在胞漿內與IRF3的結合,妨礙IRF3的二聚化,但不影響IRF3的磷酸化,從而負調控固有免疫[32];在大腸癌細胞中,β-catenin能夠與IRF3結合并阻礙IRF3的核轉位[33];STAT1活化抑制蛋白(Protein inhibitor of activated STAT 1,PIAS1)能夠妨礙IRF3與DNA的結合[30];轉錄因子MafB通過阻礙共刺激分子CBP的招募來阻礙IRF3的轉錄功能[34]。
2.5IRF3的降解 泛素-蛋白酶體降解系統是降低或終止轉錄因子的轉錄活性的重要機制,也是負性調控IRF3 轉錄活性的重要方式。病毒感染細胞后,內源性IRF3表達水平逐漸降低,此過程可以用蛋白酶體抑制劑MG132或者乳胞素抑制,提示IRF3蛋白可以通過蛋白酶體途徑降解。前文中也提到了Pin1、RBCK1、RAUL、TRIM21、FOXO1、c-Cbl等可介導IRF3發生K48泛素化并降解。
近幾年研究證實IRF3也能通過自噬體降解。病毒感染后,IRF3發生二聚化,TRIM21作為一個自噬受體蛋白,其C端的SPRY結構域能夠與IRF3的二聚體相結合,介導IRF3到自噬體內降解,從而抑制Ⅰ型IFN的表達[35]。IFITM3(Interferon-induced transmembrane protein 3)是IFN誘導產生的ISG,通過與IRF3的N端結合,介導IRF3經自噬體降解,從而抑制IFN的產生[36]。
2.6IRF3與病毒逃逸 病毒如何主動改變宿主細胞狀態以及免疫應答以便于逃逸免疫清除、進而有利于病毒本身復制和存活,是免疫學和病毒學競相研究的重要科學問題。最新報道了一種非編碼長鏈RNA(lncRNA-ACOD1)能夠通過調控宿主細胞的代謝狀態,以反饋方式促進病毒免疫逃逸和病毒復制[37]。此外,病毒逃逸機制與IRF3的關系也十分密切。HIV可通過分泌多種病毒蛋白Vpr、Vif、Vpu抑制IRF3表達和活化,造成機體對病毒的清除作用減弱,甚至產生免疫逃逸[38]。SARS病毒的PLpro-TM能夠與TRAF3、TBK1、IKKε、STING和 IRF3結合,而破壞復合體的形成,并且PLpro-TM也能降低RIG-I、STING、TRAF3、TBK1和IRF3的K63泛素化[39]。塞內加谷病毒(Seneca valley virus)能夠降低IRF3和IRF7的磷酸化水平,促進IRF3和IRF7的降解[40];中心地帶病毒(Heartland virus ,HRTV)破壞了TBK1-IRF3的連接[41];其他如登革熱病毒、人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tory syncytial virus,RSV)和乙肝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等,對IRF3的激活都有抑制作用,造成抗病毒效應減弱和免疫逃逸。
3 IRF3的其他功能
IRF3的功能比較廣泛,除了介導抗病毒固有免疫應答外,還參與適應性免疫應答,對細胞生長、凋亡、腫瘤等也發揮一定的作用。
IRF3對適應性免疫應答具有調控作用。在抗原提呈細胞中,IRF3能夠調節IL-12、IL-23和IL-27之間產量的平衡,從而影響Th1、Th2和Th17細胞的分化和炎癥反應[42]。實驗性自身免疫性疾病腦脊髓膜炎是經典的Th17依賴的模型,IRF3敲除的小鼠呈現更嚴重的病情和對Th17的反應[43]。此外,病毒感染RLR信號通路依賴的IRF3的活化減少了IL-12/23 p40的表達。因此同時感染VSV和李斯特菌,Th1(IL-12 誘導)和Th17(IL-23 誘導)所致的免疫應答效應與單一李斯特菌感染相比顯著降低[44]。在充滿灰塵和螨蟲的情況下,發動Th2細胞的反應和氣道高反應需要IRF3依賴的信號通路的參與[45]。
IRF3在病毒感染后誘導細胞凋亡中發揮重要作用。研究發現SeV感染的細胞容易發生細胞凋亡,并且發現不是IFN而是IRF3在這過程中發揮作用。RIG誘導IRF3產生的細胞凋亡(RIG-I-like receptor-induced IRF3 mediated pathway of apoptosis,RIPA)中的IRF3不是利用其轉錄因子的功能,而是需要IRF3特定的賴氨酸發生線性的泛素化,LUBAC與TRAF2和TRAF6復合體介導IRF3 K193、K313/K315的線性泛素化是RIPA活化必需的。IRF3誘導的細胞凋亡是通過C端的BH3結構域與前凋亡蛋白BAX相互結合。IRF3與BAX復合體轉移至線粒體,引起細胞色素C釋放至胞漿,從而活化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Cysteinyl aspartate specific proteinase,Caspase)發生細胞凋亡。RIPA使得病毒感染初期,被病毒感染的細胞發生死亡從而阻止病毒的復制。缺乏RIPA,即使IRF3的轉錄功能已經活化產生IFN,細胞也會受到病毒的持續性感染[46]。
IRF3對腫瘤的影響比較復雜,在不同的腫瘤細胞中,IRF3通過不同途徑和機制來抑制或促進腫瘤的生長。在正常和腫瘤細胞中,過表達IRF3都能夠抑制依賴p53的細胞分化促進細胞衰老。在黑色素瘤細胞中,IRF3能夠促進細胞因子的產生和招募炎癥細胞,過表達IRF3能夠抑制腫瘤[47]。在肺腺癌細胞中,IRF3呈現高表達,對其腫瘤的生長呈現抑制作用[48]。然而,IRF3能夠促進急性髓系白血病產生。IRF3能夠結合miR-155的啟動子,miR-155是能促進急性髓系白血病產生的微小RNA。過表達IRF3能夠促進白血病細胞的生長和生存,表明IRF3能夠成為急性髓系白血病治療的新靶點[49]。IRF3也能夠促進胃癌的發生。IRF3作為YAP的激動劑,能夠與YAP和TEAD4形成復合體,能使YAP保留在核內并活化。過表達IRF3和YAP都能使病人的生存率下降[50]。
4 結語
PRR識別入侵病毒的病原相關的模式分子,通過不同的信號轉導途徑激活抗病毒免疫應答。這些激活的信號途徑匯聚到IRF3,共同促進IRF3的活化以及Ⅰ型IFN的表達。因此,IRF3是細胞抗病毒信號調控網絡中的核心,在調控宿主與病毒的相互作用中發揮重要的功能。近年來的研究雖然明確了IRF3激活的信號轉導通路和調控機制,但仍有許多重要的問題亟待深入探討,如從靜息到活化過程中,IRF3的內部結構具體是怎樣變化的,IRF3的磷酸化、二聚化、入核和降解等過程的分子機制間的先后順序以及相互聯系,在病毒持續感染情況下,機體如何平衡各種機制調控IRF3,使其表達和活化不至失控。通過對IRF3調控的深入研究,將有望針對病毒逃逸以及疑難性感染病提供有效治療的新靶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