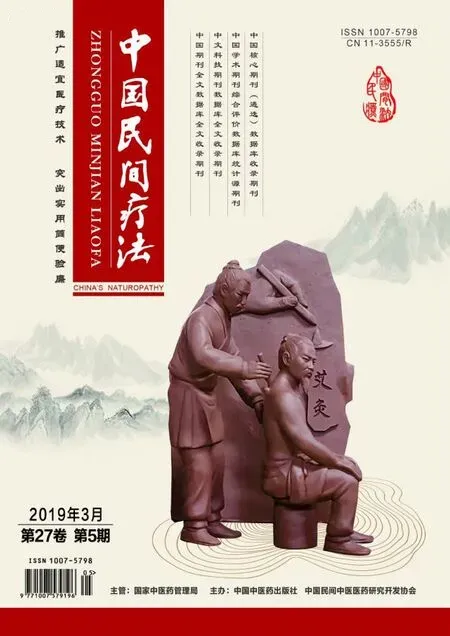針灸治療慢性尿路感染1例
張 旭,趙建新?,田元祥
(1.北京中醫藥大學第三附屬醫院,北京100029;2.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醫臨床基礎醫學研究所,北京100000)
患者,女,67歲,于2018年3月12日初診。主訴:反復尿路感染,排尿燒灼感,尿液渾濁8個多月余。既往子宮多發肌瘤病史20年。2016年9月因帶狀皰疹后出現尿頻、尿痛、小便燒灼感,于北京醫科大學第三附屬醫院就診,診斷為“急性尿路感染”,予以頭孢地尼分散片口服治療后癥狀好轉。2017年9月再次出現尿頻、尿痛、小便燒灼感、小腹脹痛等不適,于同仁醫院住院1周。查膀胱鏡顯示:膀胱黏膜多發粟粒樣小結節,雙側輸尿管口形態正常。診斷為“間質性膀胱炎”“慢性尿路感染”,予以林霉素治療1個月后癥狀稍緩解。患者自行于當地社區醫院行火針和針灸治療,主要針刺腰背部腧穴,火針隔日1次,針灸每日1次,具體針刺穴位不詳,治療后期艾灸腎俞、神闕,癥狀略有減輕。2018年1月初于北京醫科大學醫院就診,診斷為“子宮息肉”“盆腔炎”,建議手術治療,患者未行手術治療。其后患者癥狀改善不明顯,遂至北京中醫藥大學第三附屬醫院針灸科就診。刻下癥:神清,精神差,尿頻,尿痛,小便燒灼感,尿液渾濁,有棉絮狀沉淀物,小腹脹痛,腰背酸痛,口干口苦,焦慮不安,納差眠差,舌紅苔白膩,脈弦滑。尿常規正常。中醫診斷:淋證。中醫辨證:肝郁腎虛,濕熱下注。中醫治法:補腎疏肝,清熱利濕。針灸取穴:仰臥位取中脘、下脘、水分、天樞、中極、曲骨、氣沖、足三里、陰陵泉、三陰交、太沖、內關、印堂、神庭、百會;俯臥位取次髎、中髎、下髎、秩邊、腎俞。操作:采用東邦牌針灸針。中極、曲骨、氣沖采用0.35 mm×75 mm毫針,針感放射至前陰。次髎、中髎、下髎、秩邊用0.35 mm×100 mm毫針,針感放射至前陰,其余穴位常規針刺,行平補平瀉手法。仰臥位時連接電針,同側陰陵泉、太沖為1組,密波,頻率50 Hz,留針25 min;俯臥位時連接電針,同側腎俞、中髎為1組,密波,頻率50 Hz,留針15 min。每日1次,連續治療5次。3月15日二診,患者自述尿液排出大量皮屑樣沉淀物,尿液渾濁,但尿頻、尿痛、小便燒灼感癥狀緩解,小腹脹痛、腰背酸痛癥狀減輕,焦慮忐忑情緒好轉,納眠尚可。針灸治療取穴同前,操作同前,連續治療5次。3月22日三診,患者自述排出尿液上漂有油花樣物質,尿液渾濁癥狀減輕,尿頻、尿痛、小便燒灼感減輕,小腹脹痛、腰背酸痛癥狀消失,精神狀態好,納眠可。針灸治療仍取穴同前,操作同前,連續治療5次。
按語:慢性尿路感染臨床以持續或反復腰痛、腰膝酸軟、尿頻、尿急、尿道澀痛、排尿淋漓不盡、下腹墜脹、遇勞或情緒波動而加重為主要表現,且病程在6個月以上,遷延難愈,復發率高。
尿路感染屬于中醫“淋證”范疇。漢·張仲景在《金匱要略·五臟風寒積聚病脈證并治》中將其病機歸為“熱在下焦”,并在《金匱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脈證并治》中對本病的癥狀作了描述:“淋之為病,小便如粟狀,小腹弦急,痛引臍中。”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提出:“諸淋者,由腎虛而膀胱熱故也。”可見淋證的病位在膀胱與腎,病因以膀胱濕熱為主,病機主要為濕熱蘊結下焦,腎與膀胱氣化不利。若久淋不愈,濕熱留戀膀胱,由腑及臟,繼則由腎及脾,脾腎受損,正虛邪弱,遂成勞淋。反復發作的尿路感染屬中醫“勞淋”范疇。中老年女性因年老體弱,各臟腑功能衰減,腎氣虛弱,膀胱開合不利,無力排出尿液,殘余尿增多,尿流不暢造成尿路感染,稍有誘因便可使濕熱邪毒之氣侵入,形成膀胱濕熱,再發淋疾[1]。病延日久,可導致脾腎兩虛,膀胱氣化無權而反復發為本病。針灸治療選穴,仰臥位取中脘、下脘、水分、天樞、中極、曲骨、氣沖等任脈穴位,培補元氣、導赤通淋;天樞、足三里為足陽明胃經穴位,陰陵泉、三陰交為足太陰脾經穴位,可調理人體氣血,健脾化濕;太沖為足厥陰肝經之穴,內關為手厥陰心包經之穴,可疏理肝氣,調理心神,加督脈印堂、神庭、百會穴鎮心安神;俯臥位取次髎、中髎、下髎、秩邊、腎俞,八髎穴是支配盆腔內臟器官的神經血管會聚之處,可調節一身氣血,且八髎穴位于骶尾部,針刺時使放射感到達前陰,有清利下焦之功;秩邊、腎俞為膀胱經背俞穴,取之可補腎益氣,通陽利水。諸穴共用補腎疏肝、清熱利濕。
西醫治療尿路感染主要以抗生素為主,但其不良反應較大,較易引起菌群失調及霉菌感染,停藥后易復發,反復發病易導致患者免疫功能低下,治療困難[2]。近年來,眾多中醫學者在臨床治療中不斷尋求治療慢性尿路感染的有效方法,針灸治療展現出良好的臨床應用效果,其不僅是臨床治療尿路感染的非藥物療法,且無副作用,易被患者接受,所以應加強推廣針灸對慢性尿路感染的治療,以期在此領域獲得更多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