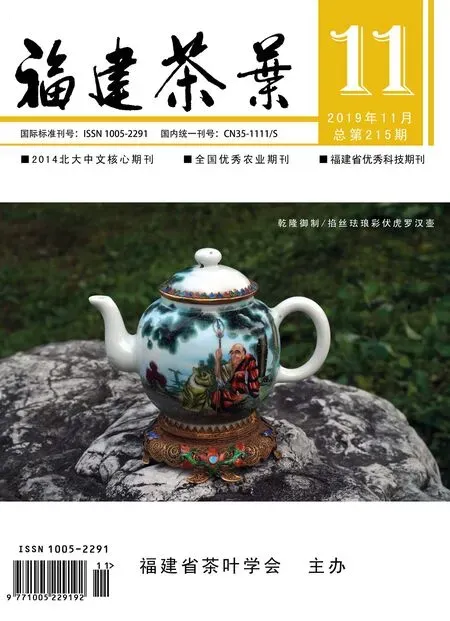利用詞語塊匹配進行英語寫作信息化評閱的探究
井朔宇
(湖南警察學院,湖南長沙 410138)
引言
閱讀與寫作教學是我國傳統英語教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寫作能力考察更是貫穿英語教育始終的考察點。英語寫作所考察的不僅是學生詞匯量的豐富程度,更要求學生把所掌握的單詞用恰當的搭配、正確的語法、豐富的內涵以篇章的形式創造性地呈現出來。傳統的英語寫作評價一般為主觀印象式評分或根據錯誤數量酌情扣減,缺乏全面客觀評價。而善用Michael Lewis與Miller的詞塊、語塊理論,將寫作內容與選定語料對比匹配,則能從用詞與搭配兩個層面檢驗作者寫作能力水平,成為一種寫作題目客觀化評價的解決手段。
1 傳統主觀評價的弊端
1.1 評價效率低
在信息化手段介入教學的今天,主觀題目評價已成為智能評閱的掣肘頑疾。而傳統的人工評價,受大量重復性工作影響,如果需要對學生的英語寫作進行逐句閱讀,并針對性地給出改進意見,無疑會增加教師的評閱工作量。
外語主觀題評閱與客觀題不同,易受到如字跡、涂改等言外特征影響。在大量寫作評閱任務下,教師的評閱效率勢必隨時間推移呈現下降趨勢,而除去主觀精力消耗的因素外,造成評閱速度、效果下降的主要客觀因素即為不同的字跡、卷面效果給人工評閱帶來的識讀障礙。
1.2 評閱主觀性過強
一方面,傳統人工評閱為定檔扣分式評閱。以四級寫作考試評分標準為例:寫作總分評分計為15分,分五檔,其中14分檔的評分標準為“切題。表達思想清楚,文字通順、連貫,基本上無語言錯誤,僅有個別小錯。”,而11分檔的評分標準為“切題。表達思想清楚,文字連貫,但有少量語言錯誤。”,兩者在定檔描述上僅用“基本”、“個別”、“僅有”、“但有”這樣的區別解釋,而兩檔所造成的得分相差卻有21.3分之多,無疑影響評分客觀性。
另一方面,多人分工導致評閱標準不統一。在大型考試中,為按時公布考試成績,組織方被迫安排多人分工進行主觀題評閱,而對評閱標準的理解因人而異,對于評分標準的把握只能實現定性,無法定量。因此在理論上,評閱人數與評閱客觀性呈反比效果。
1.3 易導致模式化寫作
模式化寫作,或稱模板化寫作,是指為了迎合閱卷人評閱習慣而在特定位置嵌套“模板句”的寫作方式。模式化寫作背離了寫作考察學生就一般性主題表達個人觀點的初衷,學生抓住評閱人評閱時間有限的特點,用事先準備好的固定句子進行拼湊,營造出文章觀點明確、條理清楚、語句通順的假象。
造成模板化寫作的首要原因是快速人工評閱習慣被利用。在大量人工評閱中,評閱人傾向于關注寫作文章的首、尾段與邏輯關鍵詞,以期迅速把握文章主旨大意,理清邏輯結構。不乏有學生利用“速成寫作技巧”,在文章開頭或末尾堆疊大量與文章主題關聯不大的長難句以展現語言功底,或在文章中有意使用復雜詞匯以展現其豐富詞匯儲備,而忽略文章題材與語域設定,違背語言搭配的日常習慣,期望達到“以一敵百”的取巧效果。
模板化寫作的不良結果是導致學生養成不良寫作規律,忽視語料輸入對寫作輸出的決定性提升,只聚焦于基于句子模板和替換詞匯的公式化寫作產出。
2 以詞語塊匹配為基礎的信息化評閱
2.1 詞語塊的概念和分類
詞(語)塊的概念最早由Becker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首先提出的。詞、語塊可以被理解為是一種介于詞與句之間的過渡性語言單位。母語者除掌握母語的詞匯外,還會將詞與詞、詞與詞組之間的約定搭配組成固化的語料單位存入記憶。在有表達輸出的需要時,母語者從腦海中以同樣固化的預料單位為整體進行提取組合進行輸出。在Becker的概念中,詞塊是兼顧功能與形式的,即其是主動內涵詞匯與語法的語言單位。Nattinger和DeCarrico(1992)對于詞塊的定義略有區別,他們認為詞塊是“允許進行某些語言變化,以整體組合存在于在人腦記憶中的語言集合單位。”而Michael Lewis將詞語塊的語法概念進行了進一步強化,他強調語言的形式單位是語法化的詞匯集合,而不是單獨詞匯通過嚴格語法邏輯產出的。語言的輸出使用,并非是如數學公式化地組合,即臨時地根據表達需求,通過提取所必須的單詞,再按照語法規則進行語句建設,而是先提取在預設場景中所記憶下來的詞塊(lexical chunks),再進行有限地語法適應而得出的。
在國際上,以Lewis和Nattinger、De Carrico對于詞語塊的分類法最廣為接受。
Lewis的分類法中,詞塊可以大致歸為四類:(1)單詞(words)與短語(poly-words),即傳統意義上的單字詞匯(single words)與動詞短語(phrasal verbs)。(2)詞語搭配(word-collocations),即以較高組合頻率出現的詞組。如形容詞作定語與名詞所構成的修飾組合、動詞和名詞作賓語所形成的動賓組合。(3)習慣性組合(institutionalized utterances),這是指以語法模塊為內涵的,形式固定或半固定、具有約定語用功能的單詞組合。習慣表達既可以是完整的句子,如“How do you do?”、“Thank you.”,也可以是慣用話語,如“How come?”、“Not at all.”。(4)句子框架和引語(sentence frames and quotations)。與習慣性表達類似,次類詞語塊在形式上和功能上也相對固定,但其使用可以跨越單句,是超越語句的、作為邏輯組合關聯的語用單位。如“first and formost…last but not least”、“on the one hand…on the other hand”。
相似地,Nattinger、De Carrico兩人也將詞語塊分為四種:(1)聚合詞匯(poly-words),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詞匯組合形成的固定短語,而在使用上不允許改變其形式,如“look forward to”、“on account of”等。(2)習慣性表達(institutionalized expressions),這同樣是指不允許進行形式改變的約定語、俗語,如“Good bye!”、“Long time no see.”(3)短語限制語(phrasal constraints),這一類詞語塊是允許進行詞匯和詞類變化的框結構性語快,如“as long as”、“water is to fish what air is to us.”。(4)句子框架(sentence builders),這類詞語快同樣是超越語句的銜接框架,廣泛存在用于書面語中,如“both…and...”、“for one thing…for another”。
2.2 非英語專業大學生寫作中的詞語塊特征
非英語專業學生未設置專門的英語寫作課程。盡管英語寫作在各類英語考試中分值占比很高,是各種考試的必備考題,但作為公共必修課,大學英語課程課時卻很少,講授以精讀為主要內容。教師只能在平時教學中注重篇章結構劃分、寫作技巧總結等要點的講解,在講解的深度以及訓練的頻度和廣度上都差強人意,很難實現學生寫作水平的提高。根據雅思考試中心2017年數據統計,中國學生的平均寫作水平普遍較低,只有5.37分,與母語者寫作者的英語水平相去甚遠。這其中的重要因素就是語塊搭配、使用的差別。在寫作中,語塊組合恰當與否比詞匯或短語的使用具有更大的語用意義和價值,其在提升英語語言表達的準確性與貼近英語表達習慣方面更具優勢。語塊在口語中占有很高的使用比例,因此許多研究者提倡將語塊作為語言教學的基本單位。
學生在課堂中、教材中學到的詞語和語法用法并不常是母語者在日常會真正使用的語言。如日常英語寫作素材中所常見的“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句式,在眾多的寫作模板素材、參考范文、甚至是教師授課的過程中都有提及,常解釋為“隨著我們國家的發展”。但其實際卻是在英語寫作中不常見到的提法。詞匯教學的組合層模塊主要為詞匯形式、語法規則、功用等,無法上升到交際使用層面,語言學習這者要清楚詞匯的句法功能,并要知曉如何在語境中靈活使用。
2.3 通過詞語塊方法進行的自動寫作評閱
以詞語塊進行寫作評閱的的信息化解決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優勢:首先,從對用文本特征的匹配能力上看,機器更有優勢。數字化寫作評閱系統可以精確統計一篇作文里的單詞個數、句子長度、單詞使用層次、以及語言錯誤的數量,再按照Lewis和Nattinger、De Carrico的主流分類,對文章詞語塊使用與給定范文進行比對,從而得出綜合分數。第二,從對評分標準的執行忠誠度來看。機器評閱不會受到情感影響、或對于評分標準的理解區別等其他因素干擾,能夠按照給定規則嚴格執行評閱,因此能確保系統對每篇作文采用的評分標準都是一致的,增加考試嚴肅性。最后,從評閱效率上看,機器評閱速度更快,能更好地向學生及反饋量化評閱信息。通過評閱系統,不僅可以實現對一篇文章進行評分,還以從文章結構、銜接連貫、詞匯搭配和語法等各個層面上對一篇文章提供綜合評價,標注出一些詞匯和語法錯誤并提出修改意見,甚至提出搭配修改意見。在評閱后期,也能定制化地向學生提供寫作學習建議,推薦學習文章與語料。依靠大數據,在極短的時間內學習學生寫作模型,并給出“因材施教”的教學資料。
3 結論
數字化手段結合語料庫應用在英語語言教學應用中已經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貢獻,而基于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的數字化解決系統也在不斷發展進化,大學英語教師必須與時俱進、加強跨學科知識學習,將傳統語言應用理論與數字化解決方法相結合,積極培養個人數字化意識,不斷順應教學數字化改革的發展變化潮流。在日常教學實踐中,我們也應當不斷主動尋求來自互聯網的新鮮思想,研究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結合傳統教學工作中的難點與痛點,充分利用數字化資源和大數據統計手段,反思寫作教學中可以采取的改進措施,服務教學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