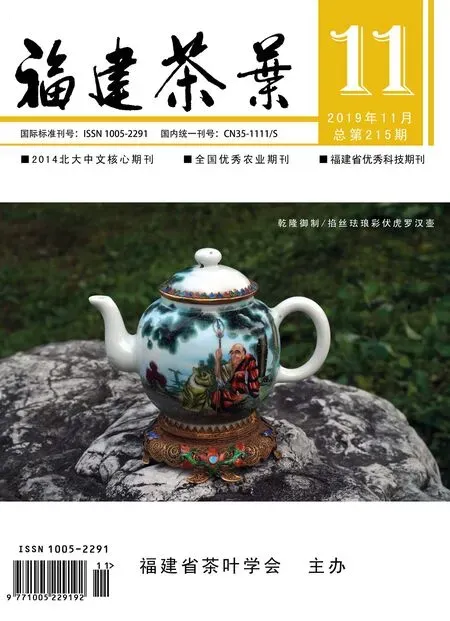中小企業法律保護的產業政策法路徑
余 平
(中國計量大學,浙江杭州 310018)
1 中小企業的法律保護的現狀
《關于促進中小企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指出,從營造良好發展環境、提升創新發展能力、改進服務保障等方面推動中小企業的發展。這也是繼2017年修訂《中小企業促進法》以來解決中小企業的發展困境、回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迫切需求的又一關鍵性文件,尤其是提出了政府采購向專精特新的中小企業傾斜。中小企業作為最有活力的市場主體,作為市場中的“大多數”,是市場發展程度的晴雨表,亦是宏觀調控法的關鍵著力點。
對中小企業發展的鼓勵和促進,在國務院及各部委的相關文件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2015年《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中指出將中小企業作為創新的關鍵主體;2015年7月17日,財政部發布了《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規范和加強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的管理和使用。2018年8月5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全國深化“放管服”改革轉變政府職能電視電話會議重點任務分工方案》中要求簡政放權建設服務型政府,為企業發展降低成本、營造更好的企業發展的服務環境。
2 法律保護內在邏輯的再構建
但是關于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相關法律及其配套文件,都顯示出了一種極度的無秩序。第一,中小企業保護的規定散見于各種文件之中,大多以行政性文件的方式存在,盡管在職能部門內部形成了制定方針到具體實施優化這樣一個內在邏輯,但從中小企業的法律規范體系來看,這種邏輯沒有被表達出來;其次,盡管存在《中小企業促進法》這種專門立法的存在,但更多的是原則性規定,就以《意見》作為參照物,顯然作為一般性政府文件更為全面具體,反而更有指導性意義;第三,政策與法的關系是宏觀調控法的永恒課題,在各司其職的基礎上以最終的法律制度為依歸是宏觀調控法治化的路徑。作為更多的是被應用于執法環節的中小企業促進相關法律規范,不同于依靠司法的私益保護,就更應注重具體條文的內在邏輯性及可操作性。雖然政策所體現出的靈活性、階段性、實驗性及易變性在促進中小企業發展上更有力,但是為了避免政策過多地被部門利益、地區利益、行業利益所干預,必須建立中小企業在宏觀調控法領域,一個獨立而完整的法律規范的內在邏輯,在市場與政府關系的巨幕之下找到中小企業法在宏觀調控法領域的體系邏輯,是貫徹法治精神、促進自由競爭的題中應有之義。
產業政策法對于中小企業的法律保護的邏輯化提供了很好的理論工具,產業政策法因產業政策的分類而被分為產業組織政策法、產業結構政策法、產業布局政策法、產業技術政策法。筆者試從這四個方面對中小企業的法律保護的體系化做出探索,探求其內部的法治邏輯:
2.1 產業組織政策法:完善政府的服務職能
《中小企業促進法》提出要實現中小企業退出的便利化,《意見》在營造良好發展環境一章的第一項提出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退出機制和準入機制一樣重要。放寬準入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基礎,而建立高效便利的退出機制,則是市場配置資源的必由之路。在宏觀調控法領域,這種理念依然存在,只不過是對政府的準入與退出的規制。宏觀調控法的目標之一就是限制政府權力,而限制政府權力的關鍵就在于兩點:一、宏觀調控只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為公共利益而“出場”,也是經濟法追求的實質公平、社會本位的理念內涵;二、如果在解決某個問題上,政府干預不能比市場自身調節更有效,那么應該由市場進行調節。
鼓勵、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絕不是扶持所有中小企業,像支持國有企業的規模經濟效應那樣,不是政府主導方向的改變,而是為了激發市場的潛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維早已不是“輸血式”扶持,哪怕在脫貧攻堅這樣的國家主導的促進產業發展和社會分配公平的領域內,都選擇了尊重地方特色、因地制宜地“造血式”發展。尊重企業的自主經營權,完善財政政策,促進稅收制度的體系化。
2.2 產業布局政策法:地方利益的保護及限制
在推動地區經濟發展時,地方政府的作用就顯得尤其重要,在相應中央關于創新產業發展、培育優勢產業的號召下,要理性發揮地方的積極性,拒絕一刀切。地方政府應該加強對本地資源情況的調研,開展多方的評議,暢通意見反映渠道,找到準確的地方產業定位,因地制宜。《意見》中指出研究修訂政府采購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暫行辦法,采取預算預留、消除門檻、評審優惠等手段,落實政府采購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政策。地方部門對于地方產業布局的把握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地方經濟的發展。以青海省為例,以標準先行的方式將虹鱒魚納入三文魚項下,在行業內和法學界都引起了巨大的爭議,政府的績效指標不能說明一切,以效率取代正義是不可取的,隨之帶來的就是資源的浪費、擾亂正常的市場秩序。因此在增強第三方機構的作用的同時,更要保證第三方機構的獨立性,第三方機構承擔宏觀調控職能,代表著政府管制的放松,是在宏觀調控中引入“市場思維”。但是,也要防止第三方機構濫用其權利,仍然要科學審慎地對待其在地方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2.3 產業技術政策:加大中小企業的創新支持
《意見》提出在政府采購活動中,向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傾斜。第一次將中小企業的發展方向定義為專精特新。發揮中小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的作用,應當做到:
首先,在充分尊重中小企業的經營自主權的前提下,構建中小企業的職務發明制度。知識經濟的背景下,創新已經成為企業在競爭中不可或缺的生產要素,中小企業也不例外。中小企業應發揮自身體量小、管理靈活的特點與優勢,重視科技成果的轉化,提高技術的實用性,即“變現”能力。技術在產業化過程中才能發揮其生命力,而產業化過程也會促進技術本身的不斷更新,使科技創新成果不至于被“束之高閣”。相應地,在中小企業科技成果轉化環節加大財政支持,對于中小企業創新的實質發展更具有實際意義。
其次,重視技術產業集群效應,國有企業是以規模經濟見長,而產業集群是對規模經濟理論的優化改進,能夠克服龐大企業內部的非效率性,工業園區就是一個很好的代表,園區內企業間共用基礎設施、統一的物流服務體系、土地優惠政策以及相應的會計、法律服務,使得中小企業在發揮自身優勢的同時,也擁有了規模效應所帶來的政策福利。
最后,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基礎技術的開發,中國制造缺少的除了高新技術領域的核心技術以外,也缺乏制造業的基礎技術。技術創新是兩條路徑,基礎技術開發是高新技術發展的基石,在高新技術重點突出的同時,也要發揮中小企業在基礎技術領域的作用。
2.4 產業結構政策法:中小企業應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
科斯指出:“從本質上來說,市場也是一個集體學習的機制。市場為參與經濟的所有角色提供了一個通過試錯方式不斷學習、不斷挖掘現有機會并開創新機會的平臺。”中小企業在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下,作為市場中的大多數,是進行學習的重要主體。從宏觀調控法的基礎理論出發,尤其是產業政策調整方面,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之下,在特朗普提出要求削弱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的當下,中小企業在產業政策法上的重要性可見一斑。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浪潮的40年浪潮里探尋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必須明確的一點是,在促進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良性互動層面,我們的中國特色應當是在具體政策上的因時而變因勢而變。中小企業作為產業政策的重要抓手,在推動創新、促進就業等方面都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不能放棄法律至上的價值追求,這是任何法治社會的起點,亦是其永恒的追求,這中間是在不同社會系統間不斷地調適的一個過程。
3 結語
中小企業法律保護制度體系化的產業政策法路徑,旨在促進中小企業在法治化框架內發展的同時,推動產業政策的法治化進程。法始終是所有經驗證有效的政策的終點。如果說改革開放是群策群力、邊緣革命的成果,那么中美貿易戰背景下,中小企業的崛起就是又一次邊緣革命。以市場邏輯為基本遵循,以產業政策為工具,充分發揮政府的經濟服務職能,從而維持或爭取本國產業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優勢地位是最佳選擇。中小企業促進法律制度體系的建立,就是將這種邊緣革命在經歷漫長的草根式生長之前,助力其發展,以免中國經濟陷入停滯不前的狀態。中國經濟的深化改革勢必要會實現的,但如何實現就變得至關重要。我們能否承受一個過于漫長而慘痛的轉型期,與我們能否渡過轉型期是兩種性質的問題。改革開放是我們的第一次學習,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面對新的經濟發展態勢,我們必須完成第二次蛻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