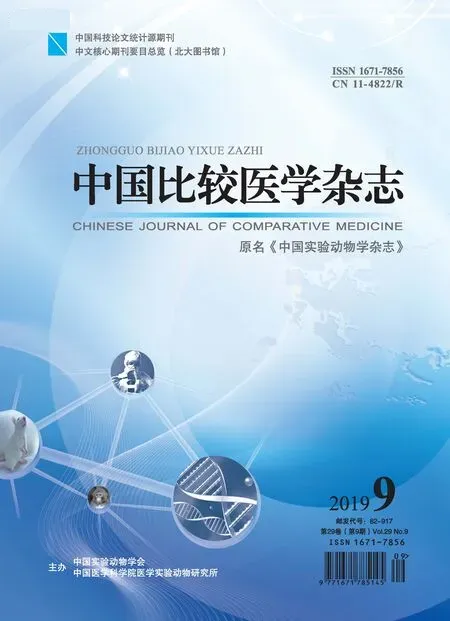血管外膜炎癥在動脈粥樣硬化中的作用及研究進展
韓淑嫻,王春淼,李玉潔,楊 慶,翁小剛,陳 穎,蔡維艷,
李 琦1,朱曉新1,2*,王婭杰1*
(1.中國中醫科學院 中藥研究所,北京 100700; 2.天津中醫藥大學,天津 301617)
動脈粥樣硬化(atherosclerosis,AS)是冠心病、腦梗死等多種缺血性心腦血管疾病的基礎病變,廣泛累及大、中動脈。主動脈、冠狀動脈、頸總動脈等大、中動脈主要由內膜、中膜、外膜構成。關于AS發病機制,Ross提出了“損傷-反應”假說,該假說認為AS病變是由血管內膜損傷引起的[1],即“由內而外”發生的;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外膜在AS的發生、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AS病變也可能是“由外而內”發生的[2-5],提示動脈外膜在AS的發生、發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視。
1 外膜炎癥是參與或促進AS早期病變形成的重要因素
血管外膜除起到支撐血管的作用外,還可感受并響應血管的損傷,調節多種細胞因子的生成、釋放,從而影響血管壁的結構和功能[6]。隨著人們對AS發病機制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血管外膜炎癥可能是推動AS發生、發展的原因之一。通過對AS患者進行尸檢,Watanabe等[2]發現約80%的患者冠狀動脈病灶處外膜存在T淋巴細胞浸潤,20%的存在B淋巴細胞浸潤,其浸潤程度與AS的嚴重程度密切相關。提示血管外膜在AS發生發展過程中不僅僅起到支撐血管的作用,外膜炎癥可能參與AS早期病灶的形成和發展。Ogeng’o等[3]對108名平均年齡為34.6歲的肯尼亞黑種人進行尸檢發現,14.8%、11.1%的人在左前降支和頸總動脈出現AS病變特征;其中,有6.5%的左前降支和3.7%的頸總動脈的外膜發生增厚,但是不伴隨內膜增生。通過對60周齡的ApoE-/-小鼠心臟心底進行連續切片,在冠狀動脈的細小分支內發現了原位形成的“獨立病灶”;在獨立病灶出現之前,外膜已出現明顯的炎細胞浸潤,且其面積大于病灶面積;另外一些部位的血管外膜觀察到炎細胞浸潤,但內膜尚未形成病灶[7]。II型膠原酶消化并鈍性剝離ApoE基因敲除小鼠頸動脈外膜,破壞動脈外膜結構的完整性,結合普通飼料喂養兩周后,損傷處血管內皮細胞排列紊亂,內膜明顯可見增生性病變,內、中膜可見大量表達SM-α-actin,表明血管外膜損傷能誘導內膜增生性病灶的形成[8]。這些發現提示,在AS形成過程中,血管外膜不僅出現炎癥浸潤,且形成時間早于內膜炎癥;炎癥浸潤后繼發的血管外膜增生也先于內膜,而外膜增生與AS早期病灶形成密切相關。
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球囊擴張及支架植入術等血管腔內治療不僅損傷血管內膜,可能通過激活血管外膜炎癥反應引起外膜功能障礙觸發AS級聯反應,而導致再狹窄發生。有研究發現,球囊損傷大鼠頸總動脈內膜后,損傷處外膜首先發生增生,術后7 d外膜增厚最為明顯,而內膜只有少量增生;術后28 d,內膜及整個血管壁顯著增厚,血管腔明顯狹窄[9]。提示動脈外膜炎癥可能是AS以及介入治療后血管再狹窄發生的重要誘因。
2 AS中動脈外膜的病理變化
2.1 炎性細胞浸潤
炎性細胞浸潤作為AS早期病理改變已被許多報道證實,然而在AS病灶形成之前,動脈外膜出現多種炎性細胞浸潤,并且浸潤程度與AS的病變嚴重程度相關。
2.1.1 淋巴細胞
血液中的淋巴細胞受細胞因子的影響,被募集到血管內膜中,與血管壁細胞發生相互作用,推動AS發生發展。然而,在AS病灶形成前,外膜已出現大量T細胞聚集[10],可能是AS動脈壁發生淋巴細胞浸潤的主要部位。通過對111名7 ~ 25歲非正常死亡的青少年進行尸檢發現,淋巴細胞積聚在正常冠狀動脈的內膜和外膜幾乎是同步的,而此時血管內壁并未觀察到明顯的AS病灶[11]。
T細胞在AS的發生發展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其中Th1、Th2細胞與AS密切相關,尤其是Th1細胞,在AS斑塊中大量存在。Th1細胞通過分泌干擾素-γ(IFN-γ)、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12(IL-12)等促炎因子,激活巨噬細胞和樹突細胞(dendritic cell,DC),啟動或推動AS炎癥反應。與之相反,Th2細胞可分泌IL-4、IL-10、IL-13等抑炎因子,促進B細胞抗體生成,從而平衡Th1的促AS效應[12]。
傳統觀點認為,B細胞作為體液免疫的主要效應細胞,可釋放的免疫球蛋白而具有抗AS的作用。然而,在小鼠AS病變的不同階段發現了B細胞[13],但僅在人類的晚期斑塊中發現了B細胞,在AS血管的內膜和外膜中檢測到B2細胞衍生的CD22+或CD20+B細胞[14]。研究發現,B1細胞主要產生IgM抗體,并通過產生能夠識別氧化LDLs的抗體,對AS起到保護作用,而B2細胞則產生IgG和IgE抗體,促進AS發展[15]。ApoE-/-小鼠病灶處炎性細胞因子TNF-α、IL-1β和IL-18的表達減少,脂質壞死核心減小,CD4+和CD8+T細胞浸潤減少,可能與B1a細胞中TLR4-MyD88的表達有關[16]。
2.1.2 巨噬細胞
巨噬細胞在AS形成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巨噬細胞聚集一般出現在AS粥樣硬化病灶形成之前,單核細胞黏附并浸潤到內皮下,在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MCP-1)的刺激下形成單核巨噬細胞,釋放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M-CSF)等細胞因子,啟動炎癥免疫應答[17]。此外,巨噬細胞可攝取脂類,它攝入氧化的脂蛋白后形成泡沫細胞,參與脂質核心的形成[18]。研究發現,球囊損傷SD大鼠胸主動脈7 d后,損傷處血管中膜及外膜發現了大量的巨噬細胞浸潤[19]。
2.1.3 樹突狀細胞
在正常動脈的內膜及外膜中偶見樹突狀細胞(dendritic cells,DC);在AS易發區域,如主動脈弓處,存在較多的CD11c+CD11b- CD103+DC和CD11c+CD11b+CD103-DC[20-21]。高脂喂養5 d的LDLR-/-小鼠主動脈內膜中發現了DC形成泡沫細胞,在人類不穩定斑塊的斑塊肩區、破裂易發區域及斑塊核心邊緣部位也發現了大量的DC細胞[21-22]。表明DC既可調節AS初期局部炎癥反應,又可促進AS后期斑塊易損。ApoE-/-小鼠AS病變中發現大量成熟DC,外膜三級淋巴管中也存在DC累積,并且在AS病變晚期和復雜斑塊中成熟DC數量明顯增加[23]。有研究發現,在LDLR-/-、ApoE-/-小鼠中,特異性刪除CD8α+DC細胞中的樹突狀細胞NK凝集素組受體-1(DNGR-1)后,脾細胞分泌的IL-10明顯增加,病灶中巨噬細胞和T細胞數量明顯減少,斑塊面積明顯減小[24]。以上研究結果提示,樹突狀細胞可能參與了從脂質條紋期至穩定斑塊期的各個AS階段,其對內膜、外膜的炎癥均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2.2 外膜成纖維細胞
成纖維細胞(adventitial fibroblasts,AF)是血管外膜的主要細胞成分,在病理狀態下可被激活,其表型發生轉化,增殖、遷移能力增強,并分泌多種細胞因子,參與炎癥反應、血管重構,推動AS的發生、發展[5]。
2.2.1 AF激活、參與血管重構
當受到炎癥、缺氧及細胞因子等因素刺激時,AF可被激活,轉化成肌成纖維細胞(myofibroblast,MF),MF中應力纖維(stress fibers)及細胞骨架蛋白(cytoskeletal proteins)含量較高,與AF相比收縮性能較強,從而可遷移至受損的血管內膜處,參與血管重構。研究發現,球囊損傷大鼠頸總動脈內膜7 d后,損傷處頸總動脈外膜及新生內膜處α-SM-actin表達量明顯升高;球囊損傷28 d后,損傷處外膜無α-SM-actin表達,此時新生內膜及中膜存在大量的α-SM-actin表達,而且外膜I/III型膠原比率明顯升高[9],提示AF細胞被激活后轉化成為MF,特異性表達α-SM-actin,其增殖、遷移能力顯著增強,可遷移至血管內膜,參與血管重構成。脂多糖(LPS)體外誘導大鼠胸主動脈外膜AF細胞活化,活化的AF可促進直接接觸共培養的AF-SMC(平滑肌細胞)的增殖、DNA合成及TIMP-2分泌;提示活化的AF與SMC間存在相互作用,二者可能通過縫隙連接進行信號傳遞[25]。以上研究提示,在AS早期病灶尚未形成時,AF細胞被激活后轉化為MF,增殖、遷移能力顯著增強,可遷移至血管內、中膜,參與新生內膜形成,并與SMC發生相互作用,導致血管增厚、管腔狹窄;外膜I/III型膠原比率顯著升高,導致血管硬度增加,血管彈性下降,從而引起血液動力學發生改變,易形成渦流而損傷血管內膜,進一步推動AS的發展。
研究表明,轉化生長因子β1(TGF-β1)通路在AS等心血管疾病中上調[26]。TGF-β1是目前公認的直接誘導AF激活的誘導因子。高脂喂養的10周齡ApoE-/-小鼠主動脈外膜中TGF-β1蛋白水平高于同齡的野生型c57BL/6小鼠,提示TGF-β1的上調與AS病變密切相關[27]。TGF-β1誘導的AF表型轉化可能與RhoA-Roh激酶信號通路有關,研究結果提示TGF-β1上調AF細胞RhoA蛋白表達,增加Rho激酶下游底物肌球蛋白磷酸酶目標亞單位(MYPT1)的磷酸化,而不改變Rho激酶的蛋白表達[28]。
2.2.2 釋放炎性細胞因子
生理狀態下,AF呈靜息狀態,發生表型轉化成為MF后,分泌TGF-β1、TNF-α、IL-6、基質金屬蛋白酶(MMPs)等多種炎性細胞因子[25, 29],可誘導AF細胞表型轉化,招募巨噬細胞、淋巴細胞等,誘導炎性細胞浸潤,加劇血管壁的炎癥反應。與C57BL/6 J小鼠相比,ApoE-/-小鼠升主動脈外膜α-SM-actin、TGF-β1表達升高,AF細胞增殖、遷移活性增強,分泌TGF-β1、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MCP-1)和膠原蛋白,提示外膜AF細胞出現炎癥反應,分泌多種炎癥因子,參與AS早期病灶的形成[30-31]。
2.3 血管滋養管增生
外膜血管滋養管主要分布于大、中動脈外膜,是營養物質、細胞因子以及代謝物質傳輸的導管,可維持管壁物質代謝及能量平衡。動脈外膜滋養管管壁由內皮細胞、血管周圍細胞及周圍細胞分泌物形成的基底膜組成[32]。血管內膜損傷后,血管滋養管通透性增高,成為可溶性因子、氧化產物等炎性介質進入AS斑塊內的通道,增加斑塊破裂的易損性[33]。通過對32例45歲以上人尸體的大腦中動脈、椎動脈、基底動脈進行檢查發現,在AS病變或無粥樣硬化病變的動脈中,外膜新生血管滋養管增多,其密度與血管的狹窄程度成正比[34]。另有研究發現,球囊損傷腹主動脈結合高脂飲食建立Ba-Ma迷你豬AS模型,免疫組織化學結果顯示血管生成標志物VEGF和β-連環蛋白主要存在于腹主動脈外膜血管滋養管中[35]。提示外膜血管滋養管增生與AS早期病變相關,可能推動AS的進程。
3 基于動脈外膜炎癥的AS動物模型
為研究外膜炎癥在AS進程中的作用,研究人員通過機械或化學方法直接損傷血管外膜,或者炎癥因子刺激造成血管外膜炎癥等不同方法建立外膜損傷誘導AS的動物模型,探討外膜炎癥在AS病變過程中的作用。
3.1 直接損傷血管外膜
采用機械或化學的方法直接損傷血管外膜,進而研究外膜在AS發病進程中的作用及機制。
3.1.1 機械損傷法
研究人員通過在血管外膜包裹硅膠管造成外膜機械損傷,建立AS模型。暴露Wistar大鼠頸總動脈,用內徑1.5 mm,長12 mm的硅膠管包裹右側頸總動脈,左側頸總動脈作為自身對照。術后3 d,損傷處血管外膜炎性細胞浸潤,內皮增厚,管腔縮小;術后1周,損傷處外膜出現大量的炎性細胞浸潤,血管滋養管增生,內皮細胞變形并突向管腔,血管壁增厚,管腔明顯縮小;術后2周,管腔較術后1周時擴大,內膜出現彌漫性增生,新生的內膜主要為中膜平滑肌及單核炎性細胞,而外膜炎癥較術后1周時減輕[36]。結果提示,用硅膠管包裹大鼠頸總動脈造成血管外膜機械損傷3 ~ 7 d即出現血管外膜炎癥,術后2周出現具有AS早期特征的新生內膜病變。此種造模方法利用機械性刺激,造成血管外膜產生無菌性炎癥。但是此方法對硅膠管內徑及彈性要求較高,硅膠管與動脈外膜接觸的同時不能壓迫血管,以免造成人為狹窄,導致血流剪切應力發生改變而損傷血管內皮細胞。
3.1.2 酶消化法結合機械損傷法
由于機械損傷外膜的造模方法會對血管內膜和中膜造成損傷且難以控制,國內一些研究者采用酶消化和機械損傷結合的方法,嘗試只損傷血管外膜,盡量避免對中膜和內膜造成刺激。暴露新西蘭兔的左側頸動脈,以浸有2 g/LⅡ型膠原酶的棉球包裹血管30 min后,鈍性剝離外膜白色疏松組織,用硅膠管固定左側頸動脈,以高脂飼料喂養8周,對頸動脈進行油紅O染色,在左側頸動脈發現大量染成紅色的斑塊,說明高脂喂養及酶消化結合外膜機械損傷成功建立了兔AS模型[37]。與手術刀銳性剝離血管外膜的方法相比,酶消化法結合機械損傷法對血管外膜的損傷程度更容易把控,并且對血管內膜、中膜的刺激更小,造模成功率更高。
3.2 炎癥刺激
用白介素類、細胞內毒素等致炎因子對動脈外膜進行刺激,研究其對模型動物AS形成過程的影響。
3.2.1 埋線浸潤法
研究人員分離小型豬冠狀動脈左前降支及回旋支近端,用吸附有2.5 μg IL-1β瓊脂糖微粒懸液的紙巾包裹。兩周后冠狀動脈外膜損傷處管腔狹窄,光鏡下病變血管段外膜可見大量炎癥細胞浸潤,內膜增生及炎細胞浸潤[38]。采用IL-1β包裹動脈外膜可建立AS早期病變模型,對于研究炎癥因子在AS發生機制中有重要意義。
3.2.2 硅膠管聯合炎癥刺激法
通過在血管外膜包裹硅膠管結合炎癥刺激造成外膜炎癥,建立AS動物模型。將吸附有5 mg/L的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棉線放置在直徑為6 ~ 8 mm、長度為1.5 cm的硅膠管內側,并將此硅膠管固定于新西蘭大白兔的腹主動脈壁上,以普通飼料喂養4周。造模5 d,血管壁出現炎癥反應;造模10 d,血管壁炎癥增生較明顯;造模2周,血管腔出現較明顯的狹窄;造模4周,血管各層均出現大量的炎性細胞浸潤,血管病變更加明顯,以管腔狹窄和管壁增厚為主要特征,雖無明顯的粥樣斑塊,但與人類AS血管重構的部分病理變化相似[39]。此方法將硅膠管包裹與局部炎癥刺激相結合,短時間內定位構建了AS早期血管炎性增生的動物模型,可用于研究炎癥刺激對外膜的影響;可能由于造模時間短,此方法沒有觀察到AS斑塊形成。
3.3 間接刺激
研究者采用間接刺激法,如球囊法損傷血管內膜,觀察血管外膜的病理變化。球囊損傷大鼠頸總動脈內膜后,損傷處外膜首先增生,術后7 d,外膜增厚最為明顯,而內膜只有少量增生;術后28 d,整個血管壁明顯增厚,血管腔明顯狹窄[9]。此種造模方式并非直接對血管外膜造成損傷,而是損傷血管內膜后觀察血管外膜的病理變化。由于球囊損傷可嚴重損傷甚至剝除血管內膜,此造模方法與人類AS發病進程不完全相符,但是可直觀地觀察血管外膜的病理變化,可用于研究血管外膜在AS發病進程中的影響。
4 藥物對AS外膜炎癥的干預作用
針對血管外膜炎癥干預AS發生發展的藥物研究還較少,目前尚無針對血管外膜炎癥的藥物,現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抑制AF細胞表型轉化上。臨床常用的降脂藥物如阿托伐他汀、氟伐他汀,對血管外膜炎癥顯示出良好的治療作用。阿托伐他汀可能通過下調TGF-β1蛋白及mRNA表達,抑制α-SMA表達,調控ApoE-/-小鼠升主動脈AF細胞的表型轉化,進而延緩AS的進程[40]。氟伐他汀可明顯減少家兔胸主動脈外膜炎性細胞浸潤,抑制AF細胞NF-κB p65的表達,從而抑制AS發展[41]。頸動脈外周遞送臨床上用于骨轉移和骨質疏松癥治療的唑來膦酸鹽,明顯抑制球囊損傷大鼠頸動脈新生內膜增生;唑來膦酸鹽在體外明顯停滯NIH3T3成纖維細胞S期細胞周期從而抑制細胞增殖,抑制α-SMA、TGF-β1和TGF-β2的表達以及Smad2/3的磷酸化,抑制NIH3T3細胞遷移活性。以上研究結果表明,唑來膦酸鹽可能通過抑制TGF-β信號通路,抑制成纖維細胞的活化、增殖、遷移,從而抑制新生內膜增生[42]。白藜蘆醇對體外培養的SD大鼠胸主動脈成纖維細胞活力、DNA合成和遷移能力均有抑制作用,并可濃度依賴性地誘導細胞凋亡;白藜蘆醇對大鼠胸主動脈成纖維細胞的作用可能與SIRT1通路有關,轉染siRNA靶向作用于SIRT1,成功逆轉了白藜蘆醇對成纖維細胞的抑制增殖和促凋亡作用[43]。
近年來,中藥及中藥復方制劑對血管外膜炎癥,特別是對AF細胞表型轉化、膠原的合成和表型轉化、血管滋養管通透性,也顯示出良好的作用。通心絡明顯抑制新西蘭大白兔頸動脈外膜損傷導致的內膜增生,明顯減少病變組織中的脂質沉積,明顯抑制病變血管NADPH氧化酶亞單位p22pox的mRNA表達,抑制氧化應激從而抑制AS發展[44]。四妙勇安湯可減輕ApoE-/-小鼠主動脈斑塊面積,通過調節基質金屬蛋白酶-9(MMP-9)、基質金屬蛋白酶組織抑制因子-1(TIMP-1)的表達,降低斑塊外膜滋養管通透性,穩定易損斑塊[45]。
5 展望
傳統觀念認為的AS是“由內而外”發生的,然而血管內膜、中膜、外膜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個緊密相連的動態反應整體。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逐漸認識到AS的形成可能是血管壁各層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并非單純的血管內膜炎癥、損傷-反應的病變產物。越來越多的研究結果表明,血管壁的炎癥反應可能是“由外而內”的過程,這些發現是對目前較為公認的AS發病機制“炎癥、損傷-反應假說”的重要補充。
近年來的諸多研究結果提示,在AS早期,粥樣斑塊病灶形成之前,血管外膜已先于內膜出現炎癥反應,大量的巨噬細胞、淋巴細胞等炎性細胞聚集在血管外膜,并分泌各種細胞因子;作為血管外膜的主要細胞成分,成纖維細胞在各種細胞因子等刺激下被激活,轉化為肌成纖維細胞,與靜息狀態的成纖維細胞不同,肌成纖維細胞表現出較強的增殖、遷移活性,可遷移至血管內膜、中膜,與血管內皮細胞及平滑肌細胞發生相互作用,并參與新生內膜的形成和血管重構;另外,肌成纖維細胞具有大量合成膠原的能力,血管外膜中I型膠原含量顯著增加,I/III型膠原比例明顯升高,從而導致血管硬度增加、彈性下降,易形成渦流而損傷內皮細胞,進一步推動AS發展。因此,在AS發病進程中,特別是AS早期粥樣斑塊形成前,外膜不僅起到支撐血管的作用,其對血管功能的調節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血管外膜如何響應炎癥刺激,通過何種方式影響內、中膜,是否存在某種信號轉導機制,進而影響血管壁的結構和功能,尚待深入探索,進一步,外膜炎癥的發生發展對于AS中晚期是否有進一步的影響,這也是值得研究的有趣的切入點。
目前,外膜炎癥與脂質代謝紊亂和AS斑塊形成之間的關系尚未完全闡明,單純從外膜炎癥角度建立的AS動物模型仍然較少。因此,選用適當的刺激方法,在模擬外膜炎癥的同時不刺激或損傷血管中膜和內膜,從而建立基于外膜炎癥的AS動物模型,對于研究外膜在AS病理過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基于此理念的研究不但能夠多角度、多層次、全面地模擬甚至揭示人類AS發病進程,完善對AS發病機制的全面認識,對于開發新的“內外兼治”的AS防治藥物,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